《生命樹》:看到睡著也幸福的電影
記得那時排隊買票的時候,後面的老伯抬頭看著泰倫斯馬力克(Terrence Malick)《生命樹》(The Tree of Life)的售票情況,說:「咁悶都咁多人睇嘅?」他自己也是看這齣悶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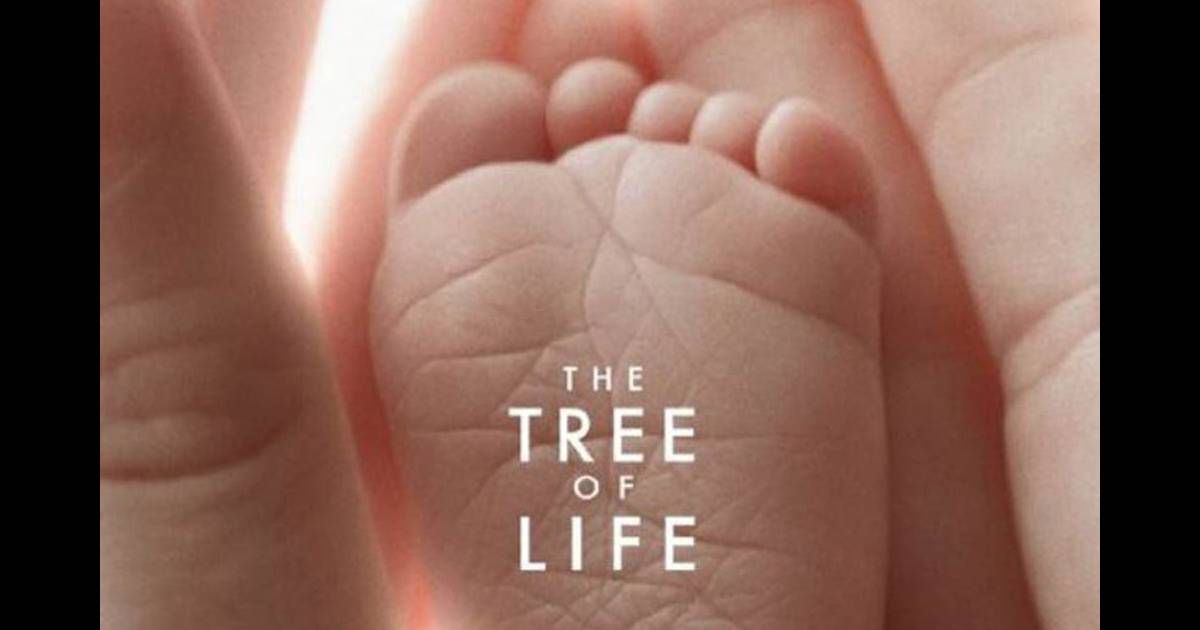
看戲是娛樂,當然怕悶。很多人形容一齣戲沉悶,就說「悶到瞓著」。那一天我也很睏;觀影的日子裡也常常「悶到瞓著」。但原來有一些電影,「悶到瞓著」,卻仍然感到美好。《生命樹》是其一;另一齣是塔可夫斯基的《潛行者》。
這就是經典:悶到瞓著所以要一睇再睇;悶到瞓著仍值得一睇再睇。
(生命不沉悶嗎?為何睡著了又要醒來?)
《生命樹》不是商業娛樂而是藝術作品,它不為消費而拍,讓人在幻想世界裡逃循兩小時再回到營役當中;它說的是宇宙與生命,平常,但不凡。不凡之處在於,導演泰倫斯馬力克帶著觀眾以一個不同的角度回看我們自以為熟悉的「人生」,其視野卻比起凡夫俗子有所超越。當觀眾步出戲院,電影不一定終結,生活未必如常,因視野已不同。

故事很簡單:主角已屆中年,事業有成,但與枕邊人相顧無言;在辦公室拼搏廝磨,於大大小小的玻璃箱子之間上落穿梭,惶惶然不知所云。
他霎然回首童年,兒時光景歷歷在目般湧現。那時候,母親仍像仙女般美麗;三兄弟有時相親相愛、有時互相傷害;與鄰家孩子天天亂跑搗蛋又怕受罰;父親之嚴苛與母親的教導充滿張力……這就像大部份人的童年,有喜有悲,充滿疑惑。在找到所有問題的答案之前,不經不覺已長大成人,那時候問題減少了,卻不是因為得著解決,而是早被遺忘。

有時候,遭人遺失在記憶森林的片斷,會在夢中像野兔突然蹦跳出來。《生命樹》其中一個讓人感到沉悶的原因是其剪接過場的手法和節奏。我們慣看了快速跳接之視覺衝擊,《生命樹》卻緩緩地淡入淡出、淡出淡入……少有連貫,卻毫不突兀。
就像人在半夢半醒之際,眼瞼半張半合,一時也分不清自己在夢裡還是在現實、在過去還是在今刻;也像胎兒在母親肚子裡,不知清醒與否的混沌狀態。看著看著,觀眾進入夢境也不為其,彷彿其內在的自我與電影有所呼應。
《生命樹》之所以能讓我們從平常人生的主題開始而有所超越,是其宗教性之探討。中年的男主角是建築師,是建立者、創造者。多少人努力發憤、日思夜想,在這競爭世界裡抓緊財富地位,以為那就能安身立命。

但男主角這一天嘎然而醒,在玻璃大廈之間的無盡倒映之中,忽爾惶然:何以豐功偉績也不是人生之安然居處?多年營役之何為?聖靈的聲音是微小的,主角童年的耳語、母親的叮嚀也是悄悄的,從遺忘的海床漸漸浮現……
為甚麼人會死?
那孩子後腦被燒,頭髮不同生長,是否他做了甚麼壞事?(我也做了很多壞事,不敢告訴大人。)
爸爸不準我們做的,為甚麼他自己卻做了?可以讓他早點死嗎?
母親說:
要愛。
要寬恕。
要感恩……
給予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那又如何?大人說要怎樣怎樣,這樣不准做,那樣必要行。那又怎樣?都沒有道理的(根本都不明白)。
只等有一天我長大,那時候我就自由了。
怎料半生過去,處於自己建造的東西之間,卻悵然失落。以前因為疑問得不到解答,以及成長時期的斑駁傷痕,使人遠離神,也遠離問題,走上「自己解決」的勞碌歲月之中。

導演不說道理,卻以意像回應:宇宙星辰、明暗生滅。上帝在黑暗中造光,把天和地分隔;天空有雲、熔岩沸騰;那時候,人在哪裡?生命從一顆顆細胞開始演化,然後恐龍統治地球,又被隕石所滅絶。那時候,人在哪裡?
小孩子遇上生死、對錯、是非之大問,探尋上帝之玄奧,終必徒勞。導演這一段拍攝宇宙星塵與自然景像,宏闊壯觀(因此這齣戲必須在電影院觀看)---- 然後男主角出生了,不也奇妙哉?脆弱的生命,為萬物之一,又渺小又偉大。
導演讓男主角走到曠野地,到岩石林,到遼闊的沙灘,遠離人手所造的,處於那些比人類還老的石頭與大海旁。這時他重遇童年的自己,還有母親、父親、弟弟;還有其他人……這是天堂嗎?上帝在那兒嗎?上帝無所不在,只是被人背向,被人遺忘。

主角童年恨父親之專橫,但父親心裡愛孩子,就想孩子堅強,苛刻也是為了他們長大後能面對殘酷的社會現實;結果主角還是跟著父親的教導,因為這社會的確殘酷----但那不是出路。也許這種對父親之反感,令人也逃避天上的父。
然而上帝還有母性:要愛。要感恩。要寬恕……母親的叮嚀重現於記憶;上帝總以溫柔忍耐的心,把走失的孩子挽回。
人面對生死對錯,勞碌營役,都是虛空,連聖靈也為人嘆息。但虛空並不是甚麼也沒有,因為神愛世人,只是恩典被人遺忘,等待某天,人終於回首,細聽那微小的呼喚,悲嘆必轉為讚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