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2 重审毛泽东的土地改革:中共建政初期的政治运动70周年的历史回顾|宋永毅
野兽按:因为谭松的《血红的土地:中共土改采访实录》,对中国土改产生了浓厚兴趣,谷歌发现加州州立大学教授、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主编的《重审毛泽东的土地改革:中共建政初期的政治运动70周年的历史回顾》一书,2020年1月由台湾和香港联合出版。该书通过四十多位专家的专题论文,以超过一千页和近百万字的篇幅,从横向和纵向剖析中共七十年前的所谓土地改革政策,揭开其前所未有的暴力性和荒诞性,及其对中国延续至今的伤害、对全体中国人所烙下的、没有愈合的伤疤,以及对当今中国的后患。
美国之音记者雨舟就该书出版引发的关注专程采访了宋永毅。
记者:中共的所谓“土改”其实也分为几个时期,那么它到底前后进行了多长时间?
宋永毅:中共的“土改”分为三段。早在30年代,中共就做了类似的事情,不过那时叫“土地革命”。而土地革命以失败告终,因为中共被民国政府军队从瑞金赶走而被迫进行长征。
1945年,国共两党开战,中共于是不搞减租减息了,但实际上到49年之间也并没有停止土地改革。
1949年中共掌权后,一部分解放区土地改革或者已经完成,或者还在进行中。中共49、50年开始颁布土地改革法。我们现在说的是包括新区的土改,就是包括四川和云贵等新打下来的地区,这就是全国性的。我们说的土改70年,其正式概念是从1949年开始算,而更具体说,中共全面土改是在50年到54年之间。
记者:土改研究者说的关于土改是谎言的提法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何说土改是谎言?
宋永毅:中共一开始信誓旦旦地说,要把土地给农民,说农民占有土地将是长久的,这就是所谓的新民主主义。但是,1950年年底,中共开始在会上说,要办合作社、要办互助组,要把土地从农民手里收回来。
我们说的谎言的意思,就是土改从理论基础、执行方法到后果全部都是谎言,而且长期以来没有被揭穿。首先,理论基础方面,土地改革法说,整个中国土地70-80%被地主富农占据,这是要搞土改最主要的论据。而今天大陆学者收集到大量证据,证明这个比例并非事实。民国政府当年的调查和今天研究人员做的调查都显示,其实地主只占有30%的土地。但是,中共如果承认这点的话,便无法把土改进行下去。
事实上,当时中共也是心中有数的。中共的土改专家杜润生当年在华中和华南地区进行土改工作,回到北京见到了毛主席。杜告诉毛,地主、富农占有的土地仅有30-40%,与你们宣布的相差很远;如果要按照70-80%的比例进行土改,只能把中农的土地也拿出来分了。毛说,你们在基层工作,当然知道情况,但是,这个比例到底是多少,我们不清楚,需要将来再认真调查。你看看,这么重要的国家大计,最高领导人竟然可以如此不负责任。
其次,在土改的执行上,《土改法》明确规定,不准使用暴力手段,要给地主保存一部分房屋、家具和用品。但实际执行则完全是另一套。叶剑英在广东进行土改被毛撤了职,因为他搞的是和平土改,不符合毛要的暴力土改的意图。叶剑英被调回北京。土改官员方方也被撤职。陶铸被派往广东继续土改,三个月之后自杀的地主便多达数万。
最后,土改的结果也是谎言。以广东为例,土改之前贴出的告示说,土地分下去之后将永久属于农民。事实上,这些土地马上便被收回。
更重要的是,这些谎言长期以来没有被揭穿,以至于一般人都认为,中共把土地分给农民总是好事,为什么要加以指责呢?
记者:那么,中共进行土地改革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宋永毅:去年刚刚逝世的人大教授高王凌曾经说过,中共土改不是为了改朝换代,而是为了改天换地;几千年来中国的皇权对国家的改换最多只到县一级,从来没有触及到村一级;中共的改天换地是要从村一级开始全面摧毁乡绅文明,换上它的民兵和它的党支部,甚至连它夺取政权时依赖的农会都予以取缔了;中共这么做的目的并非土地,所以,走的第一步就是划分阶级。这也是我们这本书的论文所指出的,土改就是为接连不断地搞阶级斗争而制造的借口。
记者:应该从哪些方面看土改被用作中共统治的工具?
宋永毅:我在导论中概括了三个方面:第一,土改为搞阶级斗争奠定理论基础,中共从此得以对人民划阶级和成份;遇罗克文革遭枪毙就是因为他发文称,人人平等,尽管人们出身不同但是拥有同等的权利;第二,土改开启了暴力革命、利用群众法外杀人的先例;第三,土改开动了政府直接对人民群众私人财产进行掠夺的国家机制。
众所周知,毛的政治运动一是土改,二是文革。文革中的大规模屠杀基本发生在农村,而且都是打着第二次土改的旗号。这是我研究文革所发现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发生在1966年8月,北京郊区一千多人被杀害。这些人都是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屠杀者都是贫下中农以及民兵。后者打的旗号是消灭土改中的阶级敌人;第二个例子是杀死数万人的湖南道县大屠杀,原因也是要搞第二次土改,于是要杀地富反坏右。而所谓的贫下中农和人民法院都是土改的产物。第三个例子是广西大屠杀,大约二十万人被杀害。广西负责指挥杀戮行动的革命委员会主任韦国清自己的统计则承认,“杀害了五六万人”,而且其中85%以上是土改中的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他说,这是填补第一次土改没有清算干净的空白。
还有其他地方,比方说内蒙古的“内人党”事件也使无数无辜者惨遭杀害,理由也是重新搞土改。因为内蒙古是少数民族地区,当年的乌兰夫脑子还算清醒,仅仅搞了温和土改。而内蒙古军区司令、解放军将领滕海清到任后则是要推翻过去的路线,重新在蒙族中划出地主,将上百万人定性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冤案。根据民间上访受害人的统计数字,估计致死4万多人;伤残14万多人;被抓、被迫害的人数大约有70万。
此外,同为边境地区的云南也类似。那时,毛的脑子还有点清醒,认为云南这样的地方既然还有蒋介石时期留下的军人旧部,应该温和些以便拉拢他们。1968年调任昆明军区政委、后任革委会主任的工程兵政委谭甫仁,公开提出搞第二次土改,导致云南出现挖心、割头、数千“站错队”群众几天内逃亡四川的悲情。
记者:继续评估土改的现实意义是什么?为什么说土改直到今天还在伤害着中国人民?
宋永毅:说到今天,迄今为止,中国农村依然没有出现发展的突破,比方说眼前,猪肉仍然要进口,原因就在于土地不属于私人。土地属于国家,政府大收红利,得以不停贩卖土地以达到不断牟利的目的。中共腐败的第一桶金就是从土地起步。这就使得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现在依然解决不了自己吃猪肉的问题。这样的后果就是土地改革留下的。
我们这套书收集的文贯中教授的研究指出,中国经济其他方面都可以发展现代化,唯一的问题是被土地所拖累。他在中国讲学时也大力提倡把土地还给农民,当然,习近平当然不会这么做。
土改是中共阶级斗争的源头,也是阻滞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源头。如果不反思土改,我们就很难解释,为什么毛时代那套阻碍发展的思维至今还能够在中国有市场;也很难了解,那套思维对中国的危害在哪里。
打个比方,现在很少有人会相信,朝鲜战争是“美帝”开了第一枪,因为国内很多学者做了大量工作,从苏联和朝鲜挖掘了大量资料,乘着中朝关系不热络的时机,发表了大量论文,厘清了人们心中对那场战争起因的迷思。所以,现在很少有老百姓会把“美帝”称作始作俑者。
我们现在在土改问题上所做的也是这样的工作。虽然我们不敢说能够做到怎样的程度,但是要一直做下去。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健康的历史记忆、如果不了解历史真相,其机体是不可能健康的。
记者:中共对土地控制的执着,是否可以解释为政治目的大于经济目的?
宋永毅:中共这么做当然有经济上的考虑。你想想,他把地主手里的土地一下全部收回,同时把地主家的金银财宝也掠夺一空。而且,金银财宝是现钞,也没有全部分给农民,而是绝大部分都装入了中央政府的口袋。同理,中共通过三反五反也掠走了很多资本家的钱。毛在195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称,那些钱“够打一年半的朝鲜战争了”。文革的抄家也让中央政府“斩获颇丰”。我的计算是,抄家收获的金银美钞占了1966年GDP的20-25%。这个数字是惊人的,而且是现金啊。这一下就让文革能够继续进行下去了。
当然,更重要的是,中共这么做是为了巩固政权、建立自己的长久专政。所以,土改是一个政治行动,就是我们说的“政治运动”。这样一来,往前看去,只要独裁专制不改变,中国的土地制度是不可能改变的,尤其从目前习近平走在回头路上的架势来看更是如此。
宋永毅:重审毛泽东土地改革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2019年09月23日
今年,2019年,是中共建政后发动的第一场政治运动—土地改革运动以及于此平行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七十周年的祭日。
由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美国劳改研究基金会主办,美国《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数据库》编辑部和台湾民主基金会等协办的“重审毛泽东的土地改革”的国际研讨会于9月18日到9月20日在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顺利进行。五十多位来自海内外的学者汇聚一堂,就中共的土地改革的国际背景、历史渊源、理论实践、暴力土改的前奏和后果等等方面进行了严肃深入的探讨。这是迄今所知的世界上第一个、也是规模最大的一个彻底否定中共的土地改革运动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大会共收到来自全球学者四十三篇学术论文,其中有二十九篇为大会演讲论文,十四篇为书面发言。其中来自中国大陆学者的论文有十六篇。会后,我们将很快又在海外出版近百万字的、上、下两册的论文集,以飨万千读者。

一个问题会迎面而来:时过境迁了七十年,是否还值得这么多学者对这一课题进行重审和辨析?换句话说,七十年后的今天再来重新研究和否定毛泽东的土地改革运动,还有什么特别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答案是非常肯定的。这不仅因为七十年来中共官方制造了种种关于他们的土改的“伟大成就”的政治神话,导致毛泽东土地改革的血腥真相至今还没有被全部揭露;还因为七十年前的土地改革的后果正滞后着中国大陆现代化的健康进程;更因为而当今的中共领导人千方百计地想让整个民族遗忘历史的教训,以便他们可以顺顺当当地延着这条独裁和极权的道路走下去。
政治运动的“原型”和不断重复的“情结”
中共建政伊始,便发动了所谓的“三大政治运动”: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朝鲜战争。一眼望去,便不难发见其中“土地改革”是最主要的核心所在。朝鲜战争前后虽然也有宣传性的政治活动,但其实质还是军事行动。镇压反革命是与之平行的,但很大程度上又是为土地改革衍生并为之服务的政治运动。中共的宣传机器,至今为止还在不断地传播着:土改把“农民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的神话。[1]恰好西方的神话学研究中有一种“原型批评”(Architype Literary Criticism)的方法,它源于20世纪初英国的古典学界崛起的仪式学派,大成于加拿大文学批评家诺斯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的《批评的解剖》(Anatomy of Criticism,1957年)。其要点在于研究神话中中反复出现的各种意象仪式、内在结构和人物类型,找出它们背后的基本形式,即神话原型。如果我们把它套用到作为政治神话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根据会议所收到的论文中的发现,我们也不难找到土地改革作为中共政治运动“原型”的一些特征和要素:1.阶级划分的运动理论基础;2.法外杀人的群众暴力形式;3.劫掠私产的国家财政机制。
第一,是“阶级划分”的运动理论基础。土地改革是中共建政以来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划分阶级成分的尝试。通过这一方式,中共撕裂了整个中国社会,建立了中国历史上从来过来没有过的以等级制为特征的身份政治制。这一土改的基本理论旨在煽动仇恨,制造敌人,挑动一部分民众去迫害和杀戮另一部分民众,成为中共后来以无休止的政治运动治国的理论基础。值得一提的是:与会的学者研究土地改革,但并不囿于“土地”,相反把批判和颠覆中共政治运动的理论基础放在首位。大陆学者叶曙明先生不乏见地地指出[2]:
历史学家认为,重新分配土地,改变土地所有制,是土改的意义所在。土地收归国家,也是对土地所有制的改变。但从土改之初许诺把土地分给农民和后来的兑现情况看,土地在农民手里,只是昙花一现的过渡,几年后就全部收归国有了。因此,土改的分田分地,拉开历史的距离来看,不过是发动群众的一种方法而已。
土改的真正意义所在,是划分阶级。……划分阶级,实际上,就成了农村未来政治的重要基石和支柱。
在他的论文〈土改阶级划分政策的恶意、随意及其后果〉,北美学者丁抒教授更进一步地指出:
对社会划分“阶级”,源自西方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固化的社会阶层,地主和农民之间不存在一条阶级鸿沟。……农民与地主的角色转换一直在乡村社会进行。中共高层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三个人的父辈都是实例。……中共的土改,要铲除传统文明,颠覆乡村社会,一是靠启用贫雇农、无业游民当村干部,二是靠极大地妖魔化地主富农,制造“阶级仇恨”,以达到“消灭地主阶级”的目标。……中共将抄没地富财产赋予“阶级斗争”的崇高名义,把抢夺解释成“土地还家”、“财产还家”。再加上“大家都抢”,平素从不偷、抢的贫雇农们也就随大流,心安理得地当了一回强盗。
纵观毛泽东时代数十次的政治运动,中共确实具有浓厚的“阶级划分”的政治情结。不仅每一个地区的土改结束后都有对于阶级划分的重新复查和再划分,即便是在农村已经走上集体合作化的道路后,中共还不停地抓所谓的“漏网地主”。比如,1955年10月22日,贵州遵义地区赤水县在县党代会的“重新划分阶级”的运动中清查出了“80多户土改中漏网地主,有些并混入互助合作组织”。为此,中共中央还专门发了一个〈关于土改中漏网地主土地处理意见给贵州省委的批复〉(1955年11月17日),表示坚决支持[3]。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四清运动里,中共中央认定:“现在农村相当普遍地存在着阶级成分比较混乱的情况,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很有必要认真地进行一次清理阶级成分的工作,就是说,经过群众的充分讨论,对每一个家庭的成分进行审查和评定,并且建立阶级档案。”[4]实际上,四清运动成了一场大规模的重新划分阶级成分的运动。到了文化大革命中,不仅全国城乡大抓“漏网地主、富农”,原来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地改革中“不划阶级”的政策也被全部推翻。中共中央于1971年8月12日发布了〈关于新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划分阶级成分问题的指示〉,“同意两个省、区在没有划过阶级成份或过去虽然划过但没有划清的少数民族地区,参照西藏社会主义改造中执行的原则和政策划分阶级成份。”[5]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的1979年2月27日,中共的国务院才发文推翻了上述“重新划分阶级”的错误文件。此外,中共的每一场新的政治运动,还会划分出新的属于“阶级敌人”的成份来,如五七年反右运动后产生的“右派分子”和文化大革命中新划出来的“走资派”。总之,中共的这一“土改情结”的目的,正是为了制造出更多无端的敌人来[6]。
令人十分忧虑的是:这一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的理论,至今为止还被铭刻在中共最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上:
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7]。
第二,是“法外杀人”的群众暴力形式。这是指即不通过起码的司法程序,煽动并通过大规模的群众(暴民)运动来杀人的形式。原中国社科院法律研究所的徐立志教授在研究这一施暴形式时指出:
按照古今出现的普适性法律和法的原理,土改中的乱象涉及到多种犯罪,其中有的属于严重犯罪,特别是有组织的法外打人、杀人……对于土改中的种种乱象,中共的基本态度是将其视为革命中的“过激”现象,是“自己人”对“敌人”的行为。……需要特别提及的是,中共处理运动乱象的基本政策,也从土改一直延续到“文革”。土改中的乱打乱杀等法外乱象,在以后的运动中一再出现,而且从事这种非法行为的人和被非法对待的人都有一些是从土改时期延续下来的,经历过土改的人都能从以后的历次运动中看到土改的影子。[8]
真可谓一语中的。如果我们把土改作为毛泽东时代第一个政治运动,把文革作为毛的最后一场政治战役,它们的共同点即是对某一社会阶层的大规模屠杀。不幸的是,这一社会阶层就是中共土地改革运动的主要打击对象—地主富农及其子女。文化大革命中有过三次震惊全国的对土改对象的大屠杀事件,其方式都是土改“法外杀人”的运动形式的延续和翻版。
其一,1966年8月26日至9月1日发生在北京大兴县的残杀土改对象—地富及其子女的事件,共杀死325人。最老的八十多岁,最小的还是婴儿[9]。
其二,1967年8月13日至10月17日发生在湖南道县及零陵地区的大屠杀事件,共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以地富为代表的土改对象及其子女占了近7000人,为76%。鉴于这场大屠杀的组织者和执行者都曾认为他们是在进行“第二次土改”,这一文革惨案就带上了挥之不去的土改“法外杀人”的阴影。而整个屠杀,都是在“土改补课”等等蛊惑人心的口号中进行的。[10]
其三,1967年底到1968年下半年的广西大屠杀。据机密文件透露,至少8.9-14万人遇难,而其中土改对象、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占了56%左右[11]。
如果我们进行一下更深入的调查和比较。还不难发现,上述三次文革中的大屠杀都不过是建国初期土地改革运动的延续和发展。例如,道县和广西发出杀人指令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其实不过是土改时期“人民法庭”的某种翻版。而施害者所采用的对受害者们先开“杀人现场会”斗争、再宣判,后用“刀杀”、“沉水”、“棍棒打死”、“活埋”、“火烧”等方法处死,完全是土改虐杀地主的全套流程。至于那些野蛮的私刑,也和土改中法外杀人的暴力一脉相承。值得注意的还有:刽子手在杀戮受害者的事前事后,还常常公开引用他们集体无意识里深深积淀的“土改经验”。例如,加害于受害者之前,凶手们常常先追逼他们的“浮财”—有的甚至是第一次土改时埋藏的“光洋”。并欺骗他们:这是“土改政策”,交出你的钱来,便可以买下你的命。[12]而在杀光了受害者全家以后,凶手们一定不会忘了土改的传统—瓜分掉受害者的全部财物—包括受害者的家庭里的青年女性。如果说有什么不同之处,那就是暴徒们再也无法从受害者那里分得土地。因为第一次土改中他们分得的土地,早已经被中共在一两年后以“农业集体化”的名义收归了国有。
行文至此,我们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到一个难以回答但一定要回答的问题:在当年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到底有多少地主在残忍的暴力下死于非命?在时过境迁七十多年、而中共又严密封锁档案的情况下,比较准确地计算出受害的地主的人数是很困难的。但是,根据一些已经公开的官方的统计材料,做一些合理的推测还是可能的。以下是根据多种官方文件推算出的中共建政初期土改中的地主非正常死亡人数的表格:
年度
总人口
所占比例
自然死亡率
地主实际人口
1950
465,900,000(农业人口)
4.75%
21,880,000*
1954
602,660,000(总人口)
2.6%**
15,669,160
1950-1953
6.88%(4年)***
1,505,344
差额(非正常死亡)
4,705,496
*这一数字来自国家统计局的《全国土地改革前各阶级占有耕地情况》一表,载黄道霞、余展、王西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第1353页。
**这一比例来自1954年23个省市,自治区1.5万多户农家资料的统计的《全国土改结束时各阶级占有耕地情况》,载杜润生主编:《中国的土地改革》,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第560页。
***1950-1953这四年的自然死亡率,根据国家统计局《1949-2003年中国大陆历年人口数据》一表得出,原载百度百科:https://wenku.baidu.com/view/16182d00b52acfc789ebc9e5.html
关于土改期间中国地主非正常死亡人数的算法是:1950年土改前地主实际人数(21,880,000人)–1954年土改结束后地主人数(15,669,160人)–4年自然死亡人数(实际人口X四年自然死亡率=1,050,240人)=差额4,705,996人。
根据以上的计算,在三年的暴力土改中,中国所谓的地主阶级的非正常死亡(被杀和自杀)人数大约高达470万人。它应当是中共建政后所有政治运动中非正常死亡人数最高的一次。这一数字,和不少长期研究中共土改的学者的估计雷同[13]。
根据有关看到过机密中共文件的作者泄露,到毛泽东死后的1977年,全中国地主大约还有279.7万人幸存[14]。换句话说,自土地改革以来的24年里,中国的地主阶级共有1808.3万人死亡。他们或是在土改后的各种政治运动中被迫害致死,或是在贫病交迫的政治歧视中漠然逝世。作为一个有两千多万人之众的中国富裕农民的“阶级”,被中共从肉体上残忍地消灭了。
第三,中共土改运动“原型”中的最后一个特征是劫掠私产的国家财政机制。这里的的“劫掠私产”当然是指对国民私人财产的大规模的抢劫和掠夺,而这些行为则又常常是得到国家政权的默认或公开鼓励的。
土地改革时期大规模的分地主“浮财”的现象可算是这类形式最早的“原型”。紧接着,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早期的“三反”、“五反”运动里,对所谓的“不法资本家”的大规模的群众斗争,追逼和没收他们的私人钱财,应当是这一“原型”的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初期,这一“土改情结”有了恶性的发展。最典型的是1966年8月,由北京红卫兵发起,继而在全国范围风行的对“阶级敌人”的抄家运动。本次会议的不少论文都揭露了造成土改大规模法外杀人的契机,常常是那些所谓的“土改积极分子”(实为地痞流氓)的“追逼浮财”。但是由此引起的种种酷刑和杀戮,从来没有得到国家政权的惩处。至于1966年红卫兵的“红色恐怖”,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竟发表了〈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的社论,公开赞扬红卫兵抄掠公民“隐藏的金银财宝”的非法行为[15]。
为什么中共的国家政权要纵容和赞扬这种光天化日之下的盗贼行为?其实背后还是有不可告人的、又非常实用和功利的财政目的的。例如,据大陆学者曹树基的研究,中共在土改初期所发动的“减租退押”运动,其隐藏的经济目的是为了把这一运动的的胜利果实来充实1951年政府的新增农业税,并以此来支持朝鲜战争[16]。同样,不久后,“三反”、“五反”运动里逼出来的工商业者的财物,也被用来解决政府的财政危机。毛泽东就高度评价了这种做法,喜形于色地称赞道:“‘三反’、‘五反’清理出来的钱,可以打(朝鲜战争)一年半。”[17]在1966年10月的中共中央十月工作会议上,颁发了一份赞扬红卫兵的“巨大功绩”的机密文件。该文件透露,仅红卫兵抄家所得的现金,就有人民币428.8亿元;美钞355.8万元(相当于人民币875万元);英镑和其他外币373.9万元(相当于人民币2566万元);黄金120万两(相当于人民币1.5亿);白银30.8万两,银元978.9万元(相当于人民币1300万元)[18]。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1966年全中国的GDP按人民币计算,不过就是1888.7亿元。仅这些几个月内抄来的现金,就有432亿之多,占1966年全中国GDP的23%,而且还是立刻可以流通的现金。对于文革初期面对因为动乱而造成的国内生产急剧下降的中国政府,无疑有雪中送炭的危机救援的作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怎么会不对红卫兵“巨大功绩”大加称赞呢?
颇具讽刺意义的是:这种劫掠私产的国家行为,竟很快就从国家纵容农民对地主富农私有财产的劫掠转化为国家对农民私有财产的持续劫掠。1952年,全国性的土地改革还没有结束,中共已经开始强力推行农业合作化。在以后的数年内,中国所有的农民——不管是被贫下中农剥夺了土地的地主富农,还是刚刚获得土地的贫下中农——全部被国家剥夺了他们的土地。不仅如此,中共还在1953年强行推出“统购统销”的政策,超额征集农民的余粮(实际上就是口粮)。因为合作化了,农民便失去了他们刚刚在土地改革中得到的土地和生产工具,其人身也不得不依附于党国的基层细胞——合作社及其干部。实现农业合作化后,全国1.1亿户个体农民,被组织到了约100万个农业合作社。农村的粮食统购统销就不需要再直接与农民发生联系了,统购与统销都可以通过农业生产合作社来进行。就这样,农民作为生产者,就不仅失去了对土地的支配权,还进一步和他们生产的粮食完成了剥离,彻底地失去了对粮食的支配权。有论者把这一过程称为“第二次土改”,也是不无道理的[19]。
作这一如是观,1958年开始的人民公社化也可以称之为“第三次土改”。毛泽东在河北徐水县关于农业生产大跃进的讨论中,总结出了公社“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军事共产主义的组织形式。既然人民公社化后的整个农村都变成了军队和兵营,那当然就不允许有农民再有任何私人财产。当时,毛就和徐水领导人张国忠等兴致勃勃地讨论过“进行共产主义教育,除生活用品外,关于房屋、树木、羊群、自留地都要转化为公有。”[20]毛泽东的倡导很快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对数以亿万计的农民私有财产彻底剥夺和劳动力的恶性毁坏。以徐水为例,“在扫除私有观念的影响下,有些村庄鸡猪和树木也归了公,把锅砸掉炼铁,户户不冒烟,全去吃食堂,有些地方甚至连箱箱柜柜都归公有。群众的基本生活资料—住房也要拆除……[21]”更有甚者,中共在大跃进—大饥荒后期的“反瞒产运动”里,对农民完全采取了土改斗地主的方式—刑讯逼取他们的最后一粒存粮。以“信阳事件”中的“反瞒产运动”为例,“全区被打致死群众达六万七千余人,被打致残三万四千余人。残害群众的酷刑在几十种以上,如吊梁、跪砖、砸牙、剪耳朵、刺手、缝嘴、火焼、铁烙、火葬、活埋等等,真是残忍毒辣,骇人听闻。[22]”曾几何时,作为中共土地改革运动的胜利者的中国农民,不仅在数年后就失去了他们的全部私有财产,还沦落为国家机器最悲惨的农奴,活活饿死了数千万人,成为中共土改运动的最大的失败者。
破除“解放农村生产力”的神话
中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开篇中说,“土地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23]。这是长期以来纠缠着读者甚至研究者们的又一个革命神话。对此,美国学者杰克·贝尔登(JackBelden)很早就提到,不少西方学者当时就都有异议。他们认为:“分配土地本身并不能在中国产生健全的农业经济。它既不能创造出工业化所需的资金,也无法消除农村人口对土地的压力”[24]。另一个美国学者马若孟(RamonH.Myers)也曾指出:“1950年以来的事实证明,1950年代土地改革与其说是促进不如说是阻碍了农业生产力和产出的增长,因为这一改革消灭了私有制,从而抑制了刺激工作和革新的动力”[25]。其实,一个简单而清楚的史实是:中国真正的全面工业化是在1978年后三十年间的“改革开放”中才实现的,这离“土地改革”已近六、七十年之遥。因此,土改“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之说实在是离题万里之谈。
中共政府和其官方学者一直用“土地改革”后全国粮食总产量的增加来说明它的革命神话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被引用得最多的是当时的政务院副秘书长廖鲁言的说法,即“一九五一年全国粮食生产量较一九四九年增加百分之二十八,今年可较一九四九年增加百分之四十左右,可超过抗日战争以前最高年产量百分之九。[26]”这其实也是经不得仔细推敲的。首先是中共的统计数字常常是因政治需要而夸大的,不足为信。廖鲁言写这篇宣传品时,尚在1952年的9月,统计数字根本还没有出来,但他就急不可耐地炮制出“百分之四十左右”的增长率了。其次,中共享和平时期、即五十年代初期的产量来和四十年代全国性的战乱年代相比--无论是抗日战争(1937-1945),还是国共内战(1946-1949)时期——都不是一种公正的比较。最后,战后中共统一了中国大陆,在和平的环境里拥有了激增的人口和多余的劳动力,可以用来大量垦荒和精耕细作,如果没有总产量上的增加才是不可思议的。
已故的中国人民大学的高王凌教授对土改素有研究,他是比较早挑战土改“解放农村生产力”的学者之一。在本书所收的〈土改的极端化〉一文中,他就指出:“土改的目地,最初的说法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但是土地改革的这种作用,一时间却难以看清,有时还不难发现相反的例证。如各地都有经验表明,土改后的头一二年,生产往往出现下降。”参加本次会议的加拿大独立学者滕春晖和大陆学者马锡昌一起递交了一篇题名为〈土地改革对农村生产力和农村社会生活的损害和影响〉的论文,也指出[27]:
大多数地主是“小地主”,往往是靠勤俭持家和种田本领及经营有方发展起来,他们几乎都亲身参加农业劳动。对他们的剥夺,就消灭了这部分人的生产能力,……所以在当时中共内部关于经济问题的多份文件中,几乎是不加掩饰的承认,土改造成了群众普遍的生产困难。1948年5月10日,中共东北局后勤部党委在《目前后勤运输状况的统一与使用》一文中说:两年来,我们的生产力比伪满时不是扩大了,而是缩小,比九一八以前恐怕也不如。减产是可以肯定的。原因:东北过去地主富农占很大数量,土改后大生产破坏了,土地小块小块分给农民;而农民组织和经营的经验不足;使我们减产。这是第一。第二,土改中打击面宽了些,使过去生产中占很大数量的中农、富裕中农被打击,因此生产情绪受到影响;第三,地主富农土改中打的狠一些,生产有困难(种子、牲口、农具)影响一些生产;第四,农村劳动力减少很多,参军参战数字很大--生产力水平回到少帅那个时代。
其实,我们即便用中共自己五十年代的一些统计数据,也可以看到在人均粮食产量上非但没有增长,相反是倒退的:
产量\年份
1936年
1950年
1952年
粮食产量(斤)
277,400,000,000
249,400,000,000
308,800,000,000
人口(人)
471,100,000
551,960,000
574,820,000
人均产量(斤)
589
451
537
数据源:国家统计局编:《伟大的十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粮食中不含大豆。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1950年和1952年的人口,根据国家统计局《1949-2003年中国大陆历年人口数据》一表得出,原载百度百科:https://wenku.baidu.com/view/16182d00b52acfc789ebc9e5.html
另外,从各地“土地改革”运动的源文件里,我们也常常发见中共的暴力土改对农业生产直接的严重破坏。例如,贵州省清镇县,原是中共“土地改革”的试验区,在土改后却出现了农民不想生产,让土地大批抛荒的现象。中共贵州省的机关报《新黔日报》如此报导[28]:
清镇一区芦荻乡右二村是今年春季土地改革试验区。土地改革后,于八月间经检查,该村丢荒田土现像很严重。……其中以贫农丢荒土地最多,自耕中农次之。全村合计共荒田六石六斗,占全村田面七十石零六升二合的9.42%;共荒土五斗七合半,占全村土面五石四斗五升的9.78%,共丢荒产量合32564斤,占全村总产量的53517斤的6.33%。所以造成如上丢荒田土的严重情况,主要原因是该地各级领导忽视领导生产,指导思想上对生产的重要性认识不明确;对土地改革后的生产问题没有深入下去了解情况,只盲目认为土地改革后群众生产情绪高,在这上面可以不必多化(花)工夫。……土地改革后,又没有讲明租佃、雇佣自由,只是机械地动员群众生产,一些缺乏劳动力者,为了避免剥削改变成分,怕把田土出租。如中农黎明春,共有七斗田,前几年出租二斗五升,今年全部收回自己种,结果荒了田二斗。
这种破坏更是在精神层面上的。因为“斗争土改”的盛行,使农民在几千年来形成的勤劳致富的信仰轰然倒塌,使他们不愿意通过生产来发财致富,在不少地方竟造成了人为的饥荒。山东的莒南县、内蒙古的赤峰市干村都是如此。据机密档案记载,整个山东暴力土改后1948年出现了空前的歉收。莒南县一直到1949年还没有摆脱灾荒的阴影[29]:
发生饿死人、卖老婆、买小孩子的严重现象,如莒县大石头区朱家庙子村一老大娘,即因挨饿而吊死,城里民村唐林民饿死,郑X仁要卖老婆,于X文要卖孩子等。
土改对农村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和社会财富的极大消耗,不少中共领导人也是有清醒认识的。1947年8月27日,董必武在全国土地会议上就说过[30]:
社会上的积蓄在土改中大量被消耗了,过去各地都发生过这种现象,领导机关不注意就消耗得更多了。在斗地主、富农时,斗来的果实吃掉了一些,用掉了一些,由集中到分散不可避免的要毁损些。有些地区中农在土改中,也故意消耗他们自己的积蓄。如在执行政策中侵犯了中农的利益,再加上地主富农的谣言,那就消耗的更多。地主富农消耗,甚至故意破坏自己的积蓄那是更普遍的现象。
经历了几十年的政治运动风风雨雨的中国人,应当起码明白文革中流行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中的两者其实并没有任何逻辑上的因果关联。在现实生活中,革命终究是破坏了生产力的,尤其是在暴力革命刚刚结束的一段时间内。当然,经历了较长时间的社会和政治震荡后,生产也会逐渐得到恢复和增长,但这不过是政治震荡后的非革命的“和平”带来的经济恢复和好转而已,它们绝非是结构性的增长,更不是中共及官方学者们所吹嘘的革命所带来的“生产力”的“解放”。
新视野·新史实·新思考
本次会议的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开场:由来自日本、台湾、中国大陆和美国的学者一起组成了题名为〈国际和比较视野下的土地改革〉的首场讨论。土地改革在世界历史上并不是自中共始的新鲜事物,也并不一定要充满流血和暴力,以牺牲几百万无辜的人命为代价。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有过日本的土地改革。五十年代几乎和中共的暴力土改同时展开的,还有台湾的和平土改。日本学者日吉秀松教授在他的〈日本的农地改革和民主化〉详细地介绍了日本战后在美国为首的盟军总司令部指导下的土地改革。他指出,虽然[40]这场土地改革是在外国势力压力之下进行的」,但是“在没有发生流血事件的情况下实施了这样的巨大改革”。日本土改的形式是和平的,是政府通过佃租地的强制收购以解决农村贫困。它不仅基本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在日本消除军国主义的基础以及在农村实现民主化之目的也获得实现,同时,日本的土改成功地在农村阻止了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台湾学者周茂春博士,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廖应豪先生和旅美华人作家余杰都就台湾和大陆土改的对比发表了精彩的见解,大大地拓展了研究者的视野。他们都认为:台湾五十年代初期的“兼顾地主”的土改是非常成功的,如余杰所言[31]:
中国的土地改革指向“耕者无田”的国家资本主义,台湾的土地改革指向“耕者有田”的利伯维尔场经济。在此一脉络之下,两岸的土地改革形成了四个重要的差别:第一,社会及历史背景不同;第二,学习和效仿的对象不同;第三,实施方式(主要是暴力程度)不同;第四,对此后两岸的经济、政治发展路径的影响不同。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土地改革都是成功的。北美的国际共运史专家程映红教授把北朝鲜和北越的土改与合作化与中共的土改和合作化放在一起考察,指出它们的共同点是[32]:
共产党革命在农村政策上的“初衷”是建立对农村的全面控制,在社会经济政策上则是通过土改建立小农制度,但很快就向集体化过渡。这个集体化可以是合作社,也可以是人民公社,总的倾向是越大越好,因为越大就意味着国家控制能力的越强。……从土改到合作化,这些国家经历的,实际上是从身份自由的个体农民沦为国家农奴制的过程。
本次会议还标志了在中共土改研究上的一些重要突破。其一是提供了长期以来被忽略了的新史实;其二是填补了以往研究中的空白。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土地改革既然是中共建政后的第一场政治运动,应当一开始便是中共以“恩施者”的名义出现,给农民分配土地。然而,本书却掀开了为重重叠叠的谎言覆盖着的昨天的真相:中共首先是以“剥夺者”的面目出现,一解放便向农民横征暴敛,激起了全国性规模的民乱和“匪变”。但多年来,在“土地改革”旗鼓的遮蔽下,学界忽视了1949-1951年新中国发生的其他历史事件。近年来,基于档案数据的开放,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有机会把关注视角转向新中国初期的征粮、减租退押、经济清算以及财政金融物价等系列运动,并取得了令人欣喜的进展。
华东师范大学王海光教授递交的〈土改的前奏曲:中共建政时期征粮问题再探讨〉和〈民变和“匪乱”——中共贵州建政第一年征粮事略考〉两文,就告诉读者“中共占领新区之初,立脚未稳,就急如星火地在当地征收1949年度的公粮,禁止银元贵金属货币流通。征粮数额大,方式简单粗暴,激起了当地民众的激烈反抗,以至酿成大规模的民变和“匪乱”。……新区征粮和匪乱的研究,呈现出了中共建政过程更为复杂的历史面相,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土地改革为建政中心事件的历史叙事。”[33]与此类同的还有曹树基教授的〈“大户加征”:江津县1950年的征粮运动〉和〈江津县减租退押运动研究〉两篇论文。曹文指出:“为增加财政收入、缓解政府压力而进行的‘大户加征’与‘减租退押’是实质性的土改,而土改中的分配土地,只具有像征的意义。在实践的层面上,‘大户加征’与‘减租退押’的本质是征粮,而土改中分配土地的目的之一,也是征粮。这是因为,经历过‘大户加征’与‘减租退押’之后,地主阶级已经无力承担高额的农业税,而分配土地,就成为调整税基的最好方式。”大陆青年学者刘诗古依据新的史实,得出了如下对官方叙事极有颠覆性的结论[34]:
我们可以形成关于土地改革的三点新认识。其一,1949-1950年,中南区各地农民已自发不向地主交租,这实质上意味着土地产权关系已发生变化。佃户拥有了该块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转让权被中共禁止,地主对土地没有了任何实质意义上的权属占有,“土改”已经发生。其二,为了避免在收不到地租的情况下,继续承担一年两季甚高的阶级累进农业税,地主阶级多希望政府早日土改,而并非如过去所言的那样,地主阶级对“土改”进行着顽强的抵抗和垂死的挣扎。其三,中共政权在新解放地区有意实行农民继续交租,随后依法减租的政策,刻意推迟“土改”时间,以便有充分理由对地主阶级征收高额的阶级累进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在填补以往研究的空白方面,会议的其他参加者们也很有建树。大陆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后研究生刘志递交了一篇题名为〈国共内战中的土改难民(1945-1949)〉的论文,揭开了土改史研究中一个长期无人注意的侧面:“土改难民”现象。国共内战期间,因中共在解放区的暴力土改,造成的空前的人道灾难——“土改难民”竟达近四千万之多!北美女学者李江琳是研究藏族和西藏问题的专家,这一次却为会议提供了题名为〈中共在民族地区的土地改革:以云南为例〉的论文,为学界了解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地改革提供了难得的窗口。其实,也有少数中共的干部比较务实,对暴力土改有所抵制。原澳门大学教授程惕洁的〈内蒙东部“温和土改”与乌兰夫的文革倒台〉一文告诉我们:原中共国家副主席乌兰夫,在主政内蒙20年间(1946-1966年),曾在东北解放区土改运动中,成功抵制并及时修正东北局的左倾政策,推行过著名的“三不两利”政策(不分、不斗、不划成分;牧主、牧工两利)。这一政策取得了极好的效果,使内蒙在大饥荒时期,接收并救助了几十万内地流民,并以余粮支援了京津沪。但是,这些都成为文革中他被毛泽东和周恩来整肃倒台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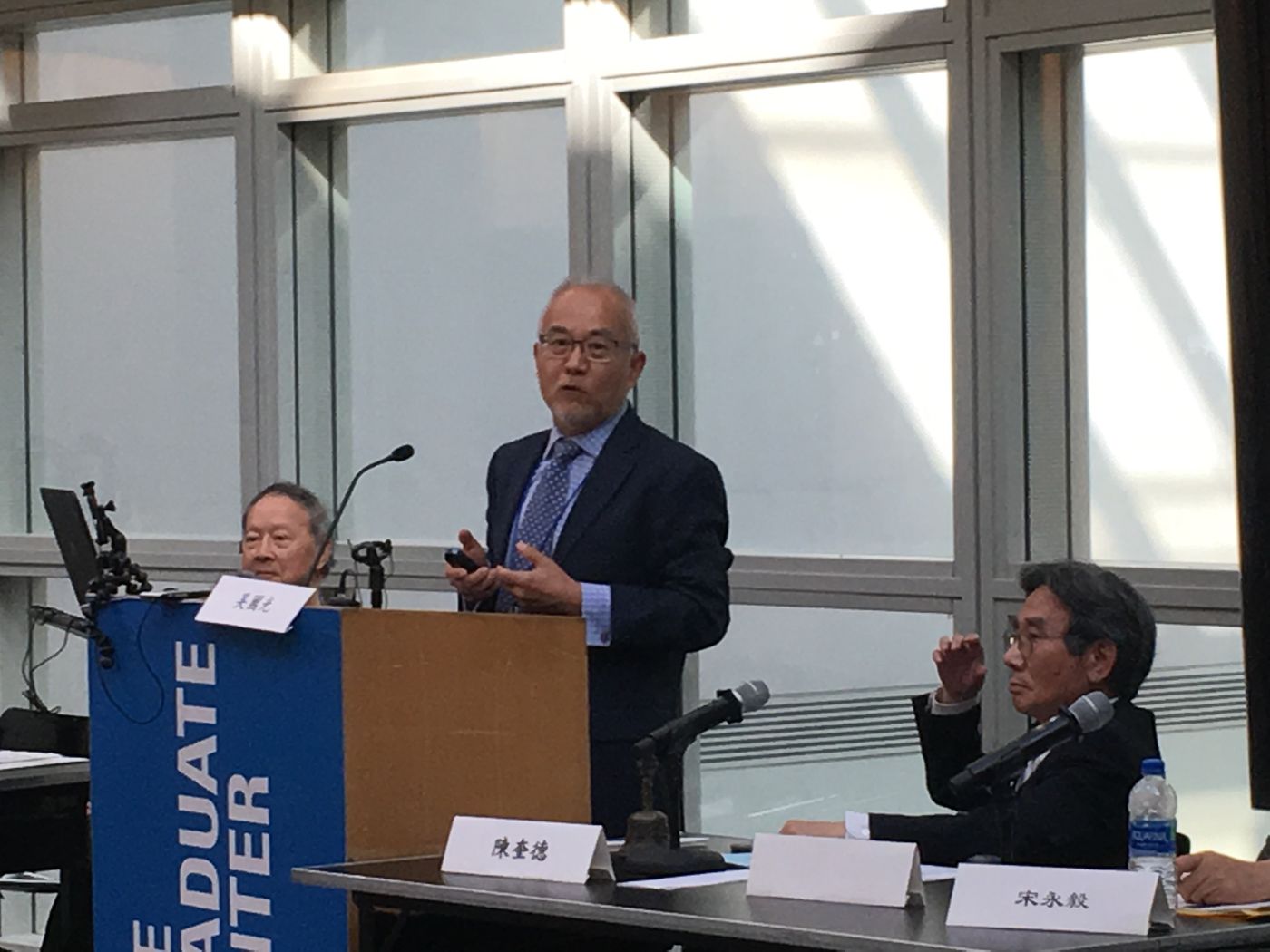
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也不乏有逆中共的暴力洪流行舟,凭着一己之力大声疾呼、反对中共土改的先知。本次会议有两篇论文介绍了当年上书毛泽东的著名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先生。北美学者丁凯文的〈董时进vs毛泽东——中共土改的回顾与辨析〉非常详细地梳理了董先生在他一系列著作中从根本上质疑毛泽东的土改思想的理论要点。这一总结提纲挈领,使董先生为岁月尘封了七十多年的前瞻性的思想得以发扬光大。大陆学者,原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郑也夫先生也递交了一篇论及四位的公共知识分子对土改态度的长文〈土改中的四位公共知识分子〉。那四位公知,除了坚决反对中共土地改革的董时进先生,还有清华大学和人民大学的吴景超教授;清华大学和中央民族学院的费孝通教授和清华大学的潘光旦教授。在土地改革问题上,后三者和董时进先生不同,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土地改革。当然,他们都反对暴力土改。另外,他们的身份既是自由派知识分子,又都是当年中共在内战中的同盟军——民盟的主要成员。由于对中共的本质缺乏清醒的认识,他们都没有像董时进先生那样,果断地选择流亡海外,而是接受了中共的统战和洗脑。最后,他们竟然都接受和认同了中共的暴力土改。因此,这一论文实际上已经把探索拓展到整个中国知识分子和土改关系的崭新领域。在该文的结尾中,郑也夫教授对知识分子的集体投降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诸如“保守主义的缺失”,“封建话语权上的放弃”和“土改中的冷血和自私”等原因。最后,他的总结给人以经久的震撼:
中国知识分子集体赞同暴力土改,是中国文化精英的良心泯灭,是中国知识阶层的集体投降。认可了这一次强暴,就很难抗拒下一次强暴。认同了对他人的强暴,也就极难阻挡对自身的强暴。因此土改中知识阶层的表现是决定性的,所谓初战就是决战,从此他们在与中共的博弈中,如同小儿,任凭摆弄。
对中共暴力土改的新探索和新思考,一直是这次会议的重点所在。
中共为什么一定要使用暴力土改?对此学界有过种种有意义的探讨。例如,清华大学的秦晖教授认为:“农民也许不会为了几亩地‘抛头颅洒热血’,但如果共产党的胜利他们可以得到好处,共产党的失败他们就会有生命危险,那当然他们就会容易被高度地动员起来。因此,一定要搞流血土改。……有了投名状就不怕发动不起来了”[35]。对此,高王凌则提供了一个更扩大的政治框架来理解土改暴力,他认为他认为中共土改的重点并不是为了分田,而是为了“推翻旧的政权,同时建立新的政权组织和政治制度,特别是在基层自下而上地进行重组……也就是说,中国的土地改革不仅是‘改朝换代’,而且是‘改天换地’,因此它不可避免地要走上‘斗争土改’的道路”[36]。原重庆师范大学外贸学院的谭松教授,因为坚持对川东地区的土改真相进行独立调查,被中共开除了公职。对中共的暴力土改,他在实地调查中得出的结论是:“中共土改时的大屠杀,自然是要对地主乡绅和所谓反革命进行肉体消灭,但是,在屠杀过程中所使用的这些手段,它所呈现出的公开性、随意性、残暴性、奇特性等,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要最大化地制造恐怖,要让那些活着的人对这个刚刚登场的红色政权心怀恐惧从而服服帖帖不敢反抗”[37]。加拿大维克多利亚大学的讲座教授吴国光博士则更进一步认为:“激发仇恨,制造仇恨,固化仇恨,既是土改暴力的原因,也是土改暴力的结果;……从而为建立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在占据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农民中打下群众基础。随后,当无产阶级专政施展威力时,农民在土地改革中刚刚获得的土地即被剥夺;土改中的暴力弥漫,也就为中共政权此后快速地强行收归土地为国有化铺平了道路。[38]”
另一个长期以来对家乡山西省平州县的土改进行实地调查的学者,澳门大学社会学教授郝志东,则以西方社会学的社会互动的理论,对土改中的暴力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他认为:“土改的暴力是干部之间、干部与农民之间互动的结果。干部需要让农民‘命运、良心、人道、面子’等传统思想,和地主富农‘撕破脸’,农民也需要接受这种发动,然后暴力土改才有可能。让干部‘放手’,让农会说了算,也经过了一个上下互动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重新定义阶级、命运、良心、面子等观念的过程”[39]。
论及暴力,与会的学者们还注意到了与土改并行并为之服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关于镇反运动的学术研究现状,杨奎松有过论述:“对于这样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镇反运动,至今尚未见多少深入的学术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当中,镇反运动的作用向来在多数人的心目中是争议最少的。”镇反运动之所以“争论最少”,根据杨杨奎松的说法,是因为“共产党领导之革命政权初创,通过镇压反革命运动,以固其根,以立其威,亦向被国人视为情理中事。”[40]新生政权的巩固和奠基是否必须来一场如此大规模而又如此血腥的镇反运动?北美独立学者和民主运动理论家胡平在他的论文〈背信弃义+残暴的史上之最——对中共镇反运动的盖棺定论〉中批驳了这一说法。他认为:“这种评价是基于对镇反运动性质的严重误解,所以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作为革命政权,中共在建政初期镇压大大小小的反革命活动,本是例行公事,是中共各级领导早就在做、而且一直在做的事。既然如此,哪里还用得着最高领导人特地出面发文件,专门搞成一场大运动呢?由此,我们可以推测,中共发动镇反运动,其实是借题发挥,是假借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名义,……去镇压那些并没有从事过什么反革命活动的另外的群体。”通过分析毛泽东自己的指示,胡平一针见血地指出:镇反运动“是假借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旗号,对那些只是历史上曾经反革命而没有任何现行的反革命活动,并因此得到当局承诺宽大处理的群体算历史旧账。”
镇反运动中的重要对象之一是所谓的“反动会道门”。长期以来,对这一课题海内外都缺乏研究。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这一次递交了一篇〈中共摧毁会道门和极权主义的建立〉的长文,填补了一个久违了的学术空白。根据沉实的历史档案,夏文首先考证出中共在取得政权之前,对所谓的“反动会道门”是一贯取“实用机会主义”态度的,“从1921年中共建立到1949年中共建政,共产党对会道门是既利用,又打击”。但是,“从1950年到1953年,共产党对所有的会道门一概定为“反动会道门”,开始了全面残暴镇压时期。”“从1954年至今,中共/中共政权对会道门和后来定位为邪教的组织开展了长期监控、露头就打的高压常态时期。”在细致地回溯历史后,夏文不无幽默地总结道:
毛泽东和中共罗列的所有指控“反动会道门”的罪行:落后封建迷信、家长制统治、教主崇拜、阴险残酷的戒律、被外国势力操纵利用、称皇称帝、对道徒剥削摧残、骗取钱财、奸污女道徒,等等,今天无一不可以用来起诉中共和它的首领毛泽东。中共对会道门成功的迫害和屠杀,主要是它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能把现代意识形态和政党方式与现代军事武器和科学结合起来,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毛主义教门。
以上种种,大会都把对中共的土地改革和整个中国当代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为学科建设树立了开拓性的典范。
重审中共土地改革的当代性和挑战性
在这一国际学术会议召开时,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新一代领导人,正在反历史潮流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方面,他们公然取消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成果,如领导人的任期制,企图把已经前行了五十年的历史车轮拉回到长夜未央的毛泽东时代去。另一方面,他们更加大掩盖历史真相的力度,动用国家机器的力量,重新制造出种种光怪陆离的革命神话来。
在本次会议中,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郭建教授提供了一篇令人兴趣盎然又寻味无穷的论文,即〈五个《暴风骤雨》中的土地改革〉。这里说的五部均以《暴风骤雨》命名的作品包括周立波的长篇小说(1948);谢铁骊执导,于洋主演的黑白故事片(1961);蒋樾、段锦川导演的独立制作纪录片(2005);凤凰卫视的5集纪录片(2012);以及何涛执导,2015年开拍,至今尚未播放的50集电视剧。前两部——周立波的小说和于洋主演的故事片——当然都是服务于中共政治的、被称作是“中国土改教科书”的红色经典。在改革开放以后,它们都收到了同名的独立制作纪录片无论在史实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的全面挑战。然而,在故事片《暴风骤雨》问世半个多世纪以后,在2015年,根据小说《暴风骤雨》改编的影视作品又在策划中,即规模颇为可观的50集电视剧《暴风骤雨》,由何涛执导,同年5月19日在黑龙江伊春开机。这部电视剧仍被称作表现土地改革的“红色经典”。但是,据“东北网”,剧本“在充分尊重原创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取舍、改编……”,在红色经典的旧瓶中装上一些如爱情、传奇、谋杀、复仇之类的离奇情节。对此,郭文一针见血评为“红戏粉唱”:“既符合官方三十年来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导向,又迎合许多观众对匪特传奇、女中豪杰的恋情,像是一种微妙的妥协,不失为寓宣教于低俗娱乐的典范。”
同样,夏明教授关于中共摧毁会道门和极权主义的建立的论述也并没有忘却从历史中观照现今。他指出:“人们担心,当下的中国是否有迹象在倒退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完成这篇论文后,我的担心是:‘文革’还有底层造反斗走资派/当权派,而当下的中国是一个教主似的‘领袖’在乌托邦理想的激励下,对持异议和反对他的‘敌人’开始了以极权国家暴力机器为主体的残酷镇压。所以我们该问,中国是否在走向‘镇压反革命’/‘镇压会道门’时期?”
捷克的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曾经说过:“民主与专制的斗争,在某种意义上便是记忆和遗忘的斗争”——中共的种种倒行逆施反而使这次研讨会有了独特的挑战意义:它是中华民族不泯良知的一次体现;它象征着海内外知识分子对学术自由的有力坚持;它还是海内外学者共同重构对所谓的“新中国”的集体记忆的不懈努力。
除了揭示历史真相,健全民族记忆外,这一重审毛泽东的土地改革的努力还有什么另外的当代意义呢?会议的发言和学者们递交的论文在这方面也有独特的贡献。他们一致指出:中共土改对当前中国的影响是一方面造成了执政党的全面腐败;另一方面是滞后了中国的现代化。例如,谭松教授的论文〈从土地革命土地改革到土地财政〉指出:因为中共的土改“用暴力将私有财产变为所谓的公有,然后又用权力将公有变为权贵们的私有”,竟成了中共当前极端腐败最主要的历史渊源:“”中共官员腐败,60%以上都与土地有关」。一方面,中共这个“党国”大地主“通过出卖土地养活庞大的地方政府官员”;另一方面,“中共各级官员在卖地中大肆私饱中囊。[41]”旅美作家余杰的思考更为深入。在参考了众多西方学者对于台湾式的土地改革对现代化的贡献后,他指出:人类历史上,除了欧洲与英美国家(英美加澳纽)之外,仅有三个国家完成开放准入秩序的转型:日本、南韩与台湾。而这三个国家,都成功地进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他认为:“台湾相对而言比较成功的土地改革,或许能为中国未来的土地改革及民主化提供有益的启发。[42]”
多年以来,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教授文贯中博士奔走于京沪之间,大声疾呼“吾民无土”[43],要求改变大陆的现有土地制度,允许土地私有。这次会议他也递交了论文〈暴力剥夺型土改,强制型农业集体化—中国城乡发展错序之制度根源〉。这一论文对我们了解中共土地改革对现代化的恶果极具启发性。该文运用诺奖得主阿瑟·刘易斯(W.ArthurLewis)的理论,来分析健康的现代化的转型要素。刘易斯认为:第一拐点是随着城市现代工商业的不断扩张,最后一个农村剩余劳动被城市吸收;第二拐点是城乡收入差的弥合。为了抵达这个拐点,必须不断地使最无务农技能和意愿,生产力最低,因而最贫困的农户首先离开农业。唯有这样,经过市场的反复淘汰,农村留下的劳力的生产效率和收入才会越来越高,农村的人均收入才能向城市的人均收入靠齐。这不但是刘易斯的预言,也为欧美和东亚的例子所证实。但中国土改的例子恰恰证明,在经历了最激进的以消灭地主和富农为目标,土地分配最为平均主义的地方,不但农业没有现代化,而且城乡收入差居高不下,离开城乡一体化的理想目标仍十分遥远。这种对比是发人深省的。其实,在刚过去的40年中,中国遇到了百年未遇的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良机。但是由于土地所有权问题无法解决,城市中的户籍制度依然存在,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的错序反而更为固定化了,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会必然地滞后。
重审毛泽东土地改革的国际研讨会在纽约举行两天后便顺利结束了。但无论是与会的学者,还是参与讨论的观众,都大有言犹未尽之感。然而,无论对“新中国”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建设的推动,还是对当代中国社会要拒绝毛泽东遗产的警告,这个研讨会都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为了更全面地反映近十年以来对中共土地改革和它的第一波政治运动研究的新成果,本论文集还收录了一些会议外的海内外学者的论文。编者希望:通过这本百万字的论著,读者不仅可以看到被中共当政者长期掩盖了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运动的真相,更可以看到史学家们不懈地探索历史真相、努力健全民族记忆的良知和坚韧。在这一意义上,本书绝不是这一探索的“结论”,而是它的新开始。
2019年9月于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校园
注释:
[1] 黄黎:〈新中国土改是“历史错误”吗?〉,北京:《社会科学报》,2016年1月19日。
[2] 见本书所收的〈由和平走向暴力的广东土改〉一文。
[3] 宋永毅主编:《中国五十年代初中期政治运动数据库》,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出版,2014年第一版。
[4] 〈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规定的修正草案的通知〉(1964年9月18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国研究中心出版,2014年第三版。
[5] 同上。
[6] “土改情结”这一提法,见颜智华〈中共土改情结与中共建国后四川涪陵地区的政治运动〉一文。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zh-tw/baitai/20190427/1119842.html
[7] https://baike.baidu.com/item/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3_2
[8] 见本书所收的〈中共土改时期革命运动法制模式的形成及其历史影响〉。
[9] 宋永毅编:《文革大屠杀》,香港开放出版社,2002年,第16页。
[10] 谭合成:《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省道县大屠杀纪实》,香港天行健出版社,2010年。第517-522页。
[11] 熊景明、宋永毅、余国良主编:《中外学者谈文革》,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8年。
[12] 同注9,第31、34,116页。
[13] 如高王凌的〈土改的极端化〉一文指出:“土改过程中约有300至500万人丧生,他们大多数是中小规模的地主,大多数是被活活打死的”。再如土改研究学者、《乡村社会的毁灭》一书的作者谢幼田也认为,“杀人数目至少是五百余万人。”纽约:明镜出版社,2010年,第268页。
[14] 冯建辉:〈党对地主富农及其子女政策的变迁〉,《炎黄春秋》,2000年12期。
[15] 〈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载《人民日报》1966年8月29日。
[16] 见本书所收的〈江津县减租退押运动研究〉一文。
[17] 毛泽东:〈团结起来,划清敌我界限〉(1952年8月4日),载《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67页。
[18] 〈请看红卫兵的辉煌战果和巨大功绩〉(1966年10月3日),载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国研究中心出版,2014年第三版。
[19] 同注7。
[20] 罗平汉:《农村人民公社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0-31页。
[21]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卷)》,(广州:南方出版社,1999年),第37-8页。
[22] 1962年7月10日中共信阳地委〈关于路宪文在“信阳事件”中所犯罪恶的处分决定(草稿)〉,见余习广《信阳事件责任人认罪书集》未刊稿,余习广提供。
[23]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0年6月28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五十年代初中期政治运动数据库》。
[24]杰克·贝尔登着,邱应觉等译:《中国震撼世界》,北京出版社,1980年,第614页。
[25] 马若孟着,史建云译:《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民发展1890-1949)》,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页。
[26] 廖鲁言:〈三年来土地改革运动的伟大胜利〉(1952年9月26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农村经济体制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414页。
[27] 见本书所收的〈土地改革对农村生产力和农村社会生活的损害和影响〉一文。
[28] 〈土改未结合生产形成严重丢荒现象芦荻乡领导已作检讨〉,《新黔日报》(1951年9月9日),载贵州省档案馆编:《黔地新生:解放初期贵州土地改革档案文献选编》,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50-152页。
[29]〈莒南上半年生产工作总结〉,临沂市档案馆馆藏档案:2-1-32。此处转引自王友明着:《革命与乡村:解放区土地改革研究,1941-1948,以山东莒南县为个案》,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73页。
[30] 转引自王友明着:《革命与乡村:解放区土地改革研究,1941-1948,以山东莒南县为个案》,第172页。
[31] 见本书所收的〈耕者无田与耕者有田:中国与台湾土地改革之比较〉一文。
[32] 见本书所收的〈是土地改革?还是通往国家农奴制之途?—有关北韩和北越土改的思考〉一文。
[33] 见本书所收的〈土改的前奏曲:中共建政时期征粮问题再探讨〉一文。
[34] 见本书所收的〈征粮、“春荒”与减租退租:对土地改革的再认识〉一文。
[35] 见本书所收的秦晖〈暴力搞土改是逼农民纳“投名状”〉一文。
[36] 高王凌:〈土地改革:“改天换地”的社会变动〉,载《土地制度研究》(第一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
[37] 见本书所收的谭松的〈土改运动中的杀人和酷刑特性〉一文。
[38] 见本书所收的吴国光的〈以暴力型塑政治:中共为什么要在土改中实行暴力?〉一文。
[39] 见本书所收的〈社会互动与暴力土改:以山西省平州县为例〉一文。
[40] 杨奎松:〈新中国镇反运动始末(上)〉,载安徽省政协文史委员会:《江淮文史》2011年第1期第6-24页
[41] 见本书所收的〈从土地革命到土地改革到土地财政〉一文。
[42] 见本书所收的〈耕者无田与耕者有田:中国与台湾土地改革之比较〉一文
[43] 文贯中:《吾民无土》,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年。
——转自《纵览中国》(2019-09-22)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70期,2019年9月13日—2019年9月29日
凌沧洲:揭开沉埋70年的血腥劫掠真相一一读宋永毅主编《重审毛泽东的土地改革》有感
70年前,一场腥风血雨的浩劫降临神州大地,无数国国人的尊严、自由、生命、人权被踩踏,土地的权属被贡上了公产主义革命的祭坛,仿佛玛雅人和阿兹特克人需要部落活人的心脏祭奠太阳神,鲜血涂满金字塔一样,古老的东方神州,伴随着地缘政治的公产主义铁血征服,暴力集团、犬儒阶层与愚民群氓合力打造的一次次政治运动,不仅让暴力集团自我造神的人造红太阳晒得神州赤地千里,而且在一场场杀戮狂欢和集体逼迫清洗中,布局了绵延70余年的公产主义黄金时代的谎言与神话,让血污、游魂与真相永远沉埋在深深的地底。
近日,由加州州立大学教授宋永毅主编的《重审毛泽东的土地改革:中共建政初期的政治运动70周年历史回顾》出版。仿佛对70年的历史中沉埋地底的血污与尸骨,进行了一次深度挖掘和科学 “考古”。70年后,在网络戏称“厉害国”进行造神新长征的时代,在“宽衣帝”指示“两个三十年都不能否定”的时代,宋永毅的声音很具穿透力:“重新研究和否定毛澤東的土地改革運動,還有什麽特別的歷史和現實意義?答案是非常肯定的。這不僅因爲70年來中共官方製造了種種關於他們的土改的「偉大成就」的政治神話,導致毛澤東土地改革的血腥真相至今還沒有被全部揭露;還因爲70年前的土地改革的後果正阻滯著中國大陸現代化的健康進程;更因爲而當今的中共領導人千方百計地想讓整個民族遺忘歷史的教訓,以便他們可以順順當當地沿著這條獨裁和極權的道路走下去。”(上册P12.)
土改时代的先知:旷野的呼喊
要对70多年前的政治运动和社会变革进行文化与科学意义上的“考古”,就必须先对“考古遗址”挖掘出的历史材料、“血污与骸骨”进行科学意义上的鉴定与探索,要定义和质疑诸如 “是什么、为什么、怎么了、人物与剧情、时间与地点、规模与手段、工具与细节、后果与效应”等问题。
关于“土改”是什么的问题,书中专家与学者都有迥异于中共编织70年的神话的判断。宋永毅认为,土地改革有“三个特徵和要素:1. 階級劃分的運動理論基礎;2. 法外殺人的群衆暴力形式;3. 劫掠私產的國家財政機制。”(上册P12.) 学者程映虹在书中横向比较了北韩与北越的土改,认为公产国家的所谓土改,本质上是一种“国家农奴制”。他写道,“得到土地,失去了自由,下一步就是沦为国家农奴。”(上册P42.)书中的大部分学者都有这一共识:土改只不过是中共控制国国人民和国国财富的手段之一。
1949年,在神州晦暗如铁、山河陆沉的血腥岁月里,无数知识精英要么趋附,要么屈膝,有一人秉承古仁人志士风范,“虽万千人吾往矣”, 先是向毛泽东上书,请毛泽东“立即下令停止分地”(下册 P85.),此人最后被迫出走流亡。1951年他在香港出版《论公产党的土地改革》和《我认识了公产党》。他孤独而警醒的声音,70年后读之,仿佛能感受到华夏民族在沉沦炼狱前有人在旷野中的呼喊,如同耶利米时代堕落衰败的以色列民族即将沦亡于异族前遭到先知耶利米的泣血哀求与怒斥警告。此人就是国国的农业专家董时进。董时进的文字,使我们得以一窥那个时代先知的洞察力和预言能力:“ ‘中共的意向是人人不许有土地。’ ‘公产党的真正目的,并非是要耕者有其田。这不过是他们一时应用的一种策略,是在革命过渡时期用来拉拢一部分的贫农和流氓地痞的手段。他们的真实意图是要将一切土地社会化,这即是收归国有。将来一切人都不准拥有土地,一切土地都归公产党的政府,使那个政府变成独占全国土地的大地主。’……‘公产党的土地改革,实际上就是假改革之名行抢劫之实。’ ” (丁凯文《董时进 VS 毛泽东》,收入《重审毛泽东的土地改革》下册P84)。对于中共颁布的《土地改革法》,董时进先生是这样评论的:“这《土地改革法》最重要的一条即是第二条,‘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有了这一条,抢劫就合法化了。这个‘法’的产生没有经过民主合法的手续。现代国家的通例,凡是立法必须经过人民自己或其代表的承认,然而这个《土地改革法》仅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少数几个人便将人民大家的土地财产,不问罪名,不加审判,一起没收了。假使这也可以算是‘法’,那末,一群强盗,向人民大众宣布,他们的财产都要一齐交给强盗,也应该算是‘法’了。”(同上)。
土改这场浩荡的暴力抢劫运动,虽然没有像蒙元满清征服与立国之初,搞出无数屠城的剧目,也未必如秦国虎狼之师击败六国,坑杀降卒,伏尸百万,流血漂杵,但却也是赤祸绵延,杀人盈野。宋永毅指出:“如果我們把土改作爲毛澤東時代第一個政治運動,把文革作爲毛的最後一場政治戰役,它們的共同點即是對某一社會階層的大規模屠殺。不幸的是,這一社會階層就是中共土地改革運動的主要打擊對象——地主富農及其子女。 文化大革命中有過三次震驚全國的對土改對象的大屠殺事件,其方式都是土改「法外殺人」的運動形式的延續和翻版……1967年底到1968年下半年的廣西大屠殺。据機密文件透露,至少8.9-14萬人遇難,而其中土改對象、四類分子及其子女占了56%左右。如果我們進行一下更深入的調查和比較 ,還不難發現,上述三次文革中的大屠殺都不過是建國初期土地改革運動的延續和發展。例如,道縣和廣西發出殺人指令的「貧下中農最高法院」其實不過是土改時期「人民法庭」的某種翻版。而施害者所採用的對受害者們先開「殺人現場會」鬥爭、再宣判,後用「刀殺」、「沉水」、「棍棒打死」、「活埋」 、「火燒」等方法處死,完全是土改虐殺地主的全套流程。至於那些野蠻的私刑,也和土改中法外殺人的暴力一脈相承。值得注意的還有:劊子手在殺戮受害者的事前事後,還常常公開引用他們集體無意識裡深深積澱的「土改經驗」。例如,加害之前,兇手們常常先追逼受害者的「浮財」——有的甚至是第一次土改時埋藏的「光洋」。並欺騙他們:這是「土改政策」,交出你的錢來,便可以買下你的命。而在殺光了受害者全家以後,兇手們一定不會忘了土改的傳統——瓜分掉受害者的全部財物——包括受害者的家庭裡的青年女性。如果說有什麼不同之處,那就是暴徒們再也無法從受害者那裡分得土地。”(上册P15-P16.)
宋永毅根据中共的官方材料,统计出:“自土地改革以來的24年裏,中國的地主階級共有1808.3萬人死亡。他們或是在土改後的各種政治運動中被迫害致死,或是在貧病交迫的政治歧視中漠然逝世。作爲一個有兩千多萬人之衆的中國富裕農民的「階級」,被中共從肉體上殘忍地消滅了。”(上册P18.)
仅仅土改的几年时间的暴力死亡人数,应该远超历代征服屠城的人数;如果把暴力土改、大饥荒、反右、文化大革命以及六四屠杀等受难的人数累积相加,则是古今哪个暴力王朝和政权都望尘莫及的。
杀戮狂欢:神州处处是刑场
今天当我们追溯1950年代时,绝对想象不出那个时代由毛氏“总导演兼总策划”、亿万国国人出演龙套、配角、道具、炮灰的暴力大片是如何血腥、荒诞、残忍、不伦与野蛮。清代著名诗人徐述夔曾写下:“江北早已无净土,乾坤何处可为家?” 我觉得套用于1950年代的国国,也无比贴切。不仅是“神州何处可为家”,而且是“神州处处是刑场”。
学者谭松在《土改运动中的杀人和酷刑特性》说,“中共土改运动中的大屠杀,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就是把杀人现场布置得轰轰烈烈,热闹非凡。首先广泛动员,尽可能四面八方的人都前来观看……其次是组织文娱活动,如打腰鼓、扭秧歌、演唱……还有就是组织啦啦队,像观看体育比赛一样,把杀人现场搞得热火朝天。”(下册P224.)
谭松叙述目击者讲的故事:“1952年的3月2号,秀山枪毙了一个名叫杨卓之的名人。我亲自到现场观看。杨卓之跪在地上,一枪打了。打了之后,我看到杨卓之的脚还在一抽一抽的。这时上去了三个人。一个手提一把菜刀,另一个拿了一个小锅和一个菜板…….”(下册P242-243.) 简言之,就是在刑场十多米处,烧起火架起锅子,爆炒杨卓之的心脏。
至于暴力土改的残暴下流,对妇女儿童的摧残,那就更不在话下。谭松列出了当时一些对妇女的酷刑,可堪与与唐代酷吏来俊臣的《罗致经》中的十大酷刑一拼,都可以载入史册。其酷刑手段有:“钓美人鱼”,“吊秤砣”,“吊乳头”,“猪鬃毛戳乳头”,“烧飞机洞”,“包谷球球”,“裤裆里放动物”,“用铁条(或竹条、木棍)插入阴道, “看风景”,“摸洋钱”,“火牛草磨或塞入下身”。(下册P250-254.)这些酷刑,我不必复述,仅从名称,就可窥见端倪。
南方的土改既残暴下流如斯,北方就更加没有净土。学者智效民的《晋绥边区暴力土改的背景与真相》不仅记录里“各种酷刑触目惊心”和“分房分地分老婆”(上册P255-259.),而且更记录里土改对国国传统人伦的毁灭性示范作用。在蔡家崖“斗牛大会”上,公产党的干部牛荫冠目击他的地主乡绅父亲牛友兰遭遇人生滑铁卢。“61岁的牛友兰被反绑双手,与很多地主富农跪在主席台上。斗争进入高潮后,有两个人按住他的头,将一根铁丝穿进他的鼻孔,并强迫坐在主席台上的牛荫冠下来牵上‘老牛’游街示众。牛荫冠下来后,据说牛友兰不堪这种伤天害理的污辱,用力把头一甩,鼻翼下面的脆骨被拉断,顿时血流满面……没过几天,牛友兰便惨死在关押他的窑洞里面。”(智效民,下册P251-252.)
另一个灭绝人伦的故事是这样的:“刘象坤被打死后,正好他的儿子刘武雄因为被开除公职从蔡家崖回来。刘武雄回来后就碰上批斗大会,就直奔会场,上台讲了一番话,‘大意是他受他恶霸老子的连累,现在决心要和刘象坤划清界限。’随后,他‘跳下台来,从民兵手里接过一把刺刀,冲他老子尸体胸口上捅了两刀。’ ”(智效民,下册P254.)
这些故事现在大多沉埋在地底,不会在国国主流媒体与出版物上出现。骸骨深埋地底,鲜血浇肥沃土,记忆遗忘风尘,洗脑常洗常新,这种普大喜奔的局面,最有利于谋杀者、劫掠者以及他们的继承者与后裔。因为他们屁股底下的赃物已经洗白并且合法化。集体谋杀与集体劫掠的主嫌,现在肉身已经刷金镀彩,被无数群氓愚民吹吹打打供奉进灵堂和庙宇。他们的血缘孙子们和精神孙子们在梦里都为他们的暴富和崛起笑开了花。
反观1950年代左右的国国农民,则是另一幅卑微凄凉的剧目,可怜可叹可憎的剧目。国国农民在土地--这一散发着魔力的“魔戒”前面,无法抵抗它的试探和引诱,一个个沦为谋杀犯和抢劫犯的帮凶,如同被裹挟的半兽人、强兽人的部队。几年之后,集体谋杀与抢劫得来的土地,再被暴力集团以堂皇的借口掠夺走。国国农民全体沦为农奴,继而在大饥荒年代成批饿死,这是对他们的手上也沾着受害者的血的天谴与报应。这一宏大的暴力抢劫史诗的主谋者、执行者、参与者、胁从者、旁观者、沉默者,绝大多数都得到了他们该得到的报应。权力绞肉机使今日的谋杀者、施害者很快在明日变为被谋杀者与受害者,底层群氓如是,顶层如刘少奇、林彪者也最终被权力绞肉机绞碎。即使“总导演、总策划”毛泽东氏,也难免被浸泡福尔牛林溶液中,陈尸“腊肉堂”,其尸骨未寒之际,遗孀江青即被捕,终至悬梁。
但那些在土改暴力年代断命亡身的妇孺,她们又招惹了何人?若非这个民族的愚昧、原罪与癫狂,她们何至于遭受如此血腥与恐怖报应?如果有地狱,有阴间,她们的游魂在鬼门关、奈何桥等地点与毛刘林周朱等人相遇,是不是也像话本小说中被谋杀的人物,在黑暗中厉声高叫:“还我命来!还我父兄的头颅与土地来!”
“暴力必以谎言为继”,谎言必为暴力先导
俄国文豪、诺奖得主索忍尼辛曾有名言说:“暴力必以谎言为继”, 在我看来,谎言也必为暴力先导。因而,研究土改暴力前后的谎言,也应该是真正的历史学家们不应忽略的功课。
暴力土改既是新政权杀人立威的手段,也是劫掠民财的手段,通过腥风血雨式的清洗,完成通向极权国家之路。我们只要看看这场土改30年的结局,中共在其82“宪法”中,明确地写进 “全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城市土地国有”的词句,虽然国国农民早在50年代合作化运动中已经丧失了土地,但这时腆颜将劫掠结局写进其“宪法”中依然颇具喜剧效果,因为把这一条与50年代中共在《土地改革法》中白纸黑字写下的“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对照看,就知道他们给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完美土地骗局与劫掠以“宪法”的形式背书,如同给一具具躺着这些愚昧无知、凄然无力的农奴们的早已冰凉和发臭的尸体的棺材钉下了最后一根断魂钉。本书所收裴毅然《苏区‘土地革命’实况实质》和谭松《从土地革命到土地改革到土地财政》等论文,基本梳理出了暴力集团百年来不变的土地劫掠史纲,为后来的研究者铺设了路基。
然而对于50年代的完美土地骗局,宋永毅在批陈史料之后,揭示了骗局制作者们早已经机谋秘设、等愚民上钩的真相。宋永毅写道:“但‘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革命神话,已经被史实证明是历史笑柄了。因为在全国土改还如火如荼地进行中的1952年, 毛泽东就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了《中共中央转发东北局关于推行农业合作化的决议(草案)》(1952年5月10日)。文中明确指出:“中央同意东北局关于推行农业合作化的决议草案。并将此决议草案发给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参考仿行。”换句话说,在地主们的土地刚刚开始分配、即“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还没有被消灭之际,中共已经在策划把要取代它的“农民土地所有制”也一并消灭,而以国家的集体化来没收所有农民的土地来。因而,有关“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承诺,完全是中共和毛泽东对国国农民的一场言不由衷的欺骗。”(上册 P376-377.)
迷醉外来牛列邪教乃至走火入魔的毛氏及其同谋们当然不会承认这是史上一场最成功的完美骗局与劫掠。早在国共内战快到尾声、百万生灵已经涂炭、共军挥师渡过长江之际,毛氏就如同丛林部族的酋长,拿着死人的头骨在火堆边庆祝胜利、唱歌跳土风舞一般,附庸风雅地赋诗:“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蟠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即使在饿殍遍地、农奴们面有菜色、人相食的岁月,毛氏的土风民谣依然靠着权力的力量播弄被其征服的全境:“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学者高王凌称:“国国的土地改革不仅是‘改朝换代’,而且是‘改天换地’,因此不可避免地要走上‘斗争土改’的道路。”(上册P29)我以为,是否可以更进一步地判断说,岂止是改天换地,简直就是偷天盗地,甚至是毁天灭地。当文明沦陷,野蛮癫狂,最后沦落到雾霾漫天,污染遍地的时候,这种毁天灭地的神功也是天下独步,连他们的祖师爷牛恩列斯,在坟墓里复起,也得惊诧他们的徒孙、国国红朝的毛太祖果然手段了得。奇幻文学大师托尔金《魔戒》三部曲中的黑暗魔君索伦以及白袍巫师萨鲁曼,挟戒灵、恶龙、兽人大军,都无法撼动中土,征服洛瀚国和刚多国。他们若见到毛太祖轻轻挥舞公产主义的魔棒,驱动亿万国国人癫狂奔命,千千万国国知识分子随歌匍匐起舞,万万千国国农民欣然奔赴土改的悬崖扑通扑通跳下的热烈场面,一定会将毛氏惊为魔界中古往今来第一人,拜倒在万里尘埃之中,将凝聚了世人贪欲与恐惧的魔戒,乖乖向毛太祖奉上。
2020年1月写于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