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擁有必先懂失去怎接受——讀《Hong Kong’s New Identity Politics: Longing for the Local in the Shadow of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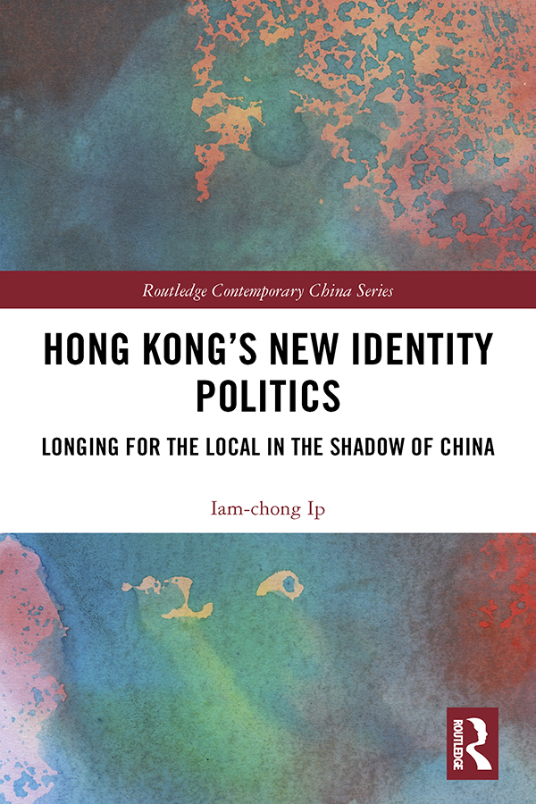
書名︰Hong Kong’s New Identity Politics: Longing for the Local in the Shadow of China
作者︰葉蔭聰 (Iam-chong Ip)
出版︰Routledge (London)
版次︰2019年12月
ISBN︰9780367814465
要一句話介紹作者,可引《明報》所述「有份創辦《獨立媒體》的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客座助理教授」,然後補多一句「被執教二十年的嶺南大學拒絕終身合約申請後終止續聘兼職教席」。計及已離任的許寶強和羅永生,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風光不再,換來是將「字意千年無改」掛在嘴邊的歷史系同儕也在法庭鸚鵡學舌講起「語境」,反正罡風覆巢,踩過界已是此城新常態。
雖然此書以英文寫成,但對於熟諳本地政治以至近年社運發展的朋友而言,書中頗有系統以逾半篇幅梳理本土派(右翼本土主義)乘勢而起的社會脈絡。儘管劉兆佳那套老掉牙的「功利家庭主義」(Utilitarianistic familism)和「低度整合社會政治體系」(Minimally-integrated social-political system)上世紀說辭至今在香港已經無人問津,不過著重個人名成利就、目標為本效益至上、蔑視公共資源和社會福利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依然是比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更優先的指導思想。從港英政府到特區政府,官方論述也一直深諳此道,與其誇誇其談甚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倒不如說大國崛起經濟騰飛,呼籲大家抓緊機遇,年輕人北上創業,老年人亦可到大灣區養老,哪怕最後碰得灰頭土臉,或成現代版《楢山節考》。
那位歷史系教授沒告訴法庭的是︰太平盛世何須興風作浪,倒是民不聊生才會官迫民反。
鼓勵香港人走進內地,本來願者上釣。看似讀懂香港這本書的京官也曾經提出「井水論」,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大家港事港辦,涇渭分明互不相干。直到香港人意識到中港逐漸合流,政治參與步入樽頸,那才成為本土派思潮的濫觴。
這種意識最初是由日常生活經驗之中習得(Acquire)的,當人們發現居住的社區愈來愈多藥房和水貨客、醫院愈來愈多「雙非」孕婦、超級市場愈來愈難買到嬰幼兒用品、公眾場所愈來愈多有損市容的行為……這些體驗首先是衍生出自我保護(Self-defending)的排外心理,然後才透過某些場合以中港矛盾的方式呈現。在矛盾能被看見之時,人們的抗拒心理已經深植其中。就算政府事後推出措施回應民情不滿,卻反過來印證中港區隔的必要,人心自此更難回歸,之後再恫嚇香港會被邊緣化云云都是徒勞。
雖然書中沒有提及社會區隔(Social segmentation)的概念,但從書中指涉中港兩地在社會、文化、經濟與生活方式的差異,大抵說明本土派眼中「香港人」的構成。這種差異甚至自我定位又多數屬於否定式(Negation),就像香港眾志「自救口罩」的標示「Not made in China」一樣語焉不詳。回溯本土派初期主張,區隔和差異並不指向分離主義(Separatism)。最初光復行動的目的僅僅為了驅逐(踢走)水貨客,純粹希望在這座城市生活如昔,即使陳雲的城邦論也不否定《基本法》的憲制地位。不過當本土派批評傳統泛民尸位素餐,每年遊行集會行禮如儀時,他們大概也要承認己方也是欠缺執政意志的「忠誠反對派」——除了站在政權的對立面提出政治訴求外,其他層面的政治願景確實乏善可陳。
換句話說,香港不吃中國那一套,但究竟香港到底是哪一套,答案一直含糊曖昧,就連表達對香港的愛也只有地道字詞點綴。雖然概念愈空洞浮泛就能吸引愈多受眾,不過正因如此,在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的政治體制下,公民社會參與族群政治時缺乏整體行動綱領,兄弟爬山各自修行。眾人出於自由意志自行演繹形形式式的臨時對策,除了經常有背水一戰的悲壯感召,客觀上有時難免出現傳統政治精英眼中的脫軌失序,譬如光復行動演變成踢喼(示威者腳踢旅客行李箱),或揮動港英旗表達對香港過往繁榮景象的期許,以至魚蛋革命(2016年旺角騷亂)及立法會宣誓風波等等,都反映本土派目標方向不清晰之餘,手法亦傾向民粹或自我表現。
以上與現實政治從不兼容的模式,顯然成為了管治階層(有意或無意地)對分離主義如臨大敵的藉口,進而利用制度優勢封殺本土派,再進而瓦解傳統泛民陣營以至整個公民社會。可惜政治從來沒有如果,沒有人知道倘若本土派規行矩步是否就能安然無恙,抑或政權步步進迫僅是時間問題。所以那些以為監獄可以上網的法官始終是聰明狡黠的法律技工,何謂顛覆根本無須勞煩專家,只需證明「可以有」(Capable of)顛覆意義便行。一切還原基本步,不是看誰說甚麼話,而是看誰還敢說話。
流行歌詞沒說錯,要擁有必先懂失去怎接受。也許在香港人命途多舛之際,才能從香港失落的碎片拼貼出屬於香港人的圖像,到那時候我們便知道「香港人加油」到底為誰而喊、有誰共鳴。這可能恰恰呼應作者在書末的期盼︰啟發更多人在日常生活持之以恆地爭取我們想要和需要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