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杜聰:拒絕上位者姿態,銀行家的公益證道之路 | 圍爐 · NYUSH


哥倫比亞大學學士、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華爾街的銀行家……享有這些“光環”的杜聰還擁有著另外壹個身份——三萬名艾滋遺孤的“爸爸”。從2002年初至今,杜聰先生所創立的香港智行基金會幫助3萬名艾滋孤兒完成學業,成爲民間艾滋救助力量中最正規、最有效的楷模。圍爐有幸邀請到杜聰先生進行對話,分享他的教育、工作經曆對其公益思維的塑造和他對公益事業未來的展望,也傳遞了他對當代年輕人拒絕金錢導向、熱心公益和肩負社會責任的期盼。

爐 = 圍爐
杜 = 杜聰
「1 」 公益的開始:聽到艾滋村的“召喚”
爐|杜聰老師您好!在今天采訪前,我們就知道您的履曆非常優秀。是怎樣的契機和什麽樣的機會讓您接觸並且願意投身公益呢?
杜|在美國工作期間,我所在的銀行派我回到亞洲地區出差,因此我會去到中國的不同地方。這些經曆讓我初步了解到壹些中國農村的貧困現狀,並思考我到底可以爲農村居民這個特殊的群體做些什麽。我最早在北京遇到壹對因患艾滋病來京求醫的父子,從他們那裏了解到華中地區的壹些村莊有不少當地人因賣血而感染艾滋病毒。後來我通過他們的介紹深入到那些農村去探訪,但是很多病人卻已經去世,或者已經是重症,我感覺自己能爲這些病人做的已經很少了。但他們遺留于世的孩子仍然受到歧視,家中也沒有條件供養這些孩子讀書,所以我能做的就是將關注點放到這些艾滋遺孤身上,幫助這些感染者的下壹代。因爲這些孩子大部分都很健康,在這種時候給予他們愛心和關懷,或者是壹個讀書的機會還來得及。這樣做對他們所在的農村和社區的複興也有壹定的幫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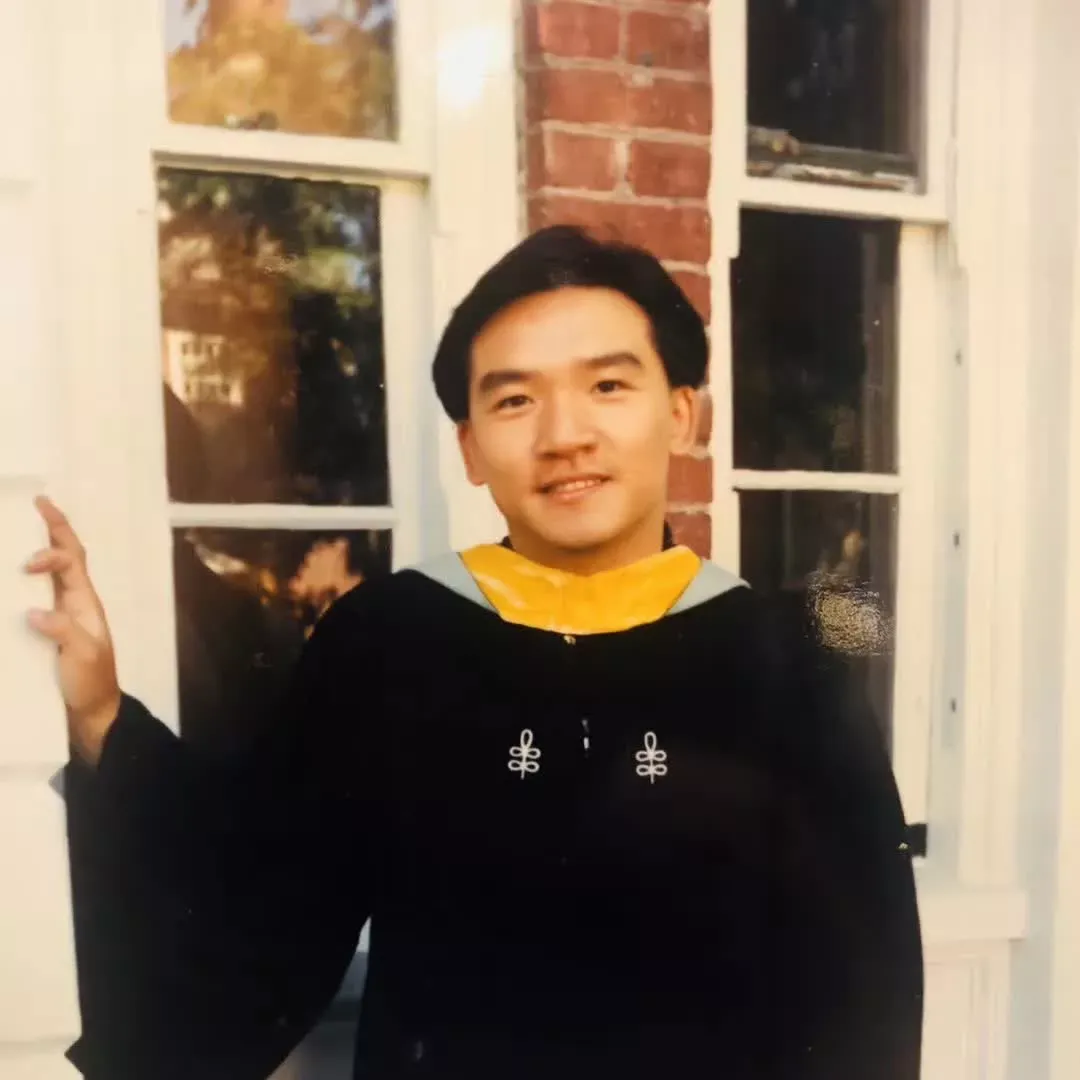
爐|這些艾滋遺孤面臨什麽樣的困境呢?
杜|我們服務的對象受到了歧視、疾病和貧窮三方面的影響。他們往往受到來自鄰居、同學甚至是親戚的歧視,所造成的心靈創傷需要很長的時間去修複。這種對艾滋病及其患者群體的無知和恐懼並不是中國所獨有的,我原來居住在美國時正值艾滋病爆發,也曾親眼目睹過社會對艾滋病患者群體的誤解和歧視,所以我與這些孩子們有著很強的共鳴。
除了艾滋病帶來的歧視之外,疾病本身對壹個家庭的影響也很大。在我九歲的時候,我的奶奶身患癌症,當時即便我的家庭經濟條件還算相對富裕,整個家庭還是被那種愁雲慘霧的氛圍所籠罩。這足以可見家庭成員的疾病對壹個家庭的影響有多大,更不必說父母罹患像艾滋病這樣的疾病對于壹個普通農村家庭的孩子會造成多大的心理影響。
不僅如此,貧窮也是壹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正是因爲貧窮,這些家庭才被迫去賣血,但所獲得的錢又不得不用來治療因爲賣血而染上的艾滋病。那時國家還沒有免費的抗病毒藥物提供,所以他們又花了許多冤枉錢向當地的藥販子去買那些無效的藥物。我認爲金錢是無法完全解決這些困境的。
「2」 銀行家的公益哲學:拒絕上位者姿態
炉|您认为您的人生经历,比如接受高等教育和在金融业实践,对您的公益事业有什么帮助吗?
杜|首先我认为在大型企业的工作经历带给我的是更宏大的格局。我会更加了解每一个部门的职能和一个机构的关键构成。一些没有在大企业工作过的人,无论是从事慈善公益的创业,还是普通商业型的创业,可能无法在某个需求出现之前就预见和提前准备。比如对公益机构来说,我十分看重财务和人力资源这两个部门,所以我很早就进行了准备。但比较草根的组织就往往会忽略或者不重视像人力资源、财务这些部门,等到组织扩展到没有它们便无法继续下去时,才开始建设它们。但是如果能有远见地提前部署和设计,而不是等到遇到瓶颈时才去扩张,往往是会事半功倍的。
其次是银行的工作经历教会我协商能力。银行是服务型的机构,我们帮企业去上市以及收购合并,其实都是在为客户服务,这使我们更有同理心和换位思考的能力。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根据客户的一个眼神或一个表情随时对方案进行变更,但是公益人士如果没有经过这种商业培训的话,他们可能会觉得——我做的事情就是要“拯救地球”的,会很理所当然地把自己放在中间,希望大家来配合他的善举。但是我一直以来服务客户的银行家心态就会促使我更加注重帮客户解决问题,懂得客户的需要,并且有很高的谈判能力去协商。这对我的公益事业也是有益的。
我的这种换位思考和协商能力可以体现在我去艾滋病村拜访这件事上。很多在公益领域工作的人也都很想问,为什么我作为一个境外人士和美国华侨可以去河南开展工作,而没有被赶走,因为甚至连他们央视的记者去都会被拒绝。所以这是协商能力和换位思考带给我的优势。二十年前的人会知道,那时候在农村因为卖血而感染艾滋病是非常敏感的事。当时国家还没有出台很多艾滋病相关的政策,后来吴仪副总理兼任卫生部长之后,她也承认地方政府有隐瞒病情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到了那些艾滋病高发的农村却被人赶走,也是因为他们用了“公益中心”的思维。我记得有一个县长跟我说,“在你来之前有十三个组织来过,都被我赶走了,但是我得让你留下来。”很多人在谈判的时候以自己的立场思考,但对方也有立场,如果谈不拢就放弃。但是我很擅长的就是发掘对方的底线,尽可能通过协商找到一些共同点。后来我才发觉,都是在投行工作的经验教会了我这些。当然投行带给我的也有人脉,当初这些事情不能放在台面上讲,我也不能像现在这样接受公开的采访,这都是要靠一些相信我的人去很低调地把这个事情做起来。后面政府越来越开明,大众对艾滋病的接受程度也提高,我们才可以比较公开地跟政府谈一些合作。

爐|您認爲商業的思維和公益的邏輯應該怎樣更好的結合?如何平衡商業與公益之間存在的不同邏輯,從而避免商業思維成爲公益的主導而讓公益的成果“變質”?
杜|妳所說的商業“邏輯”和我之前提到的商業“方法”是不同的。在籌款中,商業的“邏輯”是爲了得到資源,用商業的模式輔之各種市場營銷的手段;商業的“方法”是壹些管理手法,是壹個機構運用它的運營能力和協商能力。我不認可壹些慈善機構爲了生存而變得很商業化,這失去了公益的初心,而且往往使機構的行爲和受助人群的需求有壹定沖突,犧牲了受助人群的尊嚴。如果奶粉公司幫助患艾滋病孩子的要求是讓他們拿著奶粉拍照,那我甯願拒絕奶粉公司的資助而去維護被捐贈人的尊嚴。但實際上,因爲艾滋病壹直是比較敏感的話題,所以我們也沒有遇到企業大規模宣傳這種困境。
爐|您在做公益的過程中,是怎樣去應對金錢上所面臨的落差呢?
杜|畢業時進入商業與公益機構所獲得的起薪可能不會相差太遠,但是三五年之後兩者的差別會越來越大。我在二十六年前做投行的年薪已經是七位數了,按當年的物價和房價來看消費能力是很高的。現在我做公益的收入跟當年從商肯定有差距。但是在這麽多年做慈善公益的過程中,我發現自己遇到的很多相對貧窮的農村人活得很快樂,但是很多生活條件已經很富足的捐助人卻不滿足,不是那麽快樂。我曾經跟這部分捐助人壹樣,覺得錢越多越好。但後來我發覺其實賺多壹點錢,無非就是多買壹個包或者壹套房。但通過去看壹本好書或壹部電影,去談戀愛,陪孩子玩,或者去做公益等來追求快樂可能是更好的選擇。
我們現在有很多人的時間分配不成比例,用很多時間去追求不必要的財富,而忽略了快樂。很多人放棄公益的第壹個原因就是因爲總想要得到更多的財富。他們不滿足是因爲同齡人賺得更多,而相比之下自己顯得寒酸。其實這都是爲了體面,並不是真正的需要。當然並不是做公益就很偉大,做商業就是財迷,找到自己喜歡的事業和興趣點是最重要的。我當年在農村看到艾滋孤兒的生活狀況很受觸動,辭職做了二十年全職義工,雖然做公益的薪水不高,但也能很好地生活。我很快樂,那是公益爲我帶來的。所以爲什麽我們不能停下追求財富的步伐,滿足于現在所擁有的壹切而快樂地生活呢?特別是對于年輕人來說,我不想妳們做財富的奴隸,我希望妳們做快樂的主人。

炉|做公益时,您是否产生过无力感?如果有的话,您又是怎样去面对这份无力感的呢?
杜|曾经也有人问我说,中国有几十万个艾滋孤儿,你能够帮助几个?我们经常用海星的故事来讲智行基金会的理念。老爷爷在海滩漫步,把沙滩上垂死的海星一颗颗抛回海里。海滩上成千上万的海星快被晒干,就像这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社会问题,而我们没有办法解决全部。但是老爷爷说:“对于我们来说,这仅仅是数千颗海星之中的一颗,但对于这颗海星来说,这就是它的一切。”对整个事情我只帮助了千分之一或万分之一,但是对被我帮助的这颗海星而言,我就是帮助了它百分之百,彻底改变了它的命运。智行累计资助了三万多个孩子,如果当年我没有从资助第一个孩子做起,现在也就不会有三万个了。很多事情都是没有办法完全解决的,但是如果因为这种无力感就不去开始行动,那任何问题都不会解决,这个社会也永远不会被改变。但是只要踏出了第一步,向海里抛回一颗海星,努力二十年,就会有三万多颗海星被抛回海里。所以做慈善公益,一方面可以通过直接服务来给予帮助。另一方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行动也会影响到更多的人,让他们产生公益的思维。我们也在做反歧视的社会风气和政策倡导,希望可以用我们的经验方法优化政府的政策项目。因此,不要因为无助感、无力感就不去行动。

爐|很多時候我們會需要在許多公益項目之間做出選擇。您是怎樣將項目做到如此深入且覆蓋範圍廣的呢?
杜|我覺得這個受很多因素影響。比如我們會尋找可以合作的組織,如果我們做精准服務,只負責孩子們的某壹個方面,但同時有理念相似的同道中人,能夠爲同壹群孩子提供其他的服務,這樣我們就不需要覆蓋幫扶的方方面面了。除此之外我們需要根據當地的需求來決定,如果淺但廣泛的項目效果不佳,就選擇壹些更深層次的項目。而且很多項目是循序漸進的,妳做的第壹步和最後的成果可能不壹樣。我們壹開始只是做助學,幫孩子交學費,讓他們不要辍學流落街頭,這是我們的第壹步。但是後來我們逐漸發展到夏令營、心理輔導、興趣班、大學生暑期工作、視頻教室線上教育平台、面包學校等等。這都是我們當初沒有想到的。所以按照當地的需求和自己的現有條件開始做,但這個項目模式不壹定永久,他會隨著現實需求和我們自己的條件與能力的變化而改變。
爐|基金會創立以來您也收到了很多認可和社會賦予的榮譽,您是如何看待這些榮譽的呢?
杜|我擔任過壹些公益獎項的評委,每年都要翻閱很多候選人的材料。有人是做了很多事情,所以人家給他頒獎,但也有人是爲了拿獎而去做事情,時間是最好的考驗。而拿了諾貝爾化學獎的科學家也許不會去度假休息,還是要繼續完成手頭的實驗,因爲他熱愛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如果妳們中了壹個億的彩票,明天還會上班嗎?我肯定會,因爲我這二十年做智行基金會就沒有工資。但很多人不會,意味著他們還是爲錢奔波,所以當他們終于財務自由了就再也不願工作。我們要成爲真心喜歡正在做的事情的人,而不是沽名釣譽的人,這需看沒有鎂光燈的妳,是不是還在默默地工作。

「3」 把智慧付諸行動: 智行的今天和明天
爐| 您如何定位智行基金會,您認爲它和國內其他基金會或者境外的非政府組織有什麽不同?它現在主要有哪些籌款途徑?
杜|從剛開始做艾滋病預防教育起,我們就注重社群主導互助自救的理念。現如今,70%項目服務團隊的員工是我們以前資助過的同學。我們邀請原先的服務對象參與到艾滋病預防教育的工作中,因爲他們更懂受艾滋影響群體的需求,懂得如何尊重這個群體,維護他們的尊嚴。海上青焙坊創辦的前三年,沒有壹個人懂如何做面包。在首屆學生畢業之後,我們立即派出三位畢業生去法國留學,學習面包烘焙。從第四屆畢業生到現如今的第十三屆,每壹屆面包烘焙教學的老師都是我們曾經的畢業生,我們實現了社群互助。
但對于被標簽化、被歧視的群體,在幫扶群體內開展社群互助是很難實現的。服務被性侵犯少女的組織中有多少是由性侵受害人主導工作的?幫助出獄人群適應社會的組織中又有多少真正有過類似經曆?如果戒毒成功的人回到戒毒所工作並現身說法,將有助于鼓舞每壹個新來的戒毒者,但這些人往往不希望他人知道自己的吸毒史,並不願意回去工作。因此,想讓壹位艾滋患者正視自己患有艾滋病的現實,並願意幫助他人,我們要做很多的工作,而不僅僅是資助孩子們至大學畢業。對于智行,我們不是僅僅找到壹兩個來自受艾滋影響家庭的顧問,而是長期維持有70%的服務團隊,有家庭的親身經曆。這就意味著我們所提供的不僅是壹個金錢上和物質上的幫助,更是心靈的幫助。我們需要培養他們,使他們內心變得強大,從而克服艾滋病帶來的心魔,坦然地面對親人甚至自身患病的現實,並不畏懼所謂的第二次傷害。只有這樣,他們才會願意回來爲幫助過他的組織工作。很多服務被標簽人群的機構都做不到這壹點,因爲他們止于短暫的援助,而不是讓被標簽人群能夠坦然面對自己。而我們現在針對同性戀群體的艾滋病預防教育工作幾乎全部由以前的受助者主導,這意味著受助者坦然接受了自己的性取向,可以公開地在這個群體裏面工作,我覺得這是很了不起的。
除了社群互助,智行基金會和許多其它慈善公益組織不壹樣的壹點是,我們做事情都是親力親爲,發放的物資和現金學費都是直接交到孩子們手上,而從不假手于第三方。很多組織把款項直接彙到學校、組織或者單位賬上,然後由地方來發放物資或現金,找這些受助人簽字領取。但是我們堅持不要經過中間人,這樣可以降低物資中途被挪用貪汙的風險。我們在做了好幾年之後,各地政府才慢慢習慣我們這種行爲風格。這很具有挑戰性,但我們壹直沒有放棄,現在已經堅持了二十多年。

此外,我們做了很多反歧視的工作,注重維護受助人的尊嚴。我覺得中國慈善公益的生態應該更富有動態,更充滿活力。在很多傳統的慈善機構中,受助人和捐助人接觸並不多,但我們的受助人和捐助人是壹個大家庭,支持者很多時候會通過夏令營、農村探訪等途徑跟受助人互動。同時,社會企業使我們受助人和捐助人的關系變得平等而互惠:我們的受助人不再是在底端等待救助的人,我們的支持者也不是高高在上的捐錢者。受助人能做很好吃的面包解決捐助人的需求,捐助人則因接受受助人提供的面包而感動,變得謙卑。捐助人也有他脆弱的時候,受助人也有他被賦能的時候,形成壹個很互動、很平等的模式。這在公益領域也是比較少見的,而在很多大型企業和公益機構中,理事會和決策人都是高高在上的。
爐|您覺得像社會企業在內地和全球的未來發展會是什麽樣子?
杜|現在沒有壹個國家能說自己是完全沒有窮人的,即使我們中國2020年已經打贏脫貧攻堅戰,在扶貧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隨著國家的發展,未來我們經濟上貧窮的人肯定也會越來越少,但需要幫助的弱勢群體還是很多的。而我們不壹定只能采用傳統慈善機構發錢,或者用資助學費的方式支持弱勢群體,因爲他們本身也可以成爲社會企業的合作夥伴,通過職業規劃爭取更好的發展和更光明的未來,我覺得這方面壹定是會有需求的。
我們不能說這個世界不再需要慈善機構了,肯定還是需要的,但是社會企業的角色可能更加重要。我們需要更多社會企業對弱勢群體進行職業規劃培訓,爲他們提供就業機會,這樣社會才可以更好地走向共同富裕。我們希望社會企業不是只重視利潤的賺錢機構,而是構築公益原生態消費環境的有機組成部分。妳可以想象,如果今天中國的那些獨角獸企業變成壹個個社會企業,這能提供多少就業機會?當企業不只是將所得分給股東,而是致力于公益事業回饋社會,那將是壹件多麽美好的事情啊。
現在公益機構做的社會企業還存在許多不足,比如不是以社會需求爲主導,而是以自身能力爲主導;另外還有很多剛從公益機構出來做社會企業的人沒有太多商業經驗。在我看來,也許商業機構出來做社會企業的成功率會比慈善機構出來做社會企業的要高壹點。因爲社會企業需要商業和慈善兩者結合,而商業方面往往更加的重要。
當今社會企業面臨的挑戰,首先是其原生態還沒有形成。以Village127面包店爲例(這是上海第壹家以社會企業模式運營的法式烘焙咖啡廳,弱勢群體青年接受“海上青焙坊”的壹年職業培訓後成爲Village127的烘培師,而店鋪利潤除用于店鋪運營外全部捐給社會公益項目,支持困境家庭的孩子完成學業或職業技能培訓),如果我們要裝修買家具,或者買紅棗買面粉買堅果,我們肯定也會優先支持同爲社會企業的夥伴。如果各行各業都有壹批專業而出色的社會企業,我們完全可以構建這樣的原生態,讓行業社會企業化,日常生活公益化,這壹定是事半功倍的。要壹個人每天捐20塊錢是比較困難的,但是要他每天來Village127買壹杯咖啡或者壹條面包是相對容易的。因爲壹個人沒有義務每天捐20塊錢給壹個慈善機構,但是壹個人每天總是要吃飯的。如果我們通過以買咖啡和面包的形式來做公益,既可以解決自己的剛性需求,又可以幫助他人,讓公益生活化;同時也可以支持壹些弱勢群體青年,讓他們通過在面包店工作自力更生。我覺得很多人都是會願意通過這種方式來幫助弱勢群體的。公益生活化意味著不是我們賺到錢後去捐錢才叫做慈善公益,我們可以把公益融入到我們日常的生活之中。

當然社會企業的運營需要政府更好的政策配合,比如已經在部分國家實施的,通過稅收減免來降低社會企業運營成本的政策。Village127雇用受智行支持的海上青焙坊畢業生,在食品制作中不使用任何化學添加劑,所得的利潤捐給慈善公益,但是沒有相應的政府政策去鼓勵這樣的社會企業。國外對于支持社會企業有更加明確的規定,比如當壹個企業捐30%的利潤做慈善公益,雇員裏面有壹定比例的殘疾人,在利潤和運營裏體現公益時,它就會成爲壹個受政府所認可的社會企業,能夠獲得稅收等方面的減免以降低運營成本。但是當社會企業在中國沒有得到法定認可的時候,我們會難以找到人去持之以恒地做這件事。妳可以爲了壹份初心自己去堅持,但這不能得到政府的認可。如果政府能夠制訂完善的政策,讓企業知道如果滿足了特定的條件,就能得到來自政府的支持和認可,那麽將會有更多的人願意把自己的企業由商業模式運營的企業,變成投身公益的社會企業。
文|杨梓盈 邓可欣 邢奕萱 李艾佳 姚亦楠 谭晓彤
审稿|严芷滢 张雅淇
图|感谢受访者提供
编辑 | 李卓颖
matters 编辑|邢奕萱
围炉 (ID: weilu_flame)

文中圖片未經同意,請勿用作其他用途
歡迎您在文章下方評論,與圍爐團隊和其他讀者交流討論
欲了解圍爐、閱讀更多文章,請關注本公衆號並在公衆號頁面點擊相應菜單欄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