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本红色年代的反思——对Gavin Walker的采访(Rethinking Japan’s Red Years INTERVIEW WITH GAVIN WALKER)
Selim Nadi
Peng Yu 译、志愿者 校
(译者注:关于书名和人名的翻译,为了读者检阅搜索方便,译者只翻译了有中文译本的书籍的书名,以及有汉字或有对应中文名字的人名。同时中文以《》,日语以「」,英语以斜体为书名号标注。)

2021年的冬天,Selim Nadi受法国杂志Contretemps邀请,采访了Gavin Walker。原版法语采访稿即将面世。
Gavin Walker是麦吉尔大学历史系的一名副教授,是The Sublime Perversion of Capital (Duke, 2016)一书和Marx et la politique du dehors (Lux Éditeur, 2021)一书的作者,同时还是The End of Area: Biopolitics, Geopolitics, History (Duke, 2019, with Naoki Sakai)一书以及The Red Years: Theory, Politics, and Aesthetics in the Japanese ’68 (Verso, 2020)一书的编者,他还是柄谷行人《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Marx: Towards the Centre of Possibility (Verso, 2020))一书的译者和编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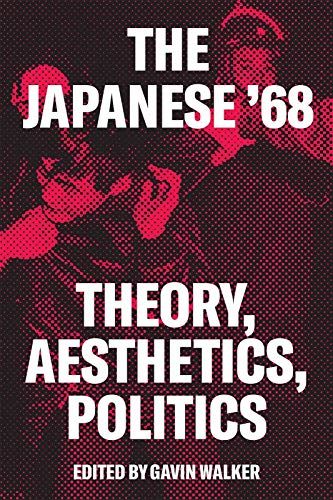
在The Sublime Perversion of Capital一书中,你写道,“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马克思主义是日本思想生活最重要的理论探索之一。”在柄谷行人的《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英译版前言中,你也说过类似的话,“可能对于大多数北美和西欧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接下来的内容是难以置信的:战后日本是地球上马克思主义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你怎么评价日本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本国以外的翻译和传播?为什么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会与日本人对马克思作品的吸纳息息相关?
让我首先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关于日本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海外的翻译和传播,我必须说,自1920年代起,日本的马克思主义作品范围甚广,程度甚深,而它在海外的传播则相对不足。当然,二十世纪早期到中期,部分日本人在英语圈里有一定接受度,譬如文化批评家、哲学家户坂润,或是政治经济学理论家宇野弘藏。从历史学到宗教研究,再到日本文学,各个领域里都有一些这样的人物,只是这些人并不一定被视为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代表。在英语圈和欧洲语言圈中,存在一些对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小范围本土化吸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Thomas Sekine作为这一领域在加拿大的先锋,对宇野弘藏的作品进行过一些独特但不全面且具有个人色彩的解读;伊藤诚在他早期的重要作品《价值与危机》中,对宇野弘藏进行过更为正统的解读,也就是说,在谱系上与宇野弘藏更为接近,这本书最近刚刚再版;富山茂树、高桥浩一郎等马克思历史学家在有关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型的国际辩论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战前马克思主义者如三木清、户坂润,他们仅仅存在于东方主义对京都学派的相当狭隘的西式接纳中。但这些只是一个庞大的传统中从各个流派中汲取的很小的一部分。在日本之外也有众多学者活跃在各种其他语言中,他们本身就广泛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因此也能追溯会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日本谱系中,其中代表就是Harry Harootunian。或许在西方世界中,谈到日本与马克思主义的最大联系,人们便会聚焦到柄谷行人的身上,我们一会儿会单独谈谈他。现在在与各个领域,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丛书的合作中,我们正试图增加这一传统的经典文献的翻译数量。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任务。
你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日本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和日本人对马克思作品的接纳息息相关?这是一个更长且更复杂的故事,一个前述未详的故事。由于篇幅原因,我们并不能在这里仔细的探讨一番,简单来说,这是日本现代人文科学形成的基础。
首先,日本早期对马克思主义的吸纳始于十九世纪末期,并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由于日本战前的帝国主义文化,日语在翻译和传播的其他国家文献领域享有霸权,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极大影响了其他亚洲国家。在这方面,三种平行的要素发展出来:
1. 对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转型的分析。它始于马克思《资本论》的历史设定。我们很难说这一转型过程在亚洲已经彻底“实现”,毋宁说正在进行中。本质上来说,这是对于亚洲社会的“历史”发展一种探讨模式。随着帝国主义经验和资本主义蚕食而来的是历史上首次形成的现代民族国家。这种探讨模式涉及世界贸易、以及更为内部的话题——农村日益尖锐的阶级斗争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社会形式的发展。因此,这种探讨将马克思的作品视为科学手段,用以理解在资本主义逐渐成为全球霸权大背景下的局部发展过程;
2.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思辨批评的发展。通过这种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种适用于理解具体现代情感、文化形式以及美学生活的社会分析模式;
3. 翻译、编辑、出版。根本上来说这是由生根于大学校园的马克思主义所支持的。
其次,战后奇异的特别之处在于,马克思主义传统在海外的代表性受到了压制。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在日本保守派和美国占领者之间的协作中,日本被限制在了明治早期第一次帝国扩张的版图内,将日本人历史性地“重新塑造”成了“同质族群”(包括被重组成冲绳的琉球王国和北海道的原住民阿依努人)。这个新创造的、被认为是同质的群岛回溯成为永恒。这事实上只是对战前帝国的一种否认,其实这个帝国的存在深刻地给亚洲二十世纪留下了痕迹。这种否认导致了一种奇怪的状况。一个新的、面向内部的日本民族中心主义在日本“国内”出现了,而美国的帝国霸权或多或少继承了之前日本帝国的遗产。在“区域研究”学科的驱动下,日本思想在日本海外的“再现”存在于一种与新的、严重的东方主义视角审视的“日本性”串通的状态之下。马克思主义、现代哲学与有关帝国的阴暗面的解读都逐渐被西方官方支持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驱动下的翻译所取代,来服务于一种“纯粹的”日本盟友的形象。比如说,像和辻哲郎这样的隐秘法西斯主义者和鈴木大拙这样的种族神秘主义者声名远播,描绘了一幅新日本与太平洋上的美式和平完全兼容的画面。
这种战后美日关系的原型结构曾在日本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传播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当然,冷战结束之后,这种结构开始瓦解。同时新的国际化潮流也开始和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联系。然而,还是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这些拥有巨大体量的作品需要跟与之相当的思想构建起话语联系。毫不夸张地说日语可能是继德语、法语、英语之后,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语料库。
柄谷行人是谁?他和宇野弘藏作品之间的思想联系是什么?
柄谷行人是一个杰出的思想家,他现在仍然活跃在思想界。毫不夸张地说,他是一个真正具有相当独特的日本传统的战后思想家。这种传统来自那些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公共知识分子。柄谷行人的政治生活始于1960年学生运动前后第一次“新左翼”的诞生,他作为文学批评领域的公共人物首次亮相。在20世纪70年代初,他关于马克思的后续作品再次让他成为一个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和知名人物。但大概是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期间,他巩固了自己在社会思想和文化批评领域的声誉。柄谷行人就读于东京大学经济系,在那里他师从铃木鸿一郎。铃木鸿一郎是解读宇野弘藏作品的重要人物。当然了,柄谷行人长期受到宇野的影响,至少在经济方面是这样。但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对于很大范围的来自马克思主义和新左翼政治政治中的人物来说,都是如此(受到宇野影响)。我不会说宇野是最主要影响柄谷行人的人,但的确是一种影响。我认为柄谷行人在耶鲁大学的影响与德里达、保罗·德曼、杰弗里·哈特曼等人接近,他们同等重要。宇野的作品受到广泛阅读,以及远远超出了所谓的“宇野学派”范围,我想我们稍后会回到这个话题详细讨论。
有意思的是,《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1974年)第一次亮相是在文学期刊《群像》中连载七篇,与很多短篇小说和连载小说并驾齐驱。此外,在这本英文版的序言中,柄谷行人写道,虽然他进入了东京大学经济系,但在那里他遇到了“宇野学派”的几个成员,他于是将重心转向了文学,对经济学失去了兴趣。事实上,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被书中的文学参考以及这些参考是如何帮助他阅读《资本论》所打动。你能谈谈柄谷行人与文学批评的关系吗?
柄谷行人的作品基本上始于文学批评领域,或者普遍地说“批评”领域。这未必与他的分析对象有关,而是与他的“风格”或是“阅读规则(reading protocols)”相关(这个德里达的引用有重要含义)。柄谷行人的“例子”在一开始就是批评家,像是小林秀雄和吉本隆明,他们都是文学和社会批评交集中的基本人物。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工作一直是与文字——书写、现代民族语言的出现、语言与主体性的关系、言语与文本的关系有关。最重要的是,柄谷行人发展出了一种关于社会、政治和哲学作品的写作方式,他赋予“文本性”特别的地位。要知道在那个时候,像是对于马克思的作品,主流阅读方式都是高度“概念性”的。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他在英文版《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新序言中的观点受到了下面三个人的一定的影响:吉本隆明、宇野弘藏以及广松涉。这三位在阅读马克思上都独具创造力,但都将注意力放在概念和理论发展上:吉本关注政治和批评领域,宇野着眼于经济学,广松则是哲学。在这一时期,人们常把柄谷行人的影响与索绪尔和结构主义的出现和发展结果联系起来。在此基础上柄谷行人创造出一条平行路线,直指解构法国和美国的文学批评,批驳文本的二元对立,追踪边缘性的指涉回到作品的中心,说明文本自我揭露的结构性难题,等等。我认为如果柄谷行人的《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在45年前首次问世之时就被翻译出来的话,将会对这一全球性时刻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因为这种风格对马克思文本的阅读和交叉阅读以及后现代文学批评尚未建立起分析模式。它对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部分原因是它为马克思主义思想指明了另一条前进的道路,用巴迪欧的话说,这是1972-73年新左派爆发以来产生的一种没有与政治“缝合”的思想。
柄谷行人阅读马克思的方法在某些方面似乎与阿尔都塞非常接近。日本新左派是否阅读阿尔都塞的作品?这对柄谷行人有影响吗?
在日本,阿尔都塞的作品过去一直受到关注,现在依然如此。可能日语是继法语、西班牙语、英语之后最重要的解读阿尔都塞的语言了。主要的左派思想家,特别是今村仁,在上世纪80年代引入很多阿尔都塞的作品并翻译成了日语,这其中包括一本1975年问世的关于阿尔都塞思想的长篇专著。今村的作品在这一领域尤其处于中心位置,只可惜在日本之外人们对他知之甚少。市田良彦也是日本批判理论和社会思想的重要人物(当然他关于阿尔都塞、福柯、斯宾诺莎等人的作品在法国也很出名),他曾说过,“就像法国有研究黑格尔的吉恩·海波利特,日本也有研究阿尔都塞的今村仁”。我认为市田的通过这句话表达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吉恩·海波利特在50年代对黑格尔语言维度的关心(像是他《逻辑学与存在:论黑格尔的逻辑》)为68年代思想的新视野提供了基础,就像今村为阿尔都塞全新全面的解读奠定了基础一样,这种新的解读方法直到几十年后才占据主导地位。自70年代以来,围绕阿尔都塞的上百本书籍通过日语出版,这也包括了市田自己的重要作品——Althusser: une philosophie de la conjonction (2015),一部基于IMEC档案馆内作品的重要解读(译者注:IMEC:L'Institut mémoires de l'édition contemporaine当代出版记忆研究院,为法国收藏所有有关当代出版及创作过程的资料库)。至于阿尔都塞对柄谷行人的影响,我认为更多的是外围的、氛围上的,而不是直接的影响。当然,柄谷行人和阿尔都塞都有一种“理论型的反人文主义”,但是他们精通的材料差别很大:阿尔都塞擅长斯宾诺莎、马基雅维利、葛兰西,而柄谷行人则喜欢索绪尔、维特根斯坦、尼采、弗洛伊德。柄谷行人的思想有他自己的谱系发展,并非源于法国68一代的思想,而更像是与之平行。
您的合集The Red Years(《红色岁月》)以日本1968年为中心,柄谷行人对马克思的解读与68一代对马克思初始形态的解读在多大程度上存在分歧?柄谷行人对《资本论》的文本性更感兴趣,这是受到索绪尔的影响?还是也收到了精神分析学家的影响?
柄谷行人对马克思的解读与68年代的马克思论著,特别是与那些以异化理论为中心的论著有明显的不同。60年代日本专注于“异化理论”的作品,将注意力集中在青年马克思身上,这是一种对“老左派”坚定的回答,正如欧洲和北美一样。“异化”逐渐意味着一切人们所反对的:形式主义和社会上保守的“老左派”、以及其斯大林主义式的思想、风格、文化(日本也是如此,法国也是如此)、新的战后消费者文化、群众社会中的疏远和孤僻、性生活和审美生活规范的变化。然而这种“异化”带来的不仅仅是与过去的决裂,而且也是形式上的延续,没有什么比一种有关“未被异化的人”的幻想更能说明问题了。仿佛一旦“异化”得到解决,政治在人类的已经实现的“仙境”中就变得没有必要了。柄谷行人与其他人当然将这些解读视为天真的、前精神分析的、政治上的乌托邦,将其视为贬义。这种穿越了分析情境的“幻想”并非一种以全然颠覆为最终目标的“治疗”,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主观化带来的影响就显现出来了。对于柄谷行人来说,他对马克思的阅读显然是以资本为中心的,任何对青年马克思的讨论都应该从马克思成熟著作中建立的理论体系和阅读模式的制高点——这与“异化理论”是完全不同的出发点。
宇野弘藏可能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对柄谷行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柄谷行人在自己的书中说到,宇野的影响力首先在于他对交换的关注。你能解释一下资本主义的本质是经商贸易的这一观点吗?
关于宇野的思想,有几点很重要。首先,宇野的作品对马克思主义和日本左翼产生了更普遍的多方面的影响,其程度远超“宇野学派”作为单一学派的影响力。从简单的研究团队到武装斗争组织,整个新左派都阅读并赞成他的作品,并视其为马克思经济思想的科学且正式的先锋。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如果你在日本从事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研究,不管你是否同意他的作品,你都必须对宇野的理论体系表明立场。这使得他身边围绕着一系列的人物,他们本身都很重要:铃木鸿一郎(曾是柄谷行人的老师)、岩田弘(他的“世界资本主义”理论在60年代很有影响力),以及很多其他人。他们并不是所有人都属于“宇野学派”。柄谷行人绝不是狭义上的“宇野学派”的产物,他的作品远离了这类高度学院派的内部讨论。
为了理解宇野的作品,我认为有必要提到几个因素。首先,宇野的思想和他独特的切入问题的方法是从战前时期的那场“有关日本资本主义”的重大辩论中产生的。这场辩论的本质是在讨论日本资本主义在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是否完全成熟?换言之,这场维新运动本身是否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是否是一场“不完全”的资产阶级革命?一场没有成功地使国族性空间完全“现代化”的革命?尽管财产关系和劳动力市场发生了变化,但日本“落后”的基本要素,如天皇制、政治阶级的地区式和家族式本性、工业和和政府中的家长式关系,仍然完整、有效,他们是“封建残余”。
当然,这场辩论基本上反映了其他非西方世界的类似辩论。在这些地区,殖民主义下的“前现代”或是“封建”因素浮于表面,他们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不稳定衔接在帝国主义政权中不断积累,这些必须被理论化。宇野认为,在日本,这场辩论的双方将马克思的《资本论》直接应用于特定的、地方的、民族的、区域的情况。辩论双方一方处理资本主义的普遍性,另一方则处理其局部的、特定的发展道路,他们并没有理解到这种直接应用理论的困难之处。从冲突双方辩论的死胡同中,宇野发展了他独特的方法论基础:三段式分析法。
1. 第一层是“原理论”层次,是“纯粹的资本主义”,“理想平均”的资本主义;
2. 第二层是“阶段论”,即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阶段以及结构性积累的水平——重商主义、自由主义、帝国主义,以及这些阶段独特的形式;
3. 第三层是“现状分析”,即结合当地和当前情况的直接的、经验的和直接的特征的形势分析(译注:conjuncture,阿尔都塞的形势概念,意指一系列偶然性的结合)。
现在,柄谷行人经常特别喜欢把有关宇野对于“交换”的讨论作为自己独特的理论发展的背景,在他提出“交换模式”理论的过去15年里,这种特征达到了巅峰。宇野经常评论说,资本始于两个群体间的相互活动或是亲密交流,最初的交换之后内化为每种形式本身。但更广泛地讲,宇野尝试理解它具体是如何的,用马克思的术语说,“资本不可能通过流通产生,同样也不可能脱离流通而产生,它必须有来自流通的起源因素,也有不是来自流通的起源因素”(原文出自《资本论》第一卷)。在这个意义上,宇野的著作,特别是他在20世纪50年代的主要理论著作,对劳动力商品在资本驱动下的特殊地位进行了完整的逻辑分析,这标志着一处在资本逻辑内部与其历史外部相互渗透的地方,在资本所谓平滑的纯粹的循环过程的核心,产生了一种不稳定的过剩力量。围绕着这一点,通过发展一种有关其不可能性和不合理性的动态的广泛理论讨论,宇野在方法论上创造了一系列独创性命题于人口的概念,以及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分析中的逻辑和历史的人物。
柄谷行人被看做一位日本“批判理论”作家的代表。你如何定义这种批判理论呢?是符合法兰克福学派?还是应该从更广义的角度去理解?
“批判理论”在英语中已经转变成一个术语,很大程度上脱离了法兰克福学派。这个词来源于“批判理论(德语Kritische Theorie)”并已成为带有批判取向的当代社会、政治和美学理论里一个通俗易懂的术语。在日语中,通常用来形容这一词的是“現代思想”,字面意思是“当代的思想”。批判理论在日本鼎盛的时期可能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随之而来的现象是所谓的“新学术主义”(日语:ニューアカ),这是读者的兴起,也意味着批判性社会和文学理论作品的主流生命力能够进入人们的视野。这种情况的发生与“法国理论”在日本重要发展是分不开的,柄谷行人和评论家浅田彰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反映了日本普遍存在的“恋法情结”,尤其是美学和文化领域。如果充分讨论日本的“恋法情结”的历史和作用(当然这与法国的“恋日情结”有着复杂的联系),会让我们偏离这次采访的主题,但重要的是要指出,在20世纪的法国哲学和社会理论被68一代所唤醒之后,日本的社会和政治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柄谷行人和浅田彰的刊物「批評空間」(《批判空间》)是他们作品的一个重要的载体,同时的还有个政治性更为清晰的刊物「状況」(《情况》),它直接形成了长期的68一代「全共闘」的经验(译者注:全学共斗会议,一个各个大学内部的联合体,实行罢课类学生运动),还有「現代思想」(《当代思想》),它是一个发展日本批判理论的重要刊物。这种“传统”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强大了,但在大学内部,却保留着重要性,在出版界更为关键。关于日本的独特特征,我想说一点,它与美国不同,在美国,“法国理论”及其发展主要局限于大学(虽然艺术领域是另一回事),但在日本,柄谷行人的作品,或者浅田彰1983年的「構造と力」(《结构与权力》),一部后马克思主义关于后68年代法国思想的重要沉思录,包括德勒兹和伽塔利、拉康、福柯和其他人,可以在普通读者层面成为畅销书。这种现象在大多数其他国家是不可想象的,即使所谓的“新学术主义”热潮在90年代消退,它的影响今日仍在发挥作用。
在The Red Years(《红色岁月》)的序言中,你写道,日本的1968年可能是地球上最漫长的1968年——从1960年的“新安保条约”到1972年联合赤军解体。您能解释一下为什么1968年会这么漫长吗?
我甚至会追溯到更早的时候。我认为日本的68一代的基础始于1955年。在这一点上,它使得这样的一个论点更为可信,即68一代是近20年(1955-1973)的一个时期的统称。当然,能这么说有一些重要依据。第一点,日本所谓的“新左派”与北美或欧洲大部分地区有着相当不同的历史。在全球范围内,人们普遍认为新左派是从1956年初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揭露”斯大林的“秘密讲话”,以及同年晚些时候苏联入侵匈牙利的社会反响中诞生的。从这一时期开始,伴随着已经发展开来的中苏分裂,理想的幻灭导致世界各地不同地点的共产主义武装分子发生重大变化。在某种程度上讲,它刺激了莫斯科之外的共产主义政治群体朝着不同于莫斯科的方向形成发展,甚至在许多年轻人中有一种感觉,官方的共产党们背叛了事业,成为了僵化保守的官僚机构。
显然,这一时期提出的历史和理论问题不能用压缩的方式来严肃对待,这里只是进行了一个过于简洁的概述。但在日本,这一进程基本上是在两年以前以一种独立的方式进行的。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是日本共产主义运动的显著时期。尽管遭到美国占领军的镇压,左翼作为一个整体还是得到了广泛的支持。1949年中国革命的成功为亚洲共产主义事业注入了新的动力和胜利的主体性。20年代50年代初,日本共产党动荡不安,内部存在着各种政治倾向。在中国路线的广泛影响下,日共内部有着一种秘密的、地下的态度,甚至做好了武装斗争的准备,以及对中国抗日游击队的“人民持久战”产生了一时兴趣。日本共产党建立了非凡的政治实验,例如所谓的「山村工作隊」,我们称之为山村行动队,在那里,青年党员和干部进入农村以及遭到剥削的外围城郊乡村并“发动革命”。这一实验的失败原因很复杂,也与美国占领下的土地改革有关。但这一地下革命的历史时刻对左派产生了长期的影响。
1955年,在日本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这次实验以及整个地下组织时期,都被斥为“极左冒险主义”,同时一种新的议会路线在党内成为了霸权。这种对过去的否认打击了年轻的激进分子,他们视其为一种令人震惊的背叛。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共产党在55年转向议会制,为党外共产主义左派创造了条件,这比全球范围内苏联和国际形势造就的新左派萌芽早了两年。这种新左派于是构成了第一次安保抗议和1960年「全学連」(译注:全国性学生组织“全学联”)一代人的社会背景,这些人后来又反过来催生了1968的“全共斗”一代。1968年的余波最终在1972年达到了顶峰。在《红色年代》(The Red Years)一书中,长原丰在一个精彩的章节了描述了这一点,他是当代日本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之一。在1972年浅间山庄时间中,联合赤军武装分子挟持人质,最后与警方进行枪战。事件发生后,该组织内部的杀戮被揭露出来,使得社会上大多数永久性的与左翼对立起来。
对于之后的学生运动,人们勉强对他们坚韧和奉献的精神表示钦佩,但到了1972年,68浪潮已经开始退去。在此之后,出现的组织,特别是东亚反日武装阵线和黎巴嫩地区的日本赤军,就不再那么中心化了,他们主要发展成为象征性和虚无主义的武装行动。前共产主义联盟的两派,「革マル」(革命马克思主义)和「中核」(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派,陷入了自相残杀的恶性循环之中,退回到他们内在的迷信核心中。这或多或少地结束了68年。这与70年代末欧洲的“城市游击队”概念大致可以相提并论,像是意大利的红色旅、法国的“Action directe(行动指挥)”、西德的RZ(Revolutionary Cells)等等。这并不是说这些政治派别和武装组织的政治取向必然是“错误的”,但这显然是成为了68运动中去政治化和道德败坏的象征,而68运动中更为广泛的群众特征则超越了自己的能力和视野,陷入了一种虚无主义。我并不反对这种虚无主义,但显然它是对沉重打击的回答。
为什么你认为给日本“红色岁月”画上一个“句号”是有政治意义的?
我认为这是政治化的,原因有二。首先,这是用一种“翻译”的口吻说这句话,就像“我们应该给90年代画上一个句号”,在其话语上表现为“历史的终结”。实际上是80年代、90年代才造就了“反68”的概念,因为这期间革命退却了、苏联垮台了、幻想破灭了、马克思主义的正面力量弱化了,同时对抗统治的政治反抗力量也可能随之遭到削弱。第二,这是对一种非常具体的编史策略的否认。但实际上这种否认在“六十年代全球史”的大多数历史记述中采用,是一种自鸣得意的幻想,一种从“68一代的轻率”中变“成熟”的幻想。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这种中年自恋,痴迷于为政治上和理论上的懦弱提供理由,从解放的政治理念滑入疲惫的自由主义。这令人作呕。没有什么比把革命当作是青年时代的产物这种校领导般的话语更不吸引人的了。仿佛青年之后,理性开始发挥作用,不成熟的幻想遭到摒弃,取而代之的则是投身于冷漠。这是对政治和思想里所包含的一切的背叛:激情、忍耐、毅力、否认、抗争、冲突、勇气、真理、奉献。今天对革命政治的历史分析是制度化社会的历史中,最令人压抑的“专业”领域之一,投身于这一事业如同自由主义的那句“伟大口号”——“它很复杂”。因此,我们必须拒绝这种对解放政治历史的不加思考的空谈,但这也不意味着我们应该为这一时期密集且精疲力竭的斗争编撰成圣贤传记或是英雄史诗。“1968年结束”这一表述,并不是要把68年作为一个“伟大的时刻”固定在历史的苍穹上,而是要重现它的活力、开放性、波动性和现实性。
在20世纪60和70年代的西德,新左派成员就新的联邦共和国结构内的法西斯主义的持续存在进行了一场重要的辩论(一些毛主义人士甚至提出了“西德法西斯主义”的论点)。日本在20世纪3、40年代不仅与德国纳粹党结盟进而侵略中国,在何种程度上,这种态度会成为日本新左派的一个议题?
毫无疑问,法西斯残余是新左派内部的一个重要甚至关键的问题。就像西德一样,战后的美国占领当局,虽然名义上关心起诉那些声名狼藉的法西斯分子,但实际上为大批法西斯政权内部的人物平反,作为对付左派和共产党的权宜之计,这也是冷战内容的一部分。当新左派作为一种主要社会力量从根本上出现之时,这些法西斯残余已经完全重新融入战后秩序,自由民主党就是例证,它几乎是战后日本的唯一执政党。
在1969年标志性的东大占领安田讲堂事件中,校门两侧的路障都镌刻着毛泽东的名言“造反有理”,另一面写着「帝大解体」的标语。在战前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东京大学自然还是东京帝国大学的一部分,是庞大的日本帝国中的旗舰高等教育机构。这意味着,1969年,日本帝国主义以其他形式继续存在。尽管如此,当下日本国的殖民和帝国主义遗产并不一定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处于斗争前沿的话题。由于战后日本自己也成为了美帝国主义的附庸,日本以前作为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角色很容易被搁置一旁。但在68年期间,冲绳、阿依努、朝鲜人、中国人、以及「部落民」这种“低种人”这些少数群体的斗争也十分引人注目。
1968年被所谓的“金嬉老事件”中断了。1968年2月,在日韩国人金嬉老在静冈县清水市开枪打死了两名黑社会成员,之后又在该县寸又峡温泉的旅馆内劫持了13名人质,他指责日本政府歧视朝鲜少数群体、维护朝鲜半岛的“分裂制度”。这一事件及其后果产生了长期的影响,特别是对金嬉老的审判(译注:金嬉老获假释后赴釜山市定居,韩国媒体称他为“与日本的民族歧视做斗争的英雄”)。金嬉老的支持者中,有法农《大地上的受苦者》的日语翻译者铃木道彦,他认为,在日本的朝鲜人后裔在日本被置于一个难以忍受的位置,一方面他们与其根源分离,但另一方面他们完全的“日本性”又遭到否认,这种处境使得他们只能在革命性冲突中爆发。两年后的1970年,身为作家和战士,津村乔写出了他非凡的作品「われらの内なる差別」(《我们内部的歧视》),恳求左派重新转向亚洲,对日本在亚洲大陆犯下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原罪作出忏悔。津村十分聪明,他的文章有一定影响力,虽然比起他应得的还是少了。
在革命政治之季末,有个叫东亚抗日武装阵线(EAAJAF)的武装斗争组织现身于臭名昭著的1974三菱重工爆炸事件,他们的“狼”小组爆破了三菱在东京的办公室,继他们之后,“大地之牙”、“蝎子”小组加入了他们地下“反帝反殖民”工业轰炸行动。EAAJAF 因其著名而且长期遭到查禁的城市游击战手册「腹腹時計」(《滴答钟》)而闻名,他们的理论工作和实践政治的立场在新左派中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他们持续不断地关注日本人在北海道阿伊努人和冲绳人的殖民遗产,关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战争责任,以及他们决然采取的非民粹路线——即只要摧毁“日本”本身就足以偿还日本侵略亚洲的债务。他们存在的实际影响虽小,但仍然是一个很少被研究且有着重大意义的时刻。
为什么你将这些“红色岁月”称之为结构性失败?
将发生于所谓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全球性1968年说成一场胜利是不可能的。我这样说,不是诋毁68一代,更不是加入反动派的行列,告诉世人68年的斗争不过是空想幼稚的。我认为1968年的很多东西至关重要,全球左派斗争也必须得到维护。然而,很简单的一个事实是,新左派即使转向武装斗争,也无法扭转他们预见的趋势:世界帝国主义的重组、资本主义社会在全球范围内的掠夺、冷战时期的地缘政治造成的战争和破坏、商品社会主导下各种形式社区团体的异化和撤出、行政官僚机构的僵化的文化趋向(cultural drift)。
今天,新左派反对的方方面面都变得更糟糕、更深入、更顽固。所以说,如果称68年是一场胜利,那纯纯粹粹是一场闹剧。这就是失败。但是我觉得长原丰在The Red Years的稿件中说了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不应该把68年看作是某种“后于事件的”,一种现在无法触及的历史事件上曾被贴上的标签,而是看作“先于事件的”,一种构成解放政治的历史特征,一个新进展和即将发生的新事件的历史基础。长原称之为“将政治传递向这场失败”。我认为,无论如何,这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把政治传递到68年,这样它就不会成为过去的失败,而是成为现在的可能。
当下日本的左派状况如何?
我不是最适合回答这个问题的,因为这个问题具有直接带有实际和形势分析的特征。像我这样的学者不应该对左派的地位发表宣言,而应该提供历史和理论中的干预以供运用到政治主观实践中。我认为,正如当今一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在日本也有一种对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历史和对解放政治的回归,这种解放的方向直指自由议会政治的死胡同。很显然,如同其他地方一样,日本的年轻人迫切渴望着使主导秩序走向毁灭的政治可能。2011年以东北地区为中心的地震和海啸之后,日本这一公司国家不断掩盖福岛核灾难,加剧了气候危机。这使得许多年轻人变得更为激进,反对起日本顽固的资产阶级议会秩序、其自我加剧的僵化,以及其在环境问题上破坏性的恶毒专制。
当然,日本大学系统中也存在着新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一直高质量地开展理论研究。有很多的重要例子,像是日本人广泛地参加MEGA(译注:Marx-Engels-Gesamtausgabe《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项目。话虽如此,像其他地方一样,日本当下的一部分“对马克思主义的回归”,包括形式上和学术上对马克思专业的回归,在政治上与和解性的社会民主结合在了一起。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巴迪欧称之为“教室里的马克思主义,使人昏昏欲睡的马克思主义”。关于马克思未出版的手稿中逗号的位置这种枯燥无味的争辩对于当代政治几乎没有丝毫用处。日本那具有创造力和战斗精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治传统应该被唤醒,尤其是1950到80那几十年的。新左派的斗争传统应该得到支持。
“人类创造历史,但其创造环境并不是可以选择的。”这是一个提醒:尽管你能创造历史,但你无法逃避它。“回归马克思”也必须是“回归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回归政治”,即在具体的形势中做马克思主义的具体政治,否则,这不过是关于“塔木德经”式关于文字的辩论。我们的任务是产生一种斗争的思想、战斗的思想,而不仅仅是提高我们对19世纪思想史的看法。如果日本的新一代发现,这个群岛的语言传统中包含着有关这种“斗争思想”的庞大百科全书,甚至到可以成为全世界的参考,那么,那将成为当今解放政治的真正有力工具。
2021年7月9日
原文网址:https://spectrejournal.com/rethinking-japans-red-yea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