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癌症患者的证词 她是如何坚持了20年? | 医学 | 半岛电视台

在世界癌症日,让我们说,绝望的癌症患者在接受治疗路上所信奉的所有危险建议和神话中,“积极”或“乐观”之类的词是最难以捉摸的,尽管这些词语似乎在呼唤生命和抵抗,但其往往会增加病人的痛苦,癌症患者竭尽全力生活,积极乐观,但却做不到。在这篇文章中,与癌症抗争了 20 年的作家凯特琳·弗拉纳根(Caitlin Flanagan)为我们讲述了“积极向上”的灾难。
如果你是一个关心来自陌生人和熟人渗透性意见的人,那么患有癌症就是其他人的意见可以渗透到你生活中的最好例子,一旦你获得了你的检测结果,就会被来自各方的建议轰炸,正如他们所说:笑,世界会和你一起笑,患上癌症,世界不会停止对你诉说。
你会一直被很多建议所包围,例如:停止吃糖,注意你的体重和你喝的东西,你应该听收音机,而不是看报纸上的新闻,进行体育锻炼,但应注意不要过于兴奋和过度劳累,按照美国运动员、自行车界最著名的专业人士之一“兰斯·阿姆斯特朗”的做法,积极、坚持不懈地练习,加入支持小组,留下回忆并拍照。你住在高速公路附近吗?你喝自来水或吃用微波炉加热的塑料盘子上的食物吗?这就是你患癌症的原因,你有没有想过对责任方提起诉讼?你有没有想过癌症是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自行消失?
在我得癌症之前,我以为我了解宇宙的运作方式,我周围的世界是如何运作的,或者至少我了解了我需要知道的那部分,但是,当我得了癌症时,我的身体崩溃得如此惨重,以至于我对我所相信的一切都失去了信心。由于徘徊吞噬了我,我觉得我必须屈服于其他人的建议,这可能是我得救的途径。但是,不幸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令人困惑,并增加了我的焦虑和不安。

我最终忽略了其他人,因为他们的建议不一致,然而,我永远无法逃避一个警告,即几乎每个人每天都告诉我,有时一天两到三遍:我必须保持乐观和充满正能量,因为这是采取积极态度的幸存者和死亡者之间的分界线,并阅读试图帮助你对癌症采取积极态度的书籍,以及观看帮助你想象肿瘤逐渐减少直至消退的冥想视频,朋友和熟人一直在向我和我的丈夫发送这些书籍和视频,旨在提供帮助,我们是如此的疲倦和疲惫,以至于让我们准备好尽我们所能生存下去。
当我们拿到诊断结果时,给我们留下了很糟糕的印象。之后,我做了一次手术,没有成功,然后又做了一次手术,成功了,然后,我开始化疗,在经历了所有这些疲劳之后,我没有一丝精力可以让我感到乐观和积极。在这种痛苦中,一天结束时,我丈夫会请我坐在客厅里,这样我就可以冥想和积极思考。
但在这样的时刻,一个人只会对其所服用的药物感到厌烦,一想到要离开这个世界,或者我的孩子没有母亲,我就会感到疲倦和恐惧。我有一种强烈的冲动,希望通过服用助眠药物,治疗恶心、呕吐和焦虑症的药物来快速入睡,但我做不到,很快,我脑海中漫无目的的思绪又积聚起来,提醒我需要改变对这种疾病的态度,如果我不这样做,我迟早会死。
人们收到诊断消息的方式不同,虽然有些人有家族病史,并跟随医生多年,而有些人的症状持续了很长时间,以至于最终诊断是这个可怕消息的确定,而不是震惊,有像我这样的人,过着平淡的生活,生活的漩涡一直困扰着他们,直到他们去熟悉的医疗大楼进行例行检查的那一天,如果这个消息落在他们头上,晴天霹雳,这一刻他们仿佛坠入了万丈深渊。

2003 年的一个下午,我发现我得了一种侵袭性很强的乳腺癌,那时我的孩子大约五岁,我所能想到的就是尽快完成 X 光检查,这样我就可以在保姆离开之前去杂货店买些物品,我一边想着晚餐,一边穿上我的病号服进行例行检查,突然,事情发生了变化,天平发生了变化,医生让我重新检查,又拍了 X 光片,最后,我感觉到了一根锋利针头的刺痛。
记得在我失去知觉前的最后一刻,我问医生要不要从我身上取个样本来检查,我问他的目的是让我放心,一切都很好,肿瘤是良性的,看看突然发生的这些变化有多可怕,但是,不幸的是,并不是人们所希望的一切,他告诉我,“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做的,我们已经在取样检测了。”后来,我想知道为什么医生在取样前没有征求我的同意。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我早已跨越了健康与病态的界限,我不得不开始一段模糊的药物和治疗之旅。
医生看得出来我有多震惊,他认为有必要给我丈夫打电话,我必须为接下来的日子做好准备,因为肿瘤属于“侵袭性”类型,但我不想让他给我丈夫打电话,我此刻最想要的就是脱下病号服立即出去,不再见那个医生,不想再看到他的办公室,甚至都不想见到那座大楼所在的街道,我被一种想要离开这个该死地方的强烈愿望所淹没,有些时候会让一个人充满负面情绪,睁开眼睛看到生活的残酷,这就是其中之一。这个消息给我们造成了非常大的打击,而且只会变得更糟,我一直处于迷糊和迷茫状态中,我的孩子们还很小,需要我,他们的形象从未离开过我的脑海。
三周后,我去肿瘤中心接受了化疗,然后,我在谷歌上搜索了化疗列表中最差和最致命的药物,我发现了阿霉素(它可以减缓或阻止癌细胞的生长),这是我注射过的具有有害副作用的药物类型,我和我的病友们都充满了毒素,以至于洗手间上的标志警告我们,马桶必须冲洗两次,以确保在健康的人——无论是护士还是家庭成员——可以使用马桶之前,所有痕迹都消失了,直到治疗后 24 小时,我才被允许抱着我的孩子,在这绝对的地狱中——在这期间,我感觉自己就像在被毒素包围的深井底部,哭泣、悲伤和恐惧——我有对正在发生的事情采取积极的态度。
乐观前景错觉

我们获得了几本美国儿科医生伯尼·西格尔 (Bernie Siegel) 所著的《爱、医学和治愈的奇迹》一书,本书于 1986 年首次出版,此后多次再版,作者似乎把更多的注意力和精力放在了“特殊患者”身上,而不是科学进步本身。他说:要成为例外,你必须告诉你的身体,你想要继续生活,你必须反对告诉你患有绝症医生的任何话,并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你必须全心全意地爱自己,并记住“简单的事实是,普遍快乐的人不会生病”,警惕没有表达出的坏脾气或被压抑的失望,因为它们可能会变成癌症,你需要摆脱这些感觉,否则它们会杀了你。
1989 年,斯坦福大学的精神病学家大卫·斯皮格尔发表了一项针对患有转移性乳腺癌(一种可能无法完全治愈或完全根除的晚期癌症)女性的研究,研究分为两组女性,第一组提供了一个支持小组,并教她们催眠,而第二组没有得到额外的社会支持,斯皮格尔发现令人惊讶的结果是,接受支持女性的存活率是对照组的两倍。
这项研究对现代关于冥想和癌症生存的信念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丈夫给我读的书中都提到了这一切,书中充满了关于治愈奇迹的其他故事,以及通过情感支持勇敢面对困难的患者,但问题是,我离这些积极的事情还很远,我从一开始就没有停止哭泣,我开始认为我的情况已经没有希望了,我已经没有办法得救了,所以我需要帮助,我想起了我丈夫和我在诊断后第一周与之交谈的一位女士。
这次谈话是我的生命线,也是恢复平静和安宁的唯一途径,这位女士是精神病学家安·科斯卡雷利(Ann Coscarelli),她是一家专门帮助癌症患者及其家人应对创伤中心的创始人,我们一开始联系了她,旨在了解我的诊断,然后,我需要她做更多的事情,在她办公室的前半个小时,我们谈到了我的病痛和恐惧,我用明显的紧张语气向她坦白,我“没有采取积极的态度,也没有乐观的前景。 ”

医生用中性的语气问我:“为什么一定要保持积极态度?”虽然我认为原因很清楚,但我回答她说,我不想死,但她还是用同样中性的语气继续说: “没有单一的科学证据表明,积极行为有助于癌症康复,而所有的研究都证明,这种观点是没有根据的。”
大卫·斯皮格尔无法复制他关于转移性乳腺癌的发现,而美国癌症协会和国家补充健康中心(美国政府机构)今天承认,没有证据表明,冥想或支持团体可以提高生存率,相反,这可以为其他伟大的成果做出贡献,例如减轻压力,让你活在当下,不再担心下一次考试,所以,我学了一些瑜伽来帮助我度过惊恐发作,久坐闭目练瑜珈让我感到无聊,无聊的感觉意味着我不再害怕,所以,我再次睁开眼睛,但这并没有意味着由于这些神呼吁,我今天还活着。
解脱时刻
当我开始明白积极的态度与治愈无关时,我终于觉得自己好像从这口深渊中挣脱出来,终于可以呼吸了,当我意识到我的消极态度不是我生病的原因时,我松了一口气,即使我采取积极的态度,这也不是我获救的原因,我的精神科医生科斯卡雷利告诉我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当一组细胞快速异常分裂时,癌症就会发生,如果阻断这个过程,治疗就会起作用,仅此而已。
我们必须意识到,每个患过癌症的人都有不同的经历,然后对什么可以帮助他度过这段疾病之旅都有不同的信念,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尊重这些信念,包括决定不接受任何治疗的患者感受,将一组未经证实的假设强加给患有严重疾病的人是虐待狂,尤其是那些首先将责任归咎于患者的假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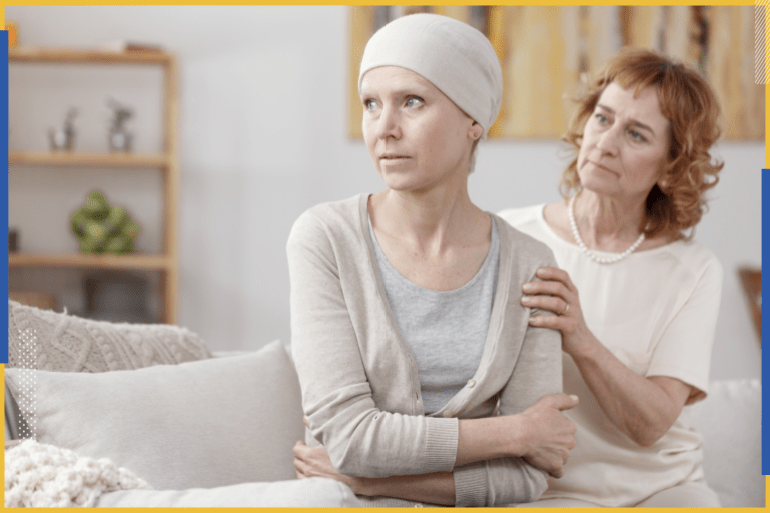
我已经和我的精神科医生会面了 18 年,从那时起,我就不再担心我的态度会害死我,虽然病了好几次,每次复发都很严重,但我还在这里,活在这个世界上,过着平常的生活,写我想写的,喝我喜欢的饮品,同时,我不会被幸福或狂野的乐观所淹没,在那次会面结束离开之前,我问了医生最后一个问题:“的确,我还没有找到克服这种疾病的方法,但是,一个人在这个过程中保持内心的纯洁和良好的品质不重要吗?这难道不会增加他的生存机会吗,哪怕只是一点点?
医生告诉我,这些年来,有许多美丽而高贵的女人拜访过她,尽管其中一些人很快就去世了,许多平凡的女人拜访了她,她们最终设法战胜了这种疾病,由于这些可笑的比较,我感觉我当时的想法还不成熟,我明白,这不取决于一个人的品质好坏,也不取决于他的积极或消极的想法,只要是这样,我想我就能打败癌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