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方萌:民主誠可貴,自由價亦高—— 讀《自由的未來》
冷戰之後,對於前蘇東國家和其他地區的民主化轉型,人們的認識也混亂不清。批評者認為民主化在這些地區導致經濟下滑和民族分裂。支持者或是淡化民主化以後的動蕩政局,或是辯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民主最終會帶給民眾一個穩定和繁榮的國度。無論支持還是批評民主化,雙方陣營常常將兩種基本價值混為一談,這就是民主與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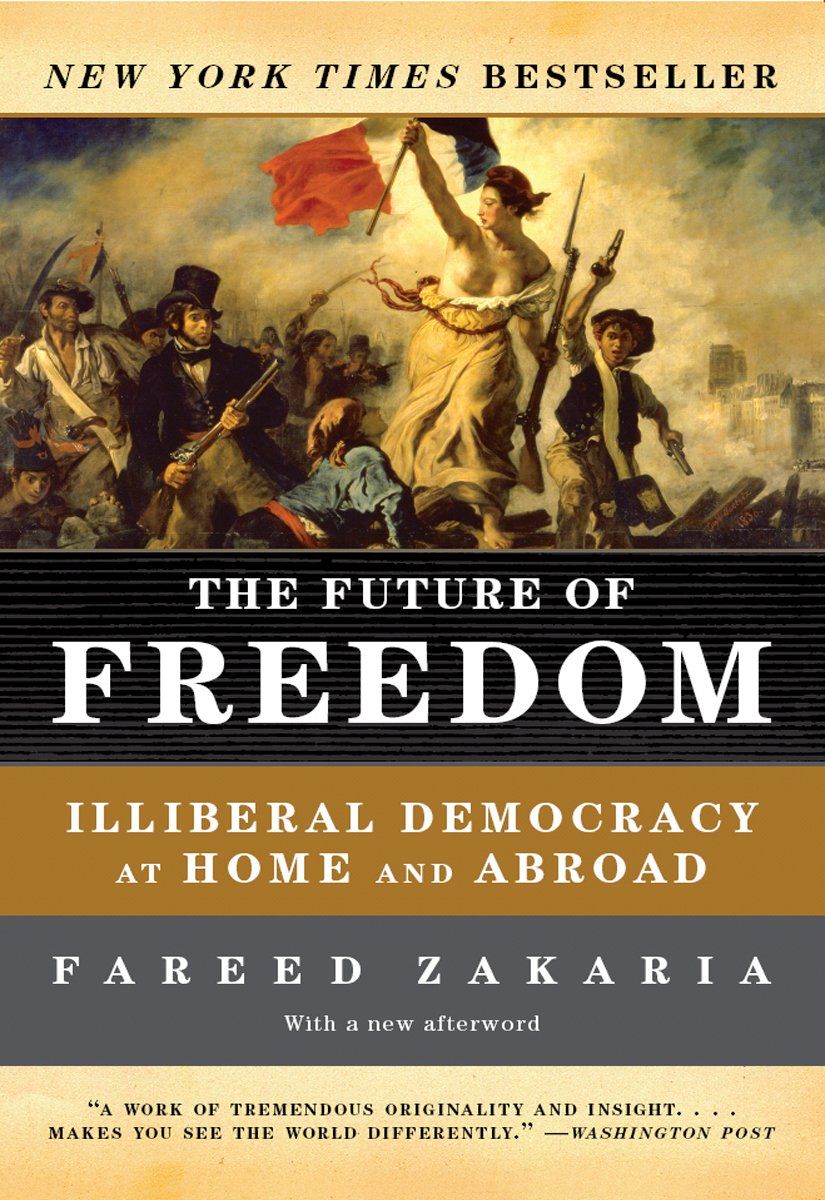
美國政論家弗瑞德·扎卡里亞(Fareed Zakaria)撰寫的《自由的未來》一書開宗明義,旨在澄清民主與自由的概念及其對應的社會體制。此書初版於十年前,最近由上海譯文出版社推出了中國大陸地區的中譯本。扎卡里亞門辯道,民主政治的要義在於通過公開公平的選舉,按照多數社會成員的意志對獲勝的候選人授予權力。自由政治的要義在於建設和完善一系列公共制度,以保障每個社會成員的政治、經濟、宗教和文化權利。典型的自由制度包括分權制衡的憲政、有效完善的法治、自由獨立的企業、媒體和社團,等等。
在作者看來,民主和自由之間存在一定聯繫,但在相當程度上是分立的。民主不一定能夠帶來自由,自由也不必借助民主才能實現。支持民主的人們常常將兩者混為一談,錯誤地把自由視作民主。民主化的批評者也存在認識誤區——政局惡化等轉型問題並不僅僅是民主化導致的,更多源於保障自由權利的制度性缺失。成熟的自由民主政體能夠有效地防止這些問題出現,民眾既能走向票箱選舉領袖,也能走上街頭抗議政府。
兩儀生四象。按照一個社會民主化和自由化的程度,扎卡里亞將世界各國的政體分作四類。第一類是自由民主政體,包括大部分西方發達國家。這些國家的民主制度已經穩定運行了幾十年,具有成熟完善的憲政體制。第二類是不自由的民主政體,包括很多近幾十年新產生的民主國家。這類國家尚能進行較為公正的選舉,但獨立媒體和社團受到政府打壓,民眾的人身權利遭到侵犯。民選領導人往往否定憲法對政府的限制,濫用民眾授予的權力。第三類是不民主的自由政體,最典型的代表莫過於香港和新加坡這兩個東亞城市。兩者皆不屬於西方意義上的民主社會,但政府廉潔高效,法治昌明有度,公民們享有多項政治和經濟自由。最後一類則是既不民主又不自由的政體,如薩達姆治下的伊拉克。
不自由也不民主的極權政體最遭世人痛恨——今天很少有人願意回到斯大林(港譯史太林)時代的蘇聯或是希特勒(港譯希特拉)時代的德國。而對於不自由的民主政體和不民主的自由政體,輿論評價可就人言言殊了。在扎卡里亞看來,後者比前者的政治文明程度略高一籌。他舉南斯拉夫為例:在鐵托的強人統治下,民族分離主義勢力受到壓制,當地民眾雖無投票權,可還能享受有限的人身權利。等到米洛捨維奇的民主時代,他們反到飽受分裂和戰亂之苦,連生命安全都成了問題。
如果缺乏保障自由的制度,民主社會很可能選出極端民族主義分子或宗教原教旨主義者。他們帶給人民的苦難會抵消人民享受的民主紅利。不自由的民主國家往往政局動蕩,最後大多回到專制獨裁政體。反觀不民主的自由社會,公民享有較多的人權和福利,只是自由權利沒有民主制度保障,統治者也缺乏合法性基礎。扎卡里亞在書中列舉諸多國家案例,說明已有自由的社會進行民主化,要比已有民主的社會進行自由化容易很多。
《自由的未來》一書的重大貢獻,在於區分了民主和自由各自包含的公共價值,以及每種價值之於社會良性運轉的意義。扎卡里亞引用政治學大師亨廷頓的著作說:「民主是一種公共之善,但不是唯一的善。」事實上,自由民主政體的設計之妙不在民主選舉,而在於許多「不民主」的設計。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在19世紀已經觀察到,美國的民主制度為了防止「多數暴政」,採取了一系列制衡措施。比如,美國的憲法修正案對多數意志進行了不少限制,即使票數再多也不能否定某些個人權利;美國高等法院的九位大法官由總統任命,而且實行終身制;無論人口多少,聯邦每個州都可以選派兩名參議員進入國會。這些制度並不是或不完全是按照民主的邏輯設計,卻有效地維護了美國公民的自由權利。可見,民主政體應當受到自由制度的節制。
面對西方國家出現的民主危機,扎卡里亞並不認為進一步民主化是正確的發展方向,他更擔心「過度民主化」帶來的負面影響。例如,上世紀60年代後,美國很多公共機構在擴大民主化的呼聲下,進行了公開化改革。此舉導致決策過程直接暴露在民意測驗和遊說集團的壓力下,反倒引發了民眾不滿。作者指出,民眾需要選舉具有公共決策能力的代議人,而不是僅僅讓他們充當多數民意的傳聲筒。
《自由的未來》還花相當篇幅討論了經濟領域和文化領域的民主化。經濟民主腐蝕了職業人士的公共責任感,文化民主則瓦解了文化精英的權威地位。這些因素部分地導致了財務醜聞大量爆發和垃圾文化大行其道。當然,這兩大領域的民主概念是政治民主的引申義,並不像政治領域那樣簡單地應用多數原則。扎卡里亞似乎更多地想通過批判民主價值的陰暗面,為西方傳統的精英主義召魂。
無論歡迎與否,民主化已經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天下大勢之一。對於尚未民主化和正在民主化的國家,《自由的未來》不啻為一篇富有啓示意義的喻世明言。如果後發國家試圖建立自由民主政體,它們應當重視自由制度的構建,而不是僅僅舉行全民普選了事。這些國家的憲政改革也應全盤考慮社會各個階層和群體的利益,精妙地設計制衡架構和法律細則,不僅反映多數民意,也保護少數團體。
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地遭受重大挫折後,不少學者開始反思美國的對外政策。如斯坦福大學教授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走在十字路口的美國》一書中就指出,「政體變換」(regime change)不等於「國家建設」(state building)。扎卡里亞則從民主與自由的關係出發,發出類似的建言。他告誡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建設自由制度比進行民主選舉艱難很多,需要富有遠見的政治家持久切實的努力。倘若只看到新興民主國家聲勢浩大的選舉活動,西方世界還不該宣佈大功告成。
就具體的民主化路徑而言,扎卡里亞總結數十國經驗教訓,主張等到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5000美元左右,政治經濟體制能夠保障公民基本權利之後,再舉行全民普選不遲。過早的民主化很可能走向民族分裂、對外戰爭,並退回獨裁政體。美國近年來在一些不發達國家推廣民主制度失敗,多少與此有關。看來,民主即使是普世價值,也具有時效性啊。
(註:本文發佈時略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