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威格死于昨日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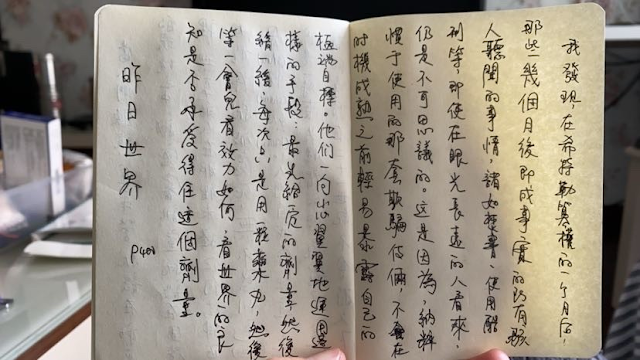
茨威格在《昨日世界》中表现出来的纯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不知道用“纯真”这个词来形容一个五六十岁、享誉世界的文豪合不合适,但我能力所限,实在想不到更好的词。
说他纯真,是因为他在描述那些和他有交情的文艺界大拿的时候,字里行间表现出的谦逊和仰视,就好像他自己是个无名之辈,是他们的小迷弟,因为见到偶像而激动得忘乎所以。无论是他回忆十六岁时第一次见到奥地利诗人霍夫曼斯塔尔,还是五十多岁在伦敦流亡其间见到弗洛伊德,甚或青年时第一次见罗丹,他对他们的赞美,都是毫无保留的。
他见罗丹时,罗丹将他带到工作室,然后自己忘我地投入工作,把他晾在一旁。而他完全没有想要显示存在感,便也在一旁忘我地看着罗丹工作几个小时后才回过神来。
二战时德国占领奥地利,犹太人被纳粹迫害,茨威格流亡到伦敦,在痛苦和焦灼中度日。他后来在伦敦见到八十多岁,风烛残年,同样因迫害而来到伦敦的弗洛伊德时,也是欣喜若狂,他将那一天形容为是“一生中很难忘的日子”,而那几个小时的会面令他“终生难忘”。
整部回忆录中提到的大人物中,最让我感动也是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罗曼•罗兰。这两个人一个是奥地利人,一个是法国人。他们在一战前建立友谊,一战中,两个国家成了敌对国。在整个世界仿佛都限入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所有文人都在为战争鼓与呼的时候,他们两个做为为数不多的“异类”,通过书信建立联系,相互鼓励和安慰,试图为促进两国之间几乎中断的文艺交流做共同努力。有次借着在中立国瑞士举行的一个文化活动,茨威格见到了同在那里的罗兰。那次见面,对他们两个来说,都冒着很大的风险。因为战争期间,到处布满暗探,敌对国的成员见面,一不小心便会被认为“里通外国”。但他们甘愿冒险,因为茨威格觉得:“这世界如此荒诞,但我们觉得我们没有义务去附和它。”
这本回忆录的时间线始于19世纪末,止于20世纪40年代,在读这本书之前,我大概只知道中华民族灾难深重,几百年来战乱频仍。世界大战,尤其一战,离我们太远,仿佛只是个名词。读完《昨日世界》才意识到,我们如今仰望的欧洲,在上个世纪上半叶,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很多城市几乎被夷为平地,那个时代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可能并不比在中国经历的痛苦少多少,尤其是从中世纪以来就被迫害的犹太人。
德法意英等欧洲主要国家,经历两次这样毁灭性的打击,竟然能迅速恢复,继工业革命以后再次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也实在是配得上“底蕴深厚”这样的赞誉。
这本书纪录了茨威格多年来四处游历的一些见闻和交友,我一直希望能看到他来中国,看到他对中国的印象。很可惜,他去了印度,去了苏联,就是没来中国。看来中国那时候的存在感确实有些低。唯一能激起我做为中国人一点点自豪感的是,他提到二战时几百万犹太人被驱离家园,上海是同意接受犹太难民的城市之一。
有一次听“故事FM”,一个生活在河南的犹太人女孩讲述身份认同,以及后来去耶路撒冷“认祖归宗”的故事,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中国有犹太人。
中国应该有很多人,各种民族,各种肤色,各种经历的。然而,很多因为小众,像同性恋一样隐匿在14亿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中,不被主流关注,甚至不允许被关注,渐渐地被融合,被同化,最终消失无踪,像没存在过一样。
《昨日世界》对我来讲最大的价值是它的“历史”价值。茨威格虽然个犹太人,二战时和整个民族一起遭到迫害,但他毕竟身处欧洲的上层,早年游历四方,可以以一个较为宏观的视角,带我们进入那个特殊的年代。然而,这本书让我有些不满足的地方,也在于此。作为一部跨越半个世纪的“回忆录”,《昨日世界》涉及到他和各种各样的文学家、艺术家、音乐家、思想家、雕塑家,甚至政治家的交往经历,但对于普通人的生活,却鲜少提及。如果说,因为身处上流社会,和普通人交集有限还可以说得过去的话,他对于家人也一笔带过,就很让人不能理解。
前半部看他怀念一战前奥地利甚至整个欧洲的文艺荣光,看他对那些“大师”们毫不吝惜的赞美之情,我甚至猜测他是不是同性恋。直到后来提起妻子,才知道猜测有误。这个提起,就真的是提起,没有任何细节。他一生结婚两次,第一次婚姻的结束,应该在一战和二战之间,他在书里写到了欧洲的艰难复兴,写到他渐次恢复的希望,但对离婚一事,绝口未提。直到二战开始,才提到他的第二次婚姻。比之第一任妻子,第二任在他的回忆录里,也不过是多当了两次背景板而已。
不知道是不是作家有意为之,也许他只想写一本纯粹的情书,献给业已故去的精神家园—欧洲,而不是身处其中的普通人,包括家人。如果是这样,那他的冷静会让我觉得可怕。要知道,他在写完这本书仅仅几个月后,便在下一个流亡地巴西的彼得罗波利斯和妻子双双服毒自杀。
一个人在绝望之中回望人生的时候,怎么能控制得了自己去讲述那些和自己的生活最紧密相关的人和事呢?我不懂,我想我不行。
让茨威格最终走上绝路的,是报纸上一则关于新加坡沦陷、英军大败的新闻,那是1942年2月的一天。那个新闻让他觉得,法西斯主义在全世界已经势不可当,他魂牵梦萦的故乡奥地利,再也回不去了。
而这则新闻,让我想起地球另一边的郁达夫。中国的抗日战争开始后一年,郁达夫移居新加坡。新加坡沦陷之后,他避难去往印尼的苏门答腊,一年后客死异乡。
做为一个“过来人”,想到他们,觉得十分可惜,坚持两三年,战争便会结束,梦中的故乡也终能到达。可惜,他们都没能等到。
茨威格笔下两次动乱年代的社会面貌,似曾相识。一战期间,他几乎失去所有朋友,因为所有人都陷入群体情绪中,为争取战争胜利煽风点火。而他自己,决心“不为战争写一首颂歌,不诋毁任何一个敌国”。二战前,希特勒焚书、使用酷刑,曾经风头无俩的茨威格作品,在德国变成禁书。
但在“封禁”这件事上,我却觉得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恶魔希特勒,手腕和当下世界的某些国家相比(对,我说的就是朝鲜),简直温柔得可爱。
希特勒上台伊始,茨威格和理查•施特劳斯正在合作一部歌剧《沉默的女人》。那之后不久,希特勒下令全德国不能上演非雅利安人创作的作品,但他们那时候又急于笼络文化名人,尤其是德国当时最伟大的音乐家施特劳斯,极力坚持要和茨威格合作。这件事搞得纳粹非常头疼,几个月来犹豫不决,最后还是希特勒本人屈服于施特劳斯,同意戏剧特例上演。虽然最后《沉默的女人》在德国只演了二幕就被紧急叫停,但这个曲折的过程让我觉得,希特勒好像毕竟还是顾一点脸面。若在朝鲜,你想想,哪里需要有什么犹豫,哪里需要金三胖亲自为难。说封杀你,便雷霆万钧,没灭你九族,便该吾皇万岁了。
《昨日世界》是我读的茨威格第一部作品,在这本回忆录里,他曾不止一次说起,他的人生信条,便是不和政治扯上关系。然而,政治最终还是扯上了他。我其实对于他的表述深表怀疑,一个社会人,要和政治撇清已经是件很难的事,遑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但我还没读他的其他作品,无法证实我的这种怀疑。也许,他对于政治的理解和我不同。在我的观念里,政治便是众人之事,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避无可避。而且,就算闪避,也是另一种政治表达。
沈从文的作品,也很少涉及明面上的“政治”。想到茨威格的结局,我也会联想到沈从文《一个天才的通信》里天才的结局:
在灯下我做了呆事了,第三次才有血出来。……但是,先生,一切完了,一个平常的结局。灯芯一捻,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