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景》:打開這幻象或約定你為何需要逃走
風景有兩種:一種是在舒適的豪宅內透過落地玻璃看山看海,是固定的;一種是在路上或海上移動中的景物,是變換的。
許雅舒以社會運動為題材的《風景》所展現的主要是後者,並質疑前者。在移動中的景觀不單是空間上的轉換,也意味著時間的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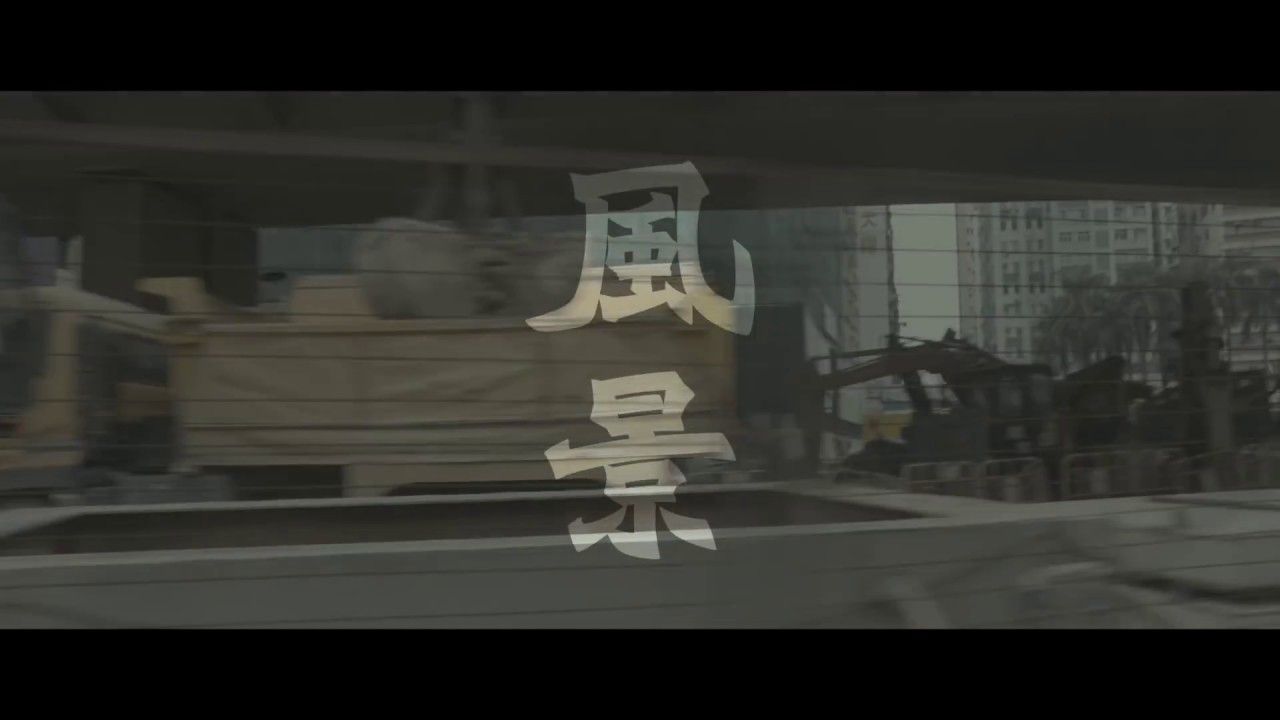
香港社運史詩
電影開始,攝影機緊隨著男主角太初在西灣河鬧市中行走,映著他的背部,經過政治集會的人群和東區裁判法院,直至他看到因示威而被判刑的女友阿宜的囚車駛過。
電影結束時,攝影機的位置在太初的面前,彷彿引領著他,從滿佈熟睡的帳篷的干諾道中穿過畢打街隧道鑽出來,聽到兩旁塞滿上班族的汽車引擎和響號。太初這樣走過了三年之間包括兩次「佔領中環」運動的歷程,越來越挫敗、越來越迷茫。
佔領運動時發生過多次衝突的龍和道就是以前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所在的位置,地方變了、名字變了,但名為「發展」的巨輪強行輾壓和改造城市的面貌的運動卻一直沒變。
人們不想風景轉,心境也不想轉,但不得不轉,若非隨著巨輪而轉動,便只能嘗試各種反抗的運動。
《風景》可說是2019年前的社運史詩,除了兩次「佔領中環」,戲中提及的社運事件包括保衛皇后碼頭、七一遊行、六四燭光晚會,以及反國教抗爭等等,讓虛構的人物出現在真實的運動場景裡,虛實揉合的手法與其說是令故事更加寫實,不如說是提醒觀眾「真實常態」之虛幻。
結局太初走過的畢打街隧道就如時光隧道,從靜謐的抗爭現場的這一端走進去,另一端走出來卻是城市機器運作的喧鬧,彷彿平行時空,現實本身便帶有魔幻感。

三種現實風景
《風景》人物眾多,分三大主線:一是太初和女友阿宜,以及阿宜的母親阿雲的故事。阿雲的丈夫早已出走,阿宜坐牢後剩下她獨守冰冷的中產家居,窗外是迷茫的風景。
二是新界鼓油廠的傳人格言和他前女友阿敏的故事。富至三代的格言售賣祖業和家族史,深感空虛迷茫而參與了第一次佔領中環,與相信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的青年(包括太初)相處了一段日子,最後他並無對社會體制的真正反省,只是往「包裝轉型」著手重整業務與人生。

追求理想的記者阿敏則在舊社區中訪問各行各業的長者(這部份是紀實的),大多是半世紀前從中國大陸過來尋求安穩生活的典型「獅子山下」式故事。格言和阿敏各自選擇了「生活態度」和「社會公義」兩種方向,使他們縱能互相了解,卻不可能復合。
第三條線是內地新移民李彌和她的男友阿彥,暫住在太初那快被遷拆重建的單位中的房間裡。阿彥是太初的好友與同事,不理會社會大事,只管吃喝性愛。他不了解李彌(因此註定失去她),不知道她多麼努力去融入「香港人」的身份而否定本來的身份。
以上的人物關係細節都可以歸納為一種尋求安頓卻永遠無法安頓的漂泊狀態,總是格格不入、時空錯置。

拆毁日常的不是社運,是發展
戲中訪問老一輩南來移民的經歷,他們的口述史彷彿是「香港人只要認真工作便能安居樂業」的見證。
其實不然,太初的母親也是「獅子山下」的一代,這類人出身基層,努力賺錢置業,當了業主還是難逃拆遷,因為資本必須流動才能增值,掌握權力和資本的人便藉著「重建」拆毁「安居樂業」的美夢。
阿宜出身中產,其父母「不安於室」更顯出的「中產家庭夢」之虛幻。香港是個永不歇息的圍城,一波一波的人要進來,一波一波的人要移民。阿宜那個階層或可賣樓出走,太初那個階層則以「還留著以前的公屋單位」為幸運。
但住在天橋底的人則只能在狹縫和陰影中偷生。是的,生存還要說成「偷」,因為他們並無依照城市的規矩去使用空間。

許雅舒借用橋底作重現社運場景便特別有意思。屢戰屢敗的社會運動常常被指控為破壞秩序,也就是阻礙了城市機器平常的時空運作,而人們甘於成為機器的一部份,正是以「安居樂業」的盼望為代價。
兩次「佔領」運動馬路等公共空間的既定用途,是以動制動,反過來提醒人們這個社會跟本就不可能「安頓」下來,不論你是哪個世代、哪個階層。
《風景》中的空間,包括小島、渡輪、酒店、社運現場、板間房、唐樓、排檔、新界的村落和農田……皆是無法穩定不變的景物,人在其中無法安穩。既然格格不入和時空錯置在是這個城市的本相,佔領運動其實是正面的迎向與擁抱之--何不主動一點去想像這個城市應該怎樣運動起來才好?何不超前地試驗一下該讓這個城市轉換出怎樣的風景才好?
[原載於《時代論壇》154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