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誰?關係本體論中的“自我” | 圍爐· 冬日文藝

兩個月前,我讀到了三聯生活周刊的一篇文章,題目為《中國關係裡的“我是誰”》。文章探索了西方“自我”概念和中國“自我”概念的不同,作者認為西方的“自我”是一個獨立的存在,而中國的“自我”是關係性的存在——在中國,人總是關係的附屬,比如作為子女、下屬、妻子、父母,並因為缺乏時間去思考、探索自己,而沒有辦法變成一個獨立的“自我”。這導致的一重結果即是自我物化——人們不重視自己的情緒,只把自己當成工具(達成某一目的的手段),然後把自我的價值寄託在外界對自己的估值和評價上。
不過我想指出的是,在大概兩百年前的時候,西方哲學就已經有了對“自我”關係性(relationality)的反思,繼而發展出了一種叫做關係本體論(relational ontology)的哲學。其中一位代表性的哲學家就是馬丁·布伯,他寫出了在西方哲學以及宗教研究上都非常具有影響力的書,如《我和你》、《人與人》等。這繼而影響了一系現象學家以及存在主義哲學家對於關係性,尤其是自我與祂人的關係的反思,哲學家中伊曼紐爾·列維納斯就是深受布伯影響的人之一。在列維納斯之後,很多當代哲學家如朱迪斯·巴特勒、麗薩·岡瑟也在她們各自的作品中探討了“關係性”的“自我”。在這篇文章中,我將沿著關係本體論在哲學中的發展思路,介紹馬丁·布伯以及上文提到的另外三位哲學家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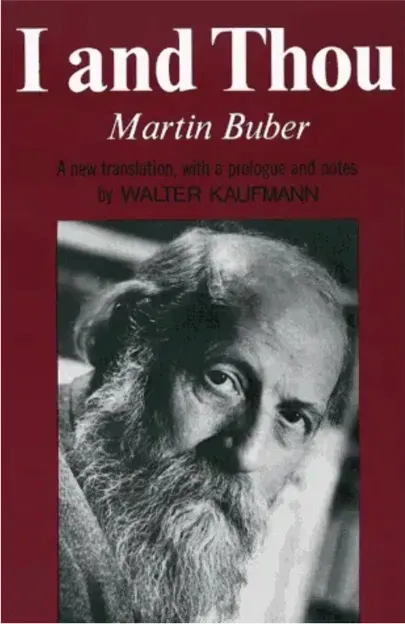
1
什麼是關係本體論
假如要探究什麼是關係本體論,則需要先探討本體論是什麼。一言以蔽之,本體論研究的是“存在”的本質,它試圖解釋什麼是終極真實的。一些問題包括:什麼是存在?存在的事物有什麼普遍特徵?在終極現實(the ultimate reality)中什麼仍然存在?
西方哲學中的本體論曾經主要是實體本體論。實體並不是指一個可以觸碰到的、非空心的物體,而是意味著一個獨立的、不依附於其它任何事物也能繼續存在的事物。換句話說,西方哲學家們曾經認為世界的終極現實是由一些獨立的、脫離了任何關係的實體所構成的。
關係本體論則認為關係先於實體,它認為一個物體不能脫離它與其環境的關係而獨立存在,任何物體都被自己的情境(context)或者關係所構成。或許更形象的比喻是,想像一些點和線,那麼我們可以把關係本體論看作是認為事物(包括人類)是網絡中的一個點,作為無數條線(關係)的交叉點而存在,也就是說,點的存在是由不同線條的交叉和移動形成的,如果沒有那些線的話就不會有我這個交點。
非關係本體論,比如實體本體論,則認為是點(實體)先存在的,然後那些不同的、已經存在的點被連接起來,再形成網絡——形成線(關係);線條或關係在實體或點的存在之後出現。因此,點的存在不再以其關係性為條件,而是變成了產生關係的前提;實體本體論有時候會更進一步地認為,每一種關係——無論是人與物的關係(如認知),還是物與另一物的關係,或是人與人的關係——都是對事物的扭曲。
2
祂心問題
在西方哲學中,一個古老的問題是祂心問題,即我們相信自己具有意識,可是我們如何知道祂人也具有意識——比如,會不會祂人只是有著表面和我類似的行為,但實際上卻是沒有意識的空殼殭屍?
行為主義給出了一種回答:人的行為就是人的心理狀態或者心智本身。當我們說一個人感受到痛苦,“痛苦”這一心理狀態並不是什麼神秘、內在的私人情感,而就是此人的行為——比如皺眉、抽噎、呻吟、哀嚎,或者訴說“我很痛”。因此當祂人展現出任何相關行為的時候,我們就有理由相信祂人具有相關的心理狀態或者意識。
然而,包括馬丁·布伯在內的這一派提出關係本體論的哲學家則給出了另外的回答:祂們認為祂心問題從一開始就不存在。
幾百年前,笛卡爾提出“我思”,將“自我”定義為一個“思考的事物”,以“我”的思索來確定我的主體性和“我”存在的確定性,因此才會出現主體(我)和客體(“我”以外的祂人、世界)之間的對立,因此出現“祂心問題” (對祂人是否具有主體性或者意識的懷疑)。
然而在馬丁·布伯看來,關係的存在先於自我的存在,並且自我與世界也並不是對立的關係,而是互相構成和成就。人無法脫離其關係存在,人的“自我”從初始就已經和祂人的存在糾纏不休了,也因而不存在部分哲學理論裡預設的原子化的、獨立的、自給自足的、分離的個體自我,也自然不存在一個跟祂人完全分離的自我、或者與自我完全分離的祂人。換句話說,在關係本體論看來,人是因為祂人的存在才產生了意識。
3
我-你和我-它:
關係世界和經驗世界
在《我和你》中,布伯區分了兩種生存模式,這兩種生存模式可以被用兩個原初詞概括:我-你和我-它。布伯認為前者屬於關係世界,後者屬於經驗世界。在他看來,我-它本質上不是一種真正的關係,它只是一種經驗和利用,是一種對對方的物化。他寫道,“我注意到了什麼,我感覺到了什麼,我想到了什麼,我想要什麼,我覺察到了什麼,我在思考什麼”(p.54)屬於典型的"我-它"經驗世界。在這裡,“我”只自我,而這個“什麼”是一個被主體思考、描述、體驗和期待的對象,是一個"它"。他還寫道,“那些體驗者並不參與世界。因為體驗是'在他們身上',而不是在他們和世界之間。世界不參與體驗者的體驗。它允許自己被體驗,但它並不關心,也並沒有任何貢獻,也沒有任何事情發生在它身上”(p.56)。
也就是說,“我-它” 經驗世界是單方向的利用,“我”去使用這個世界,把它當作一個工具或者東西;相對地,在我-你關係世界中,當"我"和"你"相遇時, "我-你"的關係出現了,它意味著一種相互的尊重,一種真正的連結,而不是單方向的利用和物化。
比如,如果我把一個人只當作功能性的存在——我只有需要人一起吃飯,或者需要人幹活,或者需要一個隨便什麼對象聽我傾訴的時候會想起祂——然後當我跟這個人相處的時候,想的只是如何能從這個人身上榨取最大的價值,那麼我們的關係就注定只是“我-它”。那麼,什麼樣的關係是“我-你”關係呢?“我-你”關係意味著在我眼裡,對方是一個獨特的、具體的人。對方不是或者不只是功能性的,也因此無法替代。
“我-你”關係中最重要也最困難的是去接受這個過程中的不確定性,也就是知道對方不是一個被我掌控,或者應該被我掌控的對象。比如,當我問出一個問題、發出一個邀約的時候,當我展露出我脆弱的一面的時候,我是無法判斷對方的回應的。在聊天過程中,如果對方分享了一段自己的經歷,我是永遠無法說“啊我經歷過一模一樣的事”或者“我有完全一樣的體驗”,因為作為具體的個體,我們的經歷無法被總體化、被還原成完全一樣的東西。在“我-你”關係中,“我”可能會覺得不安、脆弱,甚至感到危險,但是這種脆弱和不確定性是“我-你”關係中的一個固有部分。
我-你中的“我”與我-它中的“我”也是不同的。正如布伯所說,經驗世界中的"我"是一個單向的、一維的東西,而"我-你”的關係是一個互惠的、相互的關係,啟動了“我”的生命的其他維度。在一個"我-它"的經驗世界裡,"我"永遠不會是一個完整的存在,因為在一個"我-它"的經驗世界中,"我"從來沒有被"它"當作"你"來稱呼,在“我”把對方物化的同時也把自己物化了。而在我-你關係世界中, 在用“你”來稱呼對方的同時,對方也以“你”來回應稱呼“我” (ie, 我也被認真地當成“你”來對待、沒有被物化為工具),所以我-你中的“我”是多了個存在維度,或者更圓滿的“我”。
布伯顯然更傾向於我-你關係,但在他的敘述中,我-它和我-你不完全是對立的,它們也互相需要。正如布伯所說,"沒有它,人就無法生存"(p.85)。想像一下,如果沒有對世界的感知、相信、渴望、想像和記憶,簡而言之,沒有“經驗”我們怎麼可能形成關係?因此,每一個"我-你"關係都是雙重的,它同時是"我-你"關係和"我-它"經驗。所以,與其說我-它和我-你是對立,不如說它們是不同維度(也就是布伯所說的“存在的不同模式”),一個人像潮水一樣從一個我-它世界湧向另一個我-你世界,再湧到我-它世界,因為我-你關係總是危險、不安、短暫、難得的。布伯的預測幾乎是準確而悲觀的:"世界上的每一個'你'都至少要一次又一次地進入'它'的狀態"(p.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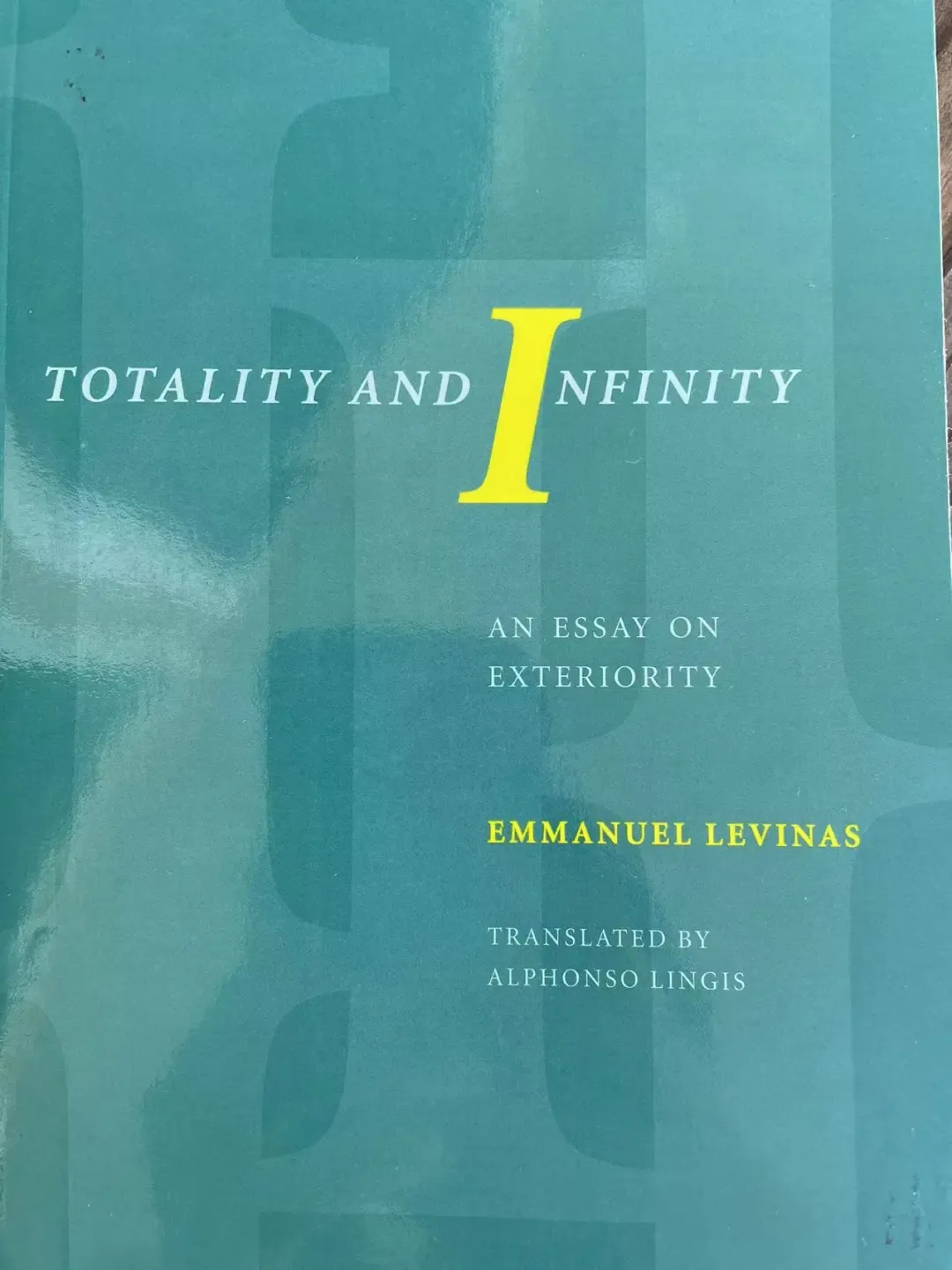
4
關係性的自我和祂者
列維納斯則在布伯的基礎上更推進了一步。在《論逃避》、《總體與無限》等作品裡,他探討了人的主體性是怎麼產生:正是由於祂者的呼喚和我們對祂者的無限責任,主體性才得以出現。
幾個世紀後,朱迪斯·巴特勒也在《Giving an Account of Oneself》裡談到主體性與社會規範(social norms)的關係。她認為,主體(比如一個“我”的存在、一個個體)和社會規範(比如道德準則)並不是先各自存在,再產生關聯;相反,主體本身是被道德規範制約並且構建的。她提到,談論一個主體如何去適應社會規範是一種思路,但去討論主體本身如何由社會規範而被構建出來則是另一種思路,她想探討的是第二種。在第一種情況下,我們預設規範(norms)在主體的外部,與主體保持著一定的距離,而主體的任務是找到一種利用這些規範、接受它們、與它們建立聯繫的方式。但是,在巴特勒看來,規範本身也預先決定了誰將成為以及誰無法成為主體,換句話說,她更想探討的是社會規範在主體的構建中的運作和作用;這也可以說是一種我-你的認識論框架,其中,自我被世界和關係創造和塑造。
社會規範總是在我們存在之前業已存在,並已經以我們無法掌控的方式塑造了我們的主體性,因此巴特勒認為一些人所想像的透明的、理性的、連續的倫理主體是一種不可能的建構——我們總是只能部分地了解自己。可是,如果連對自己,我們都是部分不透明的,那我們要如何對自己的行為負倫理上的責任?一個要求我們對不完全自知的行為負責的倫理體系難道不是一種暴力嗎?我們要如何重新構想主體、知識、規範、行為和倫理責任之間的關係?巴特勒在《Giving an Account of Oneself》的後幾章深入討論了這些問題,她解開了幾百年來倫理責任與完全的自治性(autonomy)之間的關係,而延續了列維納斯的倫理體系,把責任(responsibility)與回應(response)相關聯。責任(Responsibility)被解釋為在祂者的召喚和命令下對祂者的回應(Response),而一個人需要回應或者負責的,不只是那些由於自己的錯誤行為而造成的後果,而也包括了在自己能力範圍之外的事物,因為人與世界與祂者有著無限關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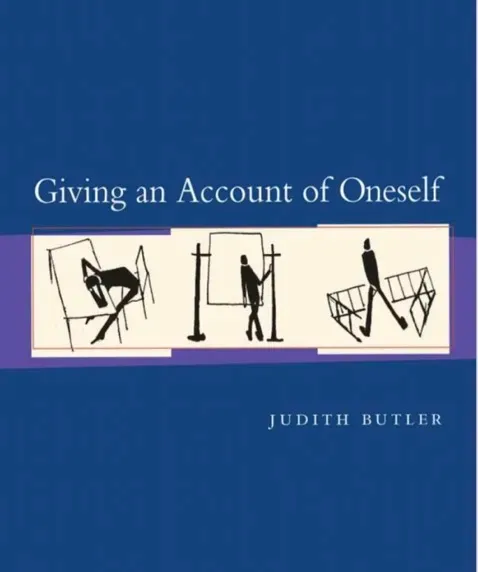
另一本書《祂者的禮物》(The Gift of the Other)中,另一位當代哲學家麗薩·岡瑟也引用列維納斯的哲學理論,探討出生倫理、責任和主體性的關聯。與巴特勒類似,她也提出,我們對於人生中最重大的事之一——出生——是無法掌控的,因此一個自給自足、自治的主體在最初就是一個幻象。而與馬丁·布伯強調的我-你關係中的相互、互惠不同,在列維納斯和岡瑟的哲學裡,倫理涉及一種非對稱的、單方向、無條件的、“我”對於祂者的回應(Response)以及無限責任(Responsibility);在這種回應中,“自我”自給自足、獨立不依的幻像被干擾和打破,“我”發現了自己跟祂者最本源的關係性以及無法斬斷的聯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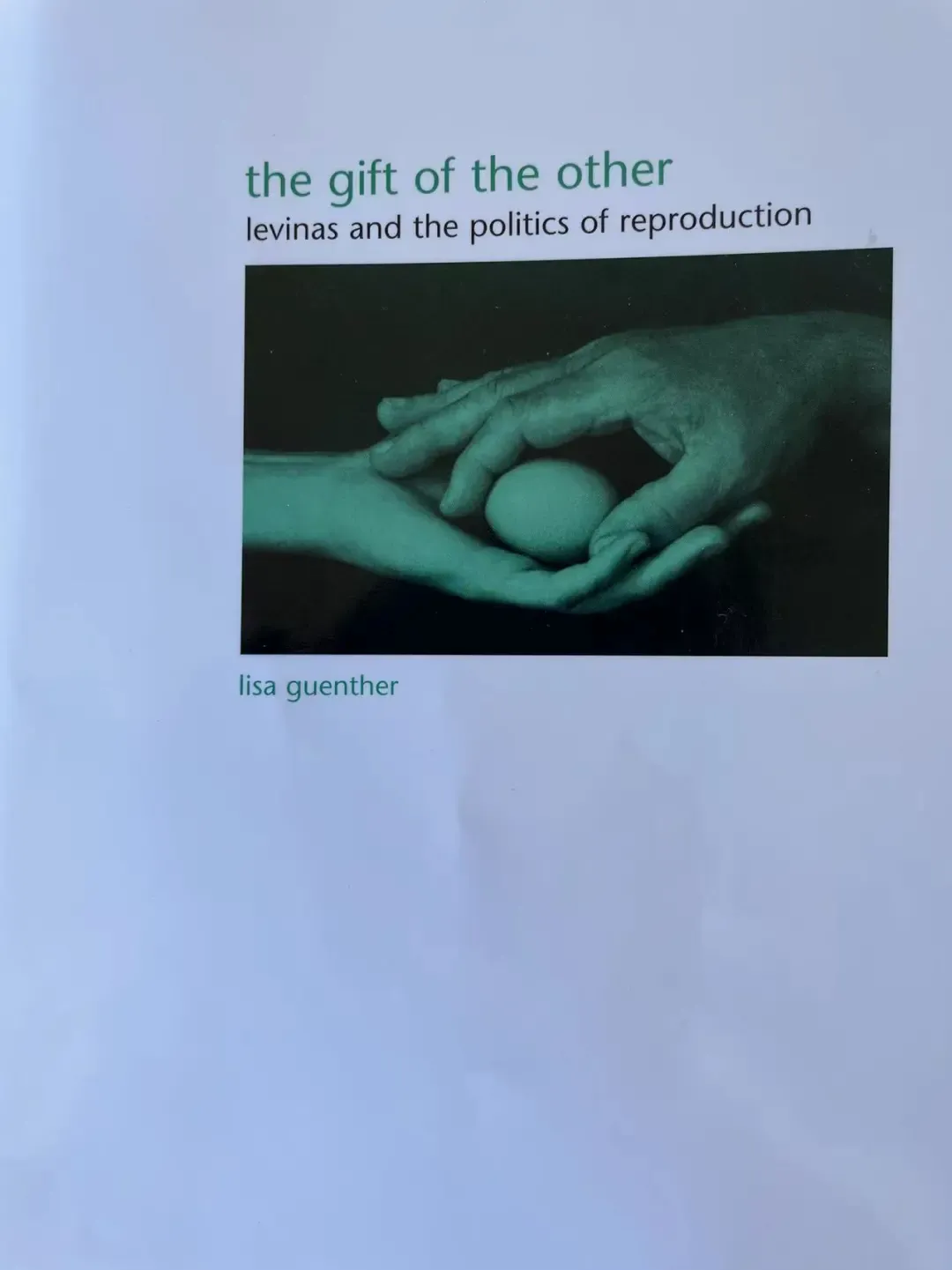
5
人是否可以跟自己
形成我-你關係?
在這篇文章的最後,我希望回到開篇提到的那篇三聯上的《中國關係裡的“我是誰”》的文章,並更具體地討論上文提到的關係本體論的一些可能的回應。
文章的作者寫到,“當一個人明確知道,他脫離了所處的家庭、社會群體、社會階層和定義時,他是誰,這就是一個獨立的“自我”了。如果一個人發展出獨立的“自我”,處理親密關係也好,其他問題也好,都會迎刃而解。但當下的中國人沒有從關係性的“自我”,發展成西方意義上的成年人具備的獨立'自我'。”
“由於自我物化是把自己當成工具,讓人完全脫離了自己是一個有生命的存在這件事情,於是,人就不會重視自己的情緒、社會和生理需要,因為'工具不需要去在乎它的感受'。不僅如此,一旦把自己看成物品,而不是擁有獨一無二屬性的存在,他自身的價值感就不穩定或者特別低。因為他把自己的價值跟外界對物件的估值等同了,而外界對物件的估值是不可控或者變化的。” 我覺得這兩段文字都非常有意思。我的觀感也有點複雜,既有贊同的部分,又有不贊同的部分。
我贊同的部分在於作者所說的人不要去自我物化,把自己當成工具和物品。換言之,我覺得一個人也要努力嘗試和自己形成我-你的關係,以動態的視角去看待自己、探索自己、與自己溝通。
另一方面我覺得發現自己的價值寄託在外界對自己的估值和評價上沒什麼好羞愧的。事實上,人就是這樣的——依賴祂人和被依賴著。一個完全獨立、自給自足的“自我”,一個全然獨立於祂人判斷的自我判斷,或許本身就是個幻象。曾經我為此掙扎著——每次因為其祂人的批評或褒獎而情緒波動的時候,我都會感到羞愧,因為我沒有做到獨立自治、自給自足。但是現在我接受了這一點,我接受了我們本來就是在不斷地影響著祂人,並被祂人影響著——而或許,這種接受也不妨被視為一種勇氣。類似地,我覺得作者所說“當一個人明確知道,他脫離了所處的家庭、社會群體、社會階層的定義時,他是誰,這就是一個獨立的'自我'了”,這也是一個偽命題。人處在關係之中,處在家庭、社會群體、社會階層之中並被其定義和塑造,或許可以被視為是人之為人最根本的境況。
但另一方面,雖然人不可能脫離全部的社會關係,但人的靈活性和特殊性在於祂的一生中能同時處於多種關係之中,這些不同的關係塑造了一個人的獨特性,就像是一張交織的網裡一個獨一無二的點。正如黑塞在《德米安》中所說:“如果我們並非獨一無二的人,如果我們真能用槍砲任意將他人從世上抹殺,那麼講故事將是多此一舉。然而人並非僅僅作為個人而存在,他同時也是獨一無二的特殊個體,永遠是一個關鍵而奇妙的點,在這個點上,世界的萬千現象縱橫交錯,充滿不可重複的偶然,因此每一個人的故事都是重要的,永恆的,神聖的。”
作為世界的萬千現象、無數關係和社會情境縱橫交錯而形成的點,關係本身的存在並不是人自我物化的原因,只有當人被禁錮於某種關係或某種身份之中、無法靈活切換到另一種關係或者身份,也無法有不被這一種關係或者身份定義的行為的時候,才會導致自我物化以及更嚴重的問題。也就是說,只有當一個關係或者一個身份吞噬了一個人的所有其它的關係和身份的時候,當一個人把自己還原到某一個特質上、並且被唯一一種關係來定義時,問題才出現了;而正常情況下,人們總是靈活地利用自己的其它身份或者關係來幫助調整自己在某一個關係裡的行為和相處方式。
參考文獻: Buber, Martin and Kaufmann, Walter (ed). I and Thou. New York: Scribner, 1970. Butler, Judith. Giving an Account of Oneself.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5. Guenther, Lisa. The Gift of the Other: Levinas and the Politics of Reproducti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6. Levinas, Emmanuel. On escap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Lévinas, Emmanuel. Totality and Infinity: An Essay On Exteriority. Pittsburgh: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1969. 莊曉丹、楊璐,中國關係裡的“我是誰”,三聯生活周刊公眾號,2021.10.11,https://mp.weixin.qq.com/s/NozTujX2W34esIjz4-TOPw 赫爾曼·黑塞,德米安,天津人民出版社,2020.
文| 劉可萱
圖| 來自網絡
審稿人| 言冰天天
WeChat編輯| 張宇軒
Matters編輯|Francis
圍爐(ID:weilu_flame)

文中圖片未經同意,請勿用作其他用途
歡迎您在文章下方評論,與圍爐團隊和其他讀者交流討論
欲了解圍爐、閱讀更多文章,請關注本公眾號並在公眾號頁麵點擊相應菜單欄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