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劇如何批判社會文化: Comedy and Cultural Critique in American Film 讀書報告
喜劇電影給很多人的印象都是娛樂性為主,和其他電影類型比較,有深度的喜劇比較少。雖然人們在電影史上總能找到一些富有藝術性和和批判性的「喜劇」,但他們所指的往往在於電影的非喜劇部份——尤其是那些有催淚情節的悲喜劇——所以其實是那些電影的戲劇內容甚或是悲劇內容令人感到有藝術深度。
問題是:除了敘事之外,喜劇設計(笑話或搞笑的噱頭)本身本身是否也有批判性或藝術性?抑或「有深度」的喜劇只能由淺薄胡鬧的gag和令人深思/感動的戲劇合拼而成?
學者Ryan Bishop的著作Comedy and Cultural Critique in American Film針對喜劇在電影的關鍵角色,指「電影本質上是喜劇的,喜劇本質上是電影的」,把喜劇和二十世紀現代性、視像科技與文化,以及美國的歷史和政治扣連起來。喜劇對電影的重要性在於,喜劇最能夠實現電影作為技術與文化的自反(self-reflexive)性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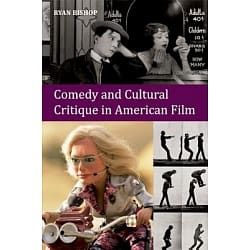
電影是機器,喜劇即故障
電影起源於工業機器時代,是一種影像複製的技術,再發展為一個娛樂產業。在二十世紀初期,兩位喜劇大師差利卓別靈和巴斯達基頓在電影的喜劇設計裡,反思工業化現代社會的機械性。攝影機和放映機等視像器材都是機器,電影生產和機械化的工業類同,整個社會都成了大機器。
初期電影反映了視像科技在文化政治中的位置,對影像的性質和視覺機械化有後設的反省。早期喜劇電影裡,物件或機器往往是主角勉力應付的對象,人要像機器一般對付這些自動機器。差利視工具為中性並抽離於人的事物,基頓則視機器為人的延伸。
差利在電影中投射身體感官的彈性,與機械重複生產的技術性對照。他的電影回應文化與媒體的機器產業化如何威脅人文主義,並作出最後抵抗。《摩登時代》是他對科技再生產(包括電影業)、機械化、自動化,以及人類作為主體的沉思:攝影機和電影機制如工廠機器生產,而他被卷進工廠機器的畫面,就像菲林/膠卷在攝影機/投影機中的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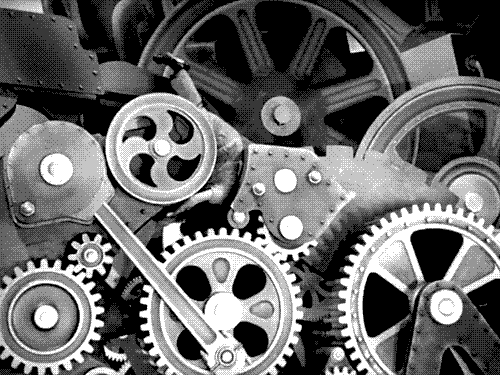
基頓在《福爾摩斯二世》則探討了現代人的生活和感知其實是媒介技術的產物。他不只反思工業,而是包括電影在內的視像科技整體。在戲裡,他飾演一個失戀的電影放映員,工作時在夢中進入了電影世界,帶來一段經典的場景轉換蒙太奇。
Bishop指出,那些不斷轉換的場景其實都指涉主角的愛情經歷,把英語中描述這些經歷的習語按字面義化成畫面。這就如日常溝通中的陳腔濫調或習語形塑了我們如何介入自身與世界,而電影的敘事及技術慣例也形塑我們的自我認知,兩者相輔相成。
基頓呈現了電影及現實互相影響的關係:人的知覺總是經過媒介的,包括我們對自己和對感官知覺本身的認知。我們是觀眾,也被電影「觀看」,如角色一般。知覺須藉物質或非物質的技術形成,使主體及媒介難分難解。
在機械複製時代,現代人是被工業塑造出來的,例如操作工廠機器的工人、被賦與慾望的消費者,以及被傳媒訓練出來的閱聽人。現代視覺文化與技術是這機械時代的一部份,而電影則是視覺媒介之一,統合了諸如攝影、小說、劇場表演等多種媒介技藝。電影是自反性在於,這種技術製造並訓練出其受眾——是電影自己教導觀眾如何「看電影」,在觀影活動中讓後者熟悉其奇觀效果,以及敘事的語法和邏輯。
基頓關注電影這種「心智技術」,電影的再生產技術也也為顛覆電影敘事慣例和藝術的機械複製模式提供了途徑。喜劇對工業技術的現代性而言,既是助力也是阻力。
喜劇電影的特色是破壞和擾亂,便先須有被破壞的對象,首當其衝的對象就是電影形式和敘事的慣例,這也是喜劇批判性的前設。觀眾因為對影像邏輯和產業機制習以為常而不自覺,喜劇的自反性批判便讓他們察覺到電影的虛構性質,呈現本來在機器背後操作的人手。

因為電影在視覺媒介和工業社會的關鍵角色,影像機器和現代世界的真實同構,前者作為後者的隱喻,喜劇的批判範圍便可以擴展至整個社會。作為文化批評的喜劇,往往突顯被壓逼者及其打破禮俗枷鎖的特性,來抗衡社會力量。
喜劇揭露的「超真實」
電影的本質是甚麼?對某一理論流派來說,電影是保存現實/寫實的技術。二十世紀至今,無所不在的影像文化維持了寫實藝術再現世界之力量,並使人們認為影像與真實之關係是理所當然。「寫實」即對再現對象不加修飾,只是紀錄其外在真實。然而寫實作為一種技術,其實同樣對其「紀錄」的對象有所加工和矯飾,雖然看來是直接明暸的再現。
在機器時代,肉眼所見已不是憑據,有圖/片才有真相。視像科技把肉眼看不到的現實呈現出來,探入更真更深的現實,改變了我們如何理解人類感官與自然世界的關係。認知現實成了技術問題,而非認識論的問題。視像科技影響了本體論和認識論,成為了知性探索的因和果。人類所認知及經驗的「現實」必須倚賴科技。
然而喜劇美學就是錯位、搞亂、破裂。影像紀錄本來以視像科技整合「現實」,但喜劇或戲仿模式以其不確定性、不可計算性和流動性擾亂了本來安穩可靠的「現實」。針對視覺機器的運作模式,喜劇提供了批判性的距離和後設視野,揭示在消費主義、視覺文化與市場推廣操作下,再現真實的技術性如何隱身於內容中,並由媒體及科技生成了現代社會的「人」:消費者。

意識形態的運作是一種技術,把社會文化建構變成「理所當然」的真實。電影也是意識形態機器的一部份,政治也是一種表演,而歷史記憶也倚靠著外部儲存的影音媒介。「真實」(Real)不是所謂社會的「客觀現實」,卻與人的慾望和想像結合,而擬像和實物也糾纏不清,繼而在不斷複製的生產模式下構築了「超真實」(hyperreal)的世界。工業社會不單生產具體的物件,也包括心智的、知識的對象;「常識」其實是意識形態,只是被視為理所當然。
喜劇則介入社會文化的建構,揭示意識形態的運作。其批判性在於擾亂這些「常識」和認知的慣性,突顯電影和其他視覺媒介如何構成這個「超真實」社會。這些拆解意識形態機器,挑戰人們認知習慣的時刻,就是引人發笑的時刻。
重點是,喜劇電影也是這龐雜機器的一部份,須從內部自我解構,而觀眾在笑聲的回音之中,會發現自身在這機器中的定位——甚至是被塑造出來的產品本身。喜劇既倚賴電影的技術和慣例,又必須擾亂其運作,成了一種「故障美學」。
喜劇也是認真的
其實喜劇是嚴肅的事情,因為它基於後者來發揮「搞笑」的作用,從而批評這些課題:從存在之困境,到社會價值及文化權力的建構性。然而喜劇對待嚴肅事物的手法往往離經叛道,因為其內核是對品味和禮節的逾矩——包括「甚麼可以用來說笑」本身——不能做的事情它偏要做。這樣產生了針對戰爭、死亡和其他社會禁忌的「黑色幽默」,不只涉及權力,也有關公眾感受的痛苦和暴力,開拓了「甚麼可以公開言說」之領域。
喜劇能舉重若輕地言說「不能說」之事,所以喜劇是危險的,也因此是重要的。

喜劇需要觀眾更主動的參與,因為其趣味往往來自創作人與觀眾之間的默契,需要觀眾自行意會笑話中的竅妙——那便是笑聲迸發的一刻。喜劇文本需要留白,讓觀眾自行詮釋其幽默之處,暗示而不說穿:我知你懂的,我也讓你知道「我知你懂的的」。在創作者、喜劇文本和觀眾之間共享著有關世界運作方式的共同認知與觸覺。
更重要的,是喜劇創作者「我在逗你笑」的自反意識,以及觀眾對此的覺察,使喜劇溝通成為可能。
戲仿是一種常見的喜劇形式,依賴創作者及觀眾對玩笑對象的共同認知。戲仿(Parody)的對象是另一個文本,是主曲/主文本/(-ode)的外部輔助或寄生(para-)。戲仿對主文本的作用是偏離、倒轉或誇張激化致使其失效。戲仿和主文本是既異且同,「仿」即有所重複,亦有修改顛覆以「戲」之。

類型電影由敘事和形式慣例構成,累積成經典,戲仿針對這些慣例來開玩笑,自成一種類型,可說是反經典的經典,反類型的類型。然而因為戲仿須倚賴慣例或經典來產生作用,引起一個有關其批判性的問題:究竟戲仿是顛覆還是重申主文本的權威?其顛覆是否總是暫時的?戲仿同時鞏固及挑戰電影敘事的類型,而觀眾先要懂類型慣例才懂得笑,也延續了觀眾對類型慣例的認知。
另一種喜劇形式是諷刺,有教化的清晰意圖。被諷刺者位於文本或美學形式之外,有別於針對其他文本的戲仿。諷刺喜劇的批判性暗藏著改變社會或文化的意圖,假設並倚賴人們在現實世界帶來改變的能動性。然而諷刺喜劇的效果總是模棱兩可,因為它倚賴人的能動性,但這種能動性又繫於電影操作的技術性和機械性。
因為喜劇創作者、文本觀眾全都在一個機械性的媒介社會中,生產諷刺電影的條件同時限制了其帶來改變的效力。若社會常態及秩序以禁忌來維持,諷刺喜劇往往是最危險的,因為它往往透過逾越禁忌來諷刺社會秩序。
但諷刺也也陷入一個悖論:挑戰禁忌即表達「不能言說者」,但一說了就不再是「不可說」。因為真的「不可說者」永遠都「不可說」。即使諷刺中有例外的言說,往往只是輕碰紅線一下,於是其「不可說」成了一種對逾矩的懷舊或祈求,其政治能動性非常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