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馬基雅維利到馬克龍(上):「出言不遜」背後的選戰考量
迄今已經持續兩年的新冠疫情,在2021-2022年交替之際不僅沒有逐漸平息,反而出現劇烈震盪的態勢。奧密克戎變異毒株導致全球多地再度進入疫情「海嘯」。儘管有樂觀聲音認為,高傳染性、低致病性的奧密克戎毒株,事實上可能將以較小代價推進群體免疫的實現。但這種前瞻尚未得到普遍性確認。疫情的自然走勢和不同國家的防疫手段如何互動,仍然值得下一步密切關注。
公共衞生危機的持久化,也在全球範圍內導致社會危機的激化,不同領域的結構性矛盾或被引爆、或被進一步深化。尤其是,當這場危機越是延續,它同選舉政治的常規週期便越能產生共振。在東歐和南美,疫情期間都出現了投票箱導致政府更迭的事例。
即將於2022年4月舉行的法國總統大選,同樣不可避免地難以脱離這一趨勢。儘管和購買力、安全、移民、就業、生態等話題相比,疫情話題並沒有在此次選戰中佔據絕對主導地位。但某種意義上仍然可以說,即將於80天後登場的這次選舉,本身就是在疫情風暴襲擊後的廢墟上進行的;這片廢墟,將是所有選戰議題的布景。
在這種背景下,今年1月初馬克龍針對抗拒接種者的一次強烈批評,也被順理成章地納入到選戰的框架下被加以審視。但這次「出言不遜」,與其說是一次選戰動作,不如說暴露出疫情以來、甚至是整個總統任期以來社會心態上的痼疾。防疫措施和疫苗接種的抗拒者,究竟是回歸到「自由」的真諦、保守着「自由」的內核,還是一群「被寵壞的孩子」在肆意驕縱?五百年前的意大利政治理論家馬基雅維利(Machiavelli),或許能為上述問題帶來某些啟示。

馬克龍的「出言不遜」
自從2020年底展開疫苗接種工作之後,經歷初期的短暫混亂與磨合,法國的疫苗覆蓋率逐步提升,如今(一月下旬)兩劑接種率已經達到91%。然而近幾個月來,接種增長勢頭已經逐漸衰減。據統計,到2022年初,在12歲以上群體中仍有約500萬人尚未接種疫苗,其中免疫低下群體(癌症治療、器官移植等)和不宜接種者約佔50萬,其餘則是對接種疫苗持抗拒態度的人群。
換句話說,如今法國的疫苗接種局面是:想打且能打疫苗的人基本都已經打了,剩下的便是出於各種客觀原因無法接種、或者出於主觀原因抗拒接種的人。
在這種背景下,法國政府將原有的「新冠通行證」升級為「疫苗通行證」,即大多數公眾場合將只承認疫苗接種證明和染疫康復證明,此前未接種者「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臨時篩檢陰性證明,將不被承認。政府試圖以此來「擠壓」這個群體,迫使他們接種疫苗。而這一升級措施,也不出意料地激起相關群體的強烈抵制。
1月4日,馬克龍在同《巴黎人報》讀者對話時,對抗拒接種疫苗者發起猛烈批評:
「我們對未接種疫苗者施加壓力、儘可能地限制他們從事社會生活的各種活動……持抗拒態度的是很小一部分人。對這些人,我們怎麼減少其數量呢?我們用進一步惹他們不爽(emmerder)的方式。就我自己來說,我不願意讓法國人不爽。我整天責備那些讓法國人寸步難行的行政管理手續。但對於不接種疫苗者,我很想讓他們不爽……我不會把他們投入監獄,我不會強制他們去接種。因此,必須得對他們說:從1月15日開始(事實上相關法案比原定日期推遲通過),你們不能去餐館,不能去喝酒,不能去喝咖啡,不能去劇院,不能去電影院……」
馬克龍用的emmerder一詞,在日常法語中頗為常見,這算不上一句髒話,卻也難登大雅之堂。而如何翻譯,卻成了各國媒體的一個難題。它的名詞詞根merde意為糞便,動詞則用來形容讓人產生一種彷彿被狗屎沾身的煩擾和惱怒,也正因此,它在外語中很難找到具有同樣不雅意味的對應表達,中文報導中有「惹惱」「難受」「激怒」「不好過」等各種譯法,但都難以到位,《紐約時報》等部分英文媒體譯為piss off,雖然並不嚴格對應,卻頗有幾分「下三路」的傳神。
在發表上述言論三天後,馬克龍在與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共同主持的新聞發布會上,再次強硬表態稱,他對此前的爭議表態「完全」承擔責任,他作為總統,面對兇猛疫情「有責任拉響警報」,並且指出,對未接種疫苗者施加限制,這是一個遍及全歐的「運動」,言外之意是,這並不是他作為法國總統的一意孤行,而是整個歐洲的普遍性潮流。

人氣崩塌的轉折點?並非如此
馬克龍在一場精心安排的媒體活動中使用該詞,迅速被媒體解讀為一種有意的「挑釁」姿態。尤其是他對於是否正式投身總統大選,仍然刻意維持一種模糊狀態(在同一次活動中,他對此仍然沒有鬆口,但強烈暗示將參加大選)。也正因如此,這一表態被認為是一種實質上的選舉動作,並隨即遭到反對黨陣營的強烈批評,後者指責馬克龍「蔑視」、「侮辱」民眾、「分裂」社會,右翼共和黨(LR)的國民議會黨團主席阿巴德(Damien Abad)更表示,在距離大選還有3個月之際,馬克龍「和勒龐、澤穆爾一樣淪入民粹主義的泥淖」,言論出現了「特朗普化」傾向。
對於許多媒體而言,更值得關注的話題是:這一表態將對大選走向造成什麼影響?鑑於一開始坊間輿情洶湧,導致有媒體大膽預言,這可能是馬克龍人氣崩塌的轉折點。然而民情走向卻並沒有證實這一點。民調機構Ipsos和Sopra Steria於1月6-7日聯合進行的民調顯示,相關言論對馬克龍的民意指數非但沒有造成削弱,反而有愈發強化的勢頭:如果立刻舉行大選的話,有26%的選民會在第一輪為馬克龍投票,這一數字比12月份還要高一個百分點。排名第二的極右派瑪琳娜·勒龐(Marine Le Pen)的民意指數(17%)也並沒有因此看漲,和共和黨候選人佩克雷斯(Valérie Pécresse)的16%不相上下;如果馬克龍第二輪和勒龐對決,將以58%比32%輕鬆獲勝,即便遭遇佩克雷斯,也能以55%比45%的明顯優勢獲勝。
更有指標性意義的是,在馬克龍講話次日,醫療就診預約平台Doctolib上的新冠疫苗首次接種預約人數達到27710次,繼續維持此前兩天的增長勢頭,達到三個月來的新高。這似乎表明,疫苗接種工作正朝着政府希望看到的方向加速——至少沒有出現明顯的逆反性下挫。
不過,要說馬克龍的這一表態完全沒有負面後果,也並非實情。此前幾周聲勢原本大為衰弱的反防疫遊行示威,在1月8日重新獲得了動力。據法國內政部的數據,當天全法各地共約10萬人走上街頭,是新年前類似活動人數的四倍。這其中有國民議會通過疫苗通行證法案的刺激,但馬克龍的挑釁性姿態,顯而易見也是一個強有力的刺激因素。但在下一個動員日(15日),上街人數隨即減半,回落至5.4萬人,表明反彈情緒正在迅速降温。

「樹立某些仇敵,以便把它制服」
通常而言,無論選戰多麼激烈,民選體制產生的政治領導人上台後,都負有彌合分歧、代表全民的義務,這種義務有時近乎一種「政治正確」,很少有正統的政治領導人向選民群體公開表達敵意、並以這種敵意作為凝聚本方基本盤的手段。但在最近數年間,以美國的特朗普、巴西的博索納羅、菲律賓的杜特爾特為代表的「非主流」領導人,不憚於將部分選民群體公開地視為敵人,這種手法也成為民粹主義的基本特徵。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當馬克龍針對拒絕接種疫苗者說「很想讓他們不爽」時,反對黨立即指責總統是在「特朗普化」。
就在馬克龍發表上述言論的次日,法國《哲學雜誌》的主編Martin Legros就發文質疑——「馬克龍忘記馬基雅維利了嗎?」他援引《君主論》第19章稱,馬基雅維利的告誡是,作為君主的最重要品質,就是避免讓自己受到憎恨或者輕視,而「君主如果被人認為變幻無常、輕率淺薄、軟弱怯懦、優柔寡斷,就會受到輕視」,因此他應當提防這一切,努力「在行動中表現偉大、英勇、嚴肅莊重、堅忍不拔」,而emmerder這種措辭,卻難以稱之為「偉大」或者「嚴肅莊重」。
所謂「忘記」,其實暗含深意。而將馬克龍同馬基雅維利聯繫起來,也不是什麼新鮮說法。畢竟這位總統的碩士一年級論文曾以馬基雅維利為題,探討「馬基雅維利筆下的政治事實和歷史代表性」。在2014年10月《紐約時報》的一篇人物特寫中,當時的這位經濟部長「笑稱」,對馬基雅維利的研究幫助他在巴黎的政治權力圈子中生存下來。當然,很難判斷這種表態是真正的袒露心跡,還是展示幽默感的媒體應對技巧;畢竟,對一篇二十年前的碩士一年級習作(並非碩士畢業論文),外界難以遽下結論,判定它和今日之施政有何內在關聯。
即便如此,以馬基雅維利作為關鍵詞、對馬克龍的治理進行評判,幾乎從這位總統剛一上台便開始了。彼時種種施政措施尚未展開,媒體從這位年輕總統聲稱的「復興」(Renaissance,與「文藝復興」相同)、以及佛羅倫薩城邦面臨的憂患展開聯想。但隨後,隨着各項施政措施觸及到具體利益,以及馬克龍的某些言論引發爭議,相關聲音開始頻頻警告馬克龍不要「被人民憎恨」,並敦促他重新温習馬基雅維利。
與此同時,另一種進路則試圖探究這兩位人物的內在相關性。歷史學家布舍隆(Patrick Boucheron)曾撰文分析馬克龍與馬基雅維利之間的「驚人相似」;2018年,一本名為《馬基雅維利和馬克龍:不可能的通信》的小冊子出版,作者朗庫爾(Eric de Rancourt)指出,儘管相隔幾個世紀,但馬基雅維利和馬克龍卻有着共同的軌跡和品味;在征服和行使權力、國家的角色、軍隊的重要性、道德在政治中的位置等方面驚人地接近。

2017年,馬克龍以「中間派」政治明星形象崛起,造成法國的政治版圖裂變,傳統的中左(社會黨)和中右(人民運動聯盟/共和黨)均出現黨內精英出走潮,令兩黨大傷元氣,至今尚未恢復。相對而言,左翼陣營受創更重,面對2022年大選呈現出一盤散沙的局面,所有候選人均民調低迷,對馬克龍來說不足為慮;而右翼則形勢詭譎:一方面,極右翼的埃裏克·澤穆爾(Eric Zemmour)以黑馬姿態殺出,雖然從民調看勝算不大,但仍然大大哄抬了極右的聲勢;另一方面,作為温和派的佩克雷斯贏得共和黨初選,但是否能夠整合競爭對手所代表的「深右」(介於中右和極右之間)選民,並抵抗住極右派的蠶食,仍然需要觀察。
在這種情況下,馬克龍投身選戰,勢必要考慮這個經典問題——「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倘若以總統大選第二輪作為敵友之辨的指標,目前從民調來看,很大概率還將出現馬克龍對壘極右的格局(除非佩克雷斯在最後三個月裏有效地收編深右選民),而在極左和極右派政客的鼓動下,日益縮水的抗拒疫苗群體,也逐漸浮現為抗拒馬克龍政府的「硬核」部分。可以想見,到了大選之日,這一群體(未必能和極左-極右選民直接劃等號,但有相當部分重合)為馬克龍投票的可能性將微乎其微,相反有極大概率投給他的競爭對手,因此從選舉策略角度來說,爭取這部分選民的邊際效用極低、成本卻極大(甚至無異於推翻此前五年的全部施政),於是他們便成了不值得再花力氣爭取的票倉。
不僅如此,隨着奧密克戎疫情海嘯式暴發、以及公眾對醫療服務(尤其是未接種者佔用的重症病房床位)的擔心,對於馬克龍來說,抗拒接種疫苗群體不僅缺乏正面價值,而且成了一個疏導民眾怨氣的現成靶子。

從這個意義上說,馬克龍對於反疫苗者的攻擊,非但不是忘記了馬基雅維利的教誨,反而在某種程度上是在踐行這種教誨。後者雖然告誡君主避免遭人忌恨,但同時也說過,「一個英明的君主一有機會,就應該詭譎地樹立某些仇敵,以便把它制服,從而使自己變得更加偉大。」(君主論,第20章)
對於這種策略,執政黨議員萊斯居爾(Roland Lescure)辯護說,總統只是「大聲說出了很多人的心裏話」,即「10%未接種疫苗者的自由,止於90%接種疫苗者自由開始的地方」。但政治公關專家墨霍-舍維羅萊(Philippe Moreau-Chevrolet)認為:「這是以攻擊性方式實施佔據輿論陣地的策略,拿少數人當替罪羊,目的是爭取大部分人;這是一種民粹主義策略。」《紐約時報》駐巴黎記者Norimitsu Onishi則更加不客氣地指出,這位「根深蒂固的政治賭徒」試圖以此開掘一條「政治富礦」:即在已經接種疫苗的多數群體中,激起針對那些抗拒接種、卻又不成比例地佔據醫院病床的少數人的憤怒。
對現政府而言,雖然每天都在因疫情應對而遭受批評,但兩年下來,法國高達91%的成年人完全接種率、經濟上全力支撐企業運營、促成經濟強勢回彈,依然是一筆顯著的正資產。而且資產越是積聚,民眾就越是擔心失去。早在去年12月中旬,總理卡斯泰已經放話稱:「數百萬法國人拒絕接種疫苗,會使整個國家的生命處於危險之中,並影響到絕大多數法國人的日常生活,這是不可接受的。」而馬基雅維利早已冷眼看到,「當多數人能夠站得住腳的時候,少數人是沒有活動餘地的。」(君主論,第18章)

因此,倘若可以認定馬克龍的這次「出言不遜」的確是一種選戰手法的話,它無疑帶有鮮明的馬基雅維利式色彩:與其等到大選第二輪攤牌時再放棄抗拒疫苗群體,不如當他們人數已經足夠少、足以不值得爭取時,「樹立某些仇敵,以便把它制服」。
從目前的民調結果來看,馬克龍儘管尚未正式下場參選,但民意指數仍然顯著超越所有競爭對手;而且從目前可以感知的疫情規律來看,2022年總統大選的時間點,相對而言更加有利於馬克龍:如果奧密克戎真的如某些醫學專家預判、將是最後一波大規模疫情,那麼馬克龍屆時便可以順理成章地宣告帶領國家走出疫情;如果其後仍然有新一波疫情,但四月份的投票很可能處於奧密克戎消退、新一波疫情尚未到來的低谷期,屆時民情士氣依然對在任總統有利。
當然,不能排除的一點是,如果疫情發生了難以想像的轉折,導致防疫工作前功盡棄,那麼馬克龍恐怕將面臨真正的危險,即曠日持久的疫情導致「抗議性投票」——民眾並不清楚自己真正想要什麼,也不知道如何才能用代價最小、最有可能性的方式走出疫情,但他們可能會將怨氣發泄到看上去最應負責的那個人頭上。而最新一期民調已經顯示出這個跡象:Ifop在1月22日公布的調查顯示,馬克龍一月份的民意認同度下挫4個百分點,從41%退居37%,雖然嚴格來說這和大選投票意向並非同一議題,但分析人士稱,它已經構成了對馬克龍的一個「嚴肅警告」。由此,未雨綢繆地引導民怨,預防落入陷阱,也是馬基雅維利「獅子與狐狸」之論的題中應有之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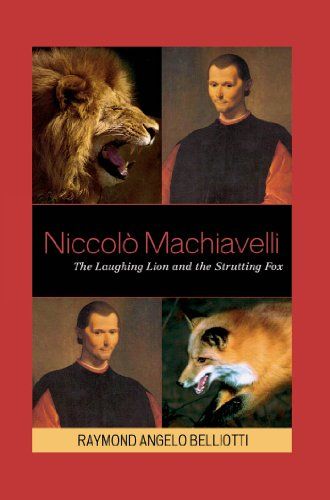
(本文首發於澎湃新聞·思想市場,轉載請註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