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郁達夫筆記(2):“沉淪”與性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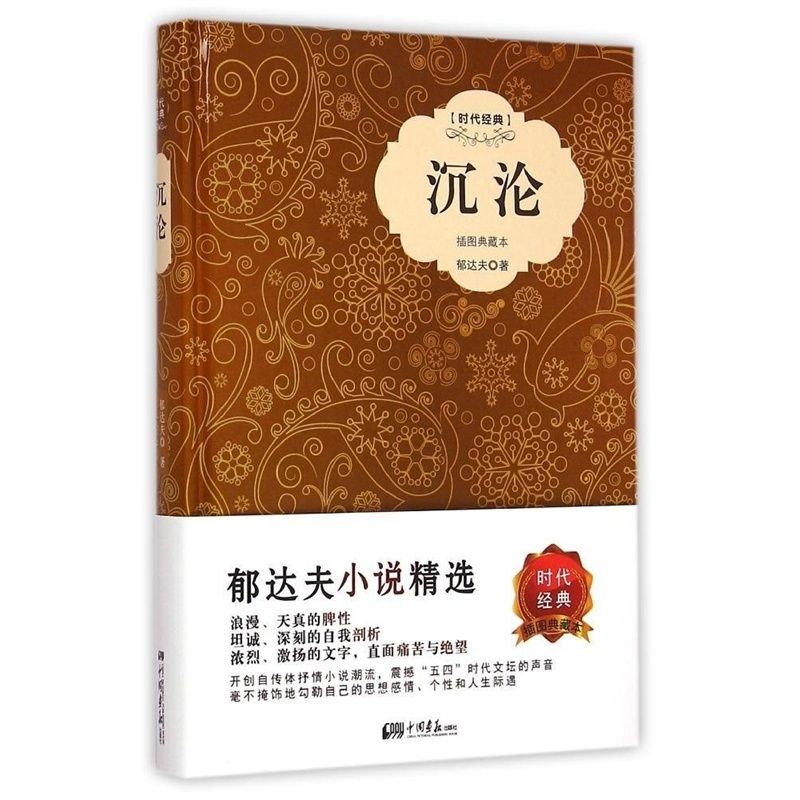
先前发表的拙文 “重读郁达夫笔记(1)” 提到郁达夫销小说中的性描写其实都乖,很克制,都是发乎情止乎礼仪,根本就没有什么赤裸裸的性行为描写。这里或许还可以补充一句:在郁氏小说中,连偷窥都没见真容活体,偷窥者顶多是远远地一窥白润的皮肤一次而心跳,如此而已。
既然如此,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便油然而生——在郁达夫发表其所谓的惊世骇俗的小说时,中国没有多少书籍出版检查,非郑痔性的检查更是没有。于是,《金瓶梅》、《肉蒲团》之类的各种色情出版物得以尽情出版,应有尽有,货品供应充足,销售渠道通畅。
在那样的大环境下,社会大众对此司空见惯,习以为常,浑不在意,既然是这样,为什么郁达夫那些包含发乎情止乎礼仪的性描写的小说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关注以致形成众口铄金式的丑闻,需要周作人这样的当时的文坛名人站出来给他辩护补台呢?
写这种事情写到这里,就应当或必须旁枝横逸,说一点题外也是题内的话,提到法国大作家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和郁达夫的老朋友周树人即周作人的哥哥鲁迅。应当说,联系福楼拜和鲁迅来研读郁达夫对深入研究或理解郁达夫其人其文非常重要。
***
必须提福楼拜是因为在文学表现及其社会反响方面,郁达夫登上中国文坛跟福楼拜以其成名作和杰作《包法利夫人》登上法国文坛的情况有一拼。只是由于当时的中国由于种种一言难尽的原因,郁达夫及其出版人和没有像福楼拜及其出版商、印刷商那样被提起公诉。
就福楼拜而言,他因为发表《包法利夫人》而连同其出版商和印刷商一道被告上法庭是文学史上的著名事实。但在中国,对这一事实本身以及对这一事实的来龙去脉的陈述多是浮皮潦草或陈词滥调,给读者造成误导。在这方面,人民人文学出版社2019年出版的《包法利夫人》李健吾译本的 “作品简介” 可谓典型:
《包法利夫人》于1856—1857年间在《巴黎杂志》上连载,轰动文坛,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司法当局对作者提起公诉,指控小说“伤风败俗、亵渎宗教”,并传唤作者到庭受审,最终以“宣判无罪”收场,而隐居乡野、籍籍无名的作者从此奠定了自己的文学声誉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这种简介所宣扬的籍籍无名的作者因为审判而获得暴得大名的暴利虽然很是投合许多人的心理,但不是事实。关于福楼拜的基本事实是,来自乡间的他根本就不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土农民或土财主。在发表《包法利夫人》的时候以及被提起公诉受审之前,他跟法国文艺界的名流熟悉,连当时的法国国王和王后也为他说好话。
尽管有国王和王后也为他说好话,然而,福楼拜及其出版商和印刷商却像中了彩票一样,莫名其妙地被提起公诉,罪名是 “伤风败俗、亵渎宗教”,尽管当时法国有很多书籍包含更露骨放肆的性描写,但那些书的作者和出版商印刷商却都一个个安然无恙,没有被提起公诉并受审。
福楼拜及其成名作为什么得到了这种待遇呢?
多年来,这个问题一直是论者闪烁其词、语焉不详的一个历史和文学之谜。1982年,美国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为《包法利夫人受审》(Madame Bovary on Trial)的专著,该书作者 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对这个谜进行了一番文学和历史的梳理和解读。
《包法利夫人受审》一书的主要内容或主旨是,当初对福楼拜的代表作提出起诉的法国第二帝国公诉人和福楼拜的辩护团队的论辩各有道理,各自代表对文学作品的认真解读;弄清他们各自的道理有助于研究者和读者更好地理解《包法利夫人》以及其他类似的引起社会争议的文学作品。
拉卡普拉的专著详细陈述和解析了控辩双方的论点,从而为推进读者更好地理解福楼拜和《包法利夫人》做出了重大贡献。与此同时,中文世界还缺类似的研究或类似的研究专著来大幅度推进读者对郁达夫和郁达夫作品的理解。
现在的研究者和认真的读者可以问:郁达夫到底是有什么绝招撩拨了当时的中国社会、中国读者的哪根神经,撩到了哪个G点,导致他和他的作品得到当时的媒体和众读者的格外瞩目,导致很有利于提升他的作品的销量的丑闻大扩散呢?
上面的问题还可以这样问:当时的社会大众和读者不关注、不在乎当时的色情出版物随意出版、供应充足,却似乎对郁达夫小说中那些温顺无害的性描写格外注意,这种强烈的反差和由此而来的丑闻就究竟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假冒伪善,莫名其妙的歇斯底里,还是当时的媒体蓄意炒作?
这里的关键词是莫名其妙。莫名其妙当然指知识空白。
***
说完了福楼拜再说鲁迅。说鲁迅是为了解说前文以及上文所说的一个跟郁达夫作品相关的社会文化现象,这就是,再郁达夫发表所谓的惊世骇俗的小说的时候,中国社会上直白地描绘性行为的的小说和画谱多得很,根本就不稀罕,因此说郁达夫小说因其性描写而惊世骇俗引人注目之说根本就站不住脚,其小说在当时和后来引人注目必定另有原因。
还是要说,截至目前中文世界对这些问题貌似没有什么正规的研究或非正规的深入探讨。这些问题显然是文学研究和历史研究的博士论文的好课题。
鲁迅跟这个好课题的联系见于他的散文/小说集《朝花夕拾》,其中有一篇题为“琐记”,包含下面这个段子:
但我对于她(邻居和儿时的朋友的母亲 “衍太太”)也有不满足的地方。一回是很早的时候了,我还很小,偶然走进她家去,她正在和她的男人看书。我走近去,她便将书塞在我的眼前道,“你看,你知道这是什么?” 我看那书上画著房屋,有两个人光着身子仿佛在打架,但又不很像。正迟疑间,他们便大笑起来了。这使我很不高兴,似乎受了一个极大的侮辱,不到那里去大约有十多天。
周作人在他解说鲁迅作品的书中说,鲁迅以回忆往事的名目写出的文章中常常含有虚构。“琐记”大有可能就是这样的文章。但这样的文章在当时之所以有人信而不认为是生编乱造,无非是因为文章中所说的事情是人们司空见惯的,一点也不觉得离谱。
“衍太太” 和她的男人将一本色情画册硬塞给在男女之事上尚未开窍的 “我” 看,看到 “我” 懵懵懂懂、不明就里的样子便高兴起来。鲁迅的这一陈述非常生动形象地展示了色情出版物在旧时的中国是多么普及,多么易得。
说到这里,我忍不住要说两个与这个话题相关的个人回忆。一个是多年前上初中的时候,老师给我们朗读并讲解 “琐记”,但对 “两个人光着身子仿佛在打架” 没有一字的讲解或评论。我也不记得课后同学有什么说法。现在回想当时感觉恍如隔世,并因此更好奇现在的中学老师会如何对学生娃讲解或评论。
此外,记得上小学高年级或初中的时候读《红楼梦》,读到第七十三回,“痴丫头误拾绣春囊 懦小姐不问累金凤”,很是为其中所说的事情不解——绣春囊怎么啦?有什么好大惊小怪,大动干戈的呢?即使是后来得知“绣春囊”其实就是绣着春画的香袋,也仍是大惑不解——春画,不就是春天的画嘛,香袋上绣上这样的画又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呢?
以上两个回忆既是个人的,也是民族/国家的,跟文学研究和阅读密切相关。总起来说,中国人传统上对所谓的男女之事/性事十分热衷,这方面的文学艺术或话语很发达(正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跟全世界各国别无二致),但又往往对这种事情讳莫如深(跟世界很多国家大不相同),导致未成年人对这种事情完全无知,只能在黑暗中摸索。
公平地说,这种明显的精神分裂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当今世界一些其他国家的问题。这里所谓的其他国家既包括非洲的一些不发达国家,也包括美国这样的毫无争议的发达国家。
***
以上是关于郁达夫小说的一些大问题,宏观问题。以下是关于他的小说的小问题,具体问题,微观问题,科学问题。希望这里所说的问题能以小见大,填补郁达夫研究的空白。
这里要关注的具体问题是郁达夫小说中的性的观念。在其1921年5月9日写就的著名小说 “沉沦” 中,读者看到一个到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整天混日子,但混得他自己心慌意乱,犯罪感强烈:
在生活竞争不十分猛烈,逍遥自在,同中古时代一样的时候,他觉得更加难受。学校的教科书,也渐渐的嫌恶起来,法国自然派的小说,和中国那几本有名的诲淫小说,他念了又念,几乎记熟了。
有时候他忽然做出一首好诗来,他自家便喜欢得非常,以为他的脑力还没有破坏。那时候他每对着自家起誓说:“我的脑力还可以使得,还能做得出这样的诗,我以后决不再犯罪了。过去的事实是没法,我以后总不再犯罪了。若从此自新,我的脑力,还是很可以的。”
然而一到了紧迫的时候,他的誓言又忘了。
每礼拜四五,或每月的二十六七的时候,他索性尽意的贪起欢来。他的心里想,自下礼拜一或下月初一起,我总不犯罪了。有时候正合到礼拜六或月底的晚上,去剃头洗澡去,以为这就是改过自新的记号,然而过几天他又不得不吃鸡子和牛乳(以弥补身体亏空)了。
他的自责心同恐惧心,竟一日也不使他安闲,他的忧郁症也从此厉害起来了。这样的状态继续了一二个月,他的学校里就放了暑假,暑假的两个月内,他受的苦闷,更甚于平时;到了学校开课的时候,他的两颊的颧骨更高起来,他的青灰色的眼窝更大起来,他的一双灵活的瞳人,变了同死鱼眼睛一样了。
“沉沦” 大概是郁达夫最著名的小说,其主人公正此时在经历青春期的精神苦闷和性苦闷。两种苦闷在他身上相辅相成,相互发明,又跟他对积贫积弱的祖国的国情认识和由此而来的作为中国人的自卑感掺和在一起导致不良的精神和生理状况。
郁达夫细腻又举重若轻地描写这些不同的精神力量在主人公身上的角力,并由此塑造出一个生灵活现的人物。毫无疑问,这是他作为一个小说家的大成就,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大成就。
这个片段就性的话题而言显示了两个有趣的问题。其中之一证实了上文以及前文所说的在小说人物所生活的时代色情出版物非常普及。在这里,读者看到那样的出版物甚至普及到了日本(无论是小说人物当初是带着那样的书去日本留学,还是在日本当地购买到了那样的小说)。
但另一个或许是更有趣、更重要、也更现实意义的问题是,这个片段展示了中国人对自慰这种性行为的毫无科学依据、毫无事实依据但又根深蒂固的观念,这就是,自慰不但是可耻的,而且也会严重损害人的精神和身体健康,甚至可以致命。
这种观念长久以来甚至直到今天仍是被广泛信以为真,被说得有鼻子有眼,导致不知多少人无端的焦虑,就像“沉沦”的主人公一样。显然,郁达夫也跟他的小说的“沉沦”主人公一样对这种观念深信不疑,虽然他对主人公的总体自我认知和国家认知大有可能不以为然。
实际上,“沉沦”这个名称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郁达夫对那主人公及其心态的判断,但不知为什么,这一事实本身在常见的评论中却很少被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