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加恩《恩格斯与〈自然辩证法〉》书评(A Review of Friedrich Engels and the Dialectics of Nature by Kaan Kangal)
﹝阿根廷﹞丹尼尔·盖多(Daniel Gaido)
陈嘉祺 译、匡红 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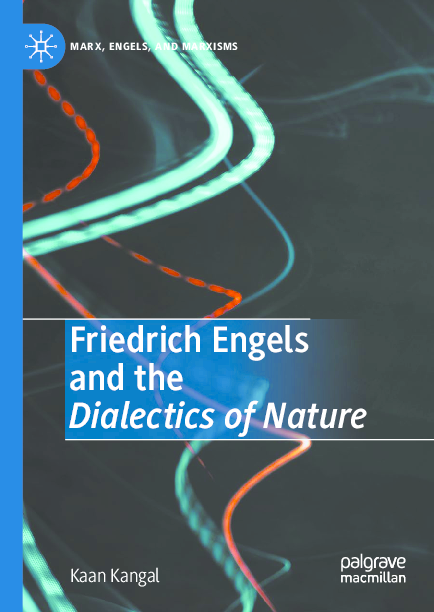
Kaan Kangal, (2020) Friedrich Engels and the Dialectics of Natur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恩格斯在其著作《反杜林论》中指出,黑格尔的存在使得哲学走到了尽头,而这对于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排除在自然与历史之外哲学而言“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提出了三项“辩证法的规律”:(1)量变质变规律,(2)对立统一规律以及(3)否定之否定规律。这些规律看似复杂,但其基本内容其实并不难理解。
现在我们来思考一下以上看似神秘的辩证法规律。身为完全的唯物主义者,我们假定起初物质世界是客观实在的。但经过138亿年的演化,宇宙中不仅孕育出了生命,还出现了人类这样具有思考潜力的物种。因此,我们必须在假设存在一种与客观实在区别和对立(同时又是客观实在的一部分)的东西,一个可能具有智慧的主观存在,同时其在哲学术语中是对前一个假设,即无主观存在的客观实在这一规定的确定或否定。但是,人类在为了生存和发展而理解外部世界的过程中,主观存在又反过来否定了这一否定,并产生了对客观实在的主观映像。这一主观映像自身就是矛盾且常常随着客观和主观的情况而变化的。这些认识反过来传达并存储在人的大脑中,它以物理、化学和生物规律的存在为前提;但就像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不能被还原成英语语法一样,其并不能被还原为纸面上的规律,比如所谓的质的飞跃。
当然,理解辩证法的基本概念是一回事,而去啃黑格尔的著作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譬如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和《哲学科学全书纲要》——最好是德文原版,因为在他的体系中经常用德语的文字游戏完成不同范畴之间的跳跃。接下来灵魂论的至暗时刻来临了。马克思在1858年1月16日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指出:“如果以后再有功夫做这类工作的话”他希望用一本50页的小册子来阐释辩证法这种“黑格尔所发现,但又被黑格尔神秘化”的方法。然而马克思将他的时间用在了另一个更有效率的地方:他与福格特先生进行了长达200页的辩论。所以现在我们就不得不自己去深入虎穴,期望能全须全尾的得到那50页的智慧。
然而我们并非无路可走,我们仍然可以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看到社会科学中辩证法的作用。马克思常以辩证法为指导分析从政治经济学最抽象(商品生产劳动的二重性)到最具体(围绕剩余价值的阶级斗争)的范畴的资本主义运动。在恩格斯的著作中也是如此,尤其是他未完成的关于辩证法在自然科学中应用的尝试。恩格斯这一系列手稿的原稿、评论和注释的合集被整理成了《自然辩证法》一书,康加恩(Kaan Kangal)[1]这部作品就是以此为主题。他引用恩格斯来说明他这一工作的本质,即“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方式的简单形式上建立起来。”任何一个啃过黑格尔这块硬骨头的人都应该因此对恩格斯抱有感激之情。
康加恩是一位博学的学者,并掌握德、俄、中、英和土耳其语和许多其他的语言。他在文中引用了恩格斯手稿完成前后大量关于黑格尔辩证法的评论(1873-1886),以及《自然辩证法》于1925年首次出版以后围绕后续版本的讨论与争议。从本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特伦德伦堡、哈特曼以及保罗·巴特等人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继承;早期杜林、朗格、日特洛夫斯基伯恩斯坦、考茨基、阿德勒以及普列汉诺夫等早期社会主义者对这一主题的讨论,其中考茨基如此评价普列汉诺夫:“他是我们中的哲学家,毫无疑问是我们中唯一研究过黑格尔的人”(P51);我们还能了解卢卡奇在不同时期的变化:他最开始反对辩证法适用于自然科学的观点,后来又拒斥自己曾经的反对;另外汽中国更重要的是在20世纪20到30年代,苏联内部关于恩格斯的论战——这场论战的两派分别以《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共产主义学院公报》、《布尔什维克与自然辩证法》等期刊为阵地。其中A.德波林(普列汉诺夫的学生,前孟什维克)和他的学生们与机械派的论战最为知名。而对于其他有关的内容,康加恩回忆道:“1924年伯恩斯坦曾询问爱因斯坦,后者认为自然辩证法的这些手稿于当代物理学而言毫无价值。但它们反映了恩格斯的有趣见解。”
关于政治与哲学关系,尤其是关于理论的作用以及工人运动中知识分子的作用的章节中,包含了很多有趣的观点,还有恩格斯这句:“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向大学要求的仅仅是律师,作为培养他们的政治活动家的最好的原料;而工人阶级的解放,除此之外还需要医生、工程师、化学家、农艺师及其他专门人材,因为问题在于不仅要掌管政治机器,而且要掌管全部社会生产,而在这里需要的决不是响亮的词句,而是丰富的知识。”
康加恩书中理论最密集的部分是其第五章,在专门讨论“自然辩证法中的辩证法”这一章中,康加恩讨论了恩格斯通过对亚里士多德、康德和黑格尔著作的详细分析,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对立。让当代读者在这些争论中难以找到方向的首要困难是与日常含义差别巨大的术语。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著作《形而上学》中写道:“在事物之中,有一个不会变假的原则,相反地,我认为要让它恒真。这就是,同一事物,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内既存在又不存在,也不允许有以同样方式与自身相矛盾的东西。”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不认为这种“无矛盾律”或由此衍生出的“同一律”(A=A)是绝对错误的,但认为它们仅具有相对的有效性。在这方面,物理学中的相变过程就是这一联系的明证:在相变过程中,物质从固态、液态或气态中的一态转变为另一态,任何物质都可以在某个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从一相变为另一相,或是在温度压力不变的情况下不发生变化。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社会科学:如加米诺夫这样具有强烈机会主义倾向的人在倒戈成为米勒兰一样的资产阶级官僚或墨索里尼一样的法西斯分子前,仍可以是一位社会主义政治家。
换句话说,辩证法的目的从来不是将形而上学完全否定,而是指出它只在特定的条件下适用并给出它赖以适用的基础——这一点就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不否定牛顿定律,而是认为它只在特定的范围内适用,在这个范围以外它将不再有效并且需要被整合进更加普适的框架当中了。康加恩再次引用了恩格斯的论断,不同于费尔巴哈试图单纯摒弃黑格尔,他认为:“仅仅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P113)从唯物主义者的视角看,这一过程并不仅仅由思潮的“自我发展”而是如恩格斯所说,由于“人的活动对他的思维的影响”:“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P172)
对于一位书评人而言,需要十分精通哲学史才能评价康加恩的很多论点,尤其是其关于“恩格斯在哲学上具有模糊性”(P125)以及这种模糊性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恩格斯最终未能完成和发表《自然辩证法》。或许是他为自己设定的任务已经超过了任何一个人所能完成的程度。马克思选择了辩证地批判一门科学,即政治经济学,来探索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发展和毁灭)。为了完成这一工作,他最终要为这一学科(剩余价值理论)完成一部三卷本的巨著。即便如此,他也未能独力完成这些工作。《资本论》后两卷的编辑任务最终留给了恩格斯。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一群精通自己学科且熟知哲学史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以及数学领域的科学家组成的团队,其他任何人能够从自然科学史中演化出辩证法规律。更不必说我们所讨论的是科学而非宗教,这不仅是一个确证辩证法可以适用于自然世界的问题,还是一个批判地验证他们,并根据自然科学的进步决定如何改进或者更替它的问题。
就一个外行人而言,从哥本哈根学派对量子力学的阐释(即波函数在观察者介入时的坍缩),到宇宙起源的大爆炸假说,当代自然科学充斥着对物理理论的唯心主义观点。而受到唯物主义启发的替代理论,如彭罗斯的“量子引力”和“共性循环宇宙”模型(这一模型试图解释大爆炸前的宇宙),但这些理论的接受度都很低。我们离自己的领域,即社会科学和哲学太远了,而在这里唯心主义已经臭不可闻。在恩格斯开始他这一未能完成的工作不久之前,达尔文从政治经济学中受到启发,用自然选择解释了物种的进化,且他用了这一学科最薄弱的分支来进行的这项工作。现如今,没有哪个头脑正常的自然科学家会从被称为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护教学毒瘤中获取灵感。而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已经将这一情况内化于心,甚至知道他们试图将自己的研究上升到专著级别,才意识到他们自己的学科已经由于资本主义的式微而衰落。而熟知康加恩书中所讲述的议论,将对两种人都大有裨益。
丹尼尔·盖多(Daniel Gaido)是阿根廷国家科学技术研究委员会(Conicet)的研究员。
[1] 康加恩(Kaan Kangal)于1986年2月26日出生于土耳其安卡拉,德国慕尼黑大学哲学博士,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哲学系副教授,精通土耳其文、德文、英文、俄文、拉丁文,主要研究方向为辩证哲学、政治经济学哲学、科学哲学和数学哲学。于2014年5月起在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和哲学系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