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期资本主义》(Late Capitalism)序言新译
﹝比利时﹞埃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
1975
田七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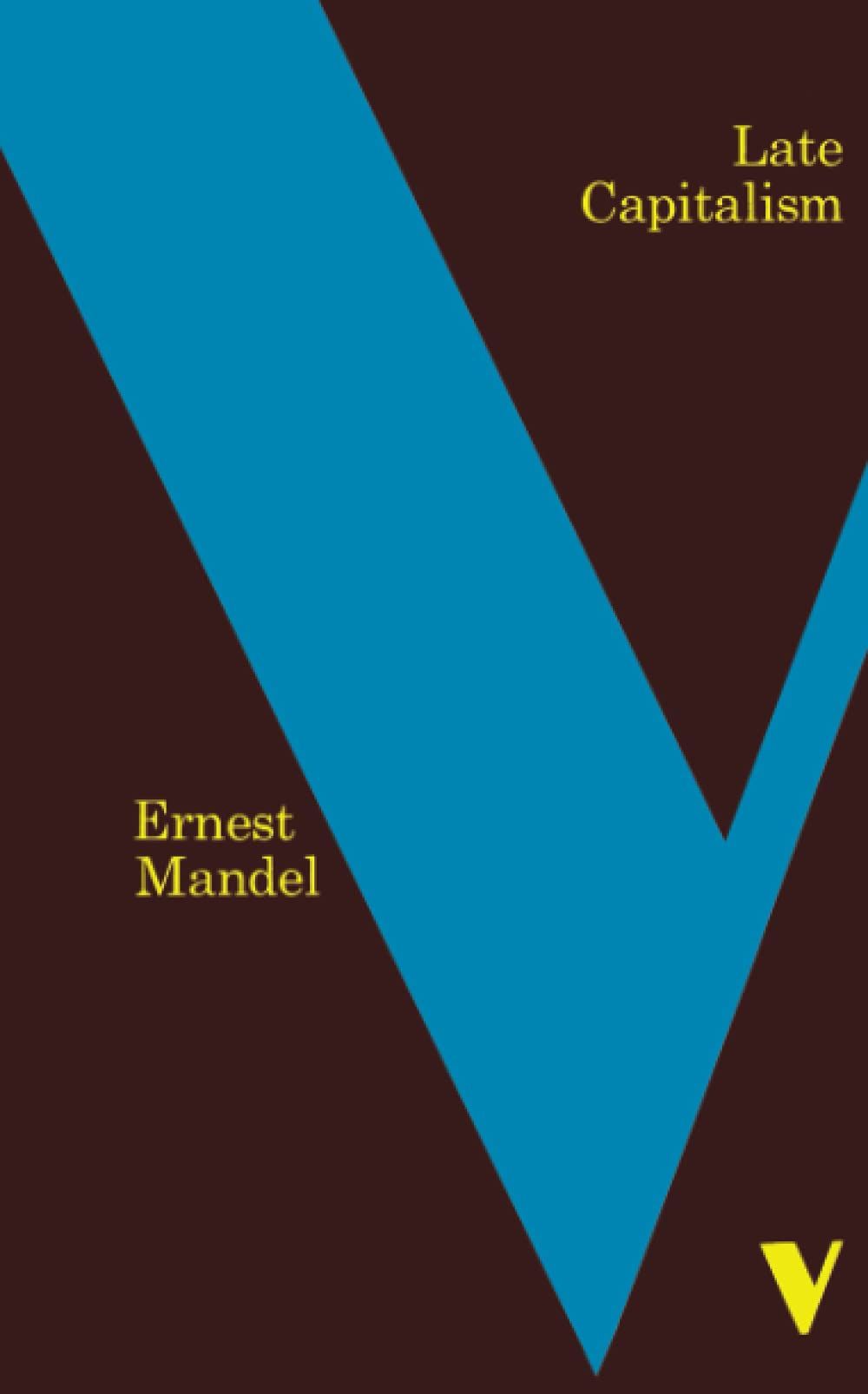
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二战”后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增长的长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与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对此感到惊讶)的成因,并且论证这一增长时期的内在局限。这些内在局限使得在快速增长的长波之后出现的,是世界资本主义经历持续恶化的社会经济危机的长波(表现为低得多的总增长率)。1970—1972年,当笔者首先以德语写下并出版本书时,尽管自1967年起国际货币体系已经出现了崩溃的先兆,尽管法国在1968年5月爆发了群众性运动,但对于许多读者来说,本书的上述基本论点尚未有经验事实的支撑,而且遭到了广泛的质疑。如今,没有多少人会质疑战后经济发展的重大转折点已经出现了(而非还只是未来的一种可能性),“长期繁荣”已经成为历史。认为“混合经济”能够保持持久的快速增长与充分就业的想法,被证明是一种荒诞的念头。本书将尝试在古典马克思主义范畴的框架内,解释为何战后经济发展必然会发生如此的转折,揭示战后资本主义的实际动态会造成怎样的后果。
在修订英文版本的《晚期资本主义》时,笔者尽量不去补充大量的新材料,不去用事实来论证我们的最初观点。相反,笔者对次要的表述进行了修正或澄清,更新了相关的数据。对本书的种种深入意见,有待正在讨论世界资本主义在当前阶段的总体矛盾及长期趋势的国际性辩论来提出,有待对《晚期资本主义》提出的一些新假设进行理解。只有历史可以检验这些假设是否充分与逻辑自洽,而我们无须惧怕历史的裁决。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结合“作为总体的资本”的运动规律及“众多资本”的具体形态,来解释20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任何努力,无论是局限于对“众多资本”的研究,还是从“作为总体的资本”直接推断出“众多资本”,要么在方法论上经不起推敲,要么没有实操性。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在考察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先后阶段及晚期资本主义的当前阶段时,理应考虑到劳资之间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国家及晚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世界贸易的多变的具体结构,以及剩余利润的多种主要形式。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本书的结构和马克思《资本论》一开始的写作计划(“作为总体的资本”、竞争、信贷、股份资本、地产、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马克思还想在讨论 “世界市场”时涉及世界经济危机)不无关系。但是,笔者并未照搬这一写作计划的每个部分,而且马克思的《资本论》本身也和这一写作计划偏离甚远。
《晚期资本主义》的前四章确立了本书的总体框架。第1章处理的是方法论上的初步问题,第2—3章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包括其种种内在矛盾)与满足其需要的社会地理环境(即世界市场)之间的关系。第3—4章讨论的是资本主义的技术发展与资本的价值增殖之间的关系。对理论不甚通晓或不感兴趣的读者可不理会第1章,或者读完整本书后再回头来看。
接下来的九个章节都是分析性的,是对晚期资本主义主要特征的研究,遵循的是“逻辑—历史”的顺序。首先,法西斯主义与战争导致工人阶级的历史性失败,这极大地改善了资本增殖的种种条件(第5章);接着,第三次技术革命进一步促进了资本的增殖(第6章);资本发展新阶段的具体特点:固定资本折旧周期的缩短,技术革新的加速(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垄断性剩余利润的主要形式就是技术革新带来的“租金”),持续的重整军备吸收了过剩资本(第7—9章);资本增殖与世界市场的特定联系,即国际范围内资本的积聚与集中(产生了跨国企业这种资本的主要的具体形态),以及以不同的平均劳动生产率进行商品生产的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交换(这种不平等交换是世界贸易的主流)(第10—11章);资本价值实现问题的新表现与“解决措施”,即长期的通货膨胀和典型的晚期资本主义贸易周期(包括了伴随着信贷扩张的古典工业周期,和以通货膨胀为标志的信贷收缩“反周期”)(第12—13章)。
相反,最后五章内容有着明显的综合性。笔者试图将前述几章的分析结果综合起来,并且尝试揭示资本运动的基本规律及其内在矛盾继续发挥作用的路径,鲜明地揭示这两者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最为极端的表现(第14—18章)。
有两点需要提请读者注意。首先,“晚期资本主义”一词绝非表明资本主义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以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列宁的《帝国主义》都过时了。正如列宁能做的只是在《资本论》的基础上考察帝国主义,论证由马克思发现的、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决定作用的总体规律,笔者想做的只是在列宁对帝国主义的研究的基础上,用马克思主义对晚期资本主义进行分析。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并非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它只是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进一步发展。换言之,列宁枚举的帝国主义时代的种种特点,依然完全符合晚期资本主义的情况。
同时,笔者必须请求谅解,因为我没能提出比“晚期资本主义”更好的术语来描述这一历史时代。“晚期资本主义”一词不能让人满意,因为它只是表明某种年代顺序,并非一种综合性的术语。尽管如此,在本书第16章,笔者解释了“晚期资本主义”依然要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一术语合适。而且,比起“新资本主义”一词,“晚期资本主义”要贴切得多。“新资本主义”一词的含义是含糊的,因为它既可以指与传统资本主义有着根本的区别,也可以指在根本上与传统资本主义保持延续。或许在不远的将来,争论会让我们总结出一个更具综合性的术语。但在目前,笔者依然使用“晚期资本主义”这一概念,认为它是目前能够使用的、最为贴切的术语。此外,笔者毕竟相信真正关键的不是怎么取名字,而是去解释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发展。
《晚期资本主义》试图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发现的资本主义运动的基本规律,去解释“二战”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换言之,本书试图证明:在当代资本主义的“具体”历史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抽象”运动规律依然在发挥作用,依然是可被证实的。因此,本书直截了当地反对当今社会经济思想的两种基本倾向。一方面,本书不接受在学术界或马克思主义者圈子里流行的假设,即认为新凯恩斯主义的手段、国家的干预、垄断势力、私人“计划”与公共“计划”或上述措施的结合(不同的作者或学派有不同的主张),能够抵消或消灭资本运动的长期规律。同时,本书也不接受相反的观点,即认为经济运动的规律是如此的“抽象”,以至于不可能在“现实的历史”中体现出来,故而经济学者能够做的只不过是揭示与解释经济运动规律在其发展中是如何以及为何受到偶然性因素的影响而发生扭曲或偏离的,而不是去揭示经济运动规律如何体现在具体的、可见的历史过程中,得到历史过程的证实。
近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复兴(正如笔者之前预估的),是近年来特别令人振奋的现象。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由眼下年轻一代的社会主义学者与工人承担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史的再诠释,是一项要求严格的艰巨任务。对于身处英国的读者来说尤是如此,他们不知晓本书(例如第1章和第4章)讨论到的大多数古典大家。笔者之所以谈及发生在1939年之前的“久远”辩论,和所谓的虔诚与博学无关。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言,那个时代的重大争论直接涉及由资产阶级社会的长期趋势与基本矛盾造成的关键问题。眼下,这些问题仍然和我们密切相关。法西斯主义与斯大林主义最终让参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争论的早前繁荣时期的几乎所有理论家噤声不语。但它们无法消灭这些理论家的思想遗产。如果不能充分地复兴这些思想遗产,要想解决当前资本主义的核心问题,将会面临更大的困难。
在最近十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复兴,是和新李嘉图学派(受皮耶罗·斯拉夫启发的剑桥学派是领导力量)对“新古典”边际主义的批判同时出现的。笔者尽管欢迎任何对劳动价值理论(哪怕是马克思主义出现前的版本)的正名,但仍然坚信在新李嘉图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综合。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义务捍卫马克思对李嘉图的所有重大的超越,新李嘉图主义者正在做的就是要抹掉这些超越。本书并不研究李嘉图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但有一点是它要关注的:在平均利润率的构成中,武器生产的角色;换言之,即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化的问题(第9章会简要地予以讨论)。
对笔者来说,写作本书时面对的最大困难是:罗曼·罗斯多尔斯基(Roman Rosdolsky),这位无论是在理论交流还是政治上都与我关系最为密切的政治经济学家,在我动笔前就已经离世了。因此,对我们共同讨论的回忆以及对他的遗作《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Zur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s Marx’schen Kapital)的研究,将会最大限度地替代对这位极具才华的理论家的建设性批评。
柏林自由大学政治科学系的社会主义学生及助理讲师曾在1970—1971年的冬季学期邀请我前往该校担任访问教授。他们让我有种“外部压力”(对于一位作者来说,这经常是必需的),以综合的方式(也就是本书)去梳理自己对晚期资本主义的理论观点。他们也让我有时间去完成这项工作。
我把此书献给我已故的朋友与同志罗曼·罗斯多尔斯基。在他的帮助下,西乌克兰共产党得以成立,他也是该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他帮助建立了乌克兰西部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其一生中,他一直忠诚于工人阶级解放与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事业,并且在这个动荡世纪最为黑暗的岁月中,延续了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同时,我想将此书献给柏林自由大学的社会主义学生与助理讲师,他们将以批判性的、充满活力的智识来延续这一理论传统。
原载《晚期资本主义》英文修订版,英国新左派书社(New Left Books,原Verso出版社),1975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