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mn:乌托邦黑客
编译自:Utopian Hacks - Limn,作者:Götz Bachmann
在奥克兰的一个实验室里,一群精英而非正统的工程师正试图重新想象计算机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正是在这里,在这个位于硅谷的实验室里(或在靠近硅谷的地方,这取决于你如何划分它的边界),我正在进行的民族志以此为基础。这个团队聚集在一个名叫Bret Victor的工程师周围,是YC研究中心人类进步研究社区(Human Advancement Research Community,HARC)的一部分,这是一个由行业资助的研究实验室,致力于开放和基础性研究。“黑客”是指这个群体的成员,就像许多其他工程师一样,充其量是一个用于尝试性工作的词(例如:“这只是一次黑客攻击”),或者是指将技术用于其他目的,而不是最初的目的。它也可以是一个贬义的术语,指的是没有考虑到业余的、低质量的技术开发所积累的后果。因此:当我研究的工程师描述他们的工作时,“黑客”不会是他们会选择的关键术语之一。然而,我想说的是,他们的一些工作实践与黑客行为有相似之处,尽管是在不同的领域。这篇文章问:工程师如何破解想象中的技术是什么,可以是什么?
我通过分析这些工程师来论证这一观点,我称之为“激进工程”,因为没有更好的术语。激进的工程师从根本上挑战现有的技术(这里指数字媒体)概念:它们的基本特征、目的和可能的未来。他们的激进性不能与政治激进性、“颠覆性”的激进性或某些工程成果的激进性相混淆。他们的激进性使他们置身于更广泛的工程领域之外,而这些领域是显而易见的、不言而喻的、经过时间考验的或是可取的。他们的立场是如此的异端,以至于他们常常不再称自己为“工程师”。但没有其他词可以取代它。他们可能会尝试使用“艺术家”或“霍斯特·里特尔方式的设计师”这样的词,但两者都不稳定,都容易引起误解。毕竟,这些人都受过电气工程、机械工程、计算机科学或数学等学科的教育,他们的工作往往需要解决高度复杂的技术问题。
Bret Victor的团队试图建立一种新的媒介。要达到这个目的,与其说是一个突然的灵光一现的问题,不如说是一个永久的、顽固的、超越现在所能想到的东西的过程。实验室采用现有的技术,如投影仪、相机、激光、白板、计算机和围棋子,并将它们与关于编程范式、系统设计和信息设计的新的或历史性的想法,以及一系列关于认知、交流、社交、政治和媒体的假设和愿景进行重组。该团队正在为一个空间动态媒介构建一系列的操作系统,每个操作系统都是基于上一个操作系统的构建经验,每个操作系统的构建大约需要两年的时间。当前的操作系统被命名为“Realtalk”,它的前身被称为“Hypercard in The World”(这两个名字都是为了致敬历史上的、非正统的编程环境:1970年代的Smalltalk和1980年代的Hypercard)。当这个团队开发这样的操作系统时,它涉及编写和重写代码的过程,以及宣言,大量的谈话,甚至更多的集体沉默的时刻,迭代和调整的咒语,消化电影和书籍,以及大量的技术论文,并建立几十个——实际上是数百个——硬件和软件原型。
实验室里到处都是原型,每周都会有新的原型被添加进来。在一个月内,参观者可以用激光对准图书馆里的一本书,投影仪就会将这本书的内部内容投射到她旁边的墙上。几周后,你会看到人们在地板上跳来跳去,玩“激光袜子”的游戏:人们试图用激光照射彼此的白袜子。几个月后,一张桌子变成了由投影仪发出的光做成的弹球机,猫咪的视频跟随在纸上画出的每个矩形周围。目前,该小组在空间媒介中实验“小语言”:基于纸、笔、剪刀、围棋棋子或线的特定领域编程语言,都具有动态属性,因此具有直接指导计算或可视化复杂性的能力。所有这些原型的重点不是那种炫目的技术复杂性。事实上,它恰恰相反。原型的目的是简单和简化——根据经验,你可以假设所涉及的代码行数越少,这些行数越简单,原型就越被认为是成功的。

尽管这些原型很有趣,但它们仍然是“工作的人工制品”(working artefacts),用“自我运动的幻觉”(illusions of self-movement)为潜在的可能性形成“陷阱”(traps)。在Bret Victor的研究小组中,原型的工作是为了捕捉和展示一个新的、空间的、动态的媒介的潜在属性。由于其理想的属性之一是简单性,那些显示这一属性的原型往往被选为成功的。每隔两年左右,整个过程就会产生一个新的操作系统,然后允许构建全新一代的原型,这些原型通常(尽管不总是)基于各自目前的操作系统的能力,同时已经在探索下一代的潜在能力。总体目标是创造一种根本性的突破,一种相当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技术飞跃,当时微处理器、个人计算机、图形用户界面和互联网的四重引入,通过将计算机变成一种媒介而彻底改变了计算。将计算变成媒介,在1960和1970年代已经意味着要与技术对抗技术:通过使用新的计算能力,一种媒介被创造出来,它不太符合当时人们对计算机“是什么”的认知,而更符合形成纸张动态版本的媒介可能是什么样子。在Bret Victor的研究小组的工作中,这种用计算对抗计算的工作形式变得激进起来。
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现实生活中,这项事业的守护神是艾伦·凯(Alan Kay),他是最著名的激进工程师之一,也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计算机领域那些突破的关键贡献者,Bret Victor的团队试图在今天赶上这些突破。让我们了解一下艾伦·凯(Alan Kay)。20世纪60年代,他在犹他大学新成立的计算机科学系开始工作,撰写了一篇堪称有史以来最大胆的博士论文之一,一个关于新型计算的疯狂技术梦想。论文的开头引用了另一位激进的工程师绝望的呼喊——“我希望这些计算是用蒸汽来完成的”(出自查尔斯·巴贝奇)——在对“反应式引擎”(reactive engine)进行了250页的思考后,论文的高潮部分是一本虚构的“Flex Machine”手册:这是一系列想法的第一次迭代,几年后在艾伦·凯的“DynaBook”(1972)的愿景中达到顶峰。在研究这篇论文的时候,凯成为了由五角大楼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IPTO)资助的研究团体中的年轻人之一,该办公室当时正朝着建立阿帕网(ARPANET)迈出第一步。20世纪70年代初,在斯坦福大学的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那里做了一段时间的博士后后,凯加入了鲍勃·泰勒(Bob Taylor)新的施乐PARC研究实验室,在那里,工程界的传奇人物如兰普森(Lampson)、萨克(Thacker)、梅特卡夫(Metcalfe)和许多其他人,正在构建ALTO系统,这是第一个连接具有高级图形能力的独立机器的系统。
一旦ALTO/Ethernet系统的第一次迭代——理解后者是一个系统而不是独立的计算机是至关重要的——开始运行,它们为艾伦·凯提供了一个强大的游乐场。艾伦·凯回顾了他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些工作,当时他分析了SIMULA(一种晦涩的挪威编程语言),并与Dan Ingalls和Adele Goldberg,以及其他一些人一起,开发出一种介于编程语言、操作系统和儿童玩具之间的混合体——Smalltalk。Smalltalk的第一次迭代是面向对象的实验,目的是在分布式消息传递系统之后从头开始对所有编程进行建模:后来的版本放弃了这一点,在最初的成功阶段之后,Smalltalk最终输给了C++和Java等语言,失去了面向对象的主导地位。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ALTO/Ethernet/Smalltalk系统成为了关于图形用户界面(GUI)以及许多现在常见的应用程序的思想爆炸的温床。因此,凯和他的“学习研究小组”的工作既可以被视为一个丢失的计算圣杯,它被资本主义在硬件和软件上铸造的计算模型破坏,也可以被看作是其后来出现的关键谱系中心之一。而正是这种双重意义,使得这部作品至今仍是如此独特和有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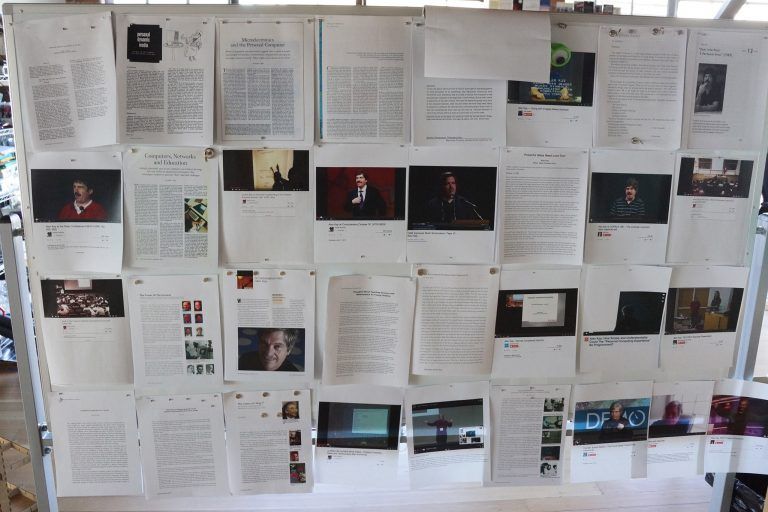
艾伦·凯(Alan Kay)对计算历史的贡献是他那个时代对计算范式和想象的彻底颠覆的结果。Kay采用了像SIMULA开创的非正统的编程技术、像Sutherland兄弟开发的新的可视化技术、McCarthy对“私人计算”(private computing)和Wes Clark的“孤独机器”(lonely machines)的渴望、道格·恩格尔巴特(Doug Engelbart)小组的增强实验,以及关于分布式网络的新想法等等。这种技术在新兴的软件工程和编程专业中并不常见,但已经开始在艾伦·凯(Alan Kay)工作的精英工程圈子中流传。艾伦·凯(Alan Kay)将它们与玛利亚·蒙台梭利(Maria Montessori)、西蒙·派珀特(Seymour Papert)和杰罗姆·布鲁纳(Jerome Bruner)关于教育学、心理学和数学的思想结合起来,并通过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时髦的媒体理论推测,进一步增加了活力。凯也很早就理解了卡弗·米德(Carver Mead)所谓的“摩尔定律”的含义,这是一条由大规模生产的集成电路引发的越来越小、越来越快、越来越便宜的计算形式的指数线,现在导致了技术发展的正反馈和新市场的创造。因此,艾伦·凯(Alan Kay)把所有这些想法、愿望、技术和机会重新组合起来。其结果是对一个新的和正在出现的社会技术想象的重要贡献,在许多方面代表了计算机作为一种数字媒介,这是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因此,艾伦·凯(Alan Kay)的工作可以被视为激进工程的基准,因为这样可以让我们批判目前大多数关于技术的想象的僵局和可能的质量下降。
但是真的那么容易吗?激进工程仅仅是一点混合的结果吗?显然,这是一个更加复杂的过程。对这一过程最有说服力的描述之一,源于另一位传奇的激进工程师,即前面提到的道格·恩格尔巴特(Doug Engelbart)。1962年,在艾伦·凯(Alan Kay)开始职业生涯的几年前,恩格尔巴特为他自己的美国空军资助的斯坦福研究所的研究小组制定了这个项目,目的是重新设计“HLAM-T”,即“人类使用语言、人工制品和方法论,他在其中接受训练”(Human using Language, Artifacts, Methodology, in which he is Trained)。这个HLAM-T一直是一个半机械人,因此它可以参与一个持续的“增强人类智力”(augmenting human intellect)的过程。恩格尔巴特认为,后者可以通过“bootstrapping”(引导)过程实现。在硅谷,这个术语可能意味着很多事情,从启动系统到启动创业公司,但在恩格尔巴特的工作背景下,“bootstrapping”(引导)是“……有趣的(递归的)任务,即开发工具和技术,使其更有效地完成任务。其有形产品是一个正在开发的增强系统,为增强系统的开发和研究提供了更强的能力”(…interesting [recursive] assignment of developing tools and techniques to make it more effective at carrying out its assignment. Its tangible product is a developing augmentation system to provide increased capability for developing and studying augmentation systems)。正如摩尔所谓的定律一样,这是一个从非线性、自我执行的反馈中出现的指数级进步的梦想。你还能更像加州人吗?
为了使Engelbart和English的描述不仅仅是一个控制论的白日梦,我们需要提醒自己,他们不仅仅是在谈论技术人工制品。简单地用原型构建原型并不是激进工程的明智之举:一旦投入使用,原型往往会崩溃;因此,对于开发进一步的原型,原型工具集并不是非常有用的。因此,“bootstrapping”(引导)作为一个过程,只有在我们假设它是一个更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其中“工具和技术”是在较长时间内随着社会结构和本地知识而发展的,bootstrapping方法才能发挥作用。过程是递归的,很像Chris Kelty描述的自由软件开发社区的“递归公众”(recursive publics):在这两种情况下,开发人员都创建了社会技术基础设施,他们可以通过这些基础设施进行交流和合作,然后传播到生活的其他部分。Kelty展示了这种递归效应不仅仅是自我强化正反馈的神奇结果。递归过程是基于政治、资源、合格的人员、关心和指导。简而言之,它们需要不断地生产。
因此,bootstrapping可以采用不同的范围和方向。尽管Engelbart和English的项目听起来雄心勃勃,但至少在1960年代,他们仍然相信在一个研究小组内进行bootstrapping会达到预期的效果。艾伦·凯的学习研究小组在20世纪70年代通过教育学和麦克卢汉媒介理论扩展了这种设定。通过引入儿童,他们旨在实现超越实验室的递归效应(recursive effects),长期目标是让整个世界都参与到类似于bootstrapping的过程中。Bret Victor和他的研究小组的bootstrapping方式就像一个多层洋葱。什么样的人应该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以及在什么时候,会导致激烈的内部讨论。一旦该小组推出“Dynamic Land”,它将进入下一个阶段。与此同时,bootstrapping已经采取了多种形式。原型涉及到bootstrapping的过程,如指针、触角、搜索、即兴重复片段、脚手架、操作系统、阻塞、表现、想象的测试用例、演示等等。事实上,在更大的bootstrapping过程中,包含了大量的原型技术。在实验室里,他们一起产生一种坐在大脑里的感觉。实验室作为一个整体——它的墙壁、桌子、白板、屋顶、机器和住在里面的人——充当了替代媒介的第一个演示。

构建操作系统系列的迭代可能需要更传统意义上的大量工程任务;例如用C语言编写内核,或用Haskell编写进程主机。但整体的努力显然不是由技术驱动的。在未来的空间媒介中,计算应该会减少。计算将扮演基础设施的角色:就像书籍需要光线,但不是模仿光的逻辑,媒介在必要时可以利用后台操作系统提供的计算可能性,但它不应该由它们驱动。相反,动态空间媒介应该受到媒介自身特性的驱动,也应该是对技术的驱动。这种媒介的特性还有待于bootstrapping过程的探索。用该小组的说法,无论是媒介还是他们生产这种媒介的方式,都是“来自未来”。这个未来不是给定的,而是取决于这个团体正在想象的媒介。因此,它取决于该群体正在探索、选择和实践的媒介的属性。一方面,技术催生了一种新的媒介,这种新媒介被想象成塑造未来,另一方面,未来被想象成塑造新的媒介,而新的媒介又应该驱动技术。
虽然这个小组的大部分工作是制造设备,但是思考也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后者使工程师能够理解原型工作揭示了什么。它还为实验室指明工作方向,激励了它的事业,也是获得资金的一部分。到目前为止,整个过程已经产生了一系列相互关联和不断演变的想法和目标:例如,一个小组是寻找新的方法来表示和理解复杂系统。第二小组旨在通过解除当代媒体的限制(如屏幕的限制,通过对复杂事物的“躲猫猫”式的访问,产生了难以理解的知识形式,比如数万亿行代码,写在屏幕上,然后盯着屏幕看),获得更多知识。第三小组探索了表现时间的新形式,第四组探索了将物理属性更有效地纳入空间媒介系统的新形式。所有这些集群会引领,所以目标和假设,更无缝的在“抽象阶梯”上下移动。似乎是为了用工程解决方案来呼应尼采、麦克卢汉或基特勒(Kittler)的媒体理论思考,一个更大的目标是让新思想成为可能,由于当代媒体的不足,这些新思想直到现在仍然是“不可想象的”。增强的具身认知形式,以及更好的合作产生想法的方式,可以治愈孤独和痛苦,这些往往是深度思考的一部分。引用一封内部电子邮件的话来说,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可能会“阻止世界分裂”。
理解这里发生的事情的一种方法是将所有这些都框定为另一种形式的“hacking”。当你“hack”的时候,你可以说是hacking apart或者hacking together。hacking apart可以被视为从拒绝接受以前的黑箱行为中发展出来的做法。转移到激进工程领域,hacking apart意味着不接受当前技术范式的黑箱,如基于屏幕的计算机,或现成的未来,如“智能城市、智能家庭”或“物联网”。相反,你会打开这样的黑箱,并对其进行剖析:关于什么被视为技术成功以及关于未来技术进步的假设,与某些版本的社会秩序相匹配,并经常与不健康的商业机会色情相结合。黑箱很可能还包含不同类型的工程师、程序员、设计师、经理等角色的想法。如果你把这些都拆开,你可能会看着这些元素,扔掉很多元素,扭曲其他元素,从其他地方添加一些元素,然后自己生长一些。你会研究不同的,通常是历史性的技术范式,以及其他关于什么在技术上是可能的(以及何时)的想法,关于社会秩序、美好生活和需要解决的问题的不同想法,需要阅读的其他书籍,媒介力量的不同用途,以及关于什么样的人和他们的专业或非专业的性质的不同观点,谁应该负责这一切。如果你幸运的话,你有条件和能力在一个漫长的、非线性的过程中完成这一切,这个过程也被称为bootstrapping,在这个过程中,你经历了多次hacking apart和hacking together的迭代,同时创造出关于技术应该做什么和可以做什么的根本不同的想法,并通过一系列的手段和实践来帮助塑造这些想法,并向自己和他人“演示”一些乌托邦可能并非遥不可及。这就是激进的工程师所做的。
虽然他们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来逃避技术解决方案的幻想,但他们并没有放弃通过建造东西来解决问题的工程方法,他们已经发展了一种方法,人们可能会称之为“激进的媒体解决方案主义”(radical media solutionism),尽管他们对后者也有矛盾的态度。为了避免误解:我和我研究的工程师都不认为真正的未来可以由一群在帕洛阿尔托或奥克兰的工程师单独拼凑而成。但我确实认为,像Engelbart、凯或者Victor的研究小组这样的激进工程师,在他们特定的、高度特权的位置上,为推动我们走向未来的复杂力量组合增添了一些至关重要的东西。我正在进行的实地工作让我对这里生产的东西感到好奇,许多参观实验室的人都同意,第一批“抵达”的产品确实令人震惊和难以置信。如果我们相信这个组织的自我认知,那么他们的技术就像黑客一样,只是为某一天可能到来的更大的事情提供暂时的临时解决方案。激进的工程师也会第一个提出同样的临时解决方案,如果停止开发并过早具体化,在贬义上是黑客的潜在来源。根据他们的故事,后者正是40年前发生的事情,当时的原型机过早地离开了实验室,进入了苹果、IBM和微软的世界,产生了大量的错误决策,导致人们现在盯着智能手机。
在这样的故事中,激进的工程师可能会采用回顾性的“本可以”的方式,混合着区别于“正常”工程师的痕迹。即使他们远离硅谷的创业文化,但他们对“加州意识形态”的隔绝可能并不总是100% 紧密。事实上,他们可能为硅谷主流提供急需的异端解决方案。然而,这些激进的工程师,却是那些旨在打破硅谷经常向我们提供的自由主义者、极权主义者和没有实权的幻想者的潜在盟友,无论是“狗屎互联网”还是“垃圾互联网”。从批判理论的角度,从社会运动的角度,或者通过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大多数硅谷当前可用的未来的概念上的贫困肯定可以变得可见。但是,如果我们把硅谷比作激进工程的乌托邦,它在思维上的胆怯也变得明显起来,而这种胆怯仅仅被它所造成的破坏所掩盖。

关于作者:Götz Bachmann是德国Leuphana大学数字媒体文化与美学研究所的数字文化教授和数字媒体专业学士的召集人。他目前也是斯坦福大学的访问学者。他是一位民族志学者,曾在德国的仓库工人、售货员和收银员中以及日本的Nico Chuu中进行实地考察。他还撰写了德国儿童漫画系列KNA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