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过的这是什么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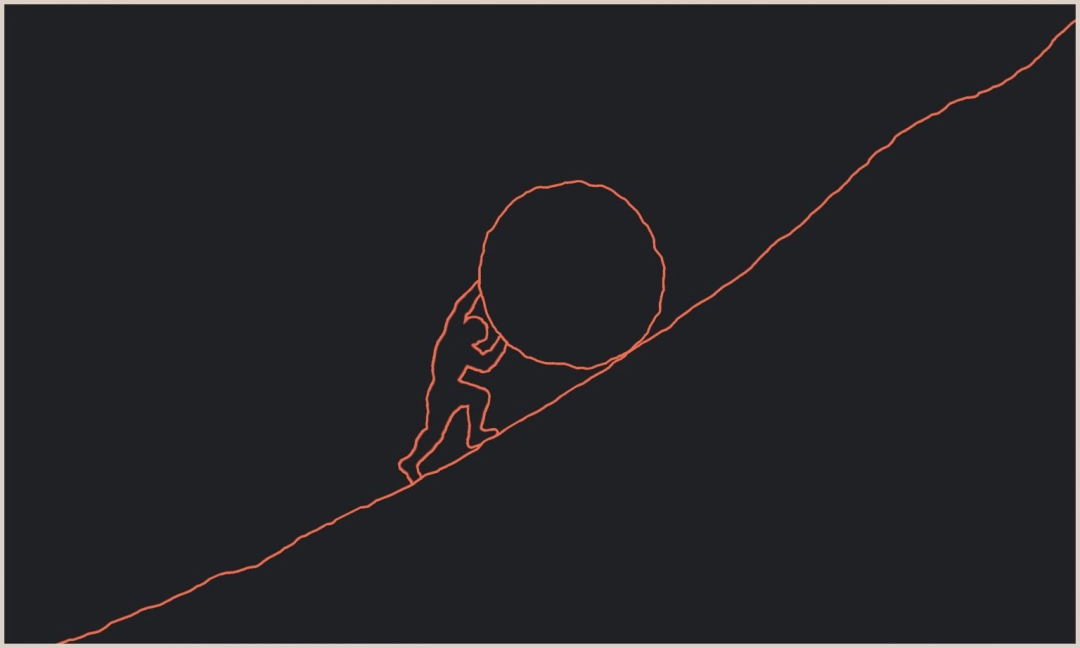
被封了近两个月,现在乡下很多老人也想开了。以前他们还指望着养儿防老,至少自己病重时有照应,但现在,别说是得病,就算是死了,再孝顺的儿女,也被封在上海回不来。
母亲说,很多老人都觉得自己已经活糊涂了,不知道这过的是什么日子,但又好像看清楚了,能好好地过一天是一天,别的都是空的,儿孙都是身外事,连原先几个最积极催婚催育的老人,都觉得无所谓了。
这种困惑和顿悟都是真实的,对中国人而言尤其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吴飞在《浮生取义》中曾说,中国人所理解的“过日子”与西方那种“赤裸生命”(bare life)的最根本不同,在于它是一种家庭内部的存在状态和政治状态,人们是在家庭中理解人性并活出人样的。
现在,防疫作为一种势不可挡的外部力量介入到这一有机的生活中,迫使人们独自面对一个陌生而庞大的无机物,那是一种卡夫卡式的困境:人们忽然发现自己被扔进一个根据直觉无法理解的逻辑所建构起来的世界里。
那就是阿甘本所说的“赤裸生命”:例外状态“能在一切语境下打散各种生命形式,终止它们与形式生命所保持的结合”,使所有人的自然生命直接暴露在主权暴力之下。在人与人之间的有机纽带遭到大规模隔断之后,个体的人赫然发现只剩下了自己,连繁衍血脉这样对中国人来说近乎宗教的信念也已丧失了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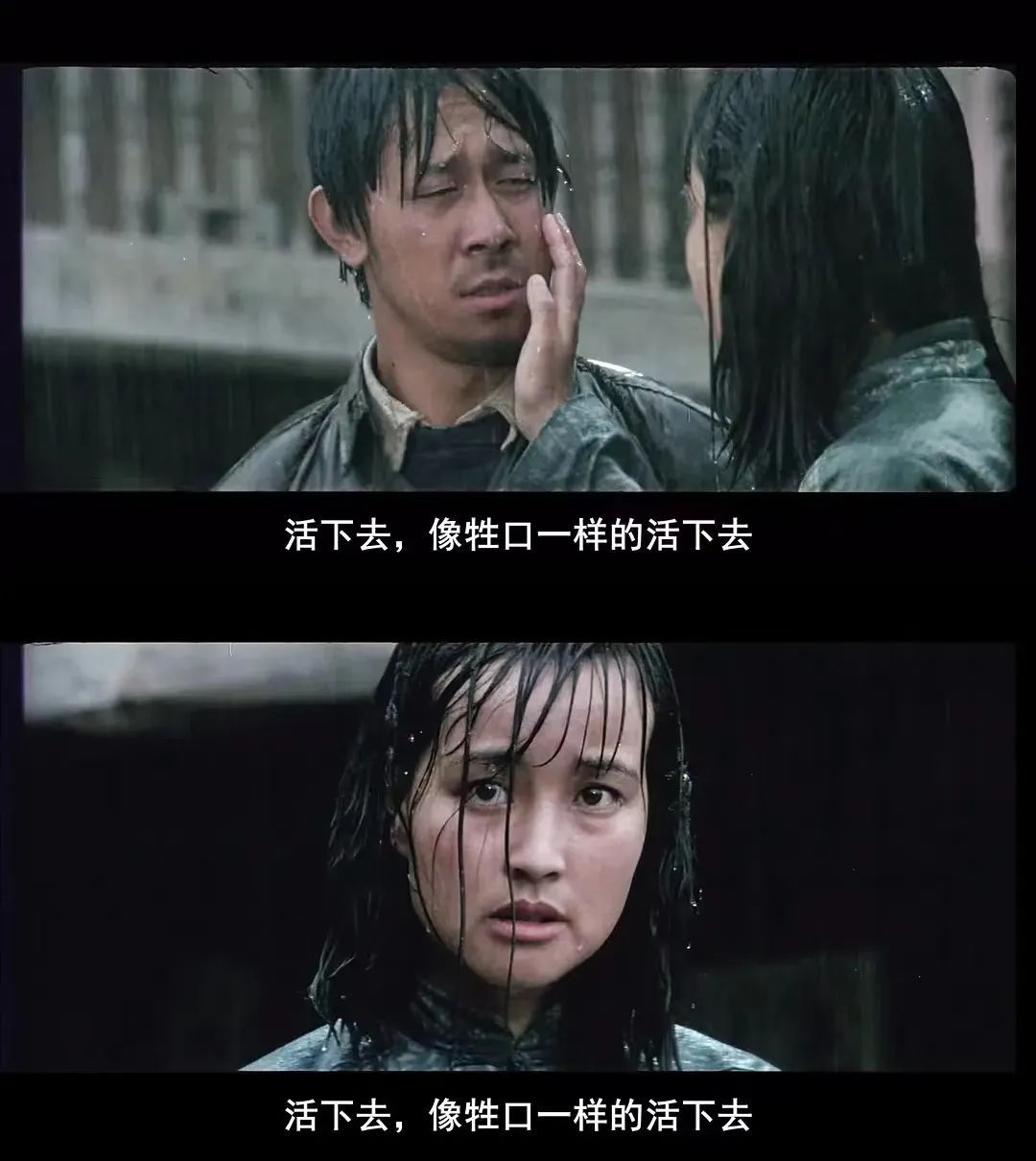
当然,我也看到一种说法:“赤裸生命”总比“没命”要好,所谓“好死不如赖活着”。这有时出自一种顽强的本能,但也有的时候,正是这种求生欲塑造了中国人的无底线的顺从和忍让——只要能活下去,没有什么是我们不能让渡的,甚至还不乏有人指责那些不肯让渡的人“矫情”。
5月5日,普陀区成为上海第一个社会面清零的城区,桃浦的居民领到出门证后,为首的举个牌子,20人一组,像小学生春游一样到指定的小超市购物,每人限购不超过300元。买完了,再原路返回,不能脱离队伍。
在郑州,有些市民因为未能遵守防疫规定,被要求在马路边罚站,承认错误并背诵防疫规定。在一段北京防疫贴封条的短视频中,对比了两户人家:一位大姐极力阻挠,非常不配合,而另一户男主人就非常“顾全大局”。
像这样的场景,这些天来已不鲜见,常常是作为笑中带泪的段子。这其中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成年人,无论他们内心是否真正认同,都像是被规训得相当乖顺的小学生。活着,在此意味着要成为一个遵守共同体规则的合格成员。
不论人们是否意识到,这难免会在他们的生活中造成一种无所不在的张力,因为这种重负威胁到人的完整性与本真性——为了满足自己所渴求的安全本能,你不得不屈抑自己,无法公开、充分地展现自我。这是一种“半自由之身”(half free)。
那就像契诃夫笔下的“套中人”别里科夫:“现实生活让他总是感到心神不安,让他害怕,为了同世人隔绝,不致受到外界的影响,他总想给自己包上一层外壳,给自己制造一个所谓安全的套子:哪怕在艳阳天出门他也总是穿着套鞋,带着雨伞,他的雨伞、怀表、削铅笔的小折刀等等。”

在此,“做自己”是有风险的,甚至堪称平凡人的英雄之举。在马路中间的倒立、对自己生活方式的捍卫,并不仅仅是冲动或矫情,它是某种让我们体验到自己存在的瞬间,由此确认:我还活着,还活得像个人样。
有时吊诡的是:人们体验到自我,往往并不是因为他们主动做了什么,而是他们发现自己丧失了太多,以至于只剩下了自我。也正是在此时,他们赫然发现,自己的顺从、配合,并没有换来作为一个人存在所应得的最低限度的承认。他们被无视了,也正是在这种被无视的状态中,他们看见了对方眼里自己的形象。
个人尊严就像空气:在稀薄的时候我们才充分意识到那是生存之本。在一个不断缩小的空间里,人们被迫专注于自我,有时是重新发现了自我。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像以往那样用某个社会身份标签来界定自己,虽然他们也许还没真正想明白现在需要成为什么人,但会越来越认同“我就是我自己”。外面那个宏大而喧嚣的世界逐渐变得像是荧幕上的一出戏剧,不知不觉中,我们的经验感知发生了可能是不可逆的变化。
伍尔夫有一句名言:“在1910年的11月,或者大致在这个时候,人类本性便发生了变化。”她以一个文学家的敏锐,捕捉到先于世界大战的那种风暴:随着一个相互协调的公共生活崩塌,现实变成多元异质、主观阐释的私人体验,人们只能在最小的私人圈子和个人处境中,在弱音(pianissimo)中,感受一种精神性体验,并由此重建人的价值。
也许多年后回望,这场疫情将被证明为我们社会的一次脱胎换骨:没有人能逃脱这样的体验,每个人都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在迷茫、挣扎和觉醒的阵痛中,有些人迎来了自己的第二次出生。那是一个新的自我。
“人的尊严”看似老生常谈,但在中国思想中其实是新事物。如果说西方是经历了文艺复兴的洗礼,在脱离了神的束缚之后才出现了“人”,那么中国的“人”从何而来?也许五四时是对“家”,冲决“家”的网罗才出现了独立人格意识,无论是当时还是之后,“人的尊严”主要是对抗外部主宰力量时而言的。
我知道,很多人把当下的自我屈抑当作一种战术性的隐忍,想着“回归正常生活”之后“重新做回自己”,但历史不可能只是简单的重复。疫情前的那种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何况现在人们所想的也是一个建构出来的过去而非真实的过去,就算我们想着“往回走”,事实上也还是在“向前走”。
无论疫情是否过去、怎样过去,个人的觉醒和自主选择是唯一的救赎之道,这需要我们每个人充分体认到对生命的尊重,活出人样。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里,当你真正意识到,没有什么能真正凌驾于人的尊严之上时,会获得一种平静的力量,我想,那就是孔子所说的,“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