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的神话》读书笔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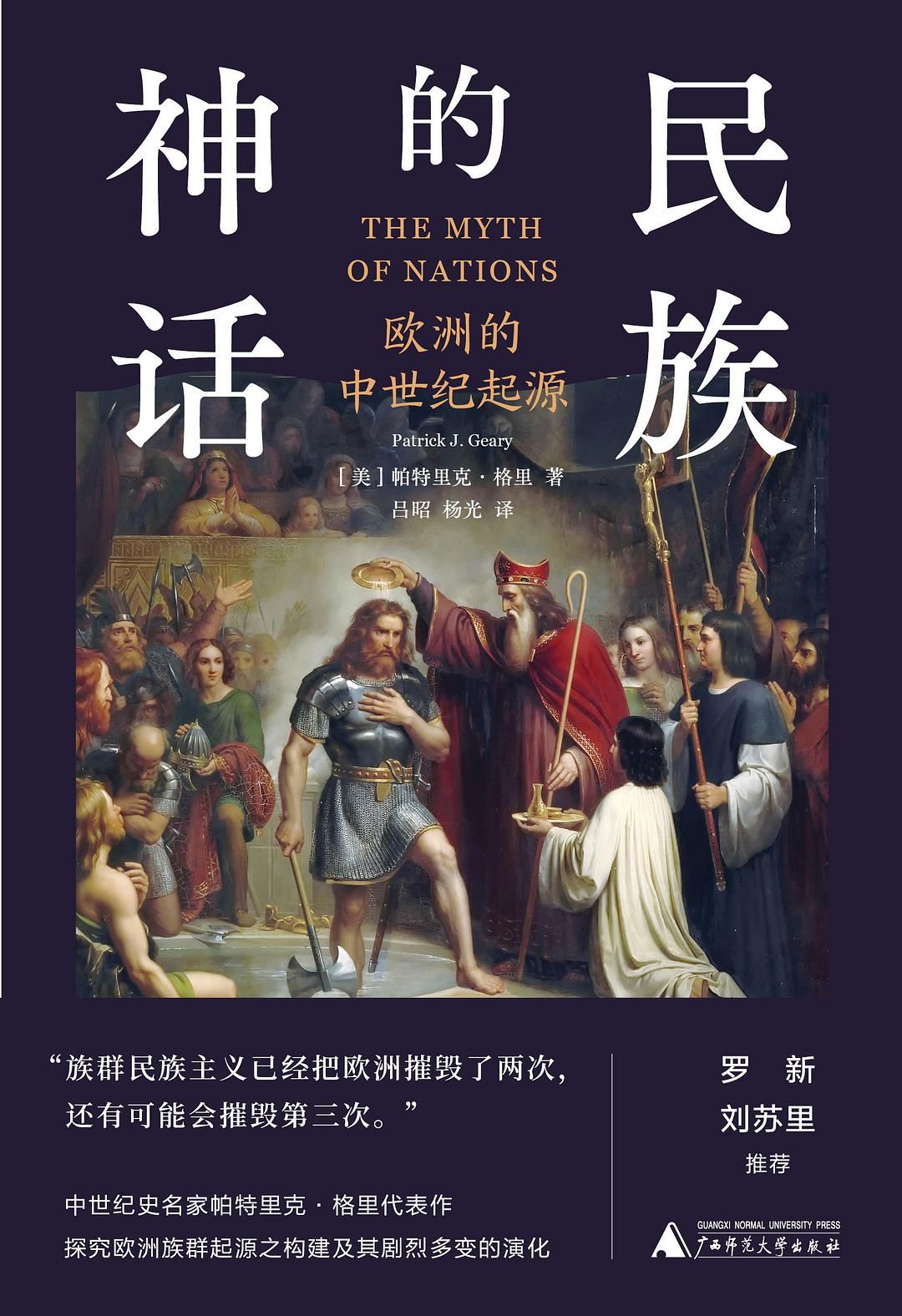
一
正如许多人已经叙述的那样,《民族的神话》一书是在对古典时代欧洲的民族观、罗马帝国晚期以来的民族大迁徙和融合过程做一叙述,指出“欧洲所谓的民族不过是在欧洲中世纪早期所形成的一种‘迷思’,是一个被构建起来的神话。”
其实,这种民族是“迷思”和神话的观点,自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就成为了民族研究学界的共识之一。以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为代表的建构主义者,以费雷德里克·巴斯为代表的人类学家对本质主义者(他们认为民族从古就有,其结构、特征与边界恒定)进行了强有力的挑战。但在现实生活和历史学的一些领域中,本质主义论述仍然顽固的占据着自己的地盘。在这些领域,人们总是倾向于对某个人群的由来给出一个单线解释,总是在强调它们的边界的稳定性。这可能是由两个方面的原因构成的——一方面当然是出于现实政治需要,人们需要简化历史,需要让现实反照过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那些古籍中就是这么记载的。古代历史学家们眼中的世界往往是条理分明、各有本源的,他们的这种理解和描述世界的方法至今仍影响着我们。
《民族的神话》就从这两个方面入手反驳之,作者帕特里克·格里一方面讲历史阐述欧洲各古代族群的变迁、融合与分裂,另一方面也对古代人的民族观进行了剖析。对前者,有很多人已经称赞作者有极精当的勾勒,此处就不赘述了。后者似乎还少人谈到,那么本文就试着讲述一下格里的叙事逻辑。
格里从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谈起。“希罗多德在叙述希波战争的起因时,同时开创了历史写作和民族志写作”(第36页)。在对当时的世界进行描述时,他按照地理和文化将众多的族群按部就班的安排在世界的不同角落。而且,他通常将族群的起源归结为某位共同祖先。在他的世界图景中,各民族就像孤岛一样存在,方便辨认。当然,希罗多德对族群的描述并不是刻板到一无是处。首先,希罗多德可以说是一个文化相对主义者,他对他人(蛮族)的文化并不持贬斥意见;其次,希罗多德在认定族群的时候,并没有完全按照客观标准(如风俗、血统、地域和政治形态)进行分类,也强调人们的主观认同;再次,希罗多德感知到了历史的变化和族群的演化,在他的笔下,族群是可以诞生和消灭的。
对于后来的罗马历史学家,如普林尼,来说,这三个“缺点”是无法容忍的。野蛮人必须比文明人要低劣,分类的方法必须更客观,更有秩序,族群应该具有永久性——可以变化,但内核一致。这样才能画出一幅清晰的、等级分明的世界地图。普林尼本人就坚持通过族群的居住地来区分不同的族群,将多瑙河以东的所有蛮族部落一概认作斯基泰人。在他的《自然史》一书中,普林尼更追溯既往,将一个新族群看成是老族群的变形——“一个老族群可能会获得一个新名字、一些新的风俗和特征,甚至是与之前截然不同的风俗和特征,但是,有洞察力的罗马人依然能够凭借对这个族群之前特点的了解而认出它。”(第45页)
假如罗马人认识外部世界的方法非常的简单粗暴,那么他们看待自己的方式却颇现代。格里指出,无论是维吉尔还是李维都能认识到,罗马人自己是从不同的蛮族中演化而来的,是政治融合的结果。换句话说,罗马人是一个制度性、法律性和政治性的存在。其他的族群是地理、文化和语言的“奴隶”,他们的身份是与生俱来的,而只有罗马人才是选择的产物。
这种看法,不得不让人联想起现代法国人和瑞士人的民族观。比方说在1882年法国人类学家勒南在索邦大学发表过一场著名的演讲,题为《民族是什么?》。勒南提出,构成一个民族的根本性要素是其成员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意愿。民族就是社会契约,是自由、平等的公民个体以理性、自愿的方式所组成的集合(勒南的这一观念很好的对应了法国的现实——法兰西民族并不基于语言、血统、种族、地理和文化标准之上,而是政治与社会构建的产物)。如果一个罗马人见到勒南的这篇演讲,一定大加赞同,认为这说的就是罗马。
这种内外观在罗马帝国基督教化的时候,又被基督教徒们进一步强化了。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徒既继承了古典民族观,又继承了以色列人的衣钵——以色列人恰好自认为也是由与上帝的约定构建起来的,而非仅仅是个血缘团体(当然,由于传教的需要,基督教徒们也需要看轻人们的先天身份)。“拉丁教父们把上帝之城的子女们看作是一个根据律法构建出来的社会群体,这个群体与罗马人和以色列人一样,都以法律和契约为基础。”(第52页)。至于蛮族,自然都是卑贱的自然群体。
到了古代晚期,发生了两件事。一是非公民与公民界限的消失。帝国境内所有人是被皇帝的一纸诏令统统授予公民身份的,帝国已经腐朽堕落,公民身份所蕴含的那种契约共同体精神已不复存在。而既然如此,人们开始迅速收缩到地方认同和血缘认同上。第二件事则是帝国为了军事需要,允许大量的蛮族进入罗马帝国的版图和社会生活中。这些新来的蛮族的自我认知受到了古典民族观的重大影响——他们虽然拥有武力,却居于“文明”下游,为了抬高身份,就必须寻找一个古老而荣耀的祖先和历史传统。这种荣耀当然只能在古典作家的历史典籍中找到。格里认为,古代晚期历史学家卡斯多里乌斯宣称,他“把哥特人的起源变成了罗马史”,就是这个意思。
在以上两件事——罗马人的契约、法律社群意识消失,蛮族有意识的通过将其集体记忆“世谱化”和重新勘定源流等大规模的文化动员来构建一个血缘共同体(这是早期的“想象的共同体”)——的推动下,古典民族志中的内外差别逐渐模糊、消失,罗马帝国分裂成一个又一个血缘和地方团体割据的世界。这样,古典民族志所依据的世界虽然消失了,它塑造的世界观却永久遗留在了现实中。
格里接着通过对历史的分析指出,在罗马帝国后期和崩溃后,各族群的语言、宗教、政治和社会组织形式都有很大的改变,但是族群的名称却没有发生改变(这是因为不断的被不同的人借用、攀附的缘故)。“这些名称就像舰艇一样,在不同的时间里装载着不同的内容。名称是可更新资源,它们能说服人们相信连续性的存在,即使不连续是活生生的现实。”(第132页)他的结论如下——“古代晚期和中世纪早期欧洲族群的历史不是关于最初时刻的故事,而是关于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的故事。它是一个关于盗用和篡改历史上继承下来的名称和表述来创造现在和未来的故事。”(第181页)。
以上,格里用简单的篇幅说明了一个道理——当代民族主义者认祖宗的行为是非常荒谬的,让•勒庞所想动员的法国人并不是查理曼的法兰克人,米洛舍维奇所动员的塞尔维亚人跟古代塞尔维亚人的关系也极微弱。格里辛辣的批评道:“一般来说,无论是在霸权国家还是在有抱负的独立运动中,‘我们曾经是一个民族’的说法实际上是在表达要‘变成’一个民族的诉求,这种说法不是以历史为基础提出的诉求,相反,它是一种创造历史的尝试。”(第29页)
二
正如前述,《民族的神话》一书是对各种“自古以来”的一支投枪。这本书虽然谈的是欧洲之古,但我看的时候,忍不住反思中国,却也严丝合缝。
如果说希罗多德是开创古典民族志的那个欧洲人,那么在中国,相同的人物就是太史公司马迁。翦伯赞、郑鹤声和白寿彝等现代史家都指出,太史公在《史记》中开创了专门的民族史书写,为北胡、西戎、东夷、南藩、远蛮立传,目光远大,开风气之先。与希罗多德相似的是,太史公也将世界与历史看成是一个井井有条、有延续性的系谱。比如王明珂先生在《论攀附》一书中直接指出,“以选材与制造来说,司马迁显然承继并发扬一个以英雄圣王为起始的线性历史,以结束一个乱世的征服者黄帝为此历史(时间)的起始,以英雄征程来描述英雄祖先所居的疆域(空间),以英雄之血胤后裔来凝聚一个认同群体(华夏)。”这种线性历史观很显然不止是用在华夏身上,对夷狄,其实太史公的操作也是一样的。比如《匈奴列传》中说匈奴种族渊源:“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 几乎是毫无例外的,太史公将各族群的起源都归于一位“英雄祖先”。
与罗马人的内外有别相似,太史公也是“内华夏、远夷狄”。姚大力先生在《司马迁和他的史记》一书中指出,“史记之受传统夷夏观的影响,不可谓不深矣。”中国与外国两相对举,中国在上,外国在下。同普鲁塔克一样,太史公区分族群的方式也是比较武断的。“川南、云贵操壮侗、藏缅等语言群的诸族,就全被它(注:史记)归入西南夷范围。”姚大力先生非常遗憾的认为,司马迁在写作史记的时候,错过了利用最新地理资料来扭转传统的世界秩序观的珍贵机会。“史记以其巨大的文化影响力,事实上又有力的强化了此种以夷夏差序、中国独大为特征的世界秩序观。”
东西历史学家不约而同的展示出共同的民族志观,倒不难理解其缘由。一方面是由于优势文明对周边的骄傲,另一方面也是出自一种人类心灵领域重要的认知倾向——人们总是试图将复杂和互不相关的事件压缩进一个连贯一致的模式中去。正如弗朗西斯·培根说过的那样,“人的理解具有特殊的性质,很容易将事物视为处于高度秩序和平衡状态,实则并非如此。”人们总是试图尽可能多地解释他们周围发生的事情,而且总是偏爱一个原因单一的解释。此外,在对外界的观察中,人们总是喜欢给人、事给出一个稳定不变的性征,而漠视其情景与变动。这种认知偏差是如此的普遍,以至于社会心理学家们给予了一个专门名词“基本归因谬误”来加以形容。
少数族群在进入文明内地之后由于政治需要根据已有文明典籍构建自身这种事,在中国也很常见。王明珂先生在《论攀附》一文中就指出,古代中华周边的边缘族群攀附一位“英雄祖先”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汉晋时期中国北边的“五胡”多攀附黄、炎帝或其子孙为其祖源。辽人耶律俨在《辽实录》中也提出契丹是黄帝之后。金、蒙古和满洲女真人对于攀附炎黄虽不感兴趣,但也各自将自己的祖源攀附至先代。比如《金史:世纪》中记载,“金之先,出靺鞨氏。靺鞨本号勿吉。勿吉古肃慎地也。”这就将金人祖先推到了先秦。在《蒙古黄金史纲》和《蒙古源流》等书中,明清蒙古人自称是吐蕃后裔(这自然是信喇嘛教的结果)。姚大力先生在《“满洲”如何演变为民族》中也指出,“构成明代女真的主要成份,实际上应是猛安谋克女真时代那些边缘部落(如兀的改人)的后裔”,是满洲统治者为了政治需要,才从汉文文献中借用、接续了金朝统绪。
简而言之,如果说格里作为一个欧美公共知识分子,对欧洲人的“自古以来”进行了反思,作为中国人的我们,其实也不妨反思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有一个线性和静止的历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