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迴響】那場火還未燒完:走過抗爭烽煙的中大校園和三個學生的日常
時間過得太快。由2019年到2021年,時間比起過往太沒實感。
自2021年9月開學,中大人終於久違地回到校園實體上課。校巴站前擠滿到現在都還不熟悉中大地形的各級學生。中大人曾標誌性的頹Tee、拖鞋穿着幾近絕跡。出入口的保安亭變成一根實體的柱,保安在旁邊看着,員生要拍卡後才能通過。
在這一年的畢業禮前夜,Ruby 從大學圖學館裡走出來。讀書累了,就拿出滑板舒壓。踩到畢業禮帳篷旁,一個保安離遠就高呼叫她不要踩。Ruby 心想:「你追到我才算吧」。脫離保安後,她又覺得不忿啦,在保安面前兜多一個圈示威才離去。誰知保安快步踏在滑板前面,截停 Ruby 道:「欸呀,不要在這裡亂來,我們要有秩序......」Ruby 無奈地心想:其實我直接駛過去,該害怕的是你。
剎那間,她察覺到這個明顯是外來的保安。她很久沒遇到這種只會嘮叨的保安了。中大保安組的保安,在這兩年間已經習慣了狐假虎威、「揸住雞毛當令箭」,一見同學不服從就會直接恐嚇,拿出手機拍照。
她摸摸頭。最近她染上了粉紅色頭髮。這是她許久以來的心願。
中學的時候,名牌女校裡的校規都很嚴,也不鼓勵個人意志。她中五那年,雨傘運動爆發。在佔領區走了一圈,一個個不同顏色的帳篷上寫着主人自己的命名,自發掃垃圾的人邊走邊說:「有沒有梁振英?」
但身邊沒有人陪伴。在班內的群組,同學說甚麼 “everything they do is legitimate and the police have every right to do anything……”(政權跟警察有絕對的權威做任何事) 她跟同學吵架後,又自我懷疑學識會不會太少。後來同學成了她女朋友。
不久,她剪了一頭短髮,枕部剷得光光。中六的聖誕派對,她心想,又有派對又會拍照,便 gel 了個頭(為頭髮上髮蠟)。到校門前,訓導老師瞪着她:「為甚麼 gel 頭?學校不可以呀。」老師叫 Ruby 到洗手盤洗乾淨頭髮,再用乾手機吹乾。
Ruby 無視了她,回到班房。訓導老師就跟她班主任告狀,生氣到要哭的樣子,班主任就帶 Ruby 到洗手間料理一下頭髮。
Ruby 到洗手間裡看着鏡子。如果用洗手盤的水沖洗頭髮,根本洗不走髮蠟,頭髮反而會以古怪的形狀挺起來。她最終甚麼都沒有做就走出去。
班主任看看她,就說,你的頭好了點呢。好吧,我們回去吧。
進大學後,她終於不怕染髮。但髮廊的人總是叫她不要染太鮮豔的顏色。她總是染成灰色。
前女友到外國讀書。她在大學裡,想過做學生報,但又覺得吃力不討好。政治的東西好像太「硬」,不如先讀多點性/別的東西。「我以為會沒那麼政治,可以做個很社交很酷很chill的人。誰知最後都是無可避免地憤青了,哈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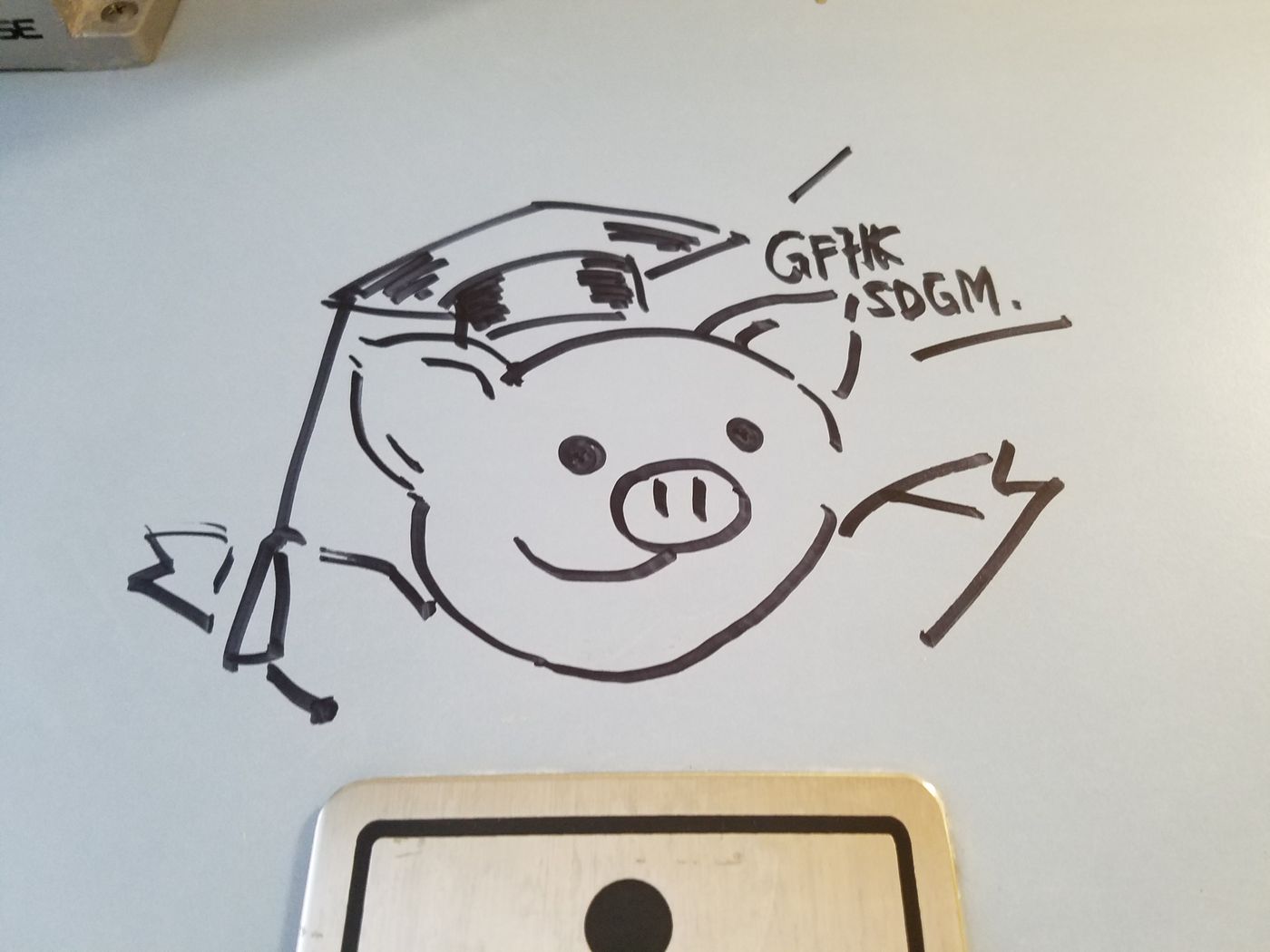
瓜瓜在一個模特人偶上畫上了乳頭。“Free the nipple” 的理念,她打算用公開展示的方式,挑戰其他人的感官認知。
昨晚,她參與 Ann 等人的會議。旁聽的時候,她覺得自己擺脫不了自己。
她想擺脫軀殼的限制,想體驗各種異質的經驗。所以她去當服務員。也想露宿在街頭。朋友阻止,就改為露宿天台。
「但我覺得都體會不到其他人的感受。因為我做的都是我自己選擇去做的。我住天台不是因為我沒家住,沒有那種迫於無奈的感覺。」
即使在「珊瑚」裡亦然。「我覺得這種孤獨不是其他人帶給我的,是逃不去、無法避免的孤獨。孤獨是我這個在講話的腦子被限制在身體裡,不論我怎麼跟你講我在想甚麼,我們還是兩個獨立的個體。所有一切無論其他人贊同不贊同,都要我一個人承擔。每個人都是這樣。」
一年前,「珊瑚」的朋友在她身上畫身體彩繪。她讓朋友畫「自由」兩個字在胸部上。
她想參與反抗,但不想被融化在集體裡。她相信行動,但她想用行動,把這個地方改變成可以容納每個奇怪的「我」的地方。

Ann 的一眾伙伴急就章地用白色油漆塗在黑色布上。「哀我中大」、「還我學生自治」、「員生共治」。三張橫額,堅持不願死去的信念。
來自幾個友好組織的他們組成「學生組織關注組」。在代表會宣布「解散」後,學生會屬會的去向頓成未知。原本所有的學生組織(「莊」),運動的、宿舍的、康樂的,都由學生會管轄。但此時校方已假設學生會「解散」為既定事實,打算由學生事務處(OSA)接管屬會管理。
他們不打算採取太激進的立場,而是主打屬會管理的問題。既然學生會懸空,就由每個學生屬會選一個代表,這群代表聯合起來組成臨時議政平台,表現更廣泛的學生民主授權。Ann 判斷,這樣做並不危險:「其實就算是『朔夜』也未真的到犯法的地步。我們也避免在媒體上太高調。只是用和平的方式去表現,以後跟校方保持討論空間。」
「現在的氣氛下,大家『縮』得好緊要。我們不可以再宣揚恐懼。」
他們的工作,印傳單、設街站、找屬會,已經延續三個月了。其他屬會的反應亦不太熱烈。學生事務處亦假裝他們的聲音不存在。或許,在畢業禮拉橫額可以讓更多人留意到他們的工作。
在這一年的畢業禮,恢復實體進行。沒了遊行,但仍有一群同學「快閃」舉起了九張紙牌,上面寫着九個名字:張俊浩、鄧希雯、高梓斌、劉晉旭、符凱晴、陳歷釋、許貽顓、陳起行、李俊皓。他們是在2019年11月11日至12日期間,因「中大保衛戰」在二號橋上被捕的學生,除了李俊皓脫罪外,其他人不是已經判囚,就是罪名成立還押待判。
在抗爭前線的人,已經陸續被捕、流亡、消沉。前排的人沒了,中排的人就變成前線。中排的人也沒了,後排的人就變成前線。一個自己判斷沒有危險的行動,彷彿都已經變得很勇敢。
在另一邊,Ann 跟同伴由中午起就一直舉起「哀我中大」的橫額,旁邊放一個箱裝滿白絲帶供人自取。學生事務處的職員在旁視察。保安想趕他們走,指他們沒有事前申請,他們就跟保安議論。職員這才介入其中。
Ruby 在校園媒體報導看到 Ann 他們跟保安議論時,打算過去幫忙吵架。去到時,保安已離開。見眾人的樣子很累,她就提出幫忙買飲品和甜品。
回來時,一個姨姨跟每個舉橫額的人四目相對,逐個上前道:「加油,小心呀。」但 Ann 心裡想的是:其實舉橫額很安全很和平,連校規都唔會犯到。其實不是真的很勇敢、很值得別人的尊重。。
Ruby 放下水糧,有點尷尬,但又不想留下。最終她留下一句,「我走喇,唔同你哋癲喇(我走了,不跟你們瘋了)。」
說了這句話,她不斷思考:為甚麼我會這樣說?為甚麼堅持舉橫額是「癲」(瘋)?2019年後,她就陷於「強弩之末」的狀態。是不是到現在仍走不出來?
離開時,她去跟以前同莊的朋友拍畢業照。當時她覺得大家疏遠了,也許是自己過份解讀。事過境遷,怨嗔都淍零成秋日乾硬的落葉。她把一根白絲帶遞給以前的朋友。
瓜瓜把畫上了乳頭的模特兒人偶放上百萬大道,看看別人會如何反應。
之前把人偶放在「珊瑚」時,有個中年人進來見到後說:這樣不好,小朋友看到不好。
晚上她想回到百萬大道回收人偶時,發現果然不見了。詢問一番後,發現是有人看了不順眼後舉報,保安組上去收走了人偶。
「我就是要讓你感覺不舒服呀。我想改變大家的不舒服,改變大家對這的看法,改變社會。」
幾日後,瓜瓜參與性/別關注組的會議。她最疑惑的反而是:中大不是號稱「暴大」嗎,為甚麼現在參與組織的人來來去去也是那些。
Ann 他們在得悉司法委員會裁定中大學生會應重啟職務後,繼續密鑼緊鼓,收集問卷,集結員生意見,跟大學輔導長陳國康對話。
秋天的中大,清風吹過 Ruby 的髮梢,一架架車輛掠過眼前。
「其實可能是我有點 PTSD(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很多東西都記不起。但大學的輔導員又跟我不合,他們都是會問那些東西。。
Ruby 喜歡自己一人在大學正門外的大埔公路等車。公路很闊,兩邊有大樹。「感覺很舒服。我喜歡等車時聽公路上的聲音,有鳥聲,有蟬聲,也適合聽歌。」
一架架車影掠過眼前。她雀躍地探頭出去,心想:「來了沒有來了沒有!」
「我喜歡的是這個『甚麼都可以做』的中大。」
2021年,聖誕前夕,在社會的壞消息沉靜了一段時間後,12月23日凌晨,香港大學忽然把紀念六四事件的「國殤之柱」(Pillar of Shame)斬件移離校園。
Ann 經過中大入口旁的民主女神像。2010年,時任中大學生會響應支聯會的計劃,在六四晚會後號召二千市民護送仿照北京八九民運的新民主女神像進入中大。此後都每年都有人會在六四來民主女神像獻花。
十年間,民主女神像就慢慢成為中大人口中的「民女」,一個員生約人聚頭的地點,一個每日出入校園都會經過的地方。中大校方也沒有再反對或追究,把雕像立於中大視為既定事實,參與維護和保管工作。在不同時期,「民女」的身上掛上過彩虹旗,掛上過校園抗爭的標語,掛上過反送中的口號。
港大不顧私有產權等法律問題,粗暴移走「國殤之柱」。在香港大專學界管理層爭相向中共諂媚的時候,甚麼時候會輪到中大的「民女」被移走?
那日,Ann 跟關注組的其他成員開會,得不出甚麼結果。大學覺得按港大先例,就算中大要移走「民女」最少也要爭論好幾個月。
Ann 迷迷糊糊就睡着了。
翌日醒來,她滑滑手機,就看到民主女神像已經被拆掉的新聞。一個每日往來都會豎立在眼前,尋常得好像家門口一樣的日常風景,過了一個晚上就消失不見了。沒有任何痕跡遺留,遺留的只有一片空地。
事前學生代表事還一直跟學生事務處、大學輔導長陳國康溝通。有學生代表表示,在國殤之柱被拆除當日,他們跟大學輔導長會面,輔導長還「拍哂心口」(許諾)表明大學沒有計劃拆除民主女神像(事後大學輔導長否認這說法)。
午後,中大傳媒及公共關係處(簡稱公關處)發出聲明,指「大學從未准許該雕像於校園展示」。因為「曾參與安排雕像於校園展示的兩個組織『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及中大學生會現已解散或無實際運作。大學作為校園管理者,經內部評估後決定移走該雕像。」
一眾學生代表立即追問學生事務處與大學輔導長。雙方均表示自己事前亳不知情。但他們都已經把學生代表的意見轉達給公關處、行政副校長及保安處。
那麼這些人的回應是甚麼?
這些人均沒有回應。
一場不知名的殺戮。不知名的人在不知名的時間殺死民主。而事後也沒有知名的人出來承認責任。就連殺戳的原因也不存在。
不是在媒體鏡頭見證下的暴力移除,不是在爭議聲中暪天過海的鬼祟舉動,而是沒有人認責、沒有人預告的失蹤。
Ann 躺在床上,不知自己哭了多久,也不知為何就哭了。直到她擦乾眼淚。
在得知「民女」被拆後不久,一群學生就已經組成了一個群組。有學生組織的成員,也有不少中國學生,事實上裡面不少人也跟學生組織關注組重合。他們立刻分工合作,有人去買蠟燭之類,有人去買鮮花,有人去找「民女」的舊照片,約定在下午三點回來集合。學生報眾人馬上開盡馬力,半日內刊出一本小小的「民女特刊」。
原本放置「民女」的空地,變成了一個小紀念場。眾人靜默地在周遭走走停停,不知說甚麼好。
雕像可以消逝,但記憶不可以。
經討論後,在場主事的同學,由代表會、校友、學生報、臨政成員如 Ann, 到在場的中國學生,都同意不要把紀念變得過於高調,免得又招來校方報警。
場面大致平靜。只是在某一刻,剛巧一人走過,大聲唱中國國歌。馬上有人大罵道:「支那狗死返中國啦!」
Ann 感到全場都靜了。

Ruby 在下午到場後,自動請膺幫忙派學生報「民女特刊」。她也不知這日自己的心情如何,只想一直派,一直派。
派刊物的期間,有個中國學生走近,問:「這是甚麼?」
Ruby 開始解釋民女代表的意義,是每個人來中大時第一個見到的雕像。說着說着忍不住梗咽。對方輕聲安撫:「沒關係,慢慢來。」
「其實我本身真的很怕跟陌生人溝通。但講完之後她也沒有走,我就問她不如一起派東西。」
對方跟着 Ruby 一起派,保安走了過來,語氣不善地問:「你們在派甚麼!」該同學似乎聽不懂廣東話,保安就從她手上徑直搶走了一份特刊離去。另一個保安走來,「派東西有沒有學生證!」Ruby 看不順眼,就走上前出示自己的學生證。
派完後,該同學還沒有離去,還問 Ruby:「要不要去吃飯?」Ruby 為她這麼空閒感到奇怪,但心裡又暗自回答自己說:她可能是個孤獨的人,不應標籤中國學生為可疑的人。
對方聲稱自己是第一年的碩士生,跟 Ruby 在飯堂聊了差不多一小時。
之後 Ruby 跟 Ann 提到這個人,提出可以招她進來,一起做事。
Ann 問:「這個人信得過嗎?」
Ruby 把所知的都告訴 Ann 後,就不知從何說起。
Ann 再追問 Ruby 跟那位同學相處的細節。Ruby 開始回想,她第一句見到 Ruby,問的是刊物是誰出版。派刊物期間,她馬上問 Ruby 取學生報的 Instagram 和 Ruby 自己的 Instagram。吃完飯後,她又很積極想要跟 Ruby 保持聯絡。
Ann 嘗試親自聯絡她。那個同學很快就跟從 Ann 的電話號碼,追蹤 Ann 的 Instagram。
這時 Ann 直截了斷說:她不可信。鬼嚟(是間諜來的)。然後叫 Ruby 和其他人馬上封鎖她。事後 Ann 再改了 Instagram 名字,叫 Ruby 當沒有認識過這個人。
Ruby 剎那間懷疑自己。懷疑自己的感受,懷疑自己的信任。
她仍然想跟自己說:「會否她真的只是一個很孤獨的人?」
之後幾日她都沒有動力做事。

晚上,「民女」原址附近的石壁上,有人用牛皮膠紙懸掛了「新民主牆」。
瓜瓜在寫完論文後,跟朋友下山時,身旁不時傳來卡啦OK的聲響。初時她們以為聲音來自鄰近的教職員宿舍,後來發現是對面山的豪宅。在民主女神像原來的位置上,蠟光在舊照和鮮花旁默默發光,一股無聲的悲戚伴隨燈火飄揚在空氣中。但另一邊卻是歌舞昇平的歡騰派對之聲,咶噪不已。瓜瓜心想:好不現實呀。
有保安看一看民主牆上的字,看完就走。於是瓜瓜走近不遠處的保安,用已經沒甚麼口音的廣東話問:「唔該你,我想問你知唔知......(麻煩你我想問你知不知道......)」上一刻保安還很自在,聞言後他就立刻變得僵硬,冷冷地答:「我唔知呀,上一更唔係我(我不知道,上一更不是我)。」
新民主牆上,最多人寫的還是悼念語句和情感表達,如 “You can’t kill us all”、「永遠都記住歷史的傷口」。除此以外,也有人寫「香港獨立唯一出路」,或比較無關的如甚麼「民主未來在中華民國」。
瓜瓜看完後,跟朋友說:「我想聽多一點那些藍絲、那些不舒服的聲音。」她在紙上寫道:我想要自由表達,也想要聽到不同聲音的自由表達。
寫完後她頓一頓,臨走前再寫多一張紙,黏在牆上。上面寫着:希望也在你心裡,不需經由政權實現。
在跟朋友回去「珊瑚」的路上,瓜瓜覺得自己跟2019年11月很像。因為過多一段時間,她就要踏上交換之旅,離開香港。為甚麼每次離開都是在這種時刻呢?她想。就好像是背叛了留下來堅持的人,就好像是背叛了跟同伴一起堅持的自己。
這是2021年12月24日,平安夜。今天應該很平安。國家應該很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