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肉食者到腐食者:评巴菲尔德《游牧帝国与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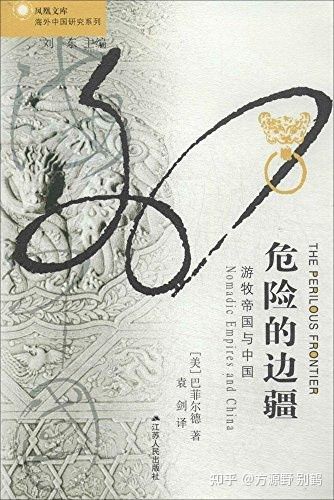
目录
一,三层与“2+1”层:自耕农与游牧的组织模式
二,“肉食者”:匈突之败、汉唐之胜
三,“腐食者”:元清之奴、宋明之亡
四,出路:辛亥革命以来的道路
2022.3 方源野(别鹤)/撰
一,三层与“2+1”层:自耕农与游牧的组织模式
因“狼图腾”“刘阿姨”等长年的歪曲影响,不少人误以为农耕等于“静止不动”,等于武力弱小,而把游牧等同于“自由精神”,以为游牧部落贵族能够依靠武力限制可汗权力,因此蛮族还是“贵族民主制”,而华夏农耕文明等同于官僚制度的自上而下一元化权力,所以某一个点被攻破就会一损俱损,全局溃败。事实与此恰恰相反。
巴菲尔德在《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指出,游牧制度,排斥个人对土地的所有权,游牧的部落统治阶级,基于对草场的武力垄断。游牧的财产积累源于牲畜的生殖,这种生殖数量不是一个三口之家能够管控的,首先需要驯化,所以游牧的大量时间和成本,会用于令行禁止的军事操练,培养全民的狩猎纪律;其次,没有土地生产,所以这是“利出一孔”的生存模式,所有部众都被迫依附于强有力的少部分狩猎集团,以换取整体的移动生存。
相比而言,一个三口之家,作为自耕农,就能够保护社区和财产和劳动力的独立性,也能积累和管控生产剩余以用于商贸,从而与其他自耕农形成契约社会,同时发展狩猎等技术进行社区自卫,推而广之,形成乡约自治,这是五胡乱华时期,华夏得以维持,并在大唐帝国依靠自耕农民兵得以复兴、横扫亚洲的根本。这一秩序,也早在远古部落联盟中由轩辕黄帝所奠定,它的格局是由三个层次自下而上构建的:1.下层,“建屏万邦”的采集和自耕农社区——2.中层,社区之间形成一个个定居群落或者农耕部落——3.上层,群落或部落再合作为部落联盟、方国联盟,并产生由天下共主所领导的治理团队,但没有游牧萨满那样的神性权力,在秦始皇以活人僭越天帝之前,最高共主的权力长期低于天帝或神性,而天帝神性以“道生一”而至“万物”的秩序,赋予了每个部落民的天然权利。此为黄帝手创之神州雏形。在权力让渡上,即使从尧舜禹启开始,出现了最高共主的“父传子,家天下”,和部落方国层面的宗族或贵族寡头,但下层的自耕农社区仍然维持了“乡举里选”的公共精神,这种乡约自治秩序一直维持到秦始皇之前尚未中断。后来汉高祖刘邦等人,把维持“秦制”刑徒经济的实际奴隶,解放为自由民,实现空前的阶层飞跃和流通,并推行耕者有其田,多方面解除秦法的禁锢,所以汉朝凝聚了第一个后部落时代的民族帝国,实际上已粉碎了“秦制”本身。
所以,华夏传统对公权力或社会权势,保持了下对中、中对上,两个层次的制约——首先,是乡约社区对部落方国的制约;其次,当部落方国聚集成周朝那样的寡头封建诸侯,或者三代以下的门阀时,它往往会与下层的乡约社区和上层的科举制等管道联合起来,表现为史官、相权文官、学校等体系,对君主、皇亲国戚,及自上而下安插的另一种官僚体系,予以一定制约。当自耕农的民兵秩序维持时,中间那个从部落方国演化的权力,进一步演化为多样化的军事功勋集团,这种集团在汉唐时期,典型的表现就是都督、都护、州牧、节度使藩镇,它可能与下层乡约联合起来制约最高权力,并较大概率地高效抵抗外族;当然,它也可能选择与君主权力共谋,压缩、让渡自己的权力,以压榨下层乡约,这种体现,在失败的一方,就是二世而亡的“秦制”,在半成功的一方,就是汉武帝开创的“外儒内法制”,在完全成功的一方,就是宋朝那样温水煮青蛙的“实际复辟秦制”,那自然掏空了下层一切自组织抵抗胡虏的秩序,并由于自身也缺乏秦那样的对外威势,内外皆空,造成亡国亡天下。
所以,不能以君主权力是否表面上受到一个“贵族联合体”的限制,来判断是不是公共精神最大化的表现,更不能把这种组织模式等同于现代意义的国会。从这个意义,我们能反过来理解游牧帝国的组织模式。
游牧帝国比起前述农耕文明,不是三层组织模式,而是一层无效模式和两层组织模式:1.下层:“无恒产”的无产阶级,没有任何自组织权力,作为牧民依附于中层贵族与上层可汗,作为狼群、齿轮、燃料一样的游牧工具人;2.中层:部落贵族,短期裹挟了下层,以人海战术和畜群优势,体现出一定的威势,表面上甚至能够制约最高可汗的权力;3.上层:可汗,拥有“绝地天通”的萨满神性权力,一旦得到部落贵族的集体认同,就拥有绝对权力。但游牧组织不是一个能够像农耕那样完成自我造血的经济体,它的财富密码在于对农耕文明的不断劫掠和敲诈,所以巴菲尔德指出,可汗通过两种方式来获取和维持绝对权力——战争,对农耕文明的进攻与征服,对内如臂使指,动员每一份人力物力的军事指挥权,并垄断战利品的分配权;和平,农耕文明互市给游牧帝国,可汗垄断财产的分配权,截断上游,控制产品的每一处下游的流向。因此,游牧可汗与部落贵族是一种基于生存的紧张关系,可汗需要不断维持这种对农耕文明的榨取,以维持绝对权力,部落贵族也乐于让渡给可汗,以获得优先分配,并控制自己治下的牧民,甚至共同打造“兄终弟及”等可汗家族的全面传承权力。因此,被游牧帝国鄙视的农耕赋税,恰恰是避免劳役,人身自由的一种交换,而非游牧帝国对人身劳力的控制裹挟。也因此,草原上的权力更迭,往往只有宫廷斗争引起,而像华夏农耕这样历代常见的下层革命、秩序清零,则非常罕见。
所以,如匈奴、突厥、蒙古、通古斯等长期存在的“库里台”或“八王议政”等,仅仅是贵族与可汗之间为了更好地榨取农耕文明和治下牧民的“自己人”利益分配,并且仅限于可汗家族之间的择优传承,以更好维持可汗家族的顶层统治和部落贵族的利益同盟。那是一个封闭的帮派模式,绝非整个游牧“共同体”的公意体现,也非限制最高权力,连“帮内民主”都谈不上,反而是对可汗神性的追认仪式。这种模式体现的公共精神,绝不会超过先秦时期“谏鼓谤木”、”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的民意表达,也从来没有超过华夏的有限君主制时期,比如唐朝的“政事堂、五花判事”等协商。
只有从这些组织模式中,我们才能理解游牧帝国和华夏农耕的特征,并进一步理解在历史上双方此消彼长的武力密码。
二,“肉食者”:匈突之败、汉唐之胜
按前述,游牧的一层无效模式和两层组织模式,巴菲尔德指出,匈奴和突厥的两层权力是:最高层,匈奴单于或突厥可汗及其官僚,掌控帝国事务;中层,地方部落首领,完全裹挟了各自的农奴、牧民和草场。这种两极结构没有试错和可替代的弹性,不堪一击,所以匈奴、突厥,预设了另一道可替代的保险,这种保险不是华夏乡约这种自下而上的兜底缓冲层。匈奴,那是单于自上而下延伸的“万骑”二十四长;突厥,那是大小可汗分跨东西两翼,如“突利”“达头”。与华夏不同的是,华夏即使诸侯、门阀那样自上而下的封建寡头,也会碰到自下而上的乡约武装,从而被迫与下层联合起来抵抗内外压迫,所以能够多次复兴。但匈奴、突厥,只有“万骑”二十四长,或大小可汗互为备胎,这样的一道保险,它顶多在失败之后更换一个统治家族内部的可汗,但它不能有效动员早已是无产阶级的各部民众,所以面对汉朝的压力,匈奴、突厥上层虽然经过了六七百年的多次平稳继承,中层却多次分化,正如匈奴的浑邪王投降汉武帝、呼韩邪单于投降汉宣帝,南匈奴投降东汉,突厥的突利可汗投降唐太宗等事件。显然,这没有构成一个“匈奴民族”或“突厥民族”的共同体。二者略微的不同是,突厥比匈奴更懂得权力的裂变和协商,所以突厥后来成了古代一切游牧帝国里,唯一一个还能多次复兴(塞尔柱、奥斯曼、帖木儿、莫卧儿四大帝国)并转型为民族共同体和现代世俗共和国(土耳其革命)的模式,此为后话。
所以,巴菲尔德把这种草原游牧的帝国联盟,称为“肉食者”,它主要以战争劫掠、和平敲诈,包括但不限于利用“朝贡体系”获得大量供奉,来维持中上层的权力联盟。但果真如巴菲尔德所言,匈奴-突厥系的“肉食者”,只愿游牧于西伯利亚一带,没有进一步南下,征服整个华夏中国的企图吗?甚至部落贵族会制约最高可汗的进一步行动吗?如果是这样,就无法解释,为何阿提拉、帖木儿、奥斯曼土耳其、巴布尔等,对华夏以外的其他农耕地区进行了大征服,并且恰恰也是他们的可汗权力达到登峰造极之时。
**巴菲尔德最大的缺陷在于,他无视华夏中国比游牧帝国多了一层有效的自组织——前述的自耕农乡约层次。他仅仅以为武力来自于像游牧那样的部落贵族武士。所以他也无视汉民族的真实武力。**比如,他把汉武帝的北伐和对东北与西域的开拓,视为无效的战争,把汉朝初期的绥靖政策,视为有效的和平手段;他也把唐太宗的彻底成功的北伐,及对西域和东北的光复和进一步开拓,称为依靠突厥人的武力,并且过分夸大了汉朝和唐朝平定内斗时对南匈奴、回鹘等游牧力量的借助。正因为巴菲尔德错误地臆断了华夏民族的武力是弱小的,所以他发现的一个“规律现象”——游牧帝国依托于统一的中国,去榨取财富以维持他们自身的统一,并随着中国统一的消散而消散——也仅仅是幻觉的表象。真实的答案是:因为汉唐有效地反击了匈奴地带,征服了突厥地带,完成了两次华夏农耕文明对游牧帝国的胜利。
历史的事实是:汉武帝面对的是匈奴不断南下的压力,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匈奴会停止南下,正如后来阿提拉的西征风暴和后文的成吉思汗。汉武帝的北伐反击,决策正确,他依靠的是汉初,高、吕、文、景,数代依托于自耕农,积累的财力。汉武帝真正的错误在于,他选择了募兵制,用“外儒内法”国进民退、强化内朝、扰乱社会的路线,取代了汉高祖和文帝的“黄帝之道”藏富于民的路线,把讨伐匈奴的战争,打成了游牧帝国最希望看到的旷日持久的人海战术。所以汉武帝未能真正解决匈奴问题,不仅汉武帝后期开始匈奴复振,并且汉武帝自身内政紊乱,财力透支,冤案迭起,甚至首建胡骑营、越骑营,还以相当于一年全国支出的巨款接纳匈奴浑邪王的归附,以填补社会秩序被朝廷进一步碾压后的真空。东汉依托于门阀和内朝,进一步疏远乡约力量,所以汉光武帝刘秀进一步放弃对匈奴地带的反击,成建制收纳南匈奴,曹魏和司马晋更是进一步让胡人组织深入内地,最终南匈奴成为五胡乱华的魁首。如此一来,刘邦以下层自耕农和中层军功集团一起肇建的民族共同体,在上层爆发出对外武勋之后,就燃烧成了一个头重脚轻的半成品,亟待第二次复兴的完整实现。
**正因为“秦制”的军事动员和全能主义治国,会透支下层的乡约自组织和民兵自耕农,与游牧的两层结构相似,所以在华夏难以立足。**而汉武帝受制于汉高祖恢复的乡约力量,也无法真正挥霍社会,并确实取得了华夏第一次对决游牧武力的有限突围,在西域、东北和正北三个方向大幅拓展。这种剩余的社会秩序力量,也确保了汉朝后期,中层的州牧与下层的屯田结合,继续讨伐南匈奴、鲜卑、西羌、南蛮,保持了对外主权大体不坠,**这一乡约力量甚至在永嘉南渡之后,还以西府、北府、坞堡等维持了汉族的自卫秩序。**所以,即使汉朝之后,连续出现三国内乱,五胡乱华,南北朝分治,隋末的虐政废墟与空前内忧外患,这四百年漫长黑暗,但由于汉朝留下的汉高祖、汉文帝、汉武帝的路线记忆,给了后来更为优秀的英雄以经验借鉴,所以华夏继汉朝之后的第二次复兴,能够熔铸完整的民族共同体,并将三层组织合为一个有机体,同步取得内盛与外强。
唐太宗李世民的秘诀与其说是君主或君主制的优越,不如说是他同时把握了前述三大层次的力量,有效遏止了君主制对这三种力量的干扰,以孤军一隅,面对十虏百傀,逆风而战,同步取得和超越了汉高祖扫除虐政乱世、汉文帝缔造开明治世、汉武帝进取挞伐胡虏的三大功勋。尤其在第三点对外战争上,唐太宗依靠汉民族自己的府兵制,捍卫永业田的权利,寓兵于农,以租庸调40税1之制,轻徭薄赋,以群星灿烂的汉族将领,北伐——灭突厥、铁勒、车鼻,唯一一次彻底扫平长城以北;西讨——灭吐谷浑、高昌、焉耆、龟兹,驱逐西突厥,光复三百年沦陷的巨土西域,并行政掌控中亚至里海之畔,重开丝绸之路;东征——驱逐高句丽,收复三百年沦陷的辽东,水陆钳制为高宗继之灭高句丽、百济,击败日本而奠基;南下——灭中天竺,驱逐吐蕃,陈兵川藏交界,护卫南洋出海。若此,李世民不仅赢得了空前的生存空间和汉民族掌控天下的文明秩序,还一举洗雪了五胡乱华和犬戎灭西周以来的历代国耻,彻底树起了华夏中国战胜游牧帝国的自信。而李世民的光辉人格,甚少天下为私之心,他有意把上层外战的果实,酿为监察制里,十道节度使的军功开放,科举制里,中央与州县的公职向庶民开放的文武并轨之制,把东汉以下的门阀削减到仅为大家族的阶层流通,这样就让中层形成了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相互补充的双保险,相当于双倍加强版的部落贵族武士;同时,比起汉高祖和吕后和汉文帝,他更为彻底的推行了耕者有其田和扶持商业,这样就再次激活了游牧所缺乏的下层自组织,并与府兵制的民兵和科举制的考试结合,让下层也有了自卫和跃升的更多保险;同时,他又对中下层唯才是举,导向上层,熔铸为尚书、中书、门下、谏议大夫与皇权的“相防过误”,和以宽简为本的成文法等划时代的制度,并最大限度遏制了冗官冗兵十羊九牧,达到路不拾遗、监狱常空、商旅野宿之效,这样他甚至在帝制时期第一次草创了准国会和立宪君主的雏形,将全国导向了公共精神。
如此一来,以**《道德经》**这样阐述黄帝精神的古宪凝聚起来的大唐帝国,在唐太宗的领导下,文武全兴,并在与游牧帝国“戎狄之盛,古未有也”的斗争中,以组织模式的优越,赢得了农耕文明的完胜。但是,由于天宝年间,均田制废弛,募兵制又起,唐玄宗引发安史之乱,养虎为患,一如汉朝以来历史循环。晚唐虽中兴,如汉末一样,靠汉族节度使之力,对回鹘、南诏、吐蕃、交趾、契丹赢得了全面大捷,但已不复初盛唐之进取。汉唐之间,五胡和北朝的实验,也埋下了汉唐之后的长线隐患。
三,“腐食者”:元清之奴、宋明之亡
为什么汉唐能够抵抗和战胜匈奴突厥,而宋明却一而再、再而三地亡于西伯利亚鞑虏?这里面的区别是什么?
巴菲尔德极具洞察力地指出,黑龙江大兴安岭以北的俄罗斯东部森林地带,即通古斯地区,出现了另一种不同于漠北草原的游牧-狩猎集团。他们时常南下,与辽东原住民汉人多有接触,熟知汉人在秦以后的帝制模式。于是,他们为自身与匈奴突厥类似的两层组织,加上了“外儒内法”的帝制官僚这一补丁,于是,为游牧-狩猎帝国的权力集中,补上了**两道自上而下的双保险:一是部落贵族与可汗的固有权力联盟,同时压榨治下牧民和外部农耕世界,二是可汗变身为皇帝,利用农耕世界中的降虏(汉奸官吏),反过来压制部落贵族。**这相当于左右两个口袋能够互相分担,当胡人皇帝压不住汉族官僚时,驱动部落贵族的铁蹄血洗华夏;当胡人可汗压不住部落贵族时,利用外儒内法的文官秩序为通天萨满加持更多的神性。但由于华夏农耕的乡约自治有着强大的革命精神,所以汉族官吏总体上必须压制在胡人贵族之下(遑论民众),这就是元代“四等人”的深层秘诀。
如此双重加码,游牧可汗和中土皇帝的合一权力,便为自成吉思汗开始,登峰造极的绝对权力,即从可汗开始层层奴役,掌控到每一个牧民和农民的一切人身、财产、家庭甚至思想的胡人极权。它在古代的顶峰就是甲申之后的清国——通过扫荡全国的刺刀下,剃发易服、圈地投奴、文字狱、四库毁书、迁海驻防、禁止结拜、割地赔款等几十项奴役,**使得被征服的民族和人民,连自身的发型、耕种、语言、历史记忆、迁移、结内、排外等一切自治自卫的,生而为人、由天道所赋的基本权利,全部扫荡殆尽,并沦为“东亚病夫”任由列强宰割。**对这一利用了汉族帝制痼疾,与游牧集团固有奴隶制相结合的新秩序,巴菲尔德精辟称之为“腐食者”。
但这一长线,非肇始于甲申与崖山。五胡北朝是辽金的先导,辽金是蒙古帝国的先导,蒙古帝国是满清的先导。
五胡乱华以来,鲜卑的“汉化”被片面美化,而忽视了其实质:魏孝文帝并非一个早期复兴华夏的唐太宗,而是一个利用汉族门阀制度,以加强鲜卑奴役集团的操盘手。与冒顿单于等匈奴独夫不同,鲜卑帝国创始人檀石槐是游牧部落里为数不多基于选举公决的人,鲜卑自身缺乏匈奴、突厥那样的等级结构,所以魏孝文帝极大加强了对门阀与帝制这一连锁盛宴的“食腐”。而六镇之乱,与其说是胡化逆转汉化,不如说是同时存在大量汉人与少数胡人的下层起义,对北魏固化的抗议,这与五胡乱华以来支撑汉族的乡约自治属于同一个基本盘,这也是陈寅恪所谓“关陇集团”的真相。只是,由于唐太宗李世民最终的文武复兴,这一逆势被真正扭转。
但这一记忆,沉淀到了同一发源地的契丹和女真,而同时,宋朝却开始了组织模式的慢性自杀。赵始皇族用尽一切手段,软性地粉碎了所有能自主抗虏、制约朝廷的社会力量,下层乡约再无钱粮兵马,中层武将被大批杀害罢黜、相权被分割包围,上层对外畏战苟安,**三个层次全部软弱无力,有秦制自缚之短,而无秦制动员之长,既无秦二世而亡之速,又有秦消磨民气之延。**当面对一个更成熟实现了上层短暂的双重加码的辽金进攻时,北宋自然迎来了靖康之耻,亡国而南渡。
这时,巴菲尔德指出了一个草原帝国的突变:以往,总是华夏中国,或占据了中土的游牧帝国,成功抵抗了北狄南下(后者如北朝压制柔然),但这时,蒙古“黄金家族”出现了铁木真。他的权力,在游牧秩序里第一次没有任何传承,作者指出,他在真正的蒙古——乞颜部落——内部也遭到半数抵制,在杀伐草原其他部落时,更是经过了无数次生死搏斗,最终由库里台大会“推举”为成吉思汗也只是败寇对成王的既成事实之追认。更惊人的变革是成吉思汗执政后,由于他缺乏部落贵族认同的合法性,他开始把征服、摧毁全部农耕文明作为纲领,以转移部落贵族和可汗的内部矛盾,如作者所言,“成吉思汗既不相信他的近亲,也不相信蒙古氏族”,所以他也进一步打压部落贵族,从他面临的金国学习了组织技术并空前强化,最终战胜了金国,其滚雪球的组织模式最终让华夏第一次亡国 亡天下——
1.提拔“伴当”家奴——拆散部落内部忠诚并以绝对的依附者作为权力核心;2.八十六个“千户”与多个“万户”——将草原全众,编户齐民,彻底消解部落贵族自治,纳入到自身亲信官吏的十进制网络中,并全部贬为人身层层控制、分配的奴隶,取消了全部自下而上的制约;3.消灭通天巫——把自身作为唯一沟通“腾格里”的萨满,实现教政合一;4.“怯薛”制度——以人质实现控制的护卫军,生杀予夺,凌驾于其他武装之上,只忠于成吉思汗,不忠于任何部落,也不忠于任何部落操作的“蒙古”概念;5.连坐制:在战斗、放牧、狩猎中,令行禁止,违者以十进制批量处死;6.大扎撒:一部规定到吃饭动作、休息姿势,动辄死刑,实现彻底驯化的法典,并且成吉思汗凌驾于这一法典之上,其任何命令都是最高法律,可任性独断,无条件执行,而且是神意;7.“达鲁花赤”,由最高汗廷指派到各个被征服地,凌驾于一切官僚组织之上。所以成吉思汗实现了人类史上第一个也是空前绝后的极端控制一切社会的绝对权力,从而也将这种权力的破坏性释放到了众所周知的空前绝后。
更为深远的连锁反应是,崖山之后,大小明王与刘福通发动的、韩宋红巾军的光复和元末第一次北伐,及他们相应以屯田民兵恢复汉唐自耕农基础的进程,戛然而止;继之第二次北伐的明朝,一方面进一步实现了收复燕云、驱蒙元于塞北、以捕鱼儿海大捷造成蒙古内部权力更迭的光辉成果,但另一方面,在起义过程中几次借势蒙元移锋于其他义军的过程,和出于帝制深化后的反应——对前朝韩宋的有意遮蔽打压,使得明初刻意利用和延续了蒙元的诸多组织模式,恢复中华的成果被极大消解:一方面,未如汉唐那样犁庭北狄、拓展西域,还让内政出现种种制约外部进取的“元制”遗毒,如废相、行省、酷刑、诛连、上层锦衣卫东西厂、基层里甲、教育控制、军户匠籍、胥吏、人殉、宗藩、史庙颂元、丑化韩宋红巾军(参考笔者《崖山之后的一体两面》,此不赘述)等,这些遗毒一直持续到中后期很长时间;另一方面,这些制度造成华夏的前述三层,未能焕发合力,使得明廷对退回塞外依然强大的蒙古,除明初一度奋发外,有持久的避战之心,既把操纵蒙古内斗的互市策略,拖延至俺答时期,又一反汉唐的北伐进取,在河套、鄂尔多斯一带长期拉锯与退弃。唯一直面草原的永乐时期,既无唐太宗扫灭十虏的清晰战略,又因明初承袭元制,而缺乏汉武帝打人海战术持久战的社会自治基础,所以明成祖陷入卫拉特与阿鲁台的权力斗争跷跷板,北伐成果极其有限,难与汉唐同论,故朱棣之后不多年,土木堡迅速反扑,明廷的战略与财政大量消耗在北面的被动防御。同时,朱棣为酬谢蒙古兀良哈对靖难之役的支持而短视放弃大宁卫,忽视东线进取,并收留通古斯以建州卫优容之,经多代壮大,努尔哈赤取得“龙虎将军”兵权,趁明与蒙古、日本耗战之际而从容崛起,最终甲申国难,神州再沉。
如果说努尔哈赤的八旗组织,还有来自西伯利亚的通古斯部落协商机制,那么皇太极则如辽金元等前辈,利用宋明以来积重难返的帝政吏制,与八旗奴隶制形成了相互咬合的双重补丁——1.下层,与前述匈奴、突厥、蒙古类似,八旗基本单位“牛录”制下,无一自由民,全部原子化散沙化编入八旗贵族;2.中层:八旗部落贵族被皇权架空,在不影响“首崇满洲”的国策前提下,与汉奸官僚、包衣奴才掺沙子、相制约,共同压制旗人底层奴隶和更为底层的广大汉族奴隶及其他少数族群奴隶;3.上层:由皇太极捏合为包含了通古斯、蒙古、部分汉人等在内的“满洲”奴隶制集团(当时决非现代意义的民族概念),并由多尔衮、康熙、雍正、乾隆等逐代深化顶层权力,将可汗、皇帝、通天教主三权合一,设置内务府、军机处等,绕开八旗部落甚至官僚组织,彻底做到深宫秘术、乾纲独断、为所欲为,于是前文所列几十项极端奴化措施,倾巢而出,“地狱沉沉二百年”。
但另一方面,明朝晚期,不同于上层多代所承蒙元遗毒,中下层开始了连汉唐也自叹弗如的飞跃性变革:如王船山、顾炎武、黄宗羲等大规模虚君、非君思潮,从轩辕黄帝的“原极”秩序,发掘出华夏习惯法的古宪,设计出了以不要帝制的方式,重建前述三层组织的规划,这一大势,沉淀到明郑、兰芳共和国、洪门大成国,甚至只称王不称帝的太平天国,最终汇流于辛亥的民族民主双重革命;又如明末清初,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无数抗清反清的起义壮举,主体为民兵自发与合作,这一大势,又积淀到了辛亥之后的护法、北伐、抗战等模式,与清末爱新觉罗遗腹于包衣军阀、勾结侵华日军、驻防于形形色色的反革命阵地,形成了数代拉锯。甲申三百年之后第一个全民外战的顶点,便是抗日卫国战争,以悬殊远超汉唐所面对匈奴突厥的差距,年无分老幼,地无分南北,最终击败倭寇,天皇投降,我中华同时一扫满清与北洋的上千不平等条约,收复汉唐之土,跻身联合国五常,并以二战战胜国身份奠定现代中国的领土主权,赢得了历史长线的第一站复兴,为后来的种种复兴,撑起了触底反弹的基石。
四,出路:辛亥革命以来的道路
巴菲尔德在最后认为,游牧帝国已经成了历史陈迹。果真如此吗?
游牧“食肉”与“食腐”的组织模式,尽管已不再大规模存续于表面上的北狄,但一方面,仍然在西伯利亚那片历代侵华策源地上,经过了种种换汤不换药的历史变形,而另一方面,则聚焦于以“元清第二”自诩,叫嚣“汉族腐朽不堪,游牧拯救汉族”的侵华日军身上,及其更大范围的种种国际替身、百足之虫上。反观华夏,总结辛亥革命“驱鞑虏,复中华,终帝制,起共和,族权生,启现代”以来的110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总结自轩辕黄帝经汉唐宋明而来的数千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可知,由孙中山先生指出的两种前途,始终摆在每一代接力奋斗者的面前:
——一种前途,是背离之:“宜先求富强,使世界各强国皆不敢轻视中国,贱待汉族,方配……否则汉族神明裔胄之资格,必随世界主义埋没以去。”
——另一种前途,是继承之、发展之:“汉族神灵,久焜耀于四海……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
天道,会护佑华夏神州,黄帝子孙,一代代做出正确的选择,与不竭的行动,直至全天下秩序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