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承诺│The Promise of Socialist Feminism
乔安娜∙布伦纳(Johanna Brenner)
Yang Chenhuan 译、K 校
重建左翼需要借鉴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传统。

在美国,女权主义“第二次浪潮”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几十年了,然而,当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关键方面被纳入统治阶级的议程时,承认这场运动的革命时刻已成为一段模糊的记忆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思想被动员起来,以支持一系列新自由主义倡议,包括紧缩政策、帝国战争和结构调整。
首先要理解这是如何发生的,这无疑是重要的。但女权主义学者最近提出的一些解释却将我们引向了一个不幸的方向。这些作家认为,第二波女权主义过度强调合法权利,及有偿工作作为通向平等的途径,在不知不觉中为新自由主义铺平了道路。这种说法令人欣慰,因为若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对我们斗争的结果有如此程度的影响,我们现在就可以改正错误,改变观念,重新取得革命的立足点。
我想提出一个不同的论点:自由女权主义将其部分纳入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秩序,资本积累制度的出现更好地解释了这一点,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全球北方和南方的经济结构。
在全球北方,这种新制度是由雇主对工人阶级、福利国家以及工人阶级的历史性防御机构——工会和社会民主党——发起攻击而引入的。这种攻击带来了新自由主义,这就是有效抵制女权主义者、反种族主义活动人士、土著人民和其他人的激进要求的政治背景。
虽然新自由主义扑灭了第二次浪潮的激进希望,但它也为工人阶级妇女领导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运动的复兴和传播创造了物质基础——无论是在正规经济、非正规经济、农村的女性,还是从事无偿劳动的劳工。
此外,21世纪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政治话语和组织策略也是左翼斗争的资源。人们有时会感觉旧形式的左翼政治行不通。在寻找替代方案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大有作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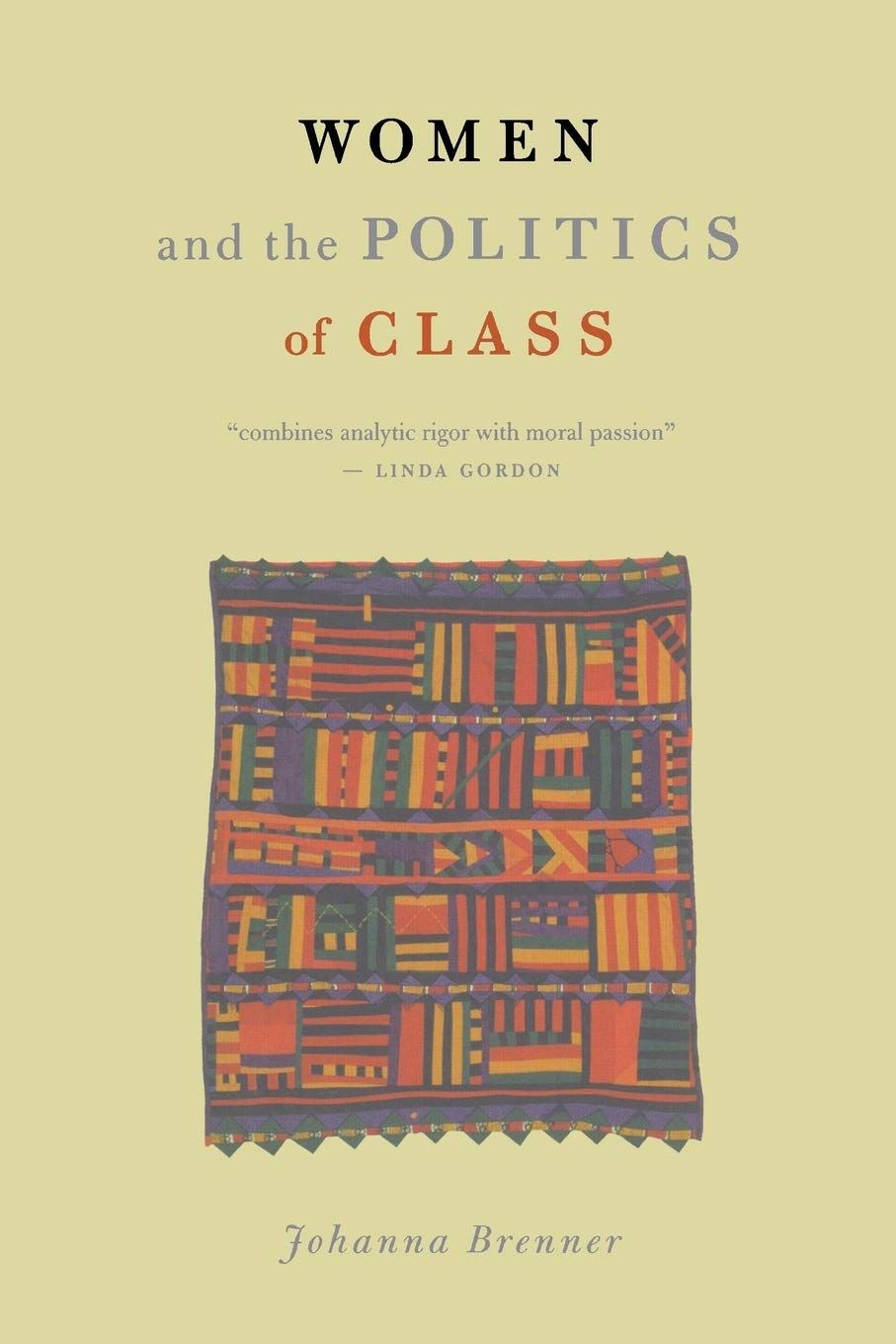
在第二波女权主义政治话语中占主导地位的并不是经典的自由主义女权主义——一种想要清除女性行使个人权利的任何障碍的女权主义——而是我所谓的社会福利女权主义。(在美国以外实际上存在着左翼政党的地方,女权主义活动人士更容易接触到社会主义政治话语,这种政治可以被称为社会民主女权主义。)
社会福利女权主义者与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同样致力于个人权利和平等机会,但他们走得更远。他们期待一个广泛而积极的国家以解决职业女性的苦难,减轻“双工作日”(译注:即同时照顾子女和上班挣钱,一天当两天用)负担;改善女性,尤其是母亲在劳动力市场的地位;提供公共服务使护理劳动社会化,并扩大护理的社会责任(例如,为照顾残疾家庭成员的妇女提供带薪育儿假和津贴)。
专业/管理阶层的富裕女性是古典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社会基础。社会福利女权主义政治的社会基础主要是在专业管理阶层的下层,特别是在教育、社会服务和卫生领域中的妇女。这些行业比私营部门更有可能雇用有色人种的专业/管理女性。女性工会积极分子在领导和组织社会福利女权主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可以大方地将工人阶级妇女/贫穷妇女和中产阶级职业妇女之间的关系描述为矛盾的,职业妇女的工作是帮助和规范那些被定义为有问题的人——穷人、不健康的人、文化上不适应的人、性变态的人、教育程度低的人。这些阶级的紧张关系渗透到女权主义政治中,因为中产阶级女权主义倡导者声称代表工人阶级女性。
这些阶级紧张关系的表达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阶级位置的其他维度的影响,如种族/民族、性别、国籍和能力。至关重要的是,中产阶级女权主义者的政治立场也会随着工人阶级女性的激进程度、自我组织和政治力量而动态变化。
20世纪70年代上半叶是这种动态变化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在黑人争取经济公平的政治背景下,在黑人工人阶级和福利权利运动(民权运动中工人阶级女权主义者的先锋)的推动下,社会福利女权主义者提出了一项具有卓见和广泛基础的计划,以扩大国家对关怀劳工的支持。
例如,在1971年,一个由女权主义者和民权组织组成的联盟赢得了一项立法,将托儿所设为一项由联邦政府资助的发展服务,向所有需要的儿童提供服务。尽管女权主义者坚定认为这一举措是为了保障妇女的就业,但他们并没有把这种福利的受益人限定为就业妇女。该方案包括为从婴儿到14岁的儿童提供医疗、营养和教育服务。服务的费用是浮动的。尼克松总统否决了该法案,但在整个70年代内,围绕该法案的组织工作一直在持续。
国家福利权利组织(NWRO)推动并宣传社会福利女权主义。NWRO最有趣的地方在于,它能够将哲学家、律师和学者往往认为相互冲突的主张结合起来。简而言之,他们打破了“需求论述”和“权利论述”之间的界限。
母亲主义(Maternalist )的政治话语是“需求论述”的典型例子。在这里,提倡者基于孩子的需要和母亲满足这些需要的独特能力提出主张。另一方面,要求男女平等就业或接受职业教育是典型的“权利论述”,坚持将已经给予男性的个人权利扩大到女性。
NWRO主张为单身母亲提供有保障的、无条件的最低收入。贫穷的妇女应该有选择如何养育子女的权利,并声称她们自己是确定子女需求的唯一合适的权威。无论她们是全职母亲还是在职父母,都应得到经济资助和社会服务。
福利权利活动人士还批评向贫困就业项目发起的挑战,这些项目试图让单身母亲接受培训,从事传统的、低薪的粉领工作。最后,他们将对做母亲是一项宝贵的工作的承认,与妇女的经济自主自决权相联系。
这种“both/and”政治也反映在有色人种妇女支持堕胎的运动中。女权运动的激进和自由主义派别关注的是妇女的身体自主权——以及拒绝生育的权利——而贫穷的有色人种妇女却面临着截然不同的攻击:在她们分娩的公立医院里被强迫绝育。此外,福利权利运动正在组织贫穷妇女,特别是黑人妇女,拒接接受对其母亲身份的诋毁和对其性别的污蔑。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结合有色人种工人阶级妇女的思想,阐述了一种超越选择论述的生育权利政治。生育权利包括做母亲的权利和在有尊严和健康的环境、在安全的社区中,在有足够的收入和住所的情况下抚养儿童的权利。
这种生育权利的各个方面构成了一项非改良主义的改革计划。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些要求可以被争取并赢得——例如,禁止种族主义绝育或歧视女同性恋母亲——但大规模的收养与资本主义是不相容的。在这方面,生育权利的政治话语将女权主义与反资本主义政治联系起来。
在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的鼎盛时期,女权主义主张将护理劳动社会化。从个人护理到社会责任的转变,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需要将财富再分配,使其从资本转移到劳工。
护理的社会责任依赖于公共产品的扩大,而公共产品的扩大又依赖于对财富或利润的征税。对员工的育儿时间进行补偿(例如,带薪育儿假)以牺牲利润为代价。此外,要求(通过条例或合同)工作场所容纳和补贴雇员在工作之外的照料,干扰了雇主对工作场所的控制,因此在私营部门往往遭到抵制。私营部门只会继续组织工作,就好像工人不需要照看孩子似的。
换句话说,推行社会化护理需要能够对抗资产阶级的力量。正因如此,二十世纪的社会福利女权主义破灭了。
面对资本阶级的权力,需要一场广泛的、激进的、破坏性的社会运动——一个将女权主义、反种族主义、同性恋权利、移民权利与工会和工人斗争联系起来的反资本主义阵线。然而,当时我们所拥有的仅仅是官僚主义的、僵化的、部门主义的工会,他们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建立任何形式的运动。
在社会福利女权主义最强大的时刻,即 1970 年代,资本主义重组的海啸到来了,开启了一个对几乎没有自卫手段的工人阶级进行攻击的新时代。随着人们挣扎着在这个新的世界秩序中求生,随着集体能力和团结变得遥不可及,随着竞争和不安全感的加剧,随着个人主义生存追求成为当今的秩序,让新自由主义政治思想通往霸权的大门打开了。
中产阶级社会福利女权主义者被夹在瓦解的工人阶级和被新自由主义掌控的民主党之间,他们开始适应现有的政治现实。 例如,中产阶级的倡导者抛弃了 NWRO 的“both/and”政治,远离了母亲主义话语——“幼儿需要和他们的母亲在一起”——尽管这些话语存在一定问题,但它们一直在扞卫为单身母亲所提供的收入支持。
面对两党对高福利养懒人的指控,他们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话语。他们接受了通过有偿工作自给自足的想法,尽管很明显,大量向单身母亲开放的工作收入低且不稳定,永远不足以支撑生活,所提供的育儿津贴(给最贫穷的妇女)也无法保证优质的儿童保育服务,而且也无法满足儿童课后活动的需要。
换言之,第二次社会福利女权主义浪潮与其说是被接受,倒不如说是在政治上被边缘化了。在这场失败的背景下,自然地,自由女权主义政治不仅来到了舞台的中心,而且融入了一个日益成为霸权的新自由主义政权。
讽刺的是,随着中产阶级倡导者的右倾,工人阶级的女权主义者,尤其是在女性成员占多数或占多数的工会中,正在取得可观的收益。他们增加了女性在领导层中的代表性,推动工会支持捍卫合法堕胎的政治动员(例如,工会妇女联盟的“支持工会,支持选择权”运动),反对歧视 LGBT 人群,并在谈判桌上要求同工同酬和带薪育儿假。然而,随着工会迅速失去谈判桌上的阵地,后一种诉求无望实现。
过去的历史是具启发性的。女权主义和其他反压迫运动必须是跨阶级运动,所以它们也必须提出“谁将主导这些运动?”的问题。这意味着谁的世界观将决定运动的要求,这些要求如何表达和证明,以及运动本身是如何组织的?
在一般情况下,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中产阶级。然而,正如在第二次浪潮运动不断激进化,工人阶级走上政治舞台的时候那样,社会运动中的权力关系可能会发生变化。
二十一世纪,通过一系列惊人的运动,妇女进入了全球政治舞台。在全球南方,妇女发现自己流离失所、从事不稳定的工作、囿于家庭、在非正规住区和城市贫民窟中挣扎求生,她们不仅成为 21 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参与者,而且还在建立基层组织项目以挑战父权制形式的组织、领导和运动。
在全球北方,这些基层项目采用了新的工人组织模式(如家务佣工运动),这些模式依赖于动员成员和建立社区联盟。当然,这些迥异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项目并非完美,但在北方和南方、社区和工作场所,它们有力地提供了关于性别平等的新话语、新的组织模式和参与式民主的愿景。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对自我组织的承诺为非等级和民主的组织结构提供了支持,因此更具包容性。 他们在关注交叉性歧视,以此作为计划和政治话语的指南——运动提出的诉求和我们用来支持这些诉求的语言——提供了克服深层社会分歧而非再生产分歧的基础。
通过了解工作场所、家庭和社区相互关联的方式,可以认识到更有效的组织模式和联盟政治的更多可能性,在通常被视为迥异和独立的问题和斗争之间建立联系。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关于领导权和领导权发展的愿景提高了积极分子参与民主决策和群体的能力。不断重塑对情感、情绪和性别的认知,并塑造着社会关系,鼓励积极分子的自我反思、同理心和对世界上不同生活方式的尊重。
如果我们要建设二十一世纪的社会主义,那么是时候关注二十以及二十一世纪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将其理论和实践从边缘转移到激进左翼的中心。
2014年9月18日
约翰娜∙布伦纳(Johanna Brenner)是一位长期的活动家,也是《妇女与阶级政治》(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Class,美國每月評論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作者。
原文链接:https://www.jacobinmag.com/2014/09/the-promise-of-socialist-femin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