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9 長樂路:上海一條馬路上的中國夢|史明智
野兽按:同一个作者的两个版本,台版初版是2017年出的,内地版是2018年出的。对照看,发现内地版删了核心人事,也不在书中说明。之前对上海译文的这套纪实系列还蛮有好感的,也大多购读了。如今是要存疑了。删可以理解,但起码要诚实说明一下自己是删节本。
书名:長樂路:上海一條馬路上的中國夢
原名:Street of Eternal Happiness: Big City Dreams Along a Shanghai Road
作者: 史明智
原名: Rob Schmitz
譯者: 葉佳怡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17/09/12
語言:繁體中文
定價:420元
內容簡介
橫跨三個世代,在上海一條馬路上共築中國夢
每個真實人生故事,都是當今中國百姓的希望與哀愁
旅居中國二十年的美國記者,勾勒出當今中國面貌
如果沒讀過這本書,就不該以為了解中國
「人們總是心懷大夢,無論處於中國哪個角落的個人夢想,或是宏大的中國夢……這是一個獨一無二的時代,我希望能捕捉這個時代的細微感受。」──史明智(Rob Schmitz)
今日的上海是國際大都市,也處於巨大變革,每日有無數懷抱上海夢的人子,不斷湧入這個以資本、想法與機會交織而成的洪流中。美國知名記者史明智就是其中一位。
1996年,他以和平隊(Peace Corps)志願者身分首次抵達中國四川,2010年遷居上海後六年,決定以自己生活環境為主題書寫中國。他居住在上海前法租界的長樂路,不但融入當地生活,更與居民發展深厚情誼。本書描繪這些尋常小人物,如何從上海的天際線看到未來天光,又如何創造命運的新機會。
書中的陳凱,八○後,從一個小城的國家企業「逃」到外省,靠銷售義大利手風琴賺到第一桶金,後來和友人合開一家小店;他是中國未來的象徵,有文化但憤怒的年輕人,他的夢想失落於大城市與鄉村之間。另位書中人物傅大嬸,五○後,是資本主義擁護者,不斷找尋快速致富的方法;她是失落的一代,一生過著挫折又貧窮,對現在中國的不平等,表現出憤世疾俗。令作者驚訝的是一盒塵封數十年的神祕信件,裡頭滿是無止盡的權勢與貪婪,不但改變荒蕪社區人民的命運,揭開的不僅是一個家庭的過去,更是中國黑暗的歷史。
這本關於21世紀中國尋常百姓的人生故事,以各具特色的人物描繪每個世代,讀者透過本書能了解這些人追尋夢想的盼望與哀愁。由旅居中國二十年的美國記者,以上海長樂路的真實故事與生活其中的尋常人家為主角,勾勒出當今中國社會的真實面貌,交織成精彩生動的眾生相。
好評推薦
獨立記者 白曉紅 導讀
自由撰稿人 汪浩
跨界評論家 范疇
──真情推薦
Amazon網路書店5顆星讚譽
《世界雜誌》(World Magazine)年度最佳選書
《電訊報》(The Telegraph)年度最佳選書
《紐時》書評(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
《衛報》(The Guardian)
一致好評
「本書令人感嘆又欣喜……透過作者生活在長樂路的見聞,讓讀者更了解中國一般百姓。」──《紐時》書評
「上海一條馬路上的眾多故事,勾勒出當今中國的面貌。」──《經濟學人》
「作者筆下的真實故事,反映出中國政府的政策如何阻礙人民追尋夢想。」──《衛報》
「作者於故事中穿插史實,引領讀者深入了解中國文化正在經歷的複雜轉變。」──《出版者周刊》
「作者揭露了中國活躍經濟下,政府的的貪腐與無能的面目,毀了無數百姓的生活……但上海的生活卻有溫柔的一面。」──《書單》
「只要讀過本書,你就不可能以之前角度看待中國崛起或中國模式。多年後,人們會再次透過本書理解這個時代的中國。」──法羅斯(James Fallows),資深媒體人
「《長樂路》是一本以上海為主題的報導作品,這條道路反映出今日中國的各種複雜矛盾,及令人驚訝的趣味視野。」──何偉(Peter Hessler),《尋路中國》作者
「史明智為我們做了珍貴的紀錄,他耐心描繪了這個缺乏耐心的國家,以及人民生活中各種真切的悲喜、貪婪與溫柔。」──歐逸文(Evan Osnos),《野心時代》作者
「在這本貼身記錄的書中,我們看到一條約三公里的街道體現了現代中國人,抱持的夢想及忐忑不安。」──張彤禾(Leslie T. Chang),《工廠女孩》作者
「《長樂路》是一本有趣、動人、悲慘,但讀來令人讚譽的作品。如果你沒讀過這本書,就不該以為了解上海或當代中國。」──明特(Adam Minter),《一噸垃圾值多少錢》作者
「偉大的城市都會有一本書捕捉它的起落,而《長樂路》屬於上海。」──梅英東(Michael Meyer),《在滿州》作者
「這是記錄中國歷史的萬花筒,從饑荒、文化大革命到一胎化政策。最重要的是,這些故事記錄活在中國夢裡的苦難與希望,以穿透人心的見解與迷人的流暢書寫。」──方鳳美(Mei Fong),《獨生子女》作者
「讀這本書,就像闊別二十年後回到外婆家,遇見許多老鄰居,生活還是這麼艱辛,你會相信嗎?可這些是真實的故事。」──汪浩,《意外的國父》作者
作者簡介
史明智(Rob Schmitz) ,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碩士,國家廣播電台(NPR)、廣播媒體Marketplace駐上海記者。1996年,以和平隊(Peace Corps)志願者身分首次到中國。他是第二位獲得蘋果與富士康同意,進入工廠採訪的記者。2012年,因撰文批判美國男演員戴西(Mike Daisey)在電視上捏造富士康血汗工廠,而獲得「調查記者與編輯獎」(IRE Awards )。他曾獲頒穆羅獎(Edward R. Murrow Award),教育作者協會(EWA)獎章。此書是他的第一本著作。
譯者簡介
葉佳怡
木柵人,現為專職譯者。已出版小說集《溢出》、《染》、散文集《不安全的慾望》,譯作有《恐怖時代的哲學:與尤根.哈伯馬斯&雅克.德希達對話》、《被偷走的人生》、《死亡之心》、《返校日》、《缺頁的日記》、《被抱走的女兒》、《為什麼是馬勒?:史上擁有最多狂熱樂迷的音樂家》、《史東先生與他的騎士夥伴》等十數種。
目錄
導讀 一條路說出當代中國社會的故事 白曉紅/獨立記者
第一章 CK及體制:長樂路八一○號
第二章 城市,讓生活更美好:麥琪里
第三章 熱熱鬧鬧:長樂路一○九號
第四章 再教育:長樂路一六九號
第五章 一盒信件:長樂路六八二弄七○號
第六章 傅大嬸的快速致富計畫:長樂路一六九號
第七章 新娘的價格:長樂路一○九號
第八章 文化青年:長樂路八一○號
第九章 被掠奪的夢想:麥琪里
第十章 逃離:長樂路六八二弄七○號
第十一章 零風險:長樂路一六九號
第十二章 農村婚禮:長樂路一○九號
第十三章 CK的朝聖之旅:長樂路八一○號
第十四章 家
第十五章 中國夢們
導讀
一條路說出當代中國社會的故事
白曉紅/獨立記者
過去十年來,每回到中國都觀察到,人們的自信心越來越強厚。這種自信心有時是以反帝的歷史觀展現出來,而有時更是以發展成頗具侵略性的民族主義情緒表達出來。記得六年前在從北京前往烏魯木齊的火車上,幾位中國人高談國際政治。一位年輕人就對中國與東南亞國家關係發表己見,認為中國要「強硬」才好。他忿忿地說,「我們今天可以抬頭挺胸了!今天的中國不一樣了。中國崛起了!」
「中國崛起」的期望,在習近平的「中國夢」口號下,得到最全面的發揮。由國家來談夢想,那這夢想就必須是普遍、全面的了。它就必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復興大業」了。而這「中國夢」對中國人民具有什麼意義呢?它究竟代表了誰的夢想?
Marketplace的駐中記者史明智(Rob Schmitz)所著的《長樂路》,就是以中國人民的聲音,來探索國家標榜的「中國夢」意義何在。史明智以自己從二○一○年以來居住上海的時間裡,在生活周遭所做的觀察體驗,著寫成這本真真實實,第一手的報導文學,可說是當代中國人民生活的縮影故事。他的人物集中在他和家人居住六年的長樂路,也就是過去屬於法國租界、故事豐富的一條路。
《長樂路》可被看作過去十年,西方出現書寫中國的趨勢的一部分:以顯微鏡式的書寫,呈現大社會。它將視角集中在一個社區,一條馬路,從個人的成長和奮鬥經歷,來呈現社會變遷,突顯個人發展和大體制之間的關係。《長樂路》書中人物來自各行各業,他們在時代變遷和國家體制之中求生存,求進展。他們的個人期許和夢想在體制中不斷受挫、妥協、扭曲,但仍必須繼續走下去。
《長樂路》的故事道出了這個城市在改革開放下的變化,而這些變化並不代表著進步。上海自一九九○年代就已由建築業改頭換面了,人民的住宅,地方政府想拆就拆,既然土地是屬於國家的,要拆房做任何開發改建,人民除了小規模的抗議也束手無策。地方政府就這麼靠著一批批的建築計畫賺錢,地方官富了,開發商富了,給居民一點補償就了事。不願被拆房的,下場有目共睹:被威脅,被暴力對待,甚至喪命的都有。
《長樂路》裡,史明智居住的樓房地點,就曾有一對老夫妻,因為拒絕搬遷,而遭開發商雇來的流氓縱火致死。官商共利的體系導致的這場無人聞問的悲劇,在史明智筆下不斷與國家的「街道精神教育」對立著:「城市讓生活更美好」和「文明」標語充斥在公共廣告空間裡,要求人民共同為「塑造文明城市」來努力。每有重要節日,地方政府更是加強精神教育,比如在博覽會數月前,全市民都收到了厚達兩百多頁的「禮儀小冊」,督促大家「如何做個好上海人」,其中指南包括如何剪髮,如何吃西餐。這是《長樂路》上不時出現的悲鬧劇,或者說,以鬧劇(「街道精神教育」)來道出悲劇(人民死亡)。
國家的「中國夢」是不是人民的夢,那在中國城市裡的上億民工那裡,最能得到答案。「中國夢」要達到理想小康社會,它的一環,就是要控制城市化。對中國當政者來說,「城市人口要是沒管理好,那國家就亂了」。三十年來的改革開放期間,許許多多農民都決定離鄉到城裡改變自己和家人的生活。中國向世界市場開放後,本國發達起來的各項製造業都需要勞工,當農村男女來到都市謀生時,像上海這樣的城市也成了世界工廠。《長樂路》上最突出的人物之一,就是來自山東一個礦村的趙小姐。她和上百萬農村人一樣,心滿憧憬的來到上海,這個對她來說連名字都美的地方。
而上海並非她夢中那個美好城市。在一家電子工廠的流水線上吃了兩年苦後,老闆開除了當時三十一歲的趙小姐。他的理由是,她年紀太大了。哭求一番也沒用,工廠政策是,女工一到二十五歲就得走人。哪裡有什麼法規來規範這些工廠的聘用規則和勞動條件呢?國家政策關心的,是要維護這樣的體制:農村來城裡工作的,只得販賣最廉價勞力,不可享有任何城裡人享有的權利。
在戶口制度下,趙小姐的孩子不能在城裡就學,成了「留守兒童」。「留守兒童」占中國兒童人口的五分之一。趙小姐將大兒子帶到城裡,想讓孩子努力學習,在上海長大。但校方知道他的戶籍後,他必須立即停學,回到礦村裡。她的二兒子因母親遠在上海,長期無人照顧關心,個性自閉,精神焦慮。
在中國探訪期間,我曾看到許許多多農民工帶在身邊的子女,在大城市裡無法享有平等的教育權,不被學校接受,不能入學,只能在農民工社區裡自設的,設備缺乏的學校裡上學。比如在北京期間,曾看到這些自發的農民工子女的學校被一一關閉,因為他們不合建校規範。而民工子女無處就學,因為國家不給他們平等教育權。這些孩子的福利和個人發展,不是中國大夢的關注。他們只能在體制的縫隙間求自保。曾有位在北京討生活的民工對我說,「我們都是在同一個天空下生存,為什麼我們沒有和他們同樣的權利?」
《長樂路》裡的趙小姐問著同樣的問題。她和她的孩子常年體驗到什麼是「城市暴力」:就是在城市裡國家政策造成的社會隔離。她知道,對她這個階級的人來說,夢想的實現,必是得吃苦一輩子才能掙得的。或甚至是吃苦一輩子也掙不得。農民的身分,在中國是從未改變的,不論中國怎麼變,怎麼崛起,怎麼強大。身為農民,就算在城裡奮鬥一輩子,還是農民。《長樂路》裡道出她不服輸的精神,她與體制搏鬥的故事。
史明智以他切身的觀察和細膩的文字,描繪出許多中國人民的夢想。《長樂路》記錄的不只是一條馬路上的故事,而是當今中國社會的故事。它是對統治者塑造的「中國夢」做出的一份深切的質疑和批判。
书摘
長樂路長約三公里,當交纏的路樹枝枒在冬日落光葉子,你就能穿過枝幹看到遠方這座城著名的天際線:金茂大廈、上海環球金融中心、上海塔。這三大巨人矗立在比鄰的幾個街區,每一棟都比紐約的帝國大廈還高。
路樹底下的人們卻忙到無暇欣賞此景。在長樂路中段的上海第一婦嬰保健院裡,許多新生兒展開了人生的首日;長樂路西側的華山醫院急診室中,許多人則度過了人生的末日。兩院間的這段則是形形色色的生活:一個蓄鬍的乞丐坐在街邊吹竹笛,情侶手牽手經過他,一堆車子被堵住圍著兩個男人按喇叭,兩人互啐口水爭論到底誰撞到誰,穿制服的學生聚在一旁圍觀,一個拄著拐杖的老婦人為了荔枝的價錢嫌惡地吼著一個小販,至於其他區段則是被川流不息的人潮推著走,不時傳來一陣陣肉包攤的鹹香及車流廢氣的苯甜味。這裡的生活喧鬧、髒亂,又生猛。
地圖上的長樂路不過是上海中心人民廣場西南側一條彎彎曲曲的細線。我家就位於這條細線的西側。從我家望出去便是樹冠,兩層樓高且幾乎終年成蔭。在那底下唯一立定不動的生命只有這些樹。有許多早晨我繞著這些樹幹迂迴前進,從人行道走上路面再回來,身處爭搶樹蔭的行人之列。
中國少有街道像這裡一樣種滿路樹。到了週末,當地工人的擾攘被中國各地的遊客取代,他們用長焦鏡頭捕捉這兩排枝幹,欣賞其中的異國風情。這些樹是在十九世紀中期由法國人所種下,當時歐洲人和美國人正瓜分此城為租界。近一個世紀後,法國人離開,樹卻留了下來。日本人曾轟炸上海,一度占領了這座城市,但最終是撤退了,留下這些法國人種的樹毫髮無傷。接著是毛澤東帶領的共產黨發起革命,階級鬥爭,數百萬人英年早逝。樹卻長存無礙。這條街現在充滿資本主義,兩側滿是餐廳與各式店家,當我在人行道上漫步,偶爾會從關閉的閘門縫隙中瞥見傾頹的歐式家屋,心想這條街目睹了多少歷史的殘酷動盪。此地猶如一朵帝國玫瑰,凋落後又重新綻放。始終屹立的只有這些樹。
在這條街上住了將近三年,我才注意到陳凱的三明治屋。這家店距離我的公寓不到一個街區,在一間很小的衣飾店樓上,且在溫暖的夏天,幾乎整間店都被茂密的梧桐樹擋住。從狹窄的螺旋樓梯走向二樓,首先會看到整片落地窗,窗外一整片枝葉搖映,將底下上海市的喧囂隔絕開來。
陳凱(音譯)──他總自稱CK──有時會彎著身體在櫃檯工作,一頭蓬亂黑髮幾乎蓋住眼睛,細瘦手指正在為一份三明治或甜點收尾,然後甩開額前鬃毛般的髮絲,轉身以機械化的動作從義式咖啡機為顧客揮出一杯滾燙的咖啡。不過店面通常空無一人。「沒關係,生意起步需要時間,夢想都是這樣的。」他如此告訴自己。每當此時他就會頹廢地坐在吧檯高腳凳上,長滿青春痘的孩子氣臉龐背對滿是樹影的落地窗。他講電話時會切換不同中國方言,為副業談生意:他還兼差賣手風琴。
他之所以想開三明治屋,是在芝加哥光顧過一家之後。那是他人生唯一的一次美國行,對美國人而言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卻讓他印象深刻,因而想為中國的外食客戶提供類似體驗。有點像是來過中國的美國人深受小麵攤啟發歸國一樣。這種看似衝動的做法,這條街上我認識的很多店主卻都是如此。身處上海這樣富裕的大城市,只要有心幾乎什麼都能賣。
CK夢想有一天能靠這間帶有藝術氣息的二樓三明治屋維生。他投入多年販賣手風琴攢到的存款,和一個朋友合資共同打造了這個空間,希望吸引跟他們一樣的年輕音樂家和藝術家前來。
「某天我突然有了一個想法:說不定我能把這些人聚集、團結在一起。我想尋找那些想要掙脫體制的人。我想要同類的朋友;那些對藝術、時尚設計或其他不同產業有獨立想法的創業家。」他告訴我。
很多人有著與CK類似的野心,在長樂路散步於是成了一趟驚人的體驗;狹窄的街道兩旁滿是與CK店面類似的小店和咖啡館,雙眼明亮的異鄉人帶著夢想爭奇鬥艷,都想在這座大城市追求成功。
成功可不容易。CK和朋友Max都沒有在餐廳工作的經驗,更別說是經營。他們相識於一家前法租界區的古董相機店,當時CK為了學習攝影在那裡打工。如同CK,Max也擁有創業家背景;經過多次搭班的長談,兩人都欣賞彼此製造及銷售商品的生意手腕。最後CK說服了Max與他合夥開一間三明治屋。
他們把店面命名為「你的三明治屋」,距離一個繁忙的地鐵站只有兩個街區,旁邊就聳立了一棟四十五層高的大樓,每天中午總有數百名上班族從大樓內湧出,尋找一頓能快速解決的午餐。但沒人能看見這間被梧桐樹擋住的「你的三明治屋」,沒人在匆匆走過長樂路時抬頭透過樹冠望見他們。
所以他們把店名改成「二樓」,暗示路過行人抬眼看看他們,新店名底下以低調婉約的字體寫了「你的三明治屋」。他們雇用一位新主廚,也打造一座提供多種飲料及進口啤酒的吧檯,而且異常執迷於在菜單上玩花樣。某天我順路拜訪CK的公寓,看到角落堆放一疊電子平板,「觸控式菜單!」CK微笑著對我說。他想必覺得,無法互動的枯燥菜單正是吸引不了i世代年輕人的原因。
他在銷售手風琴的事業上快速賺了不少錢,但作為餐廳經營者實在天真。此地的午餐食客通常是要辛苦掙房租的上班族,他們追求的是便宜的在地食物,通常也寧可選擇使用筷子入口的熟食。接下來幾個月,CK得努力適應這項現實。他開始提供價格親民的午間特餐,也稍微將三明治的價格調低。不過他自始至終都不擔心這間快餐店的命運,畢竟銷售手風琴的獲利穩定,此外,他覺得能在自己住處同時處理兩項事業非常幸運,如同一隻懂得運用資源的松鼠為了過冬在自己的舒適樹屋中囤滿堅果。
這間三明治屋可說是避難所中的避難所。附近街區原本就是為外來者建立的庇護處。一八四二年初次輸掉鴉片戰爭後,清朝將部分上海市及其他港灣城市割讓給西方強權。法國占領了城市的這個區域,將曾經廣闊的稻田轉變為專屬街區,即一八四九年確立的法國租界。打從那時起,法國就為一個個弱勢族群提供庇護,比如一八六○年,由暴動農民發起對抗清朝的太平天國起義時,此地就收容過成千上萬尋求避難的中國難民。此後即便每任該市的中國領導都表示反對,劇場、電影院、舞廳仍在法國保護下繁榮興盛,很快地教堂、寺廟、清真寺也多了起來。
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取得政權,將外國租界詆毀為受到外侮的恥辱象徵。但在他們的政黨宣傳中卻漏掉一個事實:一九二一年,二十八歲的毛澤東便是在法國租界深處的一間女子寄宿學校與其他思想激進的年輕人會面,召開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屆全國代表大會的。毛和他的同志之所以選擇這裡,正是因為租界得以提供庇護。唯有在此,該市的中國掌權機構才不容易找到他們,免於被逮捕後遭審判的命運,那會使得中國共產黨無法落地生根,將徹底改寫中國的歷史命運。
法國人依照典型巴黎城區的樣貌建造此地街區:這些狹窄蜿蜒的道路兩邊植滿了當地人稱為「法國梧桐」的樹木,意即「法國鳳凰木」,但它們其實既不來自法國,也不是鳳凰木。正如同上海混沌的歷史,這些樹更四海為家一些:它們是倫敦梧桐,為原生自中亞的東方梧桐及美國梧桐的混種。此外,第一株倫敦梧桐其實是在西班牙發現的。
喬治—歐仁.奧斯曼(Baron Georges-Eugène Haussmann)男爵是使得倫敦梧桐舉世聞名的推手。這位城市規劃師熱愛倫敦梧桐枝葉茂密的外型,於是十九世紀當他將巴黎從布滿混亂的小街道變身為由兩旁植樹的寬廣大道街區,便在整座城市內種滿倫敦梧桐。沒多久,倫敦梧桐就在全球各地出現,直到今日,還占領著許多世界級的大城市,例如羅馬、雪梨和紐約。它的葉子和楓樹很類似,現在也是紐約市公園處的徽章圖案。
上海路樹中有三分之二都是倫敦梧桐。城市規劃師將其稱為「超級樹木」,因為根系淺,而且對煙塵、極端溫差、蟲害的抵抗力極強。樹與樹之間的種植間距約五至七公尺之間,修剪時必須採取一種稱為「重複截頂修剪法」(pollarding)的技法,截斷一側以刺激枝條往道路對側生長,兩邊的枝條在路面上方糾纏形成兩至三層樓高的深綠色隧道。這種綠色拱廊能為行人遮擋夏日令人汗流浹背的烈陽,也能阻擋從東海頻繁席捲而來的猛烈暴風雨。
我在二零一零年搬到長樂路,此地的巴黎街區樣貌猶存,但中國已重新為道路命名。薛華立路(Rue Chevalier)改成建國路,賈爾業愛路(Rue Garnier)改為東平路,中文意思是建立國家及東方和平。其他用來紀念已逝法國名人的道路則改名為富民路、茂名路、瑞金路。每當走在這個新定居的街區中,我總藉著誦唸這些聽起來喜氣的路名來練習中文,像是安福路、永福路、宛平路。我所居住的大概是聽起來最喜氣的一條:長樂路,代表「長久的快樂」,但我為了讀起來更通順,於是將其英文名修飾為「永恆的快樂」(Eternal Happiness)。
不過當地人看到街名時,首先想到的不是通順或喜氣與否。舉我公寓南邊的安福路為例,「安福」其實是江西省的一座小城名稱,當地以加工豬肉成為火腿聞名。茂名路的「茂名」是一個繁榮的廣東港市。我所居住的街名「長樂」,也是福建省一座海岸城市的名字,明朝探險家鄭和就是從此出發探索了幾乎整片亞洲。當中國政府重新命名這些擁有法國名字的街道時,他們將南北向道路以中國省名或省會名稱命名,東西向則以當時繁榮的各地城市命名,而這些名字早在好幾個朝代前就已如此喜氣。
每次在長樂路上騎腳踏車,我總是非常需要好運。這條狹窄的街道是這區少見的雙向道,計程車常利用此街避開附近高速公路的車潮,但也得應付幾乎從每個縫隙竄進來的電動機車。這些電動機車通常會成群地逆向行駛,每當有車子要迎面通過時才會在最後一刻散開,好讓車子穿過這片機車陣,弄得喇叭震天價響,一片車燈亂閃。道路規則正是所謂的適者生存,路權永遠屬於體積最大、攻擊力最強的車輛。位於食物鏈頂端的是上海市公交車,它們光靠體積就能得到機車騎士與汽車駕駛的尊敬,讓路給這隻龐然大物,如同動物避開橫衝直撞大象的某種生存直覺。正因為如此,腳踏車只能在路肩或人行道上自求多福,並為了發洩穿梭於路上的人流。
我選擇和電動機車一起用路。我通常騎得夠快能趕上他們,而他們的用路習慣(移動得像環法自行車賽的主車群)也能提供我必要的保護。但每天早上騎車,我還是得時時留心周遭環境。儘管這些上路的車輛貌似一片混亂,許多駕駛卻擁有狀態良好的運動員般的專注力,遵循著路上的潛規則。他們彼此配合在路面上移動,沿著長樂路或加速或繞彎,看似混沌卻自成系統。
二○一二年一個寒冷的冬日,我爬上「二樓──你的三明治屋」的螺旋樓梯,想在角落的小卡座喝杯咖啡取暖。窗外梧桐樹的枝條裸露得像易碎的筷子,雜亂地指向各方向,每當有凍人寒風沿街掃過,就會吱吱嘎嘎地刮擦著二樓的落地窗。
日照充足的餐廳中央架子上擺著CK的手風琴,這架黑色巨大樂器前方以優雅的草書體刻了義大利名琴品牌Polverini(博羅威尼)的字樣。店裡那天是沒客人,CK抓下手風琴,頹然坐進一個沐浴在日光下的卡座,低著頭,按下放氣鈕,緩緩拉開風箱。樂器發出深深嘆息,簡直像來自CK本人。其實就在前一天,他的主廚一怒之下辭職,還帶走一半的服務生,如果今天有客人來,CK和Max只能靠自己了。
他停頓了一下,接著手指在鍵盤上快速舞動,彈奏出一首激烈的快板民謠。他隨著逐漸成形的旋律閉上雙眼,風箱收縮與擴張的律動有如流水,快速移動的手指彷彿有了自己的意志。那是一首他兒時的愛國歌曲,隨著他頭的前後擺動,回憶突然洶湧而上,驅動歌曲進行,愈來愈快。
CK是在十一歲時領悟了這件事:自殺並不容易。整整兩個月,他每天放學都在尋找可行的自殺方法。吞安眠藥似乎是最舒適的選擇,他心想,但藥師不願賣給他,「你太年輕了。」她說。從家中公寓屋頂跳下來也是個方法,但算了,他做出結論:太痛苦了。「我發現自己沒有跳下去的勇氣。」
還有一個問題:他幾乎沒有獨處的機會。他是家中獨子,父母非常強勢,奶奶(即他的外婆)只有在他上廁所時才不會跟在身邊。每天早上他都與他們坐在咫尺喝粥。沿著郊區家門前的土路一直走就是他的學校,到了那裡換老師接手控制一切。放學回家後他又回到奶奶和父母身邊,做作業,學琴,吃菜飯當晚餐。就連睡覺他都無法偷到獨處的時間,因為奶奶就睡在身旁的竹蓆上。
某天下午他父親正在桌前寫字,他下決心最後一次盤點這間寒冷荒瘠的公寓。屋外飄著來自鄰近化學工廠與挖礦設備工廠的濃重廢氣。他走過整間公寓,安靜地到處尋找最具有結束生命潛力的物件。這趟旅程終結在他唯一有正當藉口獨處的空間:廁所。最後決定就是父親刮鬍刀組中的一片直紋刀片。某天晚上就寢前,他偷偷把刀片藏入睡衣口袋。
那是一個涼爽的秋天夜晚,月光散滿屋內。夜晚一片寂靜,只剩奶奶穩定的呼吸聲。遠方斷續有火車開過。首先是一聲輕柔、悠長的喇叭,接著貨運車廂沿軌道開過,發出撫慰人心的隆隆音響,最後消失於黑暗中。CK等待奶奶睡著的同時,一邊想著這個家庭。
CK從小時候就常聽父親提到「體制」一詞。他從來不確定是什麼意思,但可以預測父親什麼時候會說出口。父親會在說之前會微微停頓,緩慢而刻意地加重語氣,使其在句子裡有所區隔,好讓兒子知道此時該留心。
「你知道嗎?凱凱,你就是不可能對抗……體制。」這個詞早以粗體銘刻在男孩的記憶中。
辛苦工作一天回到家,他父親會要兒子坐下來好好聽他發牢騷。體制不讓他選擇自己的職業。體制不褒揚有才智的人。體制不鼓勵個體表現。你永遠不可能在體制內超前別人。「中國的國情不好!」他父親會如此憤怒地說。
「我父親自詡為知識分子,他不喜歡自己的工作,對於無法選擇想要的事業也不滿意。他知道自己比其他人聰明,希望能靠才華成功,但沒辦法。體制不允許這種事發生。我母親不夠聰明也令他沮喪。他不喜歡公司的同事,更痛恨中國。」CK說。
每當CK想提問,父親都會要他閉嘴,繼續自己的長篇大論。最後CK覺得在一個沒人聆聽的家裡說話毫無意義,從此乾脆不再開口。
CK沒有任何兄弟姊妹,他出生於一九八一年,正好是一胎化政策執行的第二年。他和母親、父親、奶奶四人同住於一棟破敗四層磚樓的頂層,是鐵路局分派給他們的房子,他的奶奶在那裡工作。這棟樓的樓梯間總是滿地垃圾。CK的父親用今日體制所使用的口號(也就是鄧小平的「四個現代化」和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描述這個地方,「他稱這裡是『三不管地帶』──沒人打掃、沒人管理、沒人在乎。」
這也能用來描述CK成長的城市,衡陽。衡陽距離上海的就跟芝加哥距離紐約差不多,歷史上就是個人們避免前往的地方。衡陽位於中國中部的湖南省,在中國歷史上曾短暫出現,當時唐高宗將一名不服的臣子貶到那裡。之後許多皇帝一次次地把叛逆的高階大臣貶謫那裡,去治理一個邊疆轄區,此後幾難聽到這些人的消息。
然而現代衡陽的命運也沒好到哪去。如果看中國的運輸地圖,南北向與東西向的鐵路在此交會,在全國的中心形成一個X狀的網路。這裡是此區重工業的要地之一,到處都是化學工廠,另外還有產煤、鉛、鋅的礦場。被汙染的空氣散發腐臭味,但製造了不少工作機會:CK的奶奶就是在鐵路局工作,母親在磷肥料廠,父親則在衡陽第二建設公司。
CK的父母和共產中國同樣出生於一九五○年代初期。這個世代的成長過程隨處都是共產黨精神分裂式的口號標語、革命,以及導致數千萬人死亡、受迫害或入獄的反革命,那些年可說少有寧日。生存仰賴的是某種適應政治環境快速變動的能力,並清楚知道這就像受困洪流之中時,你必須忍住逆流而行的欲望。你總是有機會耐心地找到保全自己的出路,前提是你必須放棄試圖掌控體制。
CK的父母在青少年時期曾下鄉多年,是毛澤東掌政時期都會孩子的必經之路。毛澤東夢想一個都市人與農夫並肩工作的無產階級烏托邦,但隨著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這個夢想也隨之消逝。大部分下鄉插隊的年輕人立刻丟下鋤頭回到家人身邊。但才剛到家,黨又再度介入,將所有人分派到國營企業工作。因此直到三十歲,CK的父母都不曾為自己的職涯做過任何選擇。
「你想要畫畫或拉小提琴嗎?」一九八五年的某天CK的父母這麼問他。一家三口圍坐在飯桌上,兩個大人努力在孩子臉上尋找答案。他父親一直想當個作家或音樂家。他深信自己要是兒時得以熟習一種藝術專長,就有可能擺脫剝奪他所有職涯選擇的體制的掌控。因此,他認為應該將兒子推入藝術世界,要是中國經濟哪天又轉了風向,這將成為他的安全網。
CK的父母以家族成員的才華來收束兒子的選項。他奶奶在插畫方面非常有天分,父親則曾偶然在垃圾堆中撿到一把二胡(和小提琴有點像的二弦樂器),自學後也能演奏。這兩條顯然就是他的出路。
「畫畫或拉小提琴?」父親瞪著兒子,態度強硬。男孩想了一下子。
「畫畫。」他回答。
他的父母轉身背對他,悄悄地商量了些什麼,然後轉身回來,父親宣布,「你得學小提琴。」
CK當時才剛滿四歲。
(摘自第一章 CK及體制:長樂路八一○號)
来源:https://book.douban.com/review/10317652/
【品·鉴】长乐路大陆版和台版对比
千年萧萧 评论 长乐路 2019-07-18 15:59:14
嗯,还是上传图片版本吧,其实相差最大的就是台版的一篇序,大陆版则没有,另外翻译风格不同,但是大体意思基本一致,台版也有一些注释,大陆版则多了最后的参考书籍和资料,外国作者更偏向于纪实,看问题喜欢从小的方面入手,也可能这就是从个体到整体,真实深刻就是这个纪实系列的代名词,通过观察小人物来观察整个国家,这也是外国记者的细微洞察之处,无论如何,这本书带来的感触还是很深刻的。(前面这些字是为了凑够字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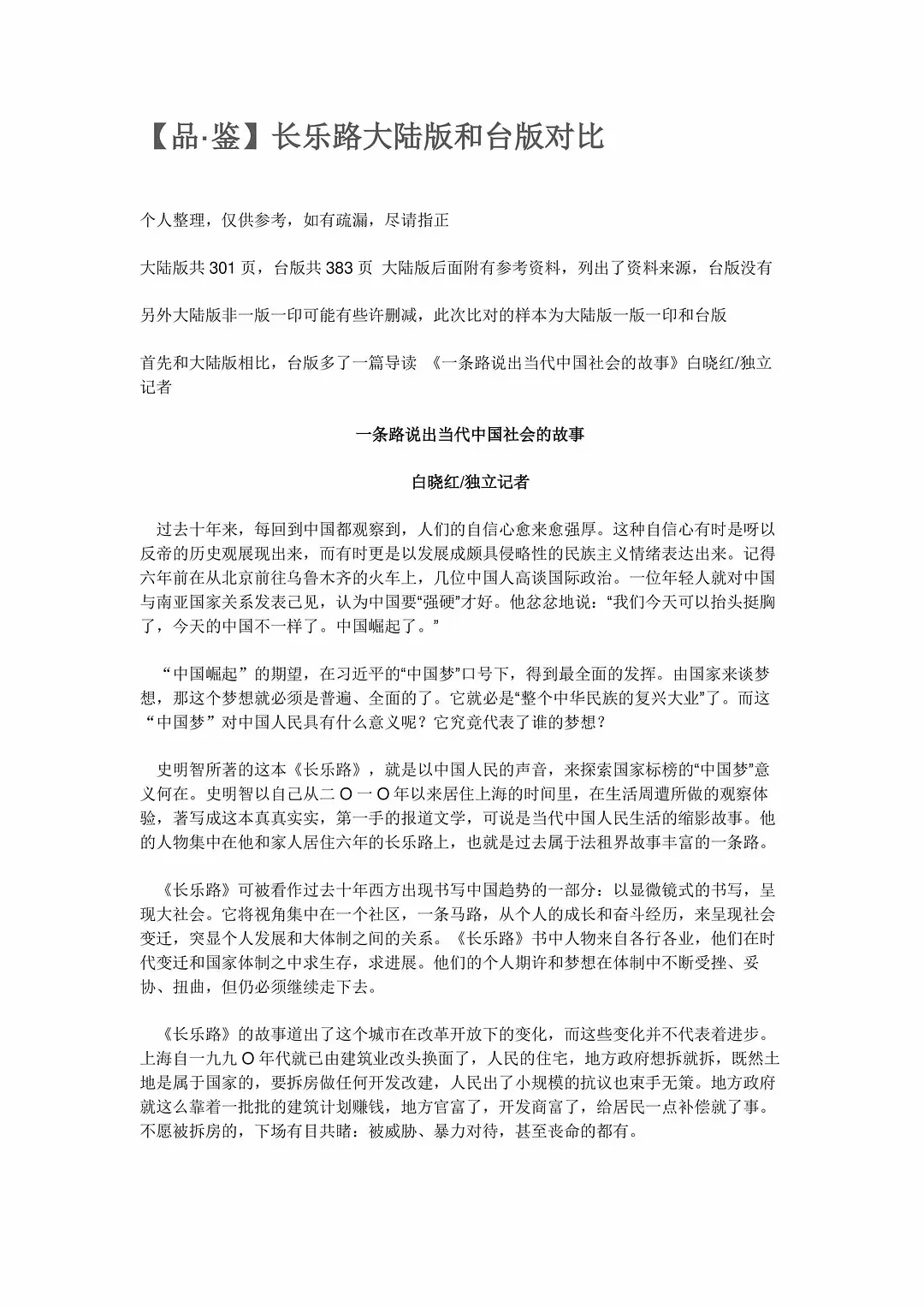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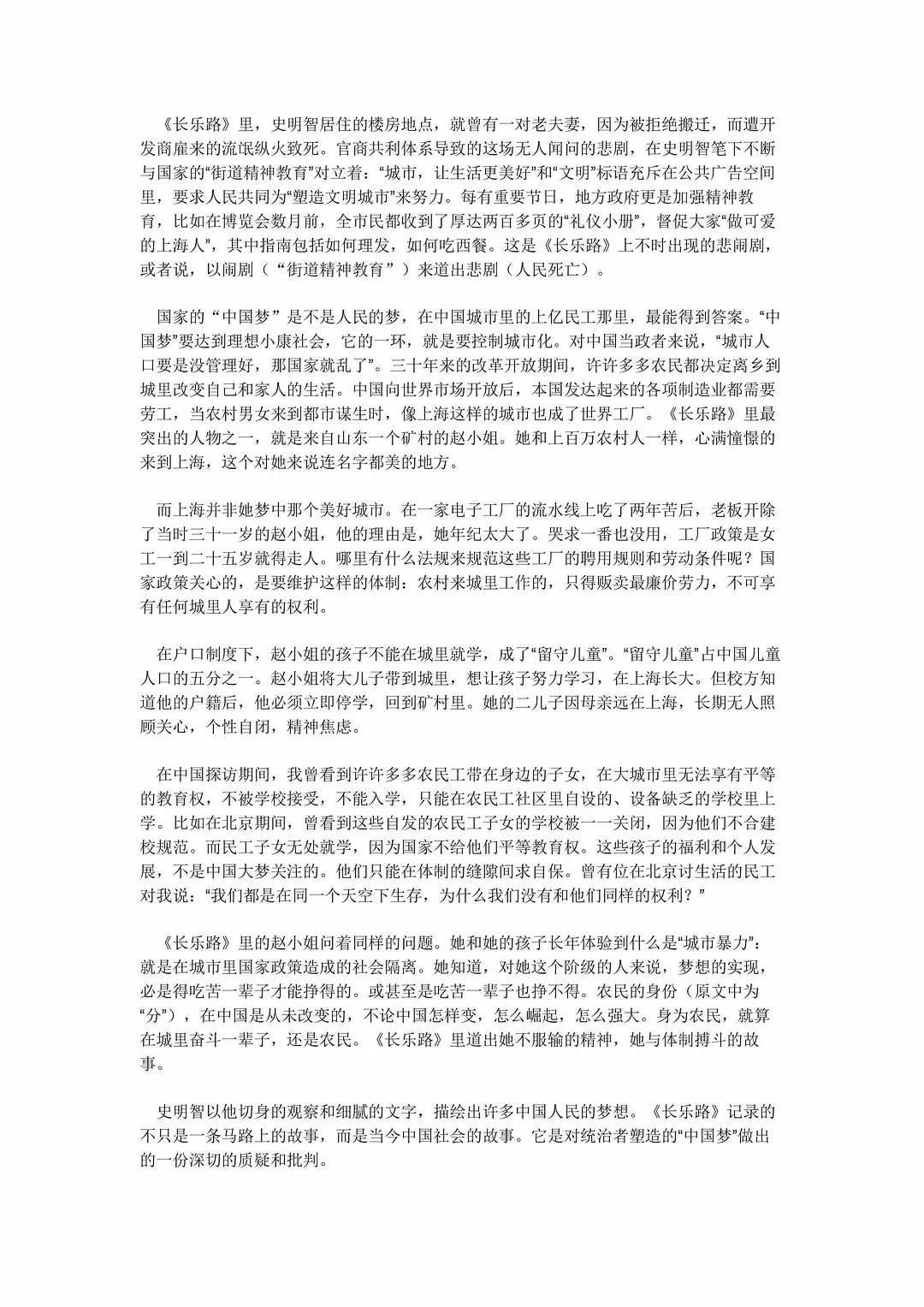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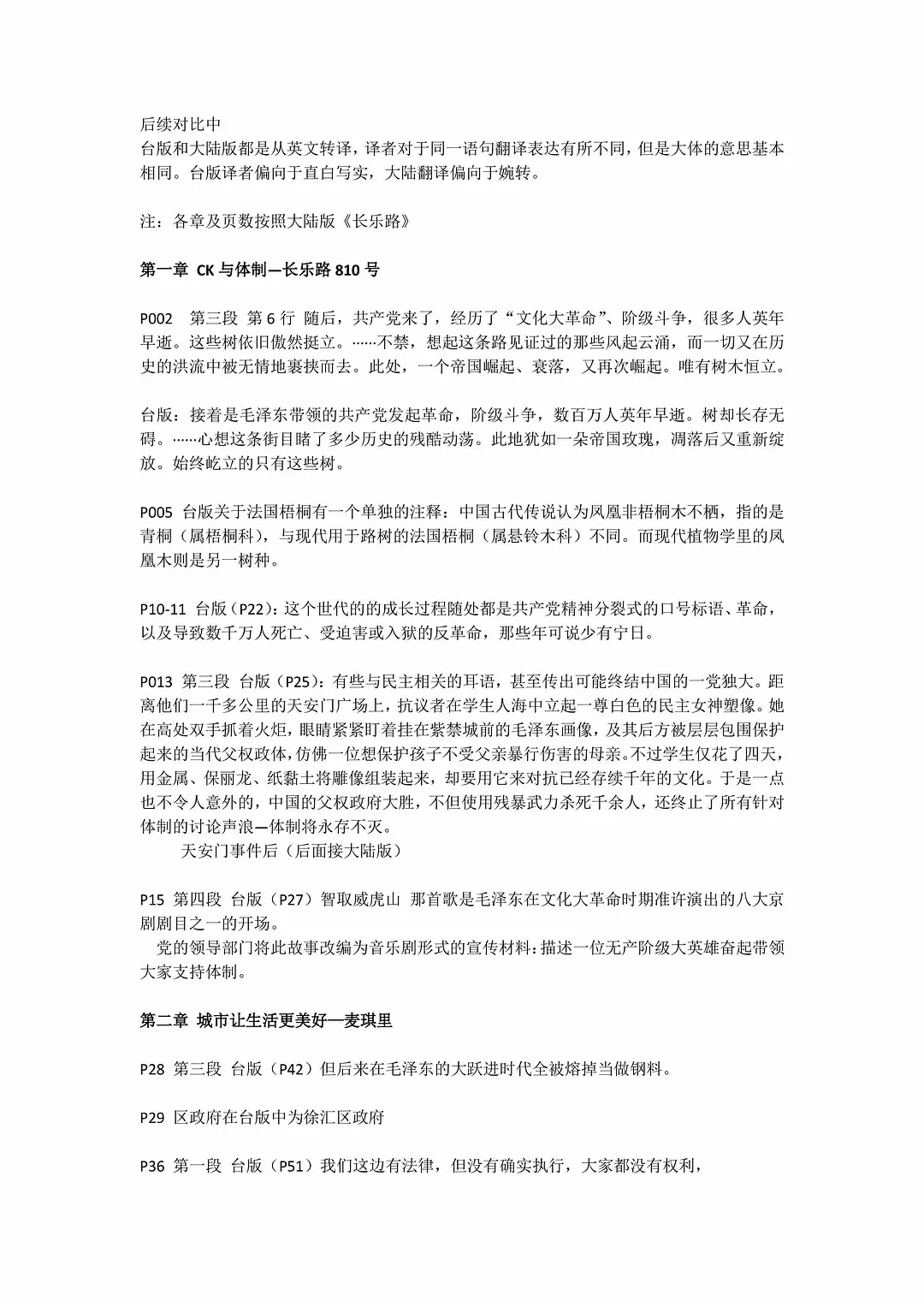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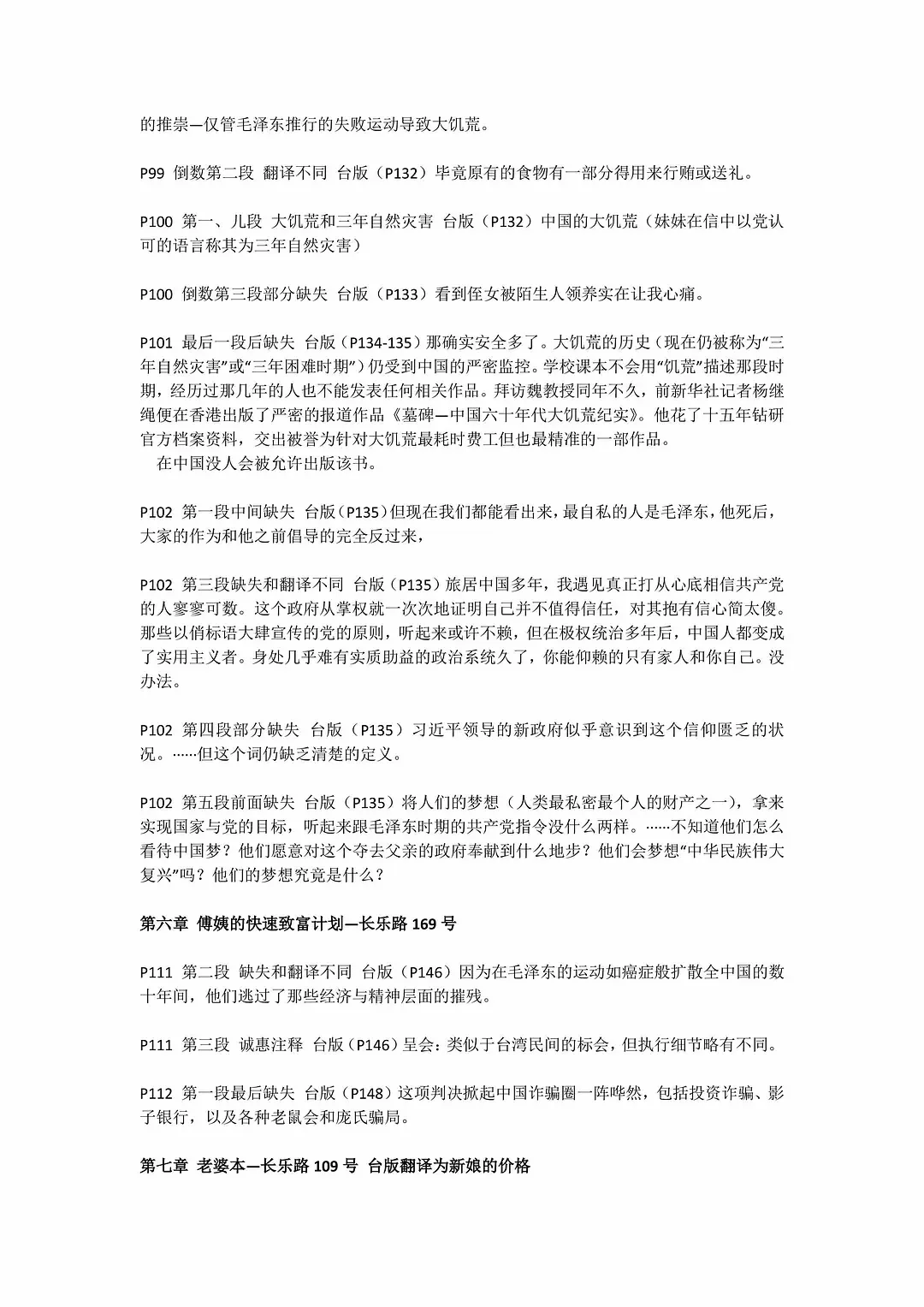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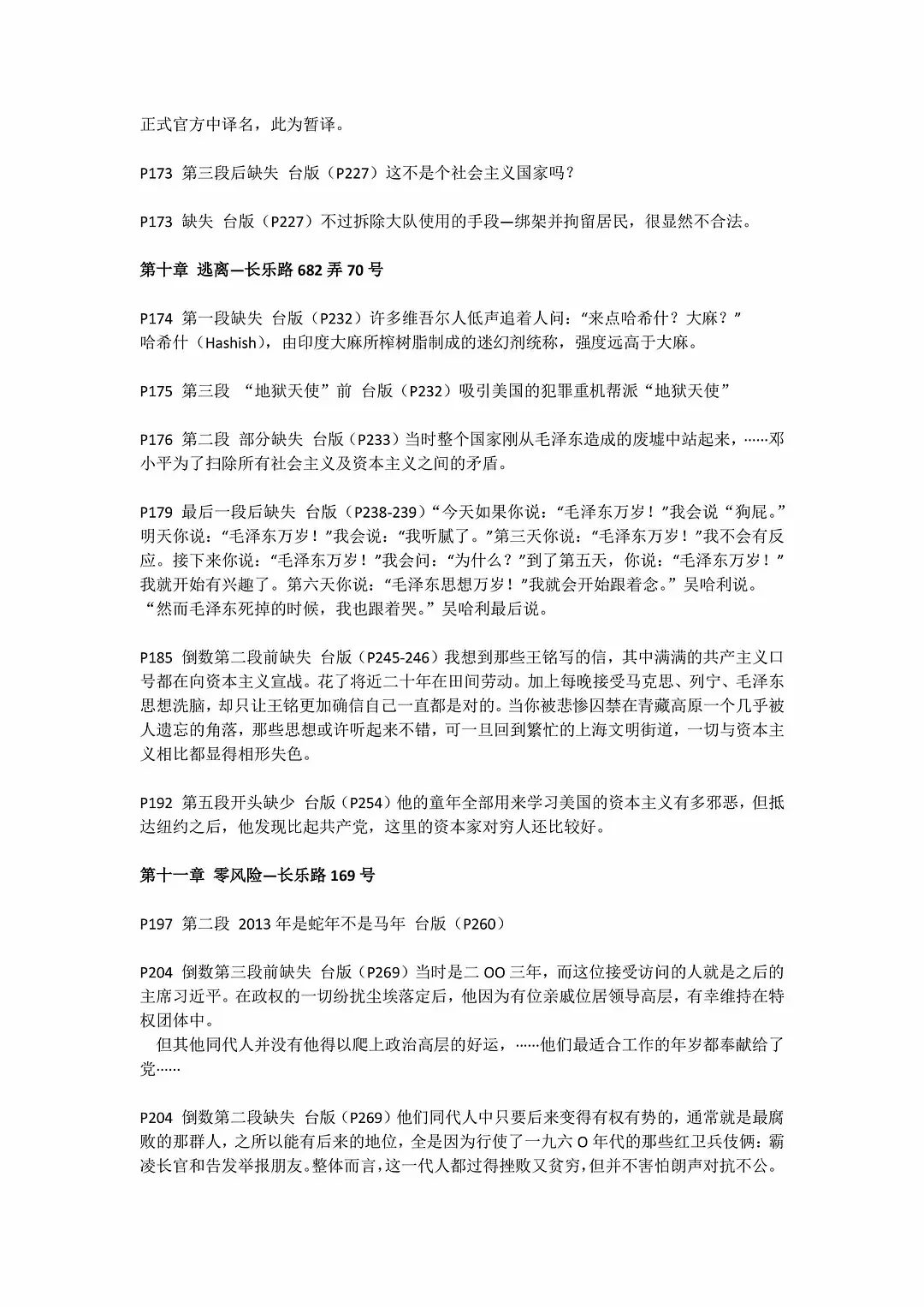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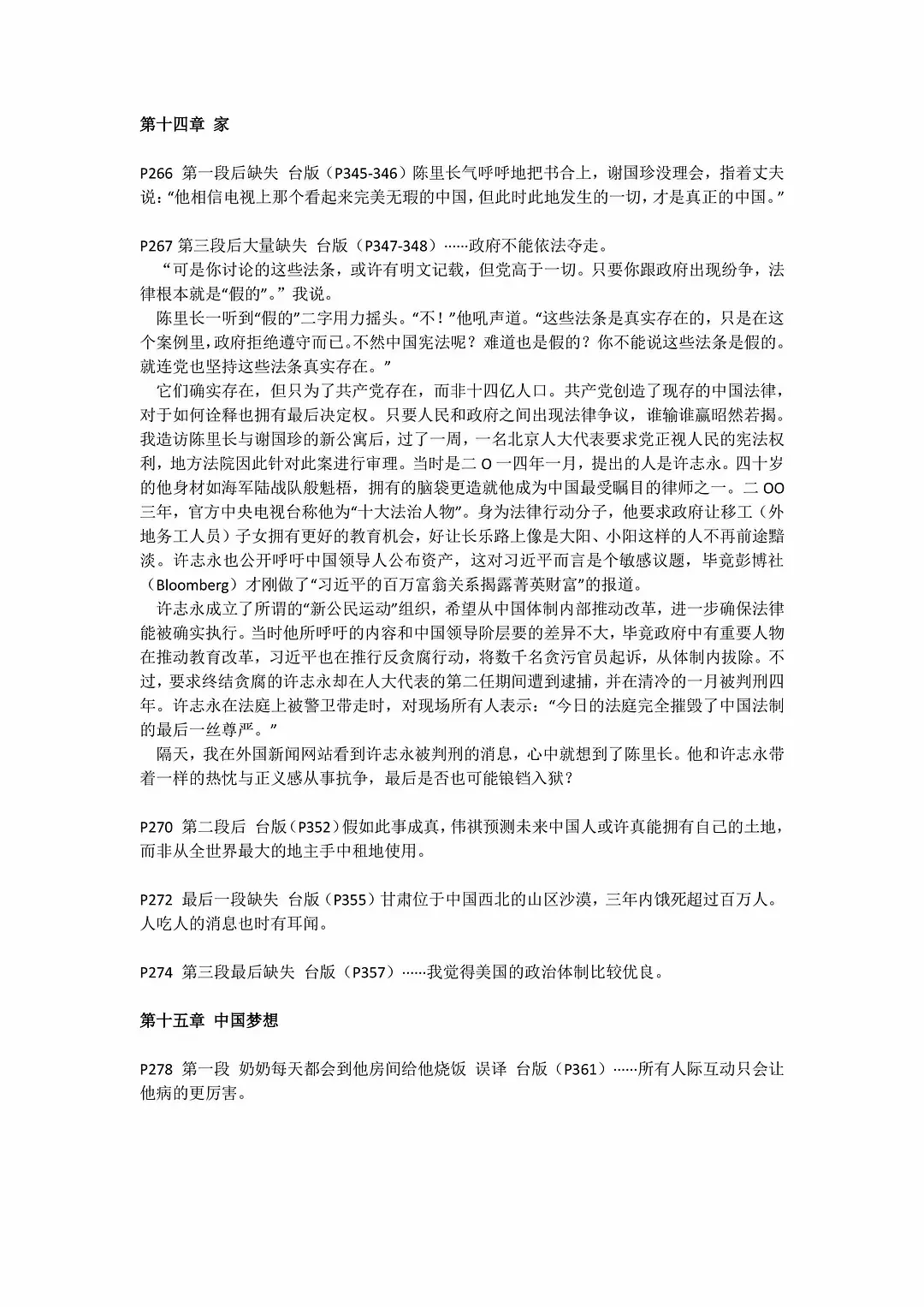

两个版本相差已经超过了一万字,各有各的优点和缺点,大陆版翻译婉约含蓄;台版翻译直接详细
禁书解读 | 余杰:上海离德令哈只有一步之遥 -- 史明智《长乐路:上海一条马路上的中国梦》
2022.05.09
那些追梦的人,如今在哪里?
一九二零年代早期,四度访问上海的日本作家村松梢风在《魔都》一书中夸张地写道:“在街上行走的,男的你就当做是盗贼,女的就当做是娼妇吧。”这种话今天可不能乱说,是严重辱华。
在辛亥革命之后五年来到中国的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每天都写报道寄回日本发表。他吃着油条,看着《新青年》,行走在上海这座比东京更繁华的城市的大街小巷。他发现,沪上文人大都有“叫局”(招妓)的风习。在雅叙园的局票上,“角落里还印有‘勿忘国耻’的字样,以鼓动反日的气焰”——这就是中国特色:招妓不忘爱国,爱国不忘招妓。他在街头看到有人买卖孩童,对方告诉他:“小点的三块钱,大些的五块钱,想要更大一点的孩子,那家的姑娘十五岁,五十块带走。”他拜会了曾留学东京大学的激进知识分子李人杰(李汉俊),聊到对时政的看法。李说,“现代之中国无民意,无民意则革命不生”。四年后,中共一大在李人杰家中秘密召开,因引起巡捕房注意,又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与会者之一就是日后将改变上海和中国的“英雄”毛泽东。李人杰一九二七年在武汉被桂系将领捕杀,没有看到中共建政后,为了提防革命而扼杀一切民意。最资本主义的上海,却是中国共产党的摇篮,这一矛盾的双重身份,至今仍然在困扰着上海。
将近一百年后,美国国家广播电台的记者史明智在上海居住数年,对已然翻天覆地的上海作了系列报道。《长乐路:上海一条马路上的中国梦》是他第一本著作,用白描手法勾勒被官方的“大梦”遮蔽的若干上海小市民(很多是外地移工)的“小梦”。他并不认同习近平的“中国梦”,认为“将人们的梦想(人类最私密最个人的财产之一),拿来实现国家与党的目标,听起来跟毛泽东时期的共产党指令没有什么两样”。他也发现,“真正打从心底相信共产党的人寥寥可数。这个政府从掌权就一次次地证明自己并不值得信任,对其抱有信心简直太傻”。他更发现,在长乐路上,很多平凡人有自己的梦想,并努力追寻其梦想,他乐观地期待由此出现中国美好的愿景。
史明智笔下,有来自山东乡村、经过多年打拼在长乐路上开了一家花店的赵女士,虽然她没有办法让两个儿子在上海读书并参加高考,但她让他们成了半个上海人;还有来自湖南衡阳的青年小陈,他靠做意大利手风琴公司的中国代理而致富,在长乐路上开了一家洋气的三明治店,虽然这家店没有赚到什么钱,但他希望这店成为梦想的起点;还有担任美国最老牌广告公司智威汤逊上海分公司企划总监的陈亨利——这名在上海长大、毕业于复旦大学的青年,相信中国年轻人正在以西方的方式追求个人主义,更相信中国的文化根源与遗产能让中国“所向无敌”;还有一个由高阶主管和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组成的重机车队,他们在工作之余驾驶着各自的坐骑到西藏和新疆旅行,由此找到一种自由情怀和生命激情。这一面的上海与中国,生机勃勃,活力四射,良善美好,有一种美国“镀金时代”的气息。然而,在史明智写下他们的故事不到十年之后,在暴力封城的上海,他们还安好吗?他们的梦想还能持续下去吗?
那些梦想被掠夺的人,不会停止抗争
史明智用更多篇幅描述那些梦想被掠夺的人。追求梦想、正在实现梦想和已然实现梦想的人,毕竟是少数;在上海和中国,梦想被掠夺的人才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极少“在沉默中爆发”,而通常“在沉默中灭亡”。史明智赶上了上海经济成长的爆发期,每天都有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但每天又都有人的尊严被践踏、人的生命被毁灭。正如郁达夫当年在《伤感的行旅》一书中所感叹的那样:“江南的风景,处处可爱,江南的人事,事事堪哀。”
史明智讲述了麦琪里遭到强迫拆迁的故事,尽管居民坚持抗争多年,仍抵挡不住政府的怪手。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屈指可数,唯一感兴趣的事情就是圈地卖钱。二零零五年一月九日,三名暴力拆迁的流氓在麦琪里四处放火,驱赶拒绝搬迁的住户。在这里居住一辈子的七十多岁的朱水康和李杏芝夫妇在屋子里被烧成两具焦尸,朱水康是曾经参加抗美援朝作战的老兵。他们是为捍卫私有财产而被烧死,跟追求言论自由和台湾独立而自焚的郑南榕、跟因抗议中共暴政在布达拉宫前自焚身亡的藏族歌手才旺罗布(以及其他数百名自焚的藏人)同样是“生得伟大,死得光荣”。未来上海成为东亚自由港或自由邦的那一天,未来上海重新恢复工部局式的自由秩序与治理的那一天,应当竖立起朱水康和李杏芝的塑像。
史明智多年追踪“钉子户”陈里长和谢国珍夫妇,坚持数年之后,他们的房子仍然被推倒,家中的一切不翼而飞。他们去徐汇区政府抗议说:“一九三零年代的日本人都没有抢走我的房子,四零年代的国民党也没有,它甚至撑过了文化大革命。但现在一群法外之徒就这样抢走了它。”他们在抗议信中写道:“只要拥有权力,你们就能践踏体制,侮辱人民,也能侵犯人民的人权。我们实在太天真,相信报纸与电视的报导,误信政府对人民所做的承诺。你们可以夺走人民的土地,但终究失去我们的信任,而信任才是国家的基石。”陈里长当着史明智的面泣不成声:“我们失去了尊严,失去了安全感。什么都没了。政府嘴巴里说着中国梦,但到底是谁的梦?”
史明智还写了将上访当做生命支柱的六十一岁的奚国珍女士的故事。强迫拆迁发生时,她被拆迁人员架走,手指被折断,丈夫被困在家中,家中很快起火。官方随后宣称其丈夫自焚身亡,而她相信,丈夫是被打死后纵火湮灭罪证。她屡屡到北京上访,被捕、被关押在黑监狱、遭殴打成为家常便饭,身体很快垮掉了。她的儿子伟祺经历了这场灾难后,拼命学习,考上美国康奈尔大学并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课题正是中国的房地产与资金流。他的父亲为此而死,母亲一辈子都在为此如西西弗般奋斗,他经过研究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是,共产党对私产的尊重与否将会决定其成败:“一旦政府懂得尊重私人财产的概念,也就有机会培养一群不必担心自身安危的权贵。一段时间后,这群人会变得相对理性,也会学会为了建立一个更好的国家而彼此妥协。”
史明智采访伟祺时,伟祺在香港的一家跨国公司工作。他的母亲因为上访的“前科”和档案中的“污点”不被允许出境,无法到香港探望儿子。伟祺到香港工作,很大原因是希望离母亲近些,坐两个小时的飞机就能回上海探望母亲。他对中国未来变好充满期待,他假设统治者跟他一样拥有理性,即便是冷酷的利己理性。然而,习近平政权毫无理性,不到几年时间就摧毁了英国统治一百多年才在香港建立起来的自由与法治。不知如今伟祺是否已离开香港、回到美国?
一场新的国进民退、化私为公的运动正在中国大力展开。最具风向标意义的一个案件是:二零二一年七月,河北民企大午集团创办人孙大午被判刑十八年。二零二二年四月十五日,其资产遭拍卖,估值逾五十亿人民币的资产以底价六亿多成交。孙大午的儿子孙福硕在致习近平的公开信中写道:“我无法解释大午案被政治化、敏感化、妖魔化的魔幻现实。”全体集资人发表声明,对集团被低价拍卖“深感震惊、痛心和担忧”,指司法机关强制拍卖,不仅对企业和员工极不负责,也损害集资参与人的利益。然而,这些抗议如犬吠火车,习近平置若罔闻,在中国保护私有产权只是一句空话。
当宗教信仰沦为装神弄鬼,就如同传销组织
习近平的“中国梦”并不能安顿中国人的灵魂,一场“中国灵魂争夺战”正在开打。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曾发布一份以此为主题的报告,研究中共宗教控制政策的演变,及公民对这些政策的反应。报告的起草人之一库克指出:“共产党严格的控制,使得得到国家认可的官方宗教机构无法满足中国社会对宗教的需要。结果是,中国存在一个巨大的宗教黑市,迫使很多信仰者在法外从事信仰活动,将政权视为不讲理、不公正、不合法的政权。他们既包括道教徒,也包括基督教新教徒,以及藏人佛教徒。”他认为,在中国灵魂的长期争夺战中,最终失败的会是拒绝改革的共产党。
普利策奖得主、前《纽约时报》驻华记者张彦有一本名为《中国的灵魂:后毛泽东时代的宗教复兴》的着作,书中写到在北京举办茶会和香会敬神的群众、在乡间为人举办丧仪看墓的风水先生、学习气功与国学的知识份子,以及成都基督教归正教会秋雨之福的牧师王怡及会众。在其笔下,这些人基本上都是真正的信徒,相信其宗教信仰能让自己变得更好,让他们与某种更高的观念与存在连结,乃至帮助更多人、改善衰败的公共生活。若没有宗教信仰,中国将变得非常可怕,北京大学伦理学者何怀宏坦陈:“野蛮残忍层层堆叠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张彦提出这样的观察:“繁荣的新时代中,却隐藏一股愤怒与暴力的暗流,人们在网际网路上更可以感受到这一点。”但正如有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张彦写出中国宗教生活复兴中的阳光,却有意无意迴避了阴影——这本书似乎只写出华人宗教信仰中“上半部”的世界,更为隐微、细碎却盘根错节的“下半部”仍躲藏在阴影之中。
史明智的《长乐路》不是以上海市民的宗教信仰生活为主题,却在部分章节中涉及这一面向。他是高度理性的无神论者,不认同传入中国的基督教等西方主流宗教,对中国的佛教等传统宗教更缺乏兴趣。但他发现,中国正深陷一场道德危机,政府无力提供出路,民众遂自发寻求能“安心”的精神资源。在他描写上海人的宗教生活时,偏重负面与荒谬的部分(或许他刚好观察到这一面)。
傅大婶带史明智去一家非官方的灵恩派教会聚会,他跟教友们一起排队吃饭,仿佛身处一个大家庭,“大家的表现都很文明,没有人推挤、吐口水或插队”,但他不喜欢五名身穿黑色迷你裙的女子在台上带领唱的新潮歌曲,也颇为排斥会众站起来鼓掌、举手、闭眼握拳唱歌的形式,认为这有点像美国南方的灵魂乐。据说当过罪犯、手上戴着劳力士手表的江牧师的讲道,更让他反感:“江牧师这套布道内容显然已经说过数十次,甚至可能有数百次,已经把笑话的用词与节奏修饰得非常完美。……他的发言有一种特别的节奏,一应一答的韵律,更教人无法抗拒。对于像傅大婶或者其他年龄够大的人,这也会让他们联想到一九六零年代的政治集会,上千名红卫兵齐声大喊‘毛主席万岁’之类的各种口号。这类重复性的字句会触发一种催眠效果。”傅大婶除了上教会,也热衷于参加传销活动,还带着史明智去传销组织面谈,企图将他发展成下线却没有成功。其实,背离真理的教会跟传销组织又有什么差别呢?
史明智还拜访了在长乐路巷弄内的“国学新知”研究中心。其创办人徐渊介绍说,中心创办仅两年,就有超过五万名年轻人参加过他们举办的活动。他希望让年轻人重新认识孔儒思想,尤其是孝亲观念。史明智注意到,其推广海报的标题是“中国梦,我的梦”,这六个字显示儒学或国学是中共当局有意倡导的。徐渊与他的前辈、张彦曾在书中写到过的、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南怀瑾一样,对儒学服务于权力的本质有深刻的认识,藉机发大财。
开三明治店的小陈带史明智去了一间位于远郊的寺庙。主持是一位低调的藏传佛教和尚,信徒或其家人大都患了中西都医无法解决的疑难杂症,前来求助。师父与信徒的对话,宛如医生诊断病人,他提出的诊治方案是非常规的:或买鳖放生,或去普陀山拜观音,或停止服药。师父自信地对一位希望解决女儿自闭症问题的母亲声称,“叫那些北京的医生去检查自己的脑袋,听起来有毛病的是他们。”史明智用颇为戏剧化的笔法描写信徒与大师交流过程,此种宗教无疑已经沦为杂耍骗术。
从“上海人在德令哈”到“上海人在纽约”
本书中最动人的一个故事,是史明智在偶然的机会发现了一包半个多世纪之前的私人书信。写信的人是一九五七年被捕的上海小资本家王铭,三十五岁的王铭被送到一千六百公里外的青海德令哈劳改农场,一直到毛泽东死才获释。在那个信件被严密检查的时代,长达二十年间的家人通信,通常以抄录毛语录开头,文字平淡、冷漠而内敛,却不乏微言大义。一开始,是王铭的妹妹给他回信,他的妻子必须假装与丈夫断绝关系才能带着孩子在上海挣扎着活下来。十年之后,王铭才收到妻子的信,他恳求邮寄去孩子的张片,以及以前的照片,特别是“我还在家里的大合照”,“每次只要沮丧,我就会反复仔细阅读你的来信和照片,这对我的健康有益”。这真是让人欲哭无泪、于无声处听惊雷。
在这里,我看到了德令哈这个地名。我第一次知道这个地名,是在北大校园诗人海子的抒情诗《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中:“夜色笼罩/姐姐,我今夜只有戈壁/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除了那些路过的和居住的。”那时,我是一个浪漫的文学青年,对德令哈充满美好的想像。后来,我在人权活动家吴宏达的自传中再次看到这个地名,吴宏达也被关押在附近,其自传中充满生吞活剥一头冬天冻僵的蛇之类的细节。再以后,我才知道德令哈来源于蒙古语中的“阿里腾德令哈”,汉语译为“金色的世界”——中共极权政府将蒙古人的“金色的世界”打造成纳粹集中营东方版的劳改营,作为蒙古人的我,岂能不怒发冲冠、仰天长叹?
王铭获释回上海的时候已经五十七岁,他的平反申请被驳回。家人对他不无怨恨,他后来孤独地死在老人院,妻子和孩子都没有出席他的葬礼。他和吴宏达的命运,是整整一代上海人的缩影。比他们更悲惨的人早已丧生在德令哈和夹边沟等很多有名无名的劳改营,连墓地都没有。那些最热爱资本主义、最热爱自由和独立的上海人都被消灭了。后半生在美国首都建立以“劳改”为名的博物馆的吴宏达,二零一六年在洪都拉斯度假时意外地溺水身亡,象征着劳改营倖存者那一代遁入历史深处。
而王铭子女的故事还在继续。王铭的第五个女儿多年前移居美国,二十年后的二零零八年,王铭的小儿子王学颂和王铭的妻子刘舒元通过亲属移民到了纽约,“上海人在德令哈”的悲惨故事终于转变为“上海人在纽约”的带有喜剧色彩的故事。法拉盛的街道赶不上上海那么巍峨宏伟,但在这里,王氏一家至少可以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史明智在法拉盛图书馆见到正在努力学英文、考取技师资格的王学颂。史明智影印了所有的信件要给他,他却拒绝收下,并表示没有家人愿意保存和阅读这些资料,下一代更对那段历史没有什么兴趣。中国人本来以历史为信仰,如今却以遗忘作为生存的前提。这位被父亲连累大半辈子的上海人,将所有的遗憾和痛苦都留在上海,鼓足干劲在美国展开其人生下半场。如今,当他看到上海封城的种种惨剧时,或许会庆幸自己在中国国力臻于顶峰、上海经济发展最快之时断然离开,上海那个不能保护私有财产的地方不是他的家,美国才是他的家。
史明智对上海的期望、对中国的期望一一落空了。上海未能像领头羊那样将中国带向更富裕、自由与幸福,恰恰相反,极权主义的幽灵再度将上海卷入一个可怕的黑洞,就像一九四九年那次一样。史明智在书中写到的形形色色的上海人,不知道谁能在这场浩劫中物质与精神毫发无损地全身而退。本书出版之后,他们身上继续发生的故事,一定更是让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