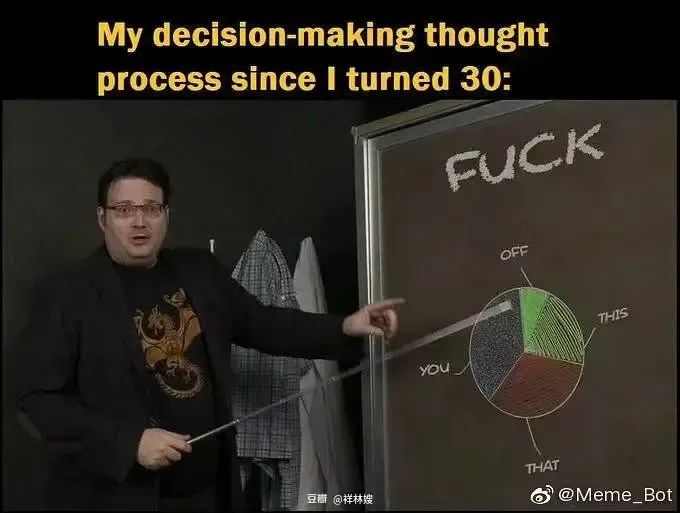我在杭州东,花了一个小时出站
我也没想到疫情过了有三年了,我遇到的最严格的管控是在杭州。我看起了疫情地图,杭州也没有病例没有中高风险,可能是在防备着从上海涌来的人群。
出站以后,先是正常程序扫描了健康码,然而并没有看到常规的做核酸的队伍,但现在出进站不看核酸也是常态,我就没有在意。又看到一个长长的拥挤的队伍,外面的牌子上写着,中高风险地区人员核查通道,于是我继续自信满满向外走,混乱的人群中有几个工作人员举着“核验人员跟着我走”,我应该要留意一下的,但是我没有。然后,到了验健康码的环节了,两道程序,前面的小哥让我过去了,后面的小哥说,你要去那边核验。
而走到他所指的“那边”,我才意识到自己要排的是刚刚那个长队。一边排队,一边填写一份承诺书,大概就是详细说明了来的车次,在杭州的住处以及抵达方式,以及是否发烧之类的身体信息,还要提供核酸截图,我填着都觉得麻烦,别说那些不擅长使用手机的中老年人了。
那个队,真的非常长,排了大概有四十多分钟,高音喇叭一直在刺激你的耳膜:填报疫情防控承诺书,往里走,里面有空调!

而最让人难受的地方在于,所有排着的人都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啥,我想,应该不是做核酸,核酸的话会直接讲清楚,而且核酸的队伍没有这么慢。走近了,看到外面的牌子上介绍抗原试剂的用法,“把试剂放进鼻孔里旋转一周…”我当时心里一沉,不会是要做抗原检测吧?
排队的过程中能明显感受到队伍的情绪是很不稳定的,队伍绕了好几个弯,终点在另外一个房间里,所以大家不知道这个队伍最后通向哪里也不知道大家要在这个房间里待多久。只有一个工作人员在维持秩序,大概是有人问了她在这里干什么,还要多久或者更专业一些的问题,她几乎是在咆哮,问我干什么?!你问我我也不知道啊?!又不是我让你来排队的?!将人群隔开的栏杆被她摔得哐哐直响,而且还不止一次,她可能是每放几个人通行的时候都在刻意地摔那个栏杆,用一种很幼稚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怒气。
排到靠近了,房间里面出现了几个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我看到一个中年男人隔着门问他们,得到的回应也非常冲。
那个时刻我也很想冲过去问他们这到底是干啥,但是我想自己可能还需要一个大喇叭。

终于,到了队伍前面,我的烦躁稍微缓和了一些。我开始走进那个门里去,只见一排长长的一排桌椅,里面是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拿着乘客的身份证在核对来处,去向等问题。大概扫了一眼,这些人虽然裹得很严实,但看起来都挺年轻。我把身份证递过去,觉得还是有必要问一下,“为什么我从低风险地区过来也要核查?”那个人一开始没有理我,我又问了一遍,他慢悠悠说,那你从队伍后面回去?
我很火大,这场核验就是给你一张已核验的纸条,没有核酸证明的去做核酸,有核酸证明的拿着另一张纸条出来。重新去出口的两道门那里扫码,查验,放行。
我还没出站呢,就扫了这段时间以来最多的码。出站口扫个码,核验点扫个码,出站广场继续扫,还必须得是用支付宝扫,这配合拳打得真是人拍案叫绝。
我对于杭州东站的行为无法理解。如果说有什么排队心理学的话,那么它完完全全地站在了反面。队伍是混乱的,因为要申报的信息比较麻烦所以大家都是边走边填,有的人填着填着就停了下来,然后后面的人就走过去了,他填好了又会理所当然地跑到前面自己原来的位置上,所以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纪律可言的。再则,队伍不透明,大家只看到前面的好几个弯,看不到最后到底在干啥,几分钟能搞定,所以更加容易焦躁。最后,工作人员的态度别说没起到解决问题的作用还加剧了大家的怒火,当然底层互啄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好解决的办法,工作人员工作压力大我们也不能过于苛责人家,而且,他们应该确实是什么也不知道。
我想起之前在家的时候,准备去某家医院做核酸,打了下核酸点的电话问具体信息,接电话的人说,她是另外一个部门的,她也不知道核酸点的情况,甚至是,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官方的通知上要留他们办公室的号码。
于是这个事情最后成为了一场双向的抱怨,我没有得到我所要的信息,她则将我当成了抱怨的对象,“我和医院反映好多次了都不行!”这种情况下,我能说什么呢,明明是医院的问题,倒显得是我不懂事了。
其实用脚趾头都能想出来,杭州站这种“严格”的防疫政策针对的是谁,长三角地区巨大的人口流动量使得这些城市对从上海来的旅客如临大敌,上半年的上海人口外流在不同的城市间都引发了恐慌,杭州也可以说自己的“受害者”,当我把这件事发在微博上的时候,有人评论,如果上海地区的人到其他地方,面临的就是直接隔离了。这背后的逻辑是,在疫情发生地出来的人,其它地区愿意让你进来,就已经是巨大的恩赐了。我们就是在这种相互比烂中寻求安慰,寻求认同感的。
而之所以给“严格”加上引号,是因为我很怀疑这样的核验是否真的有效控制了疫情,该流入的人群依然流动着,本来是为了防疫,过程中却一直进行着人口聚集(做核酸,登记),这已经被抨击了无数次了,大家好像必须要接受这种荒谬的矛盾。
而在看到那一排坐着的登记人员的时候,很难不让人联想到疫情所“解决”的失业问题。核酸检测的生意化是人们心照不宣的事情,检测人员的高薪也使得很多人趋之若鹜,但这本质上是一个畸形的就业市场。
这段时间看理查德·埃文斯的《第三帝国的到来》,惊觉其中的相似性,二战前的德国处于经济崩溃,通货膨胀率骤升,失业率极高的状态,而对外的扩张恰好吸收了国内的失业人口和过剩的产能。这是一笔稳赚不赔的生意,所以“疫情防控战”的说法简直不能再精准了,战时模式,战时状态,完美消解其他矛盾。
配合着这段时间很多地区核酸人员发不出工资集体罢工的新闻来看,很想要苦笑,但是我相信杭州地区不会有这种问题,丰厚的地方财政基础应该能支撑得起大家一起捅喉咙捅到地老天荒。
排队过程中经受的工作人员的态度也很容易引起大家的愤怒,首先要承认,这不是一件普遍的事情,也不应该就此对所有的工作人员一棒子打死,再则大家都是人,都有怒气要宣泄,所以我并不是将矛头对着这些普通人,我也确实相信他们说的不知道是真的对流程中的其它部分,对整场活动的管理层面一无所知,大家只是负责自己岗位上的事情,查健康码的只是待在入口,引领人员只是举着牌子把大家引导到核验区域,控制着栏杆的人也只是在前面的人走得差不多的时候放后面的人通行。他们自然会觉得你的这些问题只有管理人员才知道,他们也确实对你们的追问感到委屈。
又是很熟悉的场景,开着装满了犹太人的车厢的火车司机可能也是这么委屈,负责登记犹太人身份的登记员也委屈,你们来这里干什么,这要问纳粹长官啊,我怎么能知道呢?我只是按照规程办事而已,而我的规程,可能只有一行字,mind your own business.
庞大的,精细的,不透明的组织架构,长官隐藏在通知文件的背后,你甚至不知道ta是否是一个具体的人。
在杭州还有一件我觉得简直是将人按在地上摩擦的事情,除了扫码太多外(一个场所可能要扫好几次码),所有的场所码必须要用支付宝扫,很多次习惯性地打开微信却发现扫码无效。更为离谱的是,有几次扫码,页面竟然跳转到了饿了么,没有完全加载出来,我的手机就尴尬地停留在一个只有标题的页面里,每次我都感觉自己在被人喂屎。
我非常愤怒,可是我的愤怒得不到发泄,上午坐了两个多小时的车抵达杭州,偏头痛又在此刻找上了我,我忍着恶心呕吐的感受挤在人群里。而在这种时刻,我才对这些疫情管控严格地区的人的经历稍微有一些感同身受。上半年看了很多的新闻,但是得承认,鞭子没有打在自己身上,我是感受不到真切的苦痛的。你也可以说我太过于矫情,一个小时的队不至于长篇大论,但是我觉得愤怒只有抒发出来,才会降低得乳腺增生的风险。
《第三帝国的到来》详细记载了纳粹是如何上台,德国的其它各党总是认为他们不过是一些没有文化的野蛮人,就算进了议会也可以很好的控制,普通百姓则认为暴力针对的只是犹太人和激进的共产党员,和我没有关系。也是在阅读完这漫长的过程之后,我才对那句经典的“起初,纳粹抓共产党人的时候,我沉默,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当他们抓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时候,我沉默,因为我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当他们抓工会成员的时候,我沉默,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当他们抓犹太人的时候,我沉默,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最后当他们来抓我时,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有了更深的感受。我们总是在自己的生活里岁月静好着,觉得这些事情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然后,铁拳来了。
所以我不再怀疑人生怀疑自己了,造成今天这个局面,每一个德国人都有责任,我们是在平庸的恶里丧失自己的领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