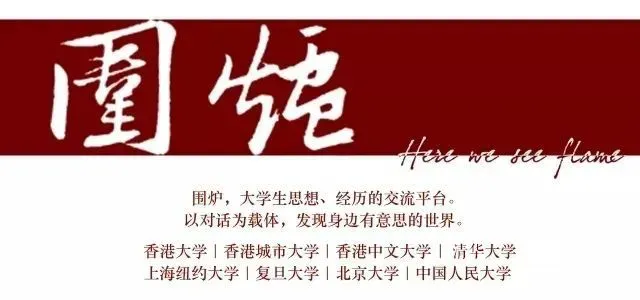對話唐淩:社會學與藝術|圍爐·HKU


唐淩,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本科、MPhil,牛津大學博士。2019年——2020年疫情期間在牛津創辦滑倒樂隊,偶爾在牛津街頭拿著吉他唱歌。2021年回到香港,目前在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創意媒體院教授酷兒影視理論,實踐將社會學與藝術結合的想法。作為女性主義者的她,也試著在音樂創作中加入女性主義和酷兒的視角。在日常生活中,Ta堅持著「用個體打動個體」的女性主義實踐,同時關註身邊和試著重建附近。我們一起去南丫島(香港的一個島嶼)清理過很多次海灘,Ta也會和伴侶在生活中拿著小口袋打掃街道。在一次采訪中Ta提到,作為女性主義者不可能有回頭路,「女性主義是從你的身體,你的感知,你的壓抑,你的情緒開始的。」
Ta或許不是典型意義上的學者,但卻保有對學術最純粹的感動與真誠。Ta說自己也許是野草,無論是在牛津的街頭唱起自己關於山火的歌,還是在滑倒樂隊裏用聲音的印記留下學術的半影,都是日常與學術的交互。同時Ta也參與了知識的網絡分享,在公眾號《見樹又見林》裏寫下學術思考,以視頻播客的形式進行知識分享,嘗試將學術視角帶入媒體。我和Ta也是兩年前在社交媒體上認識,在最困頓的高三時期我把Ta當成樹洞很久,Ta也給了我很多鼓勵和溫暖。
因為日常習慣稱呼Ta為牛牛,所以以下都這樣稱呼。

爐 = 任李菲陽
唐 = 唐淩(牛牛)
爐|關註牛牛的微博@Lyn-Dawn 很久,發現簽名一直都是「把社會學作為藝術,反之亦然」,或許可以簡單介紹一下這句話和寫下這句話的原因嗎?
唐|你關註我的微博應該是在2019年吧,其實我也是在那個時候開始重新使用微博的,因為人生中發生了一些大大小小的轉變。一個原因是那一年我在牛津和幾位朋友一起創辦了滑倒樂隊,但其實我們樂隊的朋友分散各地,一位在西安音樂學院的朋友負責作曲,我和另外一位香港科技大學畢業的朋友一起填詞,一人負責文學,一人負責社會學,還有一位在牛津的朋友負責歌唱的部分。我們就這樣開始進行歌曲創作,也接著有了更多分享的契機。

加之那段時間我也有和好朋友王婧宜@維羅妮卡是一只小藍山雀一起在微博上製作學術視頻,創辦了學術啾,參與了一些社會問題的探討。社會學、藝術、媒體與我自身的互動也就這樣進一步呈現在了日常當中。那麽說到社會學與藝術的關系,我自己從本科到博士階段一直是社會學方向,所以在音樂創作裏也就會更多地加入社會學視角的思考,在填詞的時候也就會帶有社會學的影子。以社會學為藝術,對於我來說,是在音樂創作裏和社會學進行一個雙向的溝通,把自身的生命經驗和藝術相交融,同時也在音樂裏試著尋找更多元和豐富的表達方式。反過來,藝術作為社會學,將藝術的一部分帶回社會學的視野,不僅是社會學突破自身邊界、尋求與個體鮮活感知、表達對社會認知可能性的體現,也是從自身的視角出發,對我們的周圍和現實世界的重新思考和交流回應。在逐漸進入這種創作模式之後,我也發現早已有很多在堅持進行類似實踐的社會學學者,Ta們跳出傳統意義的學者身份,進入到更廣闊的創作領域,產出了很多很新穎和富有創造力的表達,他們的創作對社會、社會學和藝術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其實也正如博伊斯講的「人人都是藝術家」 ,Everything could be Art(萬物皆可為藝術),藝術創作本身是很富有彈性和張力的。只是我自己在最開始進行創作的時候,還是會帶有一些不確定性和不安,但在後來寫了一些歌之後,我進一步找到了與藝術鏈接的平衡點。不過不同於Everything could be Art,Everything could be Sociology(萬物皆可為社會學)也許並不完全成立,社會學往往還是會更強調偏結構性視角的部分,所以這個視角也是我自己嘗試著通過音樂創作去呈現的。
爐|聽到對於藝術和社會學互動的分享,也有回憶起來牛牛在牛津的展覽還有近期新創作的歌。感覺每一次藝術實踐也是新一次對自我的探尋,所以也想問問這些年的創作對於牛牛自身的生命來講意味著什麽?又或者這些創作帶來了什麽新的體驗?
唐|藝術對於我自己來講是一個窗口,也是一份解放吧。我自己開始進行藝術創作的時候是在讀博士的階段,那個時候自己有了一些對於學術和學術圈整體的倦怠感。其實主要也是因為自己在進入牛津的時候,依舊是帶著「牛津是學術的最高殿堂」的期盼的,但是在真正來到這裏之後,還是會不時感受到比較深的離地感和對於學術圈內部生產的些許失望,可能這也與牛津整個的新自由主義氛圍有關。那個時候我自己的博士論文也遇到了一些瓶頸,當時項飈老師在我的博士資格考中也給我提出一些很關鍵的問題。總之,自己當時相對處在一個比較不清晰的狀態。所以遇到音樂和開始進行藝術創作,對於我來說在很大程度上算是一份短暫的解放,也是一個新的擺渡期。後來蠻神奇的也在於,我們滑倒樂隊去到北京科技館演出的時候,我非常偶然地接觸到了韓炳哲老師的作品,裏面的一些理論給自己的博士論文帶來了很多新的靈感。


雖然這些經歷並不是直接和音樂藝術相關,但是這部分「遇見」和「偶然」本身也給到了自己新的感知。藝術和社會學的交融對於我自己來講,是在不確定裏重新探尋自我和生命軌跡的一個過程。沒有一種體驗是渺小的,恰恰是這些很小的點引出了更奇妙的所在,不同的線條、樂音、遇見交織和混合在一起,互相構成彼此關照的支點。這也是在這些年的實踐裏自己越來越喜歡這兩者結合的原因,取下兩者看似堅硬的外套,內裏結合的無限是很柔軟和豐富的。二零年我回港大做博士後的那段時間,自己不時也會有對於發表文章數量等等的焦慮,在高濃度的壓力裏偶爾也會比較無措,但是我很慶幸這些年一直有音樂陪著我。而音樂和藝術一方面可以讓我用非學術化的語言進行更有創造力的社會學表達,尋找到另一個支點,另一方面也給自己感知自我和社會帶來了不一樣的打開方式和體驗。
爐|聽牛牛講述社會學和藝術與個體生命軌跡相互牽引的部分,感覺實在很奇妙,同時我也非常受觸動,擁抱這些相互交織的事物感覺也是在擁抱生命的不確定性本身。同時也很好奇對於牛牛而言,社會學學者和音樂創作者這兩個身份對於自己分別意味著什麽?它們又分別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唐|這個問題也讓我想起來有一次和何式凝老師聊天,那時也是我比較迷茫的時候,我們聊到關於到底要做一個怎樣的學者的問題,記得當時她笑著對我說:「不然呢!難道你要做Boring Academic嗎?肯定是要做Creative Academic的呀!對吧!」聽到這句話的時候我當時一邊點頭,一邊也很感動很受鼓舞。一方面是真的很謝謝式凝,她每次說話都是那樣真誠和有力量,另外其實式凝她自己這麽多年來也是真的有在把這兩者努力結合,就像她自己有在拍很多電影和紀錄片的同時,也在非常非常認真地當好一個老師和學者,並且她也一直結合得非常非常好。我想這也是那段對話給我的影響持續至今的原因。藝術和社會學一樣,都需要看見個體和看見人,它們是感知世界的方式,也是介入社會的行走的語言。而且不論是作為藝術創作者還是社會學學者,很重要的一點都是要對自己和自己的作品做到真誠。雖然學術圈現在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了高度重復性的內部生產,並且哪怕是作為學術殿堂的牛津其實也沒有那麽好,但是我想或許正如《見樹又見林》裏那句「社會學作為生命、承諾和實踐」一樣,這也是我自己作為社會學學者一直抱有的態度,也正如藝術創作要對自我真誠,這兩者其實是相似和互相支撐促進的,它們都在時刻提醒著我那些最原初的感動和那些堅持寫作和創作最樸素的緣由。

爐|記得牛牛在「見樹又見林」的第一期播客裏以搖滾樂為主講述了對於藝術和社會學的理解,最後提到了韓炳哲老師寫的那句:「最光滑的藝術就是在光滑的表面看到自己的折射」,或許可以詳細講講對於這句話的理解以及怎麽樣看待藝術創作者和觀眾之間的關系?社會學的視角在這之中給藝術創作帶來了什麽新的可能性?
唐|其實韓炳哲寫「最光滑的藝術是在光滑的表面看到自己的折射」是關於Jeff Koons的金屬作品。韓柄哲主要是想借由這些作品表達對於藝術創作者的一些反思和批評。對於我自己來說,社會學的視角的確是在提醒我跳脫出那個過於「放大的自我」。這也是因為對於很多藝術創作來說,最終完成作品的那一刻還是在和觀眾產生連接的那一刻。就像觀看藝術不是單一被動的消費藝術,而是可以變成屬於藝術和觀眾兩者共同的世界。同樣社會學的反身性不僅讓我把自身作為作品的材料,同時也讓我可以把社會和觀眾,以及對於真實世界的體感和反思一起融入作品當中,這也是藝術和社會學學者這兩個身份交織給到我重要啟發的點。「互動」帶來「他者的加入」,「加入」延長了理論和藝術相互依存的時間和生命,也延伸了創作者的涵義。社會學和藝術一起構築了彼此的橋梁,也一並表達個體的生命體驗與延展開來的社會記憶。
爐|提到藝術和社會學,布爾迪厄也寫過關於知識和文學生產可能會造成的「區隔」和「符號暴力」,牛牛在創作的過程中會不會有類似的顧慮?牛牛怎樣看待文學藝術可能會帶來的門檻?
唐|關於門檻,我覺得可能更像是馬克思講的階級引發的區分,布爾迪厄提到的類似「區隔」可能是一個更隱形的概念,是在進入一個不熟悉場域之後內心難以言說的不安。我覺得類似的區別和區隔,不管是在藝術還是文學領域,又或者是在一些專業性的圈子裏,肯定都是會有的。但也要分開來看,因為這也與講述和介入的方式緊密相關。就像最近我唱的一首新歌,是我一位牛津的好朋友Tara寫的詞,整個歌詞裏面有很多非常晦澀的英文單詞,但是其實她自己並沒有要刻意去強調所謂的區隔,而是希望通過歌詞創作去表現那些詞句的美,因為她自己也的確是非常喜歡古典英語文學。所以好的介入方式其實是可以連接所謂的不同的,異質性並沒有被強調的那麽大。又比如馬克思的作品,其實他的語言和表述本身也很復雜,其實是不太能直接達到團結工人的效果的。所以除開創作者自身的意識,更重要的是創作者和參與者的整體互動,從而去完成對於整個作品的解讀。這些反而可能是更抓住人的地方,而這也在某種程度上越過了所謂的顯性和隱性區分的區隔。平等與包容的對話狀態,是美可以成為美而非再度被分割,也是音樂「遇見有緣的耳朵」這一最純粹的感動所在。

每次和唐淩(牛牛)對話和聊天,都會給自己留下很持久的感動和溫暖。也正如Ta自己提到過的「個體打動個體」,從幾年前到現在,我也一直都是那個被Ta打動著的個體。每次聽到Ta新發出的歌,也會讓我一次又一次想起那些和Ta對話的時刻、Ta講過的故事和話語、還有Ta這些年做過的大大小小的嘗試。在不確定性越來越強的當下,願Ta的音樂不停,也願這些微小的堅持和真誠可以一直都在。

统稿 | 任李菲阳
图 | 来自网络
编辑 | 张宇轩
matters編輯|邢奕萱
围炉 (ID:weilu_fl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