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都死了这么多年了,你们爱咋咋地吧
前几天看到一则新闻:考古学家倡议停止进行人骨的性别划分,因为生物性别并不代表了他们对于自身的性别认知。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Whaaaaaaaat? 瞬间有一种被后现代解构主义浪潮击打在沙滩上一动不动的感觉,看着远处离自己三米远的咸鱼,感叹这个世界的疯狂。
接着我的感受是,考古学终于能够参与到公众议题的讨论中去了……
再接着我的感受是,LGBTQ群体又要承受本不该承受的骂名了……
该倡议是由一个叫做黑铲的组织(Black Trowel Collective)发出的,他们自称是一个无政府组织,他们致力于消除当今世界既有的不公正的垂直等级秩序,通过提供小额捐助的方式“积极支持来自工人阶级和历史上被掠夺的社区的考古学生,改变学术界的种族、阶级、性别等偏见。”
在archaeologists for trans liberation的声明中,他们说到,组织支持跨性别群体,希望能够打破对跨性别者的歧视,在具体行动方面,他们提出了如下的倡议[1]:
1、 Archaeologists must center the fluidity of gender in their archaeological practice.考古学家必须在考古实践中关注性别的流动性。
2、Archaeologists must make fieldwork, research, education, and workplace contexts safe for trans people.考古学家必须确保跨性别者在田野、研究、教育和工作场所的安全.
3、Archaeologists must use their expertise about the past to fight against harm to current people.考古学家必须利用他们对过去的专业知识来抵抗对当下人群的伤害。

更为直接的说辞似乎只存在于单个学者的发言中,如Emma Palladino在推特里说:You might know the argument that the archaeologists who find your bones one day will assign you the same gender as you had at birth, so regardless of whether you transition, you can’t escape your assigned sex。 (你必须要知道,有一天发现你骨骸的考古学家会给你分配与你出生时相同的性别,所以无论你是否转换了自己的性别认知,你都无法逃脱这种性别的分配。 )
他们提出这一观点的证据是,不同的性别鉴定方法具有不同的准确率:在已知样本中,蛋白质组学(蛋白质分析)在染色体性别方面准确率是100% ,DNA 是 91% ,而形态分析(骨骼研究)的准确率只有 51%(Buonasera et al. 2020)。而且,染色体与生殖器外观、性激素和其他元素一样只是我们称之为生物性别的元素之一(Davis and Preves 2017: 80)。科学家估计,1-2% 的人口在生物学上是双性人(Blackless et al. 2000)。双性体有多种形式:一些是染色体双性体,但表型为男性或女性,另一些则具有生殖器或器官差异。[2]
也即,虽然考古学家现在已经在努力区分生物性别和社会性别,大家对于社会性别的流动性已经有了一定的共识,但他们仍然坚持,即便是生物性别,也是非二元的,而当下基于人骨形态的测量方法是不可靠的。
倡议者提供的另一项证据是,不同文化对性别的认知是不一样的,而当下社会中最为广泛的二元性别划分实际是欧洲殖民霸权在全世界传播的结果。他们最常用的例子如印度的海吉拉,墨西哥的muxes,波利尼西亚的māhū,拉科塔地区的winkte,[3]这些或早或晚近的社会文化中一直有跨性别者存在,而这些存在往往被当下的历史研究忽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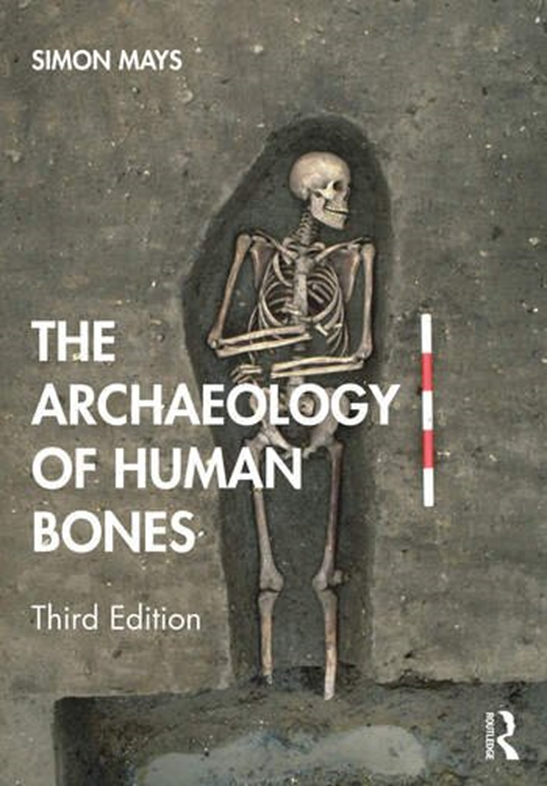
这场倡议本质上是少数群体的政治诉求,它引起争议的原因是,他们的诉求错了对象。仔细想想,考古学家在进行人骨性别划分的时候,他的目的是什么。考古学一直在强调,历史不可能百分之百复原,只能无限可能地去逼近真相。那么在绝大多数人群确实非男即女的情况下,面对一片墓地进行统计学意义上的性别划分,是当下所能做的最为贴近事实的研究了。在做了性别判断之后,考古学家的下一步工作可能是人口构成,社会分工,贫富差距,丧葬观念等等,他们的研究成果能够对当下的社会,特别是人的性别刻板印象产生多大影响呢?很显然是微不足道的。而在主观目的上,他们也从来没有刻意去打压和抑制性少数群体的诉求(其实我很怀疑他们是否关注到了这一点)。
当然现在整个网络上的口风还是批评多于支持, Spectator上的一篇文章用辛辣的口吻指责了这种行为其实是用意识形态的包袱去破坏真实的历史记录: " This isn’t science. It is politics with a trowel.”[4]TVPworld 上的一篇文章更是严厉地指出, They do not even appear to realize that for anthropologists who aim to determine the sex of an individual, that person’s idea about their own gender, which is a matter of identity, goes neither here nor there. [5]
其它学者如埃克塞特大学历史学名誉教授Jeremy Black说, “It is an absurd proposition, a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enders, just a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religious, social and national groups, are key motors in history……This very ideological approach to knowledge means that we’re in danger of making knowledge itself simply a matter of political preference.’[6](这是一个荒谬的命题,因为性别之间的差异,就像宗教,社会和国家群体之间的差异一样,是历史上的关键动力……这种非常意识形态的知识方法意味着我们有可能陷入使知识本身成为一个政治偏好的问题的危险中。)
实际上,近些年来随着女性视角和性少数视角的加入,考古研究中越来越多地关注transgender/bionary的存在了。人们不再以二元的性别观念去简单地将人划分为男性或女性,而是寻求更加多元、更加具体的阐释。
Megan Cifarelli分析在伊朗北部Hasanlu遗址中的五十一座墓葬中出土的遗物,其中针、别针和珠宝和被鉴定为和女性的人骨同出,金属容器、武器和盔甲则与男性人骨有很强的关联性,而其中有20%的墓葬则显示出了这两种搭配的混杂,Hansanlu遗址还发现有相拥在一起的两具人骨(hansanlu lovers),而其性别均被鉴定为男性,考古学家认为这可能是一对同性恋人。[7]在布拉格发现有一具男性头骨和女性随葬品合葬的例子,该人骨属于青铜时代的corded ware文化,距今有5000多年的历史,在这种文化中,男性人骨总是朝着西方并且和随葬武器,而这具骨骼朝向东方并且和日用容器随葬在一起。[8]
如同罗新教授在访谈中多次提到的那样,并不是学史使人明智,而往往是我们对当下的理解影响了我们对于历史的认知。考古学也是如此,这一套男女二元的性别观念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上发展而来的,可能要追溯到农业社会的诞生以及父权制的发展,而性别的流动性,则是相当晚近的发明与再发现。如同圣何塞州考古学教授Elizabeth Weiss所说, Recent spike in the number of people identifying as transgender suggests that the trend is “social and not biological” and that “retroactively de-sexing [of long-dead individuals] obscures this obvious fact.”(被认定为跨性别者的人数激增表明,这种趋势是“社会性的,而不是生物性的”,并且“追溯性地对(长期死亡的人)进行去性行为掩盖了这一明显的事实。)

这些研究多少还是有点争议,当研究者认为某些物品和某一性别的搭配“不合常理”的时候,这个“常理”在多大程度上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在研究墓葬中的器物群的时候,很难看到严格的二元对立,因为从根本上我们就不能确定随葬品和死者之间的关系,是死者的生前所属物?是生者的纪念物?或是两者兼而有之?
所以非常实际的情况上,在面对一门局限性和不确定性都如此大的学科的时候,如果还是要推翻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科学方法,那就有些太矫枉过正了。当一门学科只是服务于某个群体的诉求和表达的时候,也难怪会被人指责为政治化了。
我们无法在抛弃科学性的基础上盲目拓展后现代的理论与方法。这其实是全体社会科学所要面对的问题,到目前为止,考古学的大部分理论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的借用,但宾福德的遗产在热闹的后现代思潮中仍然占据了一席之地,究其原因,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仍然具有客观性的部分。
性少数群体反对父权制话语的诉求面向的更多是公众和政策制定者,放弃人骨分析很显然对于达成这一目标没有助益。我们在完成了性别划分并且逐渐意识到了性别的非二元性后,才会纠正以往考古研究和历史研究中对于性别分工,家庭观念,女性地位等问题的认知。
但如果我们仔细看黑铲组织的声明,会发现诉求本身是合理的,而且我一直认为在平等尚未实现的时候,激进的政策可以也应该被理解。提供新的性别视角,在具体工作中切实考虑每个个体的权益,以及利用学科本身去抵制某种霸权主义,这些也确实是历史学科所应该做的。只是其中个别的支持者可能发言过于激进,才会在学界引发如此大的讨论。
这又反映了当下性少数群体的另一个问题,当诉求过于激进的时候,社会公众会在第一时间反驳其中的不合理处而忽视其中的合理处。当舆论演变为一场骂战的时候,当特殊群体的权益呼吁成为外界眼中的“反智”和“反常识”的时候,他们就很难实现他们最初的目的了。
我一直觉得公众考古想要发展,就必须去关心当下群众最关切的话题,所以身份认同比一件“浸透了劳动人民血汗的青铜器”更值得人们关心。我也一直期待考古学能够参与到这样的公众讨论中来。而现在,我突然疑惑了,考古学能否承担得起这样的任务?考古与身份政治之间,到底有无合谋的必要?
在大多数人眼里,考古的目的仍然是非常单纯的,复原历史,甚至是更为单纯地辅佐历史研究,只是我们在强调学科重要性或者在申请研究经费的时候会将其拔高到诸如追寻文明的起点追溯人类的本源之类高大上的意义上去。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确实应该警惕考古的政治性,这是建立于对它的局限性的承认之上的,让上帝的归上帝,让凯撒的归凯撒,让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大政府主义者放过这门学科吧。
[1] https://blacktrowelcollective.wordpress.com/2021/07/06/archaeologists-for-trans-liberation/
[2] https://anthrodendum.org/2021/08/06/archaeologists-for-trans-liberation/
[3] https://www.sapiens.org/archaeology/transgender-people-exist-in-history/
[4] https://spectator.com.au/2022/07/how-dare-you-assume-the-gender-of-ancient-skeletons/
[8] https://www.pinknews.co.uk/2011/04/06/5000-year-old-transgender-skeleton-discovered/
题图:奥古斯丁修道院 Nick Saff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