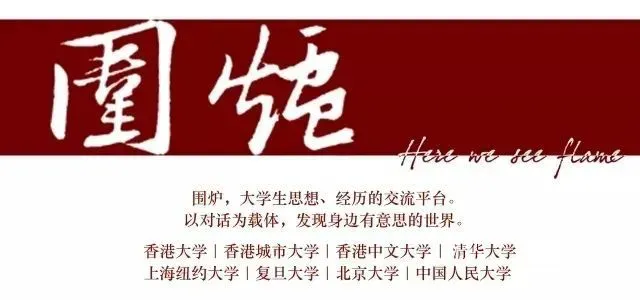對話梁君健:影像的田野,田野的影像 | 圍爐 · PKU&THU

梁君健,1983年生,博士,導演。副教授、博士生導師,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人類學系訪問學者,學術作品見於《人民日報》《當代電影》等刊物,並在世界人類學大會、英國皇家人類學會電影節等學術會議上報告過自己的影視人類學研究與民族誌電影創作。
從事紀錄片拍攝,曾執導作品《喜馬拉雅天梯》《我在故宮六百年》等,曾獲中國電影金雞獎提名。
影像已經成為時代文本。
從藏地天梯到西南邊陲,從短視頻到虛擬現實,影像精準地捕捉了現代社會那些易逝的碎片與永恒的瞬間。對人類社會而言,它早已不僅是一種記錄方式,更在形塑我們的生活。
自2012年起,梁君健老師開始執教於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學生們親切地稱他作「梁導」,他講授的課程為許多年輕學子打開了理解影像、理解社會的大門;作為一名紀錄片導演,他創作的《大河唱》《一張宣紙》等作品已然成為影像中國的留存。
從影十年,梁導的視野橫跨紀錄片與人類學。
對他來說,田野也許有兩層含義:既是鮮活的人類學場景,也是知識與想象的原野。在鏡頭前,他記錄田野的影像;在課堂上,他為更多人開拓影像的田野。
1|影像緣起:課堂十年
問:您現在的研究方向比較廣泛,包括影像人類學、媒介與社會等領域。您的學術興趣具體是從什麽時候開始形成的?
答:我是在研究生的階段開始慢慢對學術感興趣的。因為從本科我動念想轉系開始,一直到研一研二的時候我都比較希望做創作,做紀錄片攝影師和導演。但是到了研究生之後,個人的視野得到了進一步的開闊。現在回想起來,其實我特別得益於那時候新聞傳播學院和人文社科學院一系列的課程,包括羅崗老師的文藝學、格非老師的小說敘事學,後來又選了汪暉老師、秦暉老師的課等等,但這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張小軍老師關於人類學的課程。這些課慢慢地聽下來,我開始發現,通過研究資料和社會現象去理解和更深入地回答社會問題,對我來講是一個特別有挑戰性、並且我也特別喜歡做的事。那個時候,教我紀錄片的雷建軍老師正好在曼徹斯特大學做完了半年訪學,帶回了影視人類學這樣一個交叉學科的概念。我發現在我所喜愛的紀錄片拍攝領域和人類學的田野研究有很多共通之處。所以在研二的時候,我就開始考慮要不要讀博。後來我獲得了提前讀博的機會,繼續在影像領域做研究。
問:您走上學術之路,或許在一定程度上是得益於您本科階段接觸的寬口徑通識教育。現在國內包括清華在內的很多大學正在推廣通識教育,在推動影像教育的過程中,您是怎麽看待通識教育的作用的呢?
答:通識教育能夠讓學生借助這些課程去認識不同領域的頂尖學者,感受到他們思考問題的方式和看待世界的態度,這對於人文領域來講是首要的。他們知識的廣博、理論的精深自然不必多說,然而他們對待世界和學問的態度,所提供的獨特且多元的精神世界才是最核心的價值。現在的充分分工下的社會不支持、不培養通才,因為我們最終進入社會時,不論是從事研究還是行業工作,基本上都必須是專才,但是這樣一種價值觀和看待世界的方式是要通過通識教育為青年樹立起來的。
問:您覺得影視教育是否應該作為通識教育的一部分進行推廣呢?
答:我認為是有必要的,這些年也一直在嘗試。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影視作為現代社會的大眾流行文本,不可避免地會和社會的各個領域發生關聯。我們現在所遇到的一些前沿性的問題,在價值和倫理上所經受的考驗和焦慮,都一定會反映在電影裏。所以我們會看到電影類型正在變得多樣——隨著現代科技的發展,出現了科幻片;現在人工智能發展迅速,我們又有很多電影去反思人工智能問題,去思考多元宇宙的問題等等。從這個角度上來講,電影,包括流行的影視劇,它是一種寓言,也是一種幫助我們去思考廣泛的人類處境的一個手段。我們可以通過電影去思考政治,通過電影去思考歷史,通過電影去思考未來。
另一方面,我這些年在學校上課時,以及大二暑假我們帶同學出去拍紀錄片、做清影工作坊的課程時,也體會到了影視教育的通識價值。大多數的同學畢業之後都不會直接從事影像創作,但是借助影像創作,大家可以通過鏡頭去認識自己,和不同的世界發生交集,讓自己的生命經驗得到拓展,也會在這個過程中去反思自己對待別人的態度。所以我覺得影像創作作為一種和人溝通的情境能夠激發創造力,訓練我們團隊合作的精神——尤其是在組隊拍紀錄片的任務中。另外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影像打開了我們與這個世界溝通的多元途徑。所以說我覺得從這兩個角度來講,影像教育作為通識教育是很有價值的。

問:您在從教過程中遇到過一些比較讓您印象深刻的故事和經歷嗎?
答:其實每年我看大家的作業和作品的時候,都還是挺有感觸的。但是如果說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我覺得是我在課上被同學挑戰的時候。這其實也是在教學中不斷教學相長的過程。每一年都會有學生對我的品位和我對於大家作業的要求提出質疑,比如,我會要求大家在拍攝作業的時候要盡量多地了解被拍攝對象的信息,要求大家多次反復地拍攝一個人,建立起比較深的信任和人際關系。很多時候同學會認為,這樣是不是在剝削拍攝對象?我如果希望能夠拍一個不太一樣的影像難道不可以嗎?這樣的一些問題我在教學早年沒有特別主動地去思考過,我是在把我自己所接受到的影像教育,以及我在一些作品中慢慢總結出的一套方法和價值傳遞出去。但是在課上不斷地遇到同學們的反饋、疑問和探討的時候,我也開始思考為什麽我會擁有這樣一套價值,我也在思考作為一個教師,應該在多大程度上主導課程的內容,應該怎麽樣把我自己的創作經驗和教學經驗,與大家憑直覺來進行創作和學習的情境進行更好的結合。
另一方面,每一次看到大家的作業,對我來講都是一個特別重要的鼓勵。對於任何性格和背景的學生來說,影像不僅有報道的價值,而且也確實給同學的成長提供了很重要的資源。這也會激勵我自己更好地去創作、去教學。這些都是在教學過程中讓我特別難忘的一些事情。
問:您剛剛提到您會嘗試在課堂上向同學們講授您自己學到的一些方法和價值,那麽您現在希望通過影像教育讓學生們學到什麽樣的方法,培養怎麽樣的價值觀念?
答:首先,大家在使用影像的過程中,第一步肯定要學一系列的知識和技能。大家要掌握攝像機,要掌握構圖、光線,要學會剪輯,要學會基本的視聽語言。並且在這個過程中大家要去了解、思考自己的拍攝對象。
第二點是大家要學會長期投入和不斷打磨。因為影像的學習其實就是一門語言的學習,我們不論是學習母語還是學習一門外語,都是在不斷背單詞、大量的閱讀和書寫的過程中掌握,掌握影像其實也一樣。所以我覺得影像作為一門技術和藝術需要大家不斷地訓練,不斷地模仿,不斷地去挑戰自己的既有習慣。我特別希望,如果真的喜歡影像那就一定要投入——因為一分耕耘一分收獲。你不能依靠你所期待的「天賦」 、「突發奇想」或者「魅力時刻」來完成自己的夢想,而是需要大量的努力和時間投入才能讓你在合適的時候能創作出好的作品。
再進一步來講,我希望大家首先要發展出對拍攝題材和具體的拍攝情境的親切感和好奇心。拍攝對象不是一個任務,而是一個等待你去了解,甚至在了解過程中,可能會讓你頭破血流的未知領域。要有勇氣和好奇心去打開這個自己所不太知道的黑匣子——我更願意把它理解為去認識世界的勇氣。很多時候我們生活在舒適圈裏面,有意無意地去回避可能給我們帶來刺痛的一些現實。
再接下來是基於理解包容的所謂人文關懷,或者說一種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或者「人文關懷」這樣的詞語很多時候會被濫用,會變成一種自我感動或者廉價的憐憫,一種從上往下的施舍。要去試著理解和認可他人,但是也要承認,有些時候我們真的沒有辦法完全理解別人的感受,我們只能去傾聽,去接受「完全理解」的不可能,接受我們共情能力的有限。然而,我們仍然要盡量地去理解、去表達,並且認識到這是有缺憾的、不完整的。
創作是一個「開盲盒」的過程。有些時候各種條件都具備了,拍的東西會引起很多人的共鳴,但有些時候因為技術條件和當時情境並不太理想,拍出來的東西可能只打動了少數人甚至只有你自己,但這也並不代表著失敗。這就是最後一點,我們應該怎麽看待我們的創作。不要用一種功利性的態度去看流量影響,而是要把影像作為生命中的一部分去認識它對於自己、對於報道對象更長遠的價值。
問:您之前在文章中談到過您對90後創作者的分析和觀察。90後到00後這十年,技術設備還有社會心態都發生了很多變化,您會覺得00後的學生又有什麽樣的一些新趨勢和變化?
答:首先00後的創作者對於技術和設備的熟悉感肯定增加了。我想今天的大學生或多或少都有一點自己製作視頻的經驗,最基本的也會做一些vlog,剪一些小視頻發到社交網絡上。而且大家觀看各種各樣的影視文本的機會在增加,影像越來越成為了我們主流的文化形態。因此,技術恐懼感,或者說拿起攝像機所需要跨過的技術門檻是在變低的。
但是,困難變小了也意味著我們往往容易「滑過」從業余使用者到專業使用者的訓練區間,而這個訓練區間有助於我們反思技術能做什麽和不能做什麽。因為我們常常帶著一種比較天然的技術樂觀主義去進行創作,而更少意識到影像技術的缺陷和問題。
還有一點是隨著社會和媒介的發展,這一代比上一代所掌握的知識面和所觸達的社會廣度一定是在增加的。但是反過來,這種碎片性知識的增加並不確保對於社會的理解能力的增加,
知識過多時,我們的理解能力反而會退化。因為信息爆炸之後我們不再珍惜信息,不再去對信息進行總結歸納,而越來越習慣於不自覺的去相信結論,這可能是信息過載之後給我們帶來的普遍性影響。

2|影像何為:虛擬、真實與私人敘事
问:您刚刚谈到当下信息爆炸对整个影视创作乃至青年一代带来的影响,我看到您也在去年发表的文章中谈到了新兴短视频对于视听话语形态带来的变革。作为一名研究者,您认为影像领域将来还会有什么样的发展趋势?
答:首先,影像的使用语境现在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扩展。我们现在无论做什么事都可以用影像作为文字之外的一个选项,而且往往影像会更受欢迎。在未来,我想影像会更大程度突破摄影和电影最早期“机械复制”的特点。例如,现在在网络会议上面对面的时候,人的背景都可以是虚拟的了,有了元宇宙和更强的运算能力之后,未来可能连我们的面容都可以虚拟:我们把自己的面容做了3D扫描,让AI进行学习之后,可能我甚至不需要打开摄像头,我的面容就会出现在屏幕当中。未来视频和人工智能之间的结合会更加紧密。
而且现在脑机技术也在发展当中。我们知道大脑思考时是有形象的,思考有时是先出现画面,再用语言去组织头脑中出现的画面和影像。那么有了脑机接口之后,会不会不用经过文字语言这一关,我们也可以直接通过图像去完成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我觉得这将是在我们有生之年能看到的一些重大变革。
另外还有一个方面是,影像的虚拟仿真特征越来越明显。特别是未来裸眼3D技术出来之后,我们借助影像对于环境的感知能力会发生变化,我们个人经验的重塑和获得恐怕也会发生变化。
问:您最近应该也关注到了一个关于“二舅”的视频,该视频因为有虚构成分被b站撤销了推荐,这也引起了进一步的争议和讨论。您怎么看待这样的纪录影像中真实和虚构的权衡?
答:纪录片的真实伦理一直是一个经常被讨论的话题。现在一个比较传统的观点认为,首先,纪录片一定是有真实特征的,但是这种真实不一定是完全的客观真实,它是由创作者对于客观真实的影像展开主观创作所产生的真实。我们一般认为真实性首先在于素材是真实的——当然这个也会被一些影像挑战,比如说现在越来越被认可的动画纪录片。动画肯定不是机械复制的的真实,而是根据真实的史料和个体对于历史的回忆所建构出来的。另外也包括我们在电视纪录片里面经常看到的搬演段落,特别是在一些历史类的纪录片里会用演员、在摄影棚中按照史料复原场景,这个也不是“真实”,而是跟动画有点像,都是用我们今天的影像去帮助大家理解有限的历史记载。
所以我想纪录片的真实性是在一个范围之内波动:最极端的是最严格定义上的真实,而这种真实往往是很难实现的,因为一旦我们架起了摄像机,我们就有把镜头对准哪里的选择,这其实都是在对所谓的真实进行加工建构。所以我想纪录片不存在绝对的真实,只有相对的真实。
它是行动主体,是创作者,当然也包括观众,是主体对于真实的理解,是一种再现和一种重构。
问: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影像人类学这门对中国大陆来说还很新兴的学科。
答:影像人类学是以人类学研究和文化理解为本位的,更具反思性和主动性的一种影像创作和针对性研究。
从历史上来看,这个学科其实经历了好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最早的阶段是人类学家在田野调查时用照相机和摄影机去进行记录,包括人物肖像、物质文化和仪式性文化的记录,因为影像记录会比文字更直观,而且信息量会更大。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有一批人类学电影的工作者超越了简单记录,希望把视听语言作为和文字民族志平行的手段。因为传统人类学作品,像《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等是用文字写就。到了五六十年代的一批人类学电影工作者或者是人类学电影的导演认为,也可以用视听语言、纪录片甚至是用电影的方式去完成民族志和对于社群文化的完整表达,而不只是把他们拍摄成一个档案数据库那么简单。在使用影像作为一门组织思想的语言的过程中,人们发现,因为媒介特质的区别,影像和文字在进行文化表达和民族志写作时有不同的偏向。因此除了制作人类学电影和纪录片之外,研究者也开始慢慢去研究影像本身作为一种媒介的特点,比如语言学方面的一些特点。另外还有一批做影视人类学或者视觉人类学的学者倾向于研究不同的文化群体怎么使用视觉手段,既包括没有文字的民族的用岩画等视觉符号去表意和组织他们的社会生活,也包括今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如何去看待和使用影像——影视人类学包括了这样的一些研究。
问:如果说在纪录作品中影像是不完全的真实,那么在影像人类学的研究中,影像的作用到底是什么?
答:在研究的过程中影像当然首先是一个档案。比如,我的面前发生了一个传统的仪式,我可以用影像把它记录下来并且不断地回看这些影像,去分析我在现场可能没有注意到的细节,这个就是档案和记录的重要性,它可以弥补人的认知的不全面。
另一方面,它和刚才讲的影像的教育功能是类似的,也就是说影像是一种进入和沟通的方式。当我们有了影像之后,其实是在对我们的拍摄对象,对我们所研究的社区进行介入;而当别人看到你拿着摄影机进来的时候,他们也会意识到你是在记录他们的生活,这会促进我们和拍摄对象之间的更多的交流甚至是合作。如果影像用得好的话,我们可以帮助被摄对象展现他们所认为的这个世界,帮助研究者更好地去理解他们的世界观。
我之前拍摄《一张宣纸》,是一部跟非遗相关的记录南方手工造纸的纪录片。当时我住在拍摄对象家里。我自己习惯晚上要整理素材,但拍摄对象特别热情,经常晚上也会陪着我聊天,于是慢慢地就变成我们一起看素材。当他看到我镜头里拍摄的他的生活和他的手艺,会给我补充好多新的信息,我们会围绕影像素材展开进一步的讨论。他会评价我的素材,也会给更多的建议。从他的反馈建议里面,我对他的技艺的理解,对于他的世界观的认识,也会不断得到强化。这时,影像就提供了合作和交流的渠道,而非仅仅地记录。
问:不同于影像人类学这样严肃的学术创作,近来出现了很多独立纪录片,“私影像”、“家庭影像”也大量出现。您是怎么看待这样一些独立的、地下的个人创作呢?
答:它们有自己的独特价值。因为它们是更个人化的表达,这也就意味着在表达的过程中,独立纪录片是和个人的体验,和“小世界”更加紧密相关的,更便于我们去认识和理解这个世界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像人类学会受到它的学科规范影响,在大众媒体上播出的纪录片就会受到行业规范性和观看市场的影响,它们都受缚于一种很强的外在结构。当然,独立纪录片——哪怕是vlog这样的个人创作,也并不是所谓的完全价值无涉和完全无立场,反而是个人性很明显,因此我们在观看这样的作品时,既看到了它所记录下来的客观生活,也看到了不同的个体是如何把自己的主观认知和主观情感与他们所经历的生活结合。这是今天在大众传播的平台上不可或缺的一种组成。

3|影像實踐:用影像溫暖世界
問:了解到您會參加一些電影節的選片工作,在參與電影節選片的過程中,有遇到過一些讓您印象深刻的經歷或者作品嗎?
答:前兩年我看過一個特別讓我印象深刻的紀錄片,叫《The Flat》,是2011年由以色列一個青年導演拍攝的一部紀錄片。主人公在收拾去世的外祖父的遺物時,意外地發現外祖父居然珍藏了幾份納粹的報刊。而在這與之前他對自己外祖父的理解完全相反,外祖父經歷過二戰和大屠殺,是一個與納粹英勇戰鬥的愛國主義者。因此,他很奇怪為什麽外公會珍藏納粹報刊。後來,他進一步地發現,外祖父有一個特別要好的朋友居然是納粹軍官。於是,他開始去訪問他的媽媽和爸爸,又曲折地找到了他的外祖父朋友的後人去進行采訪。當然,受訪者對這些話題都三緘其口,但是經過不懈努力,他最終奇跡般地還原出來了這段個人史。
在我們今天看起來,這樣的事情不太可能,但個人的歷史和國家的歷史在那時的確產生了特別復雜多元的交織,這是一個超乎我們對於歷史的刻板印象的和一般性認知的紀錄片。這部片子既特別私人——是一個孫輩對於祖輩生活的探尋,同時也是一個很公共的話題——它反思了我們到底應該如何理解歷史的不同面向。
問:可以聊一下最近的一些研究方向或者拍攝興趣嗎?
答:從2017年至今我在拍攝一部和流動兒童相關的紀錄片,現在還在後期的過程中。這部片子拍攝的是蒲公英中學的合唱團——一群從小生活在北京的初中生們。通過他們和音樂的故事,去看城市的發展,嘗試去理解少年怎樣對待生活。
另外我還在繼續關註非遺和歷史相關的一些題材,比如,我這些年一直在陜北地區拍攝當地的道教民俗。還有一個我特別喜歡的題目,但是一直還沒有開始拍,就是我們中國傳統一句老話叫「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我們中國的傳統文化中,人和山川草木的關系是很豐富的,這是我當時在拍攝《一張宣紙》的時候開始有所體會的。到了南方之後我發現,許多花草和動物我都完全叫不上名字來,但這些做宣紙的匠人們會如數家珍地告訴我們這個東西長在哪裏、什麽味道、能被用來做什麽。在以前那種傳統的生活中,人們發展出來了一種特別寶貴的對於自然萬物的知識和情感。我特別希望能夠通過影像的方式,把現在仍然生活在山水旁邊、飼養著牛羊的人們的生活,以及其中所體現出的自然的詩意的人與自然的相互關系表現出來。

問:現在有許多青年學生和創作者希望自己能夠拿起機器去拍攝,但他們可能會遇到各種來自自己或者外界的阻礙,您作為一個前輩對他們有什麽樣的建議和提醒呢?
答:我覺得有兩個相輔相成的方面。第一,如果不是一時興起而是心心念念要去創作,那說明影像對你的個人的生命經歷是有獨特價值的,那就去找個機會把它給做出來——不要管實現得好還是不好。就算不好也是一種人生經歷,最終會成為個人成長的養料。
第二,在開始之前仍然要謹慎。因為拍攝畢竟很耗費時間精力,不僅是自己的也包括他人的,還會影響你的社會關系,「大炮一響,黃金萬兩」。正是因為開始拍攝是一個成本很高的事情,所以事前一定要周密準備、充分調研。進一步地,在做的過程中也要自己不斷地去激勵自己。基本上我做每一個紀錄片的過程中總有那麽一段時間是充滿著自我懷疑的,覺得這個片子可能做不成,覺得這個片子可能是我做過的最爛的一個片子,這種時候一定要學會直面自己的情緒和焦慮,要多找一些能夠激勵自己的方法。比如說我會跟別人聊一聊,去看幾部好的紀錄片。
問:您參與的清影工作室的標語是「用影像溫暖世界」,您是怎樣理解影像對於這個時代的意義的?
答:首先像我之前談過的,影像是一個檔案。我們想象一兩百年之後,要了解二十一世紀初的中國,了解這個星球,可能我們會從影像中獲得很多文字中所獲得不了的知識。
另一方面,影像對於社會來講,是人類進行情感交流和凝聚共識的一個特別重要的土壤。為什麽今天許多像二舅這樣的視頻引爆全網,其實正式因為它們凝聚了我們的一些共識,在表達著我們一些共同的心理焦慮和共同的期待。雖然說這個視頻可能有誇張不實、有粉飾苦難的地方,但另一方面我們也要承認,這段影像確實切中了今天我們的心理需求,它短時間內的強大傳播力意味著我們今天需要借助影像去做一些表達和宣泄。
問:最後想請您向想進入影像世界的初學者們推薦一兩部紀錄片或者一兩本書。
答:有一個片子我自己特別喜歡,並且對於想學紀錄片的同學我覺得是很有幫助的。這部紀錄片的名字叫《有熊谷守一在的地方》,這是一部很安靜的紀錄片,看上去沒有什麽懸念,也沒有很強大的張力,但是它體現了一種獨特的生活詩意,以及微小但是美妙的生活體驗。
第二個推薦是我在我的影視製作課上會給大家推薦的一本書,是羅伯特麥基的《故事》。這本書首先是一個編劇指南,但是不管是對於虛構的編劇還是對於紀錄片的表達都是特別有參考價值的。另一方面,書理論性也很強,給我們展示了人類為什麽那麽喜歡故事,能夠給我們帶來文化上的啟示。

很長一段時間裏,我對影像的癡迷停留在一種奇觀層面——我欣賞它,把它看作一種完美的表達媒介,然而卻始終與其保持著距離,這恰像我的生活,在清華園裏終日面對行人匆匆,焦頭爛額。
直到梁導的第一堂課,他的第一次作業是以「我」為主題拍攝一組照片。在這堂課上,我們被要求在拍照時和被攝對象進行交流、建立聯系,當然也包括與自己的聯系。
從那時起我才真正觸摸到影像。影像不應該只作為一種技術、一種娛樂方式而存在,它應當成為理解的橋梁。采訪中,每每談及自己喜歡的影像和自己的創作,梁老師總是喜悅而真誠,我想,對他來說,影像已然成為一種生活,他在此流動於田野和課堂之間,用創作和教育實踐理想。
文 | 蔣一凡
圖 | 來自受訪人
審稿 | 童不四 言冰
編輯 | 李婧軒
matters編輯|邢奕萱
圍爐 (ID:weilu_fl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