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 | 纪念阿伦特 | 我们必须思考(下)
接上文:188 | 纪念阿伦特 | 我们必须思考(上)
我们这些难民
1956年,当阿伦特准备出版《拉赫尔·瓦恩哈根》时,对德国犹太人的“肉体毁灭”已经众所周知了。但是,早在1930年代,阿伦特就隐约“察觉到德国犹太人的浩劫”。1933年国会大厦被烧之后,她立刻认为“匹夫有责”,“不再认为我们可以袖手旁观”。
阿伦特的丈夫安德斯逃亡到巴黎,但是她和母亲留在柏林,掩护共产党人,并在普鲁士国家图书馆研究犹太复国主义。1933年,她被一个初出茅庐的盖世太保逮捕。虽然阿伦特被拘留了几天,但是她对他百般讨好,最终被释放。阿伦特和母亲第二天离开了德国,取道布拉格和日内瓦到了巴黎。阿伦特在巴黎待到1940年,为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工作。这些组织帮助逃出德国的犹太人,为他们定居巴勒斯坦做准备。阿伦特和安德斯于1937年离婚。
阿伦特在柏林认识了本雅明,本雅明是安德斯的远房亲戚。但是,在巴黎的难民圈子里,她与本雅明熟悉起来。这也是她认识布吕歇尔的方式。布吕歇尔并非犹太人,他是前斯巴达克同盟成员【校注:德国在一战后的左翼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也是一家性俱乐部的保安。他们于1940年1月结婚。
1939年9月,布吕歇尔和本雅明被关在讷韦尔,虽然布吕歇尔被提前释放,但是几个月后他又被逮捕。这一次的逮捕对象包括女性。1940年,阿伦特被带到埃菲尔铁塔附近的冬赛馆,一周后运往居尔集中营。她在那里待了五个星期,法国被德国占领,纪律涣散,她趁机逃离。
阿伦特在1941年11月17日给肖勒姆的信中说,她偶然碰到本雅明,他正在等签证,她和本雅明下了几个星期的象棋,后来去蒙托邦与丈夫团聚。在1940年9月19日的马赛,阿伦特和布吕歇尔最后一次见到本雅明,本雅明把一个行李箱的文件交给他们。六天后,他在西班牙边境的包港自杀【校注:本雅明的死因并没有确切定论,至少在Taussig的《本雅明之墓》一文中如是说】。

1941年初,阿伦特和布吕歇尔从法国来到里斯本,于5月登上开往纽约的船(SS Guiné)。他们打开本雅明的行李箱,大声朗读《历史哲学论纲》:象棋装置背后的侏儒、来自天堂的风暴、“紧急状态”作为被压迫者的日常。在埃利斯岛办理完手续后,他们在西95街找到两间带家具的出租房。阿伦特的母亲在几个星期后到达,和他们住在一起。
虽然三个人已经过了学语言的黄金时间,但是,他们必须学习,而且,他们学会了。阿伦特在马萨诸塞州的一个食素的家庭作为换工(au pair)住了六个星期,而且打算接受社会工作者培训,但是布吕歇尔否决了,“只有疯子或白痴才能应付这种学习”。布吕歇尔在学习英语上很困难。扬-布鲁尔摘录了他的笔记本上的一些词语,像是tickled to death, hit the jackpot, make a mess of it, nifty chick。阿伦特也喜欢一些古怪的说法,比如horned dilemmas, spades called spades, willy-nilly, pell-mell。
后来,麦卡锡试图纠正她的习惯。1970年代跟阿伦特学习的扬-布鲁尔,记得阿伦特特别喜欢说when the chips are down,而且把chips读成cheeps。当麦卡锡编辑《心智生命》时,她把这句话改成when the stakes are on the table(当赌注已上桌)。不过,在本雅明的《历史哲学论纲》中,chips笑到了最后。本雅明的德语是Wenn es hart auf hart kommt,一般译为“当务之急”,但是阿伦特的译法是when the chips are down(赌注已下)。
阿伦特比布吕歇尔更快在纽约找到一席之地。她的第一份工作是搜寻遗失和损坏的犹太文物——用一位朋友的话说,这份工作让她可以“用实际行动来哀悼”。另一份工作是为肖肯出版社工作,把卡夫卡、肖勒姆、伯纳德·拉扎尔的作品带给美国市场。阿伦特还写了一些论战性的专栏,刚开始发表在德语的犹太媒体上,后来改用热情的、玩世不恭的英语。阿伦特在《我们这些难民》这篇短小、犀利的文章中说,“显然,没有人想知道,当代历史创造了一种新的人类——这种人不是被敌人关进集中营,就是被朋友关进强制收容所……我们中间有一些奇怪的乐观主义者,他们讲了很多乐观的言论,回家却打开煤气或者爬上摩天大楼,做出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极权主义起源》
并非一蹴而就
1945年,阿伦特正在与出版商讨论将于1951年出版的《极权主义起源》。她和布吕歇尔私下叫它“我们的书”。当阿伦特在上班,玛莎在做饭和打扫卫生时,布吕歇尔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帮阿伦特阅读了大量资料。

阿伦特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中说,“结果,在毫无预备和很可能违背他们意愿的情况下,他们无可选择地(willy-nilly)创建了一个公共领域”。她后来写道,“这些实际上从来不参与第三共和国公务的人,被一股仿佛来自真空的力量卷入了政治。”个体运用它们的“主动性”,共同创建公开辩论与自由。在阿伦特看来,这就是“宝贵财富”。“这些宝贵财富就像海市蜃楼一样,总是在极不相同的形势下出乎意料地显现,又迅即消失”。
在《极权主义起源》中,阿伦特和布吕歇尔也在他们之间建构了这样的事物。正如希尔所说,这是一部“史诗般的作品”,充满历史的各种观点和角度,迪斯雷利、德雷福斯、罗德斯、吉卜林等“大博弈”的玩家们都汇聚一堂,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需要哪个角度。
在写作过程中,《极权主义起源》多次改变了形式和主旨。
希尔说,最初计划是创作一本名叫《羞耻的元素:反犹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的作品。后来,书名变为“地狱的三根支柱”,包含“犹太人通往政治风暴中心之路”、“民族国家的解体”、“扩张和种族”、“羽翼丰满的帝国主义”四个章节。这部作品的规模和方法的变化,可能是因为这项工作停顿了一阵子。但是,当她继续这项工作时,她发现把各种片段拼接起来的方式本身就是一种组织方法:“元素自身可能从未导致任何后果。如果它们,并且当它们结晶为固定而明确的形式时,它们就成了事件的起源。然后,也只有在这之后,我们才能追溯它们的历史暗流。事件昭示了其本身的过去,但是绝不能从过去推导出事件本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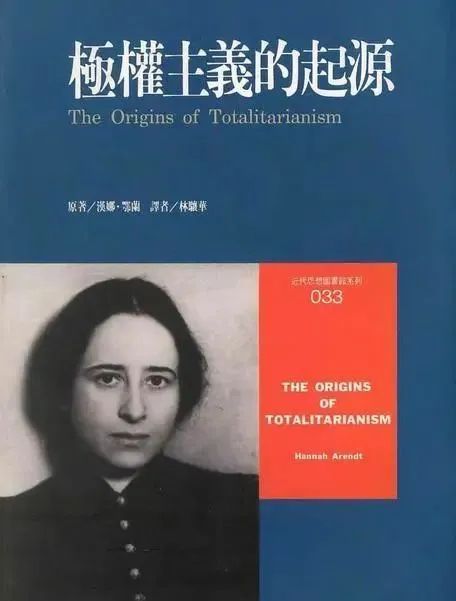
到了1948年,这个计划已经是现在读者能认出来的样子,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反犹主义”、“帝国主义”、“纳粹主义”。但是,“随着斯大林主义策略出现,随着阿伦特开始阅读苏联的材料”,她决定修改第三部分,原本针对纳粹的部分产生了延伸。“企鹅现代经典丛书”版包含了1950年的序言,展现了她分析水平的高超之处。她说,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精神上的无家可归到前所未有的规模,漂泊无根的心绪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第三次世界大战随时可能发生”;现代人的无所不能与无法理解世界的意义之间的不相称人令人沮丧;我们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政治原则,抵挡人类自身的聪明才智和愚蠢行为的毁灭性力量。
后来,阿伦特又写了三篇序言,每个部分一个序言。她还给1958年的第二版增加了一个章节,“意识形态与恐怖”。现在,第三部分针对的是一般化的极权主义:乌合之众而非阶级、阴谋主义和恐怖、对领袖的忠诚、秘密警察。虽然第三部分读起来像危言耸听的、冷战时期的畅销书,但是,它确确实实是可怕的。阿伦特认为,“世纪危机”的风暴中心是过剩的问题,是现代性的高度发展所抛弃的数百万人。这是一个政治学论断,而不是一个人口学论断。问题在于,现代政府区分了有用的人和无用的人。这个区分的过程,被阿伦特称为“功利主义”,也叫作“极端恶”。“在极权主义垮台之后,极权主义的方案仍能存在,它以一种具有强烈诱惑的形式,将会在可能的时候,以对人有利,并且能够解除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悲苦的姿态出现”。
岛屿之旅般的阅读
由于《极权主义起源》是一本巨著,厚重而又庞杂,所以,卡诺凡把它视为一串岛屿的想法很有道理。每个读者都应该找到自己的路线,而我的路线分为两个部分。“反犹主义”和“帝国主义”两部分构成了一个精彩的历史叙述,说明19世纪欧洲民族国家的发展和解体如何创造两种新的人类——边界外的难民、边界内的少数民族。而且,殖民主义不断追求新的获利方式,从而缩小了世界,让它的支配幻想越来越接近现实。与此同时,在欧洲,财富、人口、解放、权利的增长是不平衡的,打破了旧的习惯和制度,引发了对弱势群体的暴行。于是,纳粹党在德国崛起了,因为它看起来确实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当时的问题。
我想在“帝国主义”部分的最后一章停留一下。这一章讲述了1789年《人权宣言》以来的坎坷历程。在阿伦特看来,这些人权从未在任何地方得到贯彻。她认为,普世人权的观念,始终与民族主义、现代欧洲的战争和革命纠缠不清,就像一场大型的“抢凳子游戏”。每当音乐暂停,边界划定,幸运的人会发现,自己身处愿意接纳他们、能够照顾他们的民族国家。而边界两边,不幸的人会发现,所谓“人类不可剥夺的权利”对他们就是空头支票。
所谓的国际联盟?在两次大战之间,它的表现世人有目共睹,不是吗?所谓的联合国,还有《1948年人权宣言》?阿伦特在《极权主义起源》脚注中提到过它,1950年代初期的会议“只不过是一种姿态,至少需要20国代表同意,但又明确肯定参加这类会议不负任何道义责任”。“以假设人类本身的存在为基础的人权概念崩溃之时,正值那些虔诚地相信此概念的人首次面对另一种人——那些人确实失去了一切其他特性和具体关系,只除了他们还是人”。不仅如此,“战后,被认为是无法解决的犹太人问题结果解决了——其方法是先殖民后征服一块土地——但是,这既未解决少数民族问题,亦未解决无国籍问题。相反,犹太人问题的解决反而产生出一个新种类的难民,即阿拉伯人”。于是,抢凳子游戏继续开始。

巴勒斯坦人在1947年底开始逃亡,但大部分人在1948年4月至8月间离开或被赶出家园。到1948年秋天,一场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已经形成,有70多万人在逃。图源联合国档案馆,1948年
斯通布里奇在《无地之人》中说,“当流亡在冷战时期的西方成为文化和文学的一大主题,(越来越多的)无权之人退回到人文主义的氛围中,试图为欧洲传统重塑某种道德权威,哪怕欧洲的地缘政治力量日渐消退”。近些年来,这种重塑的道德权威摇摇欲坠。
我的“岛屿之旅”的第二个部分,将考察《极权主义起源》的第三部分,将极权主义视为阿伦特在结尾提出的那个问题的可怕答案。我们如何解决“20世纪危机”,甚至“21世纪危机”?阿伦特所考查的那段历史,是《天路历程》的地狱版本,我们穿越恐怖、集中营、“毁尸灭迹的坑洞”,直到伫立在悬崖面前。“甚至只有当极权主义成为陈迹时,我们这时代的真实困境才会显现其真正形式——尽管不一定是最残酷的形式”。或许,等到某种事物取代了极权主义,“世纪危机”才会爆发。
肖莎娜·祖博夫在《监控资本主义时代》中说,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之所以是20世纪的诅咒,“正是因为它以恐怖的手段解决了问题”,这个说法让她多年来“难以忘怀”。我不知道,为什么祖博夫会联想到脸书和谷歌。“机器控制主义(Instrumentarianism)”是祖博夫所谓的监控资本主义特有的更加隐蔽的支配形式。假如祖博夫多讨论马克思和福柯,她的论证会更加清晰(她的书也会更薄),不过我不能否认,她对阿伦特的运用让我不寒而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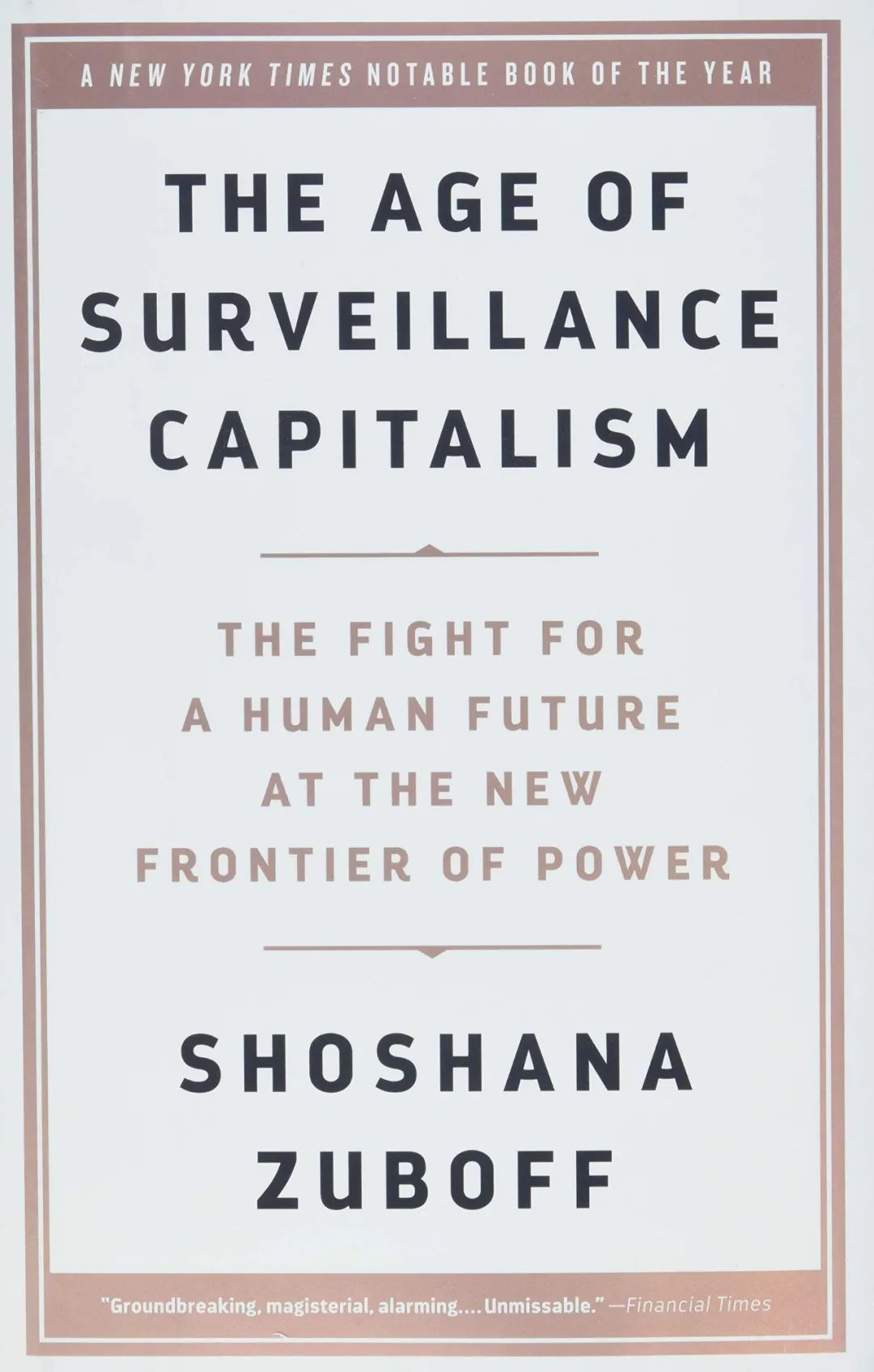
在阿伦特的作品中,恐怖、集中营、酷刑所施加的支配,是通过对自发性的破坏,通过将“人类样本“简化为一系列反应:而这组反应总是可以被另一组反应以完全相同方式表现出来的反应清除和取代”。虽然祖博夫所谓的机器控制主义更加温和、更有娱乐性,但是,它从内部瓦解了人类自由的可能性。祖博夫说,斯金纳没有亲眼看到他的“行为修正技术”通过电话和网络所展现的真正力量。阿伦特在《人的条件》结尾中说,“现代行为主义的难题不在于它们是错误的,而在它们有可能成真,在于它们其实是对于现代社会某些明显的趋势最好的概念化,可想而知,现代世界(它发动自人类活动史无前例的、前途看好的破茧而出)的终点可能是历史上最死气沉沉的、最贫瘠的消极状态”。
关于马克思的小研究
用卡诺凡的话说,《极权主义起源》中的政治理论的论述过程是“头重脚轻的”。虽然“反犹主义”和“帝国主义”两个部分是很扎实的,但是,后文对“一种全新的政府形式”的推导就纯属虚构了,因为它的证据和方法都处于建构过程中。就目前而言这的确是事实,尽管我认为跟随阿伦特的思路,你可以学到更多。
另一个头重脚轻的地方是,虽然全书用几百页讨论了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愤懑和怨恨的“潜流”,但是,它只字未提(乌托邦的或科学的)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抑或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运动。阿伦特不怀疑马克思是一位“对正义满怀热情”的“伟大学者”,但是她认为,马克思主义无疑导致了贫困化和古拉格。那么,苏联社会主义犯下如此可怕的错误在多大程度上要归咎于马克思?
阿伦特计划在“关于马克思的小研究”中处理这个问题。这项研究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哲学层面考察马克思,把他视为柏拉图以来关于工作和劳动的庞杂思想的继承者。第二个部分是马克思到列宁到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史。第三部分,后来成为《极权主义起源》的最后一章“意识形态与恐怖:一种新的政府形式”。不过,这项研究没有完成。
阿伦特越是在西方哲学的大传统中考察马克思,问题就越复杂。后来,这项研究变成了《人的条件》的“劳动”和“工作”两个部分,《过去与未来之间》中的“传统与现代”、“历史的概念”这两篇最好文章,《论革命》中的反“社会问题”部分,以及直到去世仍未发表的大量英文和德文手稿。2018年,这些手稿集结成《现代对传统的挑战》出版,是沃尔斯坦出版社的《阿伦特全集》的第6卷。正是卡诺凡1980年在档案中发现的这些手稿,导致她改变了对阿伦特思想总体方向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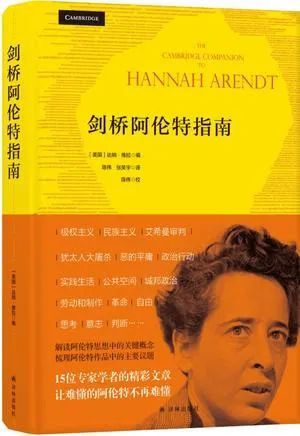
阿伦特在1953年的一份手稿中说,“人们喜欢在马克思同列宁、斯大林之间画一条直线,从而认定马克思是极权统治之父”。但是,事实上这是错误的。“我认为,马克思与斯大林的差异,比起亚里士多德与马克思的差异,不仅更多,而且更具决定性。”因此,假如我们要把斯大林的“恶行”归咎于哲学的影响,那么,我们不能仅仅责怪马克思:我们应该考察一整个“我们自身的传统”,包括马克思同样努力思考的“真正的问题和困惑”。
其中一个问题是,人们认为“沉思的生活”(vita contemplativa)比“行动的生活”(vita activa)更能带来好的政治。这是一种“哲学王式”的观念。另一个问题是,人们认为历史是人造物,我们可以不出意料地发现人造物的规律,“阶级斗争,对马克思来说,这个公式似乎是解开所有历史之谜的钥匙,正如引力法则业已表明是解开所有自然之迷的钥匙一样”。不过,马克思的最大“困惑”,是过去的“哲学王”传承下来的关于工作和劳动的庞杂思想。但是,由于工作和劳动正经历剧烈的增长和变革,所以,它成了马克思所思考的一个特殊问题。“似乎马克思,与克尔凯郭尔或尼采一样,都绝望地试图在思想中反抗思想,而同时又使用着传统本身的概念工具”。马克思不是那个时代唯一面对这个问题的作家。
阿伦特说,“整个现代世界,尤其是马克思,都震慑于西方人史无前例的现实生产力”。这些新的财富如雨后春笋般,通过人的劳动生产出来,却从劳动者那里被抢走,进了他人的腰包:这种不正义让马克思愤愤不平,而这种愤愤不平导致了“一种根本性的、公然的矛盾”。其中最大的一个矛盾是,劳动一方面是使人成为人的活动,另一方面是人为了获得自由必须打破的枷锁。
人何为人
在《人的条件》中,读者期待看到对阿伦特核心原则的澄清、界定、陈述。卡诺凡在她的第一本《阿伦特的政治思想》中,也是这么想的。后来,她放弃了,又写了《阿伦特政治思想再释》,承认阿伦特思想的很多地方有一种“费解的古怪”。打个比方,阿伦特的词汇很朴素,但是,她“在特殊意义上使用普通术语时不会事先提醒读者”,而且这些特殊用法比比皆是:“她常常所说的,远远多于读者能够轻松把握的(尤其是做了较多的概念区分)。”
翻开《人的条件》,我们就看到阿伦特不停讨论雅典的城邦(polis)、城邦与家政(oikos)的区分、行动。阿伦特所谓的“行动”,是阐释亚里士多德的“实践”(praxis)的用语,是“人们彼此之间唯一不假事物之中介而进行的活动”,是“典型的政治活动”。卡诺凡说,对雅典人的强调,让许多人把《人的条件》误读成“一次怀旧的写作”。但是,事实恰恰相反。
这本书开头就是1957年人造卫星的发射。虽然“这个无比重要的事件,就连原子弹分裂都比不上”,但是,它不过是现代性“推翻既有的人类存在”的最新尝试罢了。它是我们被炸得粉身碎骨之前确实需要讨论的问题。只是,我们无法讨论它,因为科学发展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们将永远无法理解,也就是思考和谈论我们原本有能力做的事情”。因此,我们面临的危险是“成为不会思考的生物,任由所有在技术上做得到的机械装置摆布,无论它有多么凶猛残暴”。《人的条件》的结尾提到了“最死气沉沉的、最贫瘠的消极状态”,这让祖博夫深感不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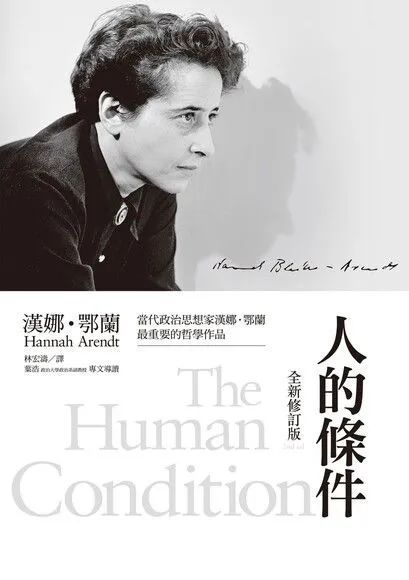
《人的条件》,林宏涛 译
没错,在这本书中间,从开头到结尾,到处是希腊语和拉丁语的词汇,但是阿伦特不是想复兴古典理论,而是想探究和反思,考察概念及其历史,迫切地寻找(像卡诺凡认为的那样)可能被遗漏的地方。其中一个被遗漏的地方,是亚里士多德对zoe和bios的区分。Zoe是自然界随处可见的生命,包括动植物的生命和人的生命,bios是专属于人的,具有人的形态与生平,“受限于开始和结束,也就是在世界中出现和殒灭的两个最重要的事件”。
另一个被遗漏的地方,则是被马克思混淆的工作和劳动的区别。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每一种欧洲语言,都有两个在字源上风马牛不相及的语词,后来被我们视为同一活动”,比如英语的work和labour,法语的oeuvrer和travailler,德语的werken和arbeiten,希腊语的ergazesthai和ponein。工作跟手艺、成就、稳定这些褒义词相关,劳动跟痛苦、麻烦、浪费、日复一日的劳作、重复这些贬义词有关。一方面,劳动是一场与死亡和衰老之间进行的疲惫的、肮脏的、日复一日的、无休止的斗争。正因为如此,雅典公民让奴隶和女人为他劳动:“奴隶的屈辱是命运的打击,是比死亡更悲惨的命运,因为它会让人蜕变成类似家畜的东西”。另一方面,工作创造的事物,建构了阿伦特所谓的“世界”——我们在大地和自然上创造的“人造物”的居所。没有它,人类文明的“共同世界”就不复存在。
可是,由于某些“显而易见的”原因,哲学家总是“忽略”工作和劳动的区分。劳动是一个非主体,一个隐藏在“家政昏暗的内部”的事务。女人负责生育子女,奴隶负责处理杂务。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劳动和工作没什么好比的。当基督教兴起之后,它同样远离私人领域的杂乱、肮脏事务。因此,千百年来,劳动和工作、私人和公共的混淆愈演愈烈。这时候,马克思出现了,这位伟大的学者第一个指出,创造价值的劳动是以人的痛苦为代价的。
可是,在马克思的时代,“家政”已经冲出了是“家庭”(household),变成了“经济”,是“全国性的家政管理”,是“自然事物的不自然成长”。“把我们凝聚在一起,又让我们不至于成为对方的绊脚石”的这个“共同世界”,已经屈服于“大众社会”的混沌无序。卡诺凡在《阿伦特政治思想再释》中说,“马克思的悲剧在于,尽管他以自由为目标……他实际上达到的是鼓舞他的追随者使自身服务于强制过程”——行为主义、自动化、极权主义。或者说,这是卡诺凡眼中阿伦特的观点。
1964年9月16日,汉娜·阿伦特接受了德国电视台主持人高斯的采访,之后以《还剩下什么?还剩下语言》(”What remains? The language remains.”)为题播出。在采访中,阿伦特和高斯都在抽着烟,他们谈论了大屠杀、哲学、女权主义、犹太性、流亡、友谊,还有她关于阿道夫·艾希曼的书。当高斯问阿伦特,她在战前长大的德国还剩下什么时,她回答说:”我不知道。“ 访谈节选来自: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V6WIipm96U
与麻烦共存
1976年,阿德里安·里奇如此评价《人的条件》:“阅读一位了不起的、博学的女性写的书,也许是痛苦的,因为它展现了一个受男性意识形态滋养的女性思想的悲剧”。在里奇看来,很明显,是女性承担了繁衍后代的大部分工作,以及家庭中的无偿劳动,“然而面对阻止女性参与共同世界的做法,阿伦特没有对此予以关注,而是视而不见”。里奇把阿伦特解读为反女权是很正确的。众所周知,阿伦特不喜欢1970年代学生中的女性解放运动。其中一位学生回忆,阿伦特指着她戴在衣领上的“芝加哥妇女解放联盟”徽章说,“这不是严肃的做法”。
里奇感叹道,“男性意识形态竟然有如此掌控女性头脑的力量,以至于让女性的头脑脱离她的身体”。可是,这种脱离,或许会开辟新的方向和角度。例如,杰奎琳·罗斯认为,阿伦特对“隐私所暗示的剥夺特征”——厨房中的阴毒!——的强调,隐含了男性对专制统治、家庭暴力的幻想:“女性成了男性对自身(男性与女性共有的)脆弱性的无意识认知的替罪羊”。阿伦特的思考不仅极力回避“必然性领域”(包含激发人类存活和奋斗的一切),而且回避怜悯、仁慈、哀恸、“人心的暗面”。这种回避提醒我们,死亡即使在今天依然是无法掌控的。正因为如此,护理人员减轻病人的痛苦和羞辱的工作,往往被“视而不见”,而且得不到应有的酬劳。
杰奎琳的姐姐吉莉安·罗斯认为,问题不在于男性暴力本身,而在于现代欧洲政治史上“自由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联系”。瓦恩哈根、卢森堡、阿伦特“经历了普鲁士和德国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危机”,“作为女性和犹太人,她们最好地见证了居间的模棱两可”。身为女性和流亡民族的一员,她们深知,关于人权的一切高谈阔论背后都是空洞和虚假的,退回到社群、民族、种族、性别的尝试无非是在不同层面上重复了这个问题。与此同时,我们必须不断尝试。这是一种“居间女性的张力”,是对于“无解的普遍主义”的培养。这种普遍主义拒绝轻易走向“任何爱的伦理直接性”。
不过,事实上,我之所以阅读阿伦特,是因为唐娜·哈拉维在《与麻烦共存》中关于艾希曼的段落,她说,“这种思考的无能,会产生那种平庸之恶。这种平庸之恶可能会导致人类纪的浩劫,导致愈演愈烈的物种灭绝和种族灭绝”。你知道这种现象正在发生,我也知道这种现象正在发生,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让它发生下去?哈拉维说,“这种后果已经迫在眉睫。我们必须思考!”我认为,哈拉维在这一点上是对的,而且在“鲁莽的乐观和轻率的绝望态度”面前,阿伦特是很好的帮助我们思考的人,正如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开头所写的那样。

唐娜·哈拉维,《与麻烦共存》
阿伦特1958年给《极权主义起源》增加了一个章节,后来又删除了它。在增加的这一章中,她把1956年匈牙利起义描写成同法国抵抗运动一样的历史时刻。在这样的时刻,分散的人群“在毫无预备和很可能违背他们意愿的情况下”走到一起,共同创建“公共幸福”(她有时这么说)或“公共自由”——“这些宝贵财富就像海市蜃楼一样,总是在极不相同的形势下出乎意料地显现,又迅即消失”,就像“漂泊的荷兰人”一样。这种宝贵财富,有点类似阿伦特所谓的“新生性”(natality),即人类出生的事实和新的开端的可能性。
老实说,阿伦特在兜售这个概念时,我并不买账,甚至感到有点尴尬。然后,我想起娜奥米·克莱因引用布拉德·维纳的作品。这位地球物理学家在2012年做一个名为《地球完蛋了吗》的演讲。他讨论了“系统边界、扰动、耗散、吸引子、分岔理论”。克莱因的结论如下:
全球资本主义已经使得资源消耗如此迅速、便捷、无障碍,以至于“地球-人类系统”正在变得岌岌可危……但是,这个模型中有个提供了一丝希望的驱力。维纳把它叫作“反抗”——这是“一个人或一群人”的运动。按照维纳的说法,这包括了“直接的环保行动,主流文化外部的反抗,比如原住民、工人、无政府主义者等团体的抗议、封锁、破坏”。……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假如我们在乎地球的未来,在乎我们与环境的未来,那么,我们必须把反抗作为这种驱动力的一部分”。
但是,就像阿伦特在《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中说的,“任何一个时期,当它本身的过去变得和我们看到的一样可疑时,必定最终遭遇语言现象,因为在语言中,过去被根深蒂固地保留下来,顽强地制止了所有一劳永逸地根除它的尝试。”这是因为,“只要我们还在使用政治这个词,希腊语中的城邦就将继续作为我们政治实体的底座,也就是,存在于深海之底”。

最新文章(持续更新)
183. 深度访谈|行走阿富汗的人类学家:塔利班是一个被动接受的选项
185. 姚灏 x 吴玥涵:细胞、数据与受苦的人
186. 田野编 | 探寻假肢的世界
187. 聊聊写作 | 许晶:不是完美主义者
188. 纪念阿伦特 | 我们必须思考(上)
189. 纪念阿伦特 | 我们必须思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