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小说特色种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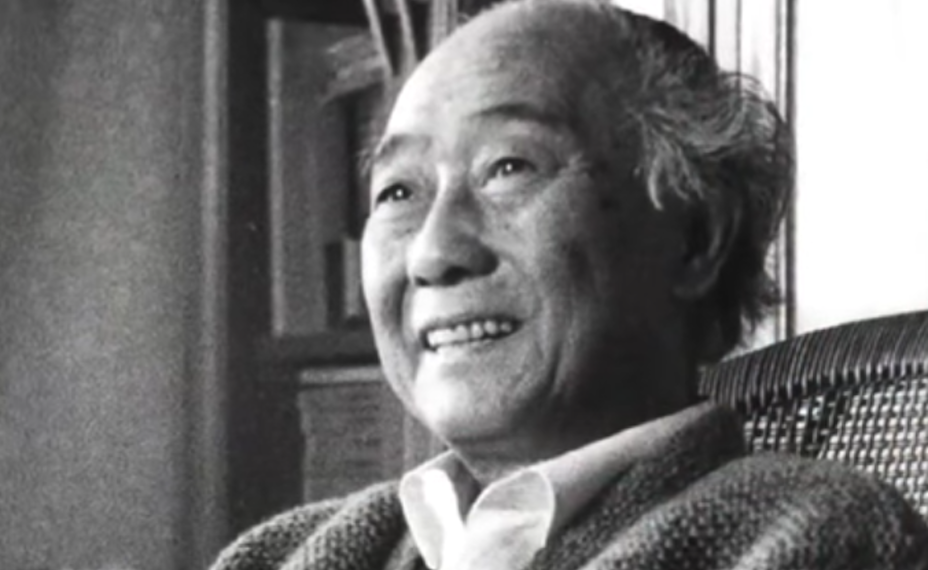
在阴雨连绵的日子里,读汪曾祺的作品可以让你感觉到干爽的舒适。在骄阳似火的日子里,读汪曾祺的作品可以让你感觉犹如喝到冰镇酸梅汤。给种种俗事弄得心烦意乱的日子里,读汪曾祺的作品可以让你情绪镇定下来,思想清晰起来,感觉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有了头绪。
在任何时候读汪曾祺的作品都可以是一种好享受,好逃避。即使你不是特别喜欢汪曾祺的风格,他的文字也不会给你增添烦恼。
汪曾祺曾经明确地说,“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益于世道人心,我希望使人的感情得到滋润,让人觉得生活是美好的,人,是美的,有诗意的。”
***
英国十八世纪的大文豪约翰生博士在编辑了莎士比亚戏剧集之后,不但对莎翁给予了高度的赞美,而且也对他发出了严厉的批评,声称莎翁为了方便而牺牲美德,更着力于愉悦而不是教化;莎翁在写作的时候似乎是没有任何道德目的。
显然,约翰生博士对莎士比亚的批评绝对不适用于汪曾祺。读者可以看到,汪曾祺说到做到,写作目的一以贯之,是标准的文以载道派,假如希望自己的作品有益于世道人心可以说是一种道的追求的话。
汪曾祺作品的句子都极其清楚干净,简单明了,绝无拖泥带水。他无论是写小说还是写散文都是这样。他的小说人物刻画也都是极其清楚干净,简单明了,没有复杂性,而且都是理想人物——理想的少男少女(纯情又纯情),理想的男人女人(绝对本分),理想的父母(对孩子绝对好),理想的商人(绝不坑蒙拐骗)。
总而言之,汪曾祺的小说人物都很理想,理想到连强盗都是盗亦有道,绝对不乱来,绝对不会肆意耍流氓残民以逞。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汪曾祺小说里没有真正的坏人。
因此,汪曾祺的小说严格地说不是小说,而是童话,是寓言。
童话或寓言力图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将纷纭复杂的世界简单化,把一个道理说个清清楚楚,只要使纷纭复杂见出简单的道理,深刻的道理,便是功德圆满。在童话或寓言中,简单就是深刻,深刻就是简单;复杂就是道理认识得不够到家。
但小说跟童话或寓言不同。小说力图展示世界的复杂,人情的复杂和变化。典型的小说,即使是篇幅短小、主题简单,如芥川龙之介的《罗生门》或《鼻子》,也是力图展示复杂的世情——原本满腔正义的一个武士几分钟之内就可以把正义抛诸脑后,变成一个强盗;人们对不幸者的同情总是基于一种恶意的优越感。
***
汪曾祺的小说貌似总是尽力回避人事或世情的复杂。
以他根据《聊斋志异》故事改编的《捕快张三》为例。“ (张三) 经常出外办差,三天五日不回家。媳妇正在年轻,空房难守,就和一个油头光棍勾搭上了。”
最后,张三发现了证据,媳妇无法抵赖,只能承认。张三要媳妇死,媳妇提条件说,要死得漂漂亮亮。张三答应这条件。
媳妇打扮得漂漂亮亮,按照约定要上吊自尽的最后一刻,看着媳妇那么美,张三后悔了,他喝住了媳妇:“ ‘回来! 一顶绿帽子,未必就当真把人压死了!’ 这天晚上,张三和他媳妇,琴瑟和谐。夫妻两个,恩恩爱爱,过了一辈子。”
故事到此结束。
这确实是一个好故事。这故事给读者的教训是,男人常常忽视自家女人的美和需求,只有到了非常的时刻才意识到自己的忽视,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意识到自己对女人的亏欠。
与此同时,这故事显然也是不动声色地宣扬了达观/宽容/大度/不咎既往(即英语所谓的grace)的美好,对人、对自己都是美事,好事。
但这好故事是一个童话或寓言,因为这故事不涉及任何现实的复杂性——戴绿帽子的压力来自社会,具体地说就是来自邻里街坊;另外,出轨的人跟有毒瘾的人一样不那么容易刹车。对这些很容易想到的现实问题,《捕快张三》没有片言只语的陈述,甚至连暗示也没有。
***
再例如,《名士和狐仙》——名士杨隐渔生活富足,很有学问,为人善良,爱上了伺候患病的妻子的女佣人莲子。妻子病故之后,杨隐渔不顾亲戚和四邻的非议,正式娶莲子为妻,教莲子识字作诗,两人琴瑟和谐,幸福美满。杨隐渔后来得了急病死了。接下来的自然而然的现实问题是:还是年纪轻轻的莲子今后的日子怎么过?
汪曾祺处理这种现实问题的办法是让莲子把杨隐渔的遗产整理得井井有条,然后就蒸发了,无影无踪了;众人随后纷纷议论道:莲子其实本来就不是人,是狐仙。
以读小说的心态来读汪曾祺小说的人会批评汪曾祺这种处理现实问题的手法过于简单化。女权主义者则很可能会有更多的、更激烈的意见——大男子主义就是把女人当作玩物,或是低级的玩物如一般的约炮对象,或是高级的玩物如莲子,无论是高级还是低级,反正不是人。
但问题是,汪曾祺本来要的就是简单化。他写的不是小说,而是寓言,是童话,目的是“使人的感情得到滋润”。至于这故事会不会让一些人感到不满意,不滋润,这样的复杂问题似乎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 。这种简单化可能会让很多成年人读者感觉没劲。
汪曾祺排斥复杂,不要变化,他的人物一出场就是定型的,一成不变的。他的小说人物都是可爱的 。甚至连坏蛋也都有几分纯情与可爱(如《大淖记事》的保安队号兵的刘号长),不会真坏到哪里去。看到这样的坏人,读者难免要想,这世界上的坏人要是都这样就好了。情绪激烈的读者(也是读书更认真的读者)甚至可能想,这都写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胡扯呐。
***
说起可爱的人物,《受戒》中的两个人物小英子和明子可以算是典型——小英子的一家,明子的一家都是可爱的理想家庭,父母是理想的父母,长辈是理想的长辈,小英子的姐姐是很可爱的姐姐。情窦初开的小英子更成熟一些,更先进一些;明子是男孩子,相对糊涂一些,落后一些;小英子初次见到明子便一见钟情,开始追逐,明子只是懵懵懂懂地感受到富有心机的小英子的情谊:
“明子!我叫小英子!我们是邻居。我家挨着荸荠庵。——给你!”
小英子把吃剩的半个莲蓬扔给明海,小明子就剥开莲蓬壳,一颗一颗吃起来。
大伯一桨一桨地划着,只听见船桨拨水的声音:
“哗——许!哗——许!”(《受戒》)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当了小和尚、法名明海的明子也开始有了青春期的性意识萌发。在这里,汪曾祺的表达可谓巧妙绝妙之至:
(小英子)挎着一篮子荸荠回去了,在柔软的田埂上留了一串脚印。明海看着她的脚印,傻了。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明海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
顺便说一句,从文本细读的角度来看,“美丽的”这个形容词在这段精巧之至的话中应当说是赘词,蛇足,败笔,属于煞风景的社评(editorializing),是高中生写作文容易犯的错误。没有这个“美丽的”,这段文字会有力,更美丽,更完美,更动人。
中国老话说,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猴子嘴里也能掉枣;西方人说,荷马也有犯困的时候(Homer sometimes nods),意思是绝顶聪明和精巧的诗人也有败笔。汪曾祺有败笔一点也不奇怪。怕就怕学生错把败笔当妙笔,教师把败笔赞扬为妙笔。
***
上文说过,汪曾祺的小说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童话(fable)或寓言(parable);童话或寓言追求的是把纷纭复杂的事情、世情简单化,使人对至关重要的道理可以一目了然。在童话或寓言中,简单就是深刻,深刻就是简单。
还是以如今已经成为汪曾祺代表性作品的《受戒》为例。这个故事简单地说就是,女孩(女子)比男孩(男子)更懂事,更成熟,更善于掌管家计过日子。
读者可以预计,小英子和明子结婚成家之后,一定还是小英子当家做主,明子会言听计从;小英子那么聪明机灵,听她的话保准没错;因此他们两人的婚姻和家庭生活一定跟童话一样美满幸福。
与此同时,世界各国的许多脱贫研究则显示,从大量的统计结果来看,就家庭理财而言,女人确实是比男人相对精明很多;男人多倾向于不负责任,挥霍钱财,女人则多倾向于为家庭和子女的未来积蓄和筹划。
因此,读者可以说《受戒》如此展示或宣扬小英子作为一个女性的聪明机敏也是一种有益于世道人心,而且,汪曾祺的这种含而不露的劝善寓言还有成吨的社会科学研究结果的支持。
***
汪曾祺的小说实际不是小说,而是童话或寓言。他的小说的语言也像童话或寓言的语言一样纯净和简单。翻开汪曾祺的小说选集,闭着眼睛随便翻到任何一页,都可以看到他的可喜可爱的纯净和简单:
全县第一个大画家是季匋民,第一个鉴赏家是叶三。
叶三是个卖果子的。他这个卖果子的和别的卖果子的不一样。不是开铺子的,不是摆摊的,也不是挑着担子走街串巷的。他专给大宅门送果子。也就是给二三十家送。这些人家他走得很熟,看门的和狗都认识他。(《鉴赏家》)
汪曾祺的这种语言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但简单中含有一种诗意的张力、神秘、悬念。它看似很简单,很口语,好像小学生或中学生也可以轻松愉快地写出来。其实他这种语言一点不简单,而是充满玄机。这种语言需要写手有很敏锐的语感,很用心的反复推敲、精雕细琢。
换句话说,汪曾祺的语言看似纯天然,其实一点也不天然。就好象是优秀的演员看起来表演犹如天然本色,其实全是极端高超的技巧,是刻苦训练和练习的结果。细心的读者可以感觉到他对自己的语言的精心打磨。
对自己的语言,汪曾祺有高度的自觉。他说,“一般都把语言看作只是表现形式。语言不仅是形式,也是内容;” “语言和内容(思想)是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语言不只是载体,是本体。”
这些话不仅显示了汪曾祺对自己的语言的自觉,而且也显示了他对自己语言的自负。他这些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我所想定的语言表现是就是我眼中的最好的,是不可取代或更改的,改只能是改坏了。”
这种由千锤百炼而来的纯净简单跟法国小说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语言很相似。杜拉斯也是追求语言的纯净简单, 但截至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所有的中文翻译都把杜拉斯的语言都是拼命给杜拉斯添枝加叶,添油加醋,把原本是通顺流畅的原文弄得颠三倒四,啰里啰唆,完全没能反映出杜拉斯的纯净简单。
***
由此可知,这种看似简单的语言其实是非常微妙的高精尖艺术品。技艺不够高的人看不出高手的表面简单的语言所暗藏的玄机,玩不转这种细瓷器活儿,一出手就会把细瓷器给弄砸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在翻译中把杜拉斯的语言弄坏的人一定都读不懂汪曾祺的人。懂汪曾祺的人一定是能欣赏纯净简单文字的人,一定会痛恨给简单纯净的文字添加花头。作文学翻译的人必须要懂文学,给杜拉斯添枝加叶添油加醋的人一定都是不懂文学的人。不懂装懂必然坏事,不可能有第二种结果。
在这里,需要一点题外话说明。其实,严格地说,大多数好作家都对自己的语言十分注重和讲究。只有像巴尔扎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债务缠身、必须拼命写作赚钱的作家才会萝卜快了不洗泥,不会花多少功夫雕凿打磨自己的语言。
如此细读汪曾祺或其他中外文学作品难免会招致有人斥责为“吹毛求疵”。其实,这样的斥责者只是不懂装懂,装腔作势,附庸风雅,冒充内行。
因为他们不懂一个基本的重要道理,这就是,高明的绘画或瓷器的鉴定者之所以高明就在于他们能看出常人看不出的瑕疵;高明的读者之所以高明就在于他们能看出糊里糊涂的读者看不出的文字破绽。高明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必须通过刻苦的学习才能习得的。学会识别瑕疵是提升鉴赏力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
***
说起杜拉斯,汪曾祺跟杜拉斯还有一个明显的相似之处,这就是汪曾祺的小说文字多是很容易视觉化的文字。美籍俄罗斯裔的小说家和学者纳博科夫痛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语言粗糙拙劣,而且常常是无法视觉化(因此谈不上生动具体、栩栩如生)。汪曾祺的小说绝对没有这方面的毛病。
汪曾祺的小说语言常常富有高度诗意的形象或音像,像是黑泽明后期的短电影。在这方面,上文所例举的汪曾祺描写小英子和明子交往的段落是很好的例子。实际上,在汪曾祺的所有小说中,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比比皆是,数不胜数:
儿子最恨下雨。小学的同学几乎全部在下雨天都穿了胶鞋来上学,只有他穿了还是他父亲穿过的钉鞋。钉鞋很笨,很重,走起来还嘎啦嘎啦的响。他一进学校的大门,同学们就都朝他看,看他那双鞋。他闹了好多回。每回下雨,他就说:“我不去上学了!”妈都给他说好话:“明年,明年就买胶鞋。一定!”——“明年!您都说了几年了!”最后还是嘟着嘴,挟了一把补过的旧伞,走了。王瘦吾听见街石上儿子的钉鞋愤怒的声音,半天都没有说话。(《岁寒三友》)
汪曾祺的这些小说语言都很容易映像化。读汪曾祺的小说,读者需要像欣赏电影一样,欣赏他的文字所呈现的画面和画外音。
“王瘦吾听见街石上儿子的钉鞋愤怒的声音,半天都没有说话”。王瘦吾没有说话,但一切尽在不言中。这样的文字需要读者足够的细心、悉心才谈得上真正的理解和欣赏。否则,读他的小说就是牛听弹琴,马耳过东风了。
另外,“街石上儿子的钉鞋愤怒的声音” 这种说法所包含的修辞手法很有西方现代派文学写手的味道。
汪曾祺自承他的写作手法受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这种技法究竟有多少是源自中国传统文学语言,有多少是借鉴西方文学语言,眼下这方面的研究貌似还是空白,需要有人下一番研究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