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毅痛批张文宏,问题在哪里?

对舆情稍有留意的人大概都注意到了,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在自己公众号“饶议科学”上再三发文,连日来痛批传染病专家张文宏,可谓火力全开。
他为什么要骂张文宏?导火索是12月17日张文宏在2022年中美临床微生物学与感染病学高端论坛上表态:“我们即将走出这次疫情已成定局,这个趋势不会再逆转。”
这番话可能让普通人感到安心,但在饶毅看来,这是“不负责任的言论”,甚至“纯系谣言”,因为“今天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断定疫情走向,没有一个人可以排除疫情永远伴随人类、一年三次、每次轻重没有规律地摇摆”。
他奚落这是“科学不足,又不肯承认,而经常说错话”,“个人的科学训练和科学前沿敏感性不够而不知道”。

两天后,他更进一步将打击面扩大到了张文宏的支持者们,影射、挖苦张文宏缺乏专业水准,所说的话只不过是为公众提供了“一出几年不衰的心理按摩活报剧”,而他的支持者“力图将一位心理按摩者捧为神仙”,是“为造神而践踏原则、牺牲科学的伪君子”。
饶毅这一轮的猛攻,让许多人深感诧异乃至震惊,虽然学术观点的分歧是常有的事,但为何出以这样大字报风格的人身攻击,实在让人看不懂,以至于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不是“饶毅说得对吗”,而是“饶毅为什么要这么做”,甚至是“饶毅怎么变成这样了?”
他为何如此反感张文宏?张明扬认为,这本质上是派系争斗:“就科学谈科学,就医学谈医学,饶毅无疑是一名高水平,有预见性的科学家”,但他多次主张封控,“一直伪装自己没有既定立场,将自己的防控偏好‘隐藏’在对‘科学态度’的反复宣示中”,实际上是个“隐蔽的防疫爱好者”。
张文宏当然并不完美,并非批评不得,但有人发现,张文宏曾说了一些和主流专家“很不一致的观点”,但饶毅的批评是有选择性的,“很少去批评深受权力宠爱的学阀权力”。换言之,批评不是不可以,但不能有失公允,“张文宏的成绩你也要看到啊,何况,你也骂骂别人呢?”
这是中国社会旁观纠纷时常见的态度,尤其容易激发人们对弱者的同情——骂得太狠,“连我看不下去了”,言下之意,“虽然张文宏可能有毛病,但你骂的时候态度好一点啊!”
另一种颇具代表性的反应更为中立,强调的是公共讨论中应遵守基本的规则,就像押沙龙所谦称的那样,“我判断不出关于饶毅张文宏他们的是非对错,只是单纯不喜欢这样的骂街而已”。
也就是说,科学家好歹是“有身份的人”,至少在观点交流时应当绅士一点,饶毅看起来是“失态”了。更进一步说,不论观点如何,都应对事不对人,不必上升到人身攻击,对错没那么重要,应当允许不同的观点并存、交流,并尊重人们的自由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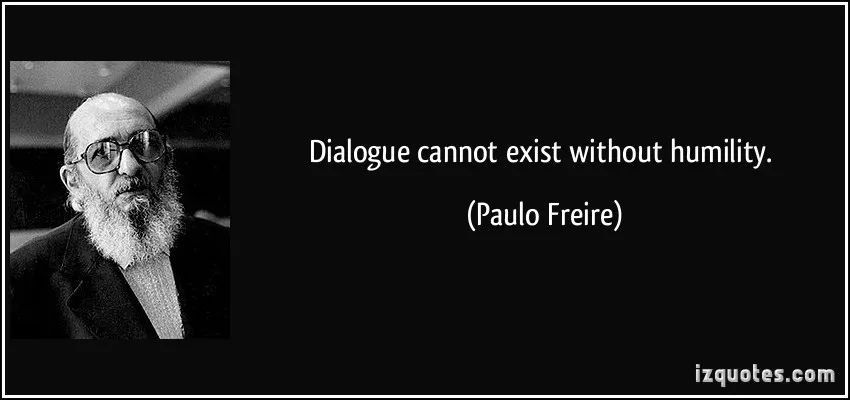
这些说法各有道理,但能说服饶毅及其支持者吗?我想是不能的。
争论中讲规则的前提是“所有观点都是平等的”,但对另一些人来说恰恰相反。林肯在面对南北战争的争论时曾对人慨叹:“你已经活了这么久,难道还不知道,对于同一个问题,两个人可以有完全不同但都正确的答案吗?”他这话肯定让许多人为之骇异,尤其我们中国人早就习惯了,每个问题都仅有唯一一个正确答案。
何况,就算政治、社会的问题有不同答案,但科学问题难道也这样?既然真理是唯一的,那么任何与之不一致的观点,就只能是错误、低劣乃至邪恶了。
这样一来,什么礼貌、规则就统统不是问题了,“态度好一点”不过是和稀泥,毕竟,对待错误的异端有什么好客气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对秉持错误观点的人心慈手软,只能意味着自己信念不坚定,还有动摇。就像中世纪的信徒对魔鬼、女巫的憎恶,在他们看来这完全不过分,黑的就是黑的,不然还要承认“魔鬼也有优点”?
在这种情况下,对手的妥协退让也无济于事,因为他再怎么样都是错的。饶毅三年来不止一次批张文宏,但张文宏似乎从未回应过,有些人认为仅此就可见张文宏的态度更可取,然而在饶毅的支持者看来,这只不过是他哑口无言罢了,甚至更可恶——以退为进来博取不明真相的公众同情。
事实上,不回应不过是“拒绝服从”的委婉表现,而在权威主义伦理学中,服从才是最大的善。只有一种行为能让你的过错得到宽恕,那就是真诚认罪,承认自己的错误,一如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弗洛姆在《为自己的人》中所说的:“即使一个人犯了罪,只要他接受惩罚并感到有罪,就会使他变善,因为这样,他就是承认了权威的优越性。”
对这样的心态,我再熟悉不过了,因为多年来,我在公共讨论中被无数人骂过。虽然我基本从不回骂,有些人赞为“辩风真好”,但另一些人则嗤之以鼻,理由很简单:你态度再好,也不能让你错误的观点变正确。最后的结果,是我在豆瓣上落下这样的名声:“维舟是好人,只是脑子不清楚。”
这就是关键所在:对这些自信找到了真理的人来说,宽容是不必要的,观点的正确与否才是至关重要的问题。那么,哪种观点才是不容置疑的真理呢?不好意思,恰好就是他本人所持有的那种。

这远不只是饶毅的问题。龚鹏程在《近代思潮与人物》中指出,“把批判对象视为恶,以自己代表善与正义”,乃是“近代知识分子权威人格的根源”。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蒋介石1927年说过的一句名言:“我就是革命,谁反对我,谁就是反革命。”
社会学研究也证实,在1960年代的城市中学里,“权威人格”是孩子们身上居支配地位的社会性格。对权威的顺从,和对异己群体的攻击,乃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因为他们不仅自信站在正确的一边,往往还抱有一种纠正“错误”的强烈使命感,为此,任何激烈的手段都是允许的。
很多人都说,饶毅可是科学家啊,他自己不也一直强调要讲科学?我的感觉是:饶毅对科学的理解是古典式的,那是一个圣殿,其中智者就像祭司,高踞在等级制的顶端,掌握着至高的权威,他说的话就是神谕。19世纪的圣西门主义就是这样,每个人都处于绝对完美的秩序之中,没有给自由地犯错留下任何余地。根据这种特殊的理解,“科学”乃是少数知识精英垄断的真理。
我不认识饶毅,但如果那些檄文确实是他本人写的,那么这就是文本所透露出的人格特质。当然,权威人格也不过是一种分类,我在意的也不是抨击饶毅,而是试图理解这种社会性格的普遍性,进而为当下的舆论提供一种解释:为什么饶毅们如此痛恨张文宏?又为何这么激烈?
答案或许是:在饶毅们看来,张文宏是假权威,是伪神,窃取了他们所看护的真理圣杯,这是最不可容忍的。这或许就是为什么饶毅一直盯着张文宏的“资格”不放,用他的话说,“绝大多数医生不是科学家,这是常识”,言下之意,科学家才掌握终极真理,而他本人当然是——张文宏讲的那些大白话,都是老百姓听了高兴的“心理按摩”,算什么学术成就?
饶毅曾被广泛视为具有理想主义的科学家,也因此,这次很多人惊讶他的表现,但对他来说,这恐怕并不矛盾。或许正是他在学术上的追求,使他更难容忍在他看来“不正确”的观点,助长了他对权威的认同,而这也与国内长久以来“专家治国”的理念契合——任何领域都离不开权威,能一锤定音地给出唯一正确的答案,而在他看来,张文宏没有这样的资格。
因此,谈什么不同观点、态度、规则,都无法从根本上驳倒他,那么他这么想的问题到底在哪里?
我想是,他对“科学”和“专业”的界定都太狭隘了。他可能太沉浸在自己所擅长的神经分子生物学领域,而用学术前沿、论文水平等科研标尺来衡量张文宏,就觉得他处处显得“科学不足”,不过是个“网红”罢了。很多人都不自觉地有这样的问题,我一位朋友曾将广受好评的散文家批得一无是处,我后来才意识到,她其实是用学术论文作为参照系来要求散文。
当张文宏判断“走出疫情已成定局”时,指的其实是这一轮高峰过后,我们终于可以告别三年来的防疫局面,生活逐步回归正常。这是公共卫生的视角,也是普通人能理解的话语。然而,饶毅说“没有一个人可以排除疫情永远伴随人类、一年三次、每次轻重没有规律地摇摆”时,所着眼的其实是病毒学的视角,浑然不顾张文宏再三说过“人类不可能消灭病毒”(那就意味着它随时可能重新出现)。视角的差异,使得他恐怕曲解对方都不自知。
他以病毒为中心,但忘记了在这样的公共卫生事件中,我们更要关心人的处境。在这里,他所遵循的是19世纪末出现的细菌理论范式,认为健康状况只是微生物层面的问题,然而,现在医学(尤其是公共医学)早已进入生物-心理-社会范式,需要全社会改变认知模式,协调各种资源,才能应对这一重大挑战。
饶毅看不起张文宏的学术能力、专业水准,就分子生物学的科研成就来衡量,这应无疑义,但如果从全新的范式来看,那么他所蔑视的“网红”和“心理按摩者”张文宏,在改变社会认知等方面,不夸张地说居功至伟,比他本人起到的作用大多了。承认这一点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如果说饶毅傲慢,那么他就傲慢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