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起度过这艰难的一年

2022年就要过去了,但我想,很多人恐怕都不愿意回顾这一年,只想它快点过去。这是中国人对待痛苦经历的惯常方式:不去想它,又或像是处理烂掉的苹果,彷佛只有那些愉快的记忆才值得保存下来,不然难道还留着过年?
我理解这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种需要,甚至是他们的生存之道,很多时候,“不能忘记”就是内心痛苦的根源,并不是谁都能承受,但那一片平滑的虚假记忆,实际上并不总能宽慰我们的内心。
不论如何,我们无法逃避这样的质问:穿过了暴风雨之后,我们已不再是原先的自己,而失去了身后那些废墟,我们也就失去了真实的过往。
6月里上海解封后,我到一位朋友家里做客,他说那段时间已经彻底想通了,无悲无喜,即便重获自由也没什么可高兴的:“你看电影里,集中营被解放的时候,没人笑的,都失魂落魄——我现在就这种感觉。”
这并不只是他一个人的感受,许多人和我谈到封控前后的生活时,我总隐隐觉得,他们似乎找不到合适的话语来叙述,内心有复杂难言的种种情绪,但到了嘴边却不知道怎么形容,以至于有时被误认为是无话可说。
沉默未必是没有话,有时正是因为有太多话无从说起,就像布莱希特笔下的1940年:
这是人们会说起的一年。
这是人们说起就沉默的一年。
老人看着年轻人死去。
傻瓜看着聪明人死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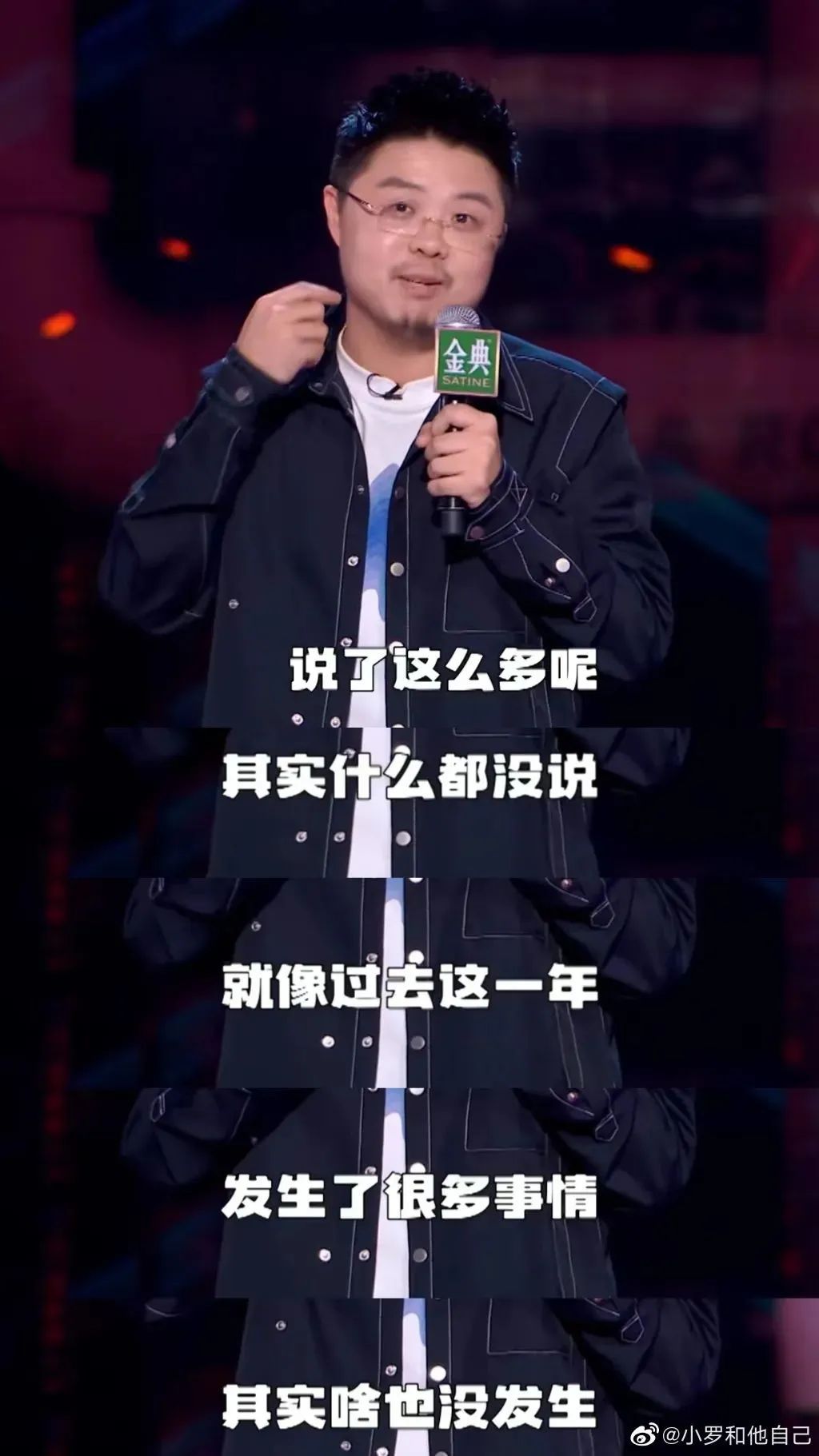
毫无疑问,就像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年份一样,在若干年后(甚至可能都不需要等到若干年后),2022年所发生的一切都会被纳入历史的宏大书写之中,但我也注意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不关心那些宏大叙事了,那似乎和自己的切身经历没多大关系,说不出的脱节、怪异、荒诞,有时甚至恐怖。
在那样一个舞台上,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没机会成为主角,有时甚至可能在背景里都看不见。好莱坞史上第一位华人影星黄柳霜曾说,她的墓志铭应该是“我死过上千回(I died a thousand deaths)”——因为她总是扮演边缘性的配角,被编剧潦草地写死。
初看时只觉得这话既心酸又好笑,现在我意识到,我们在人生中所轮到出演的,极大概率也就是这样小人物的命运。即便卑微如尘土,但这才是我们真实拥有的东西。
一位年轻朋友日前和我说,放开之后仍然觉得生活回归得好恍惚,前方的自由与幸福存疑,已经度过的三载阴霾却十分真切,知道有些事随时可以再来,也因此,他终于放下了宏大叙事的情怀,家国大事不需要自己操心,“日常的公平正义、明天更好还是更坏,只关心这些了。”
也是在这一年里,经历了封城又放开的种种事件,让我空前真实地意识到,生命其实是无比脆弱的,你意想不到的一点风险,就可能夺走一条人命。他们似乎只是被时代的大浪捎带着扫到,但却永远回不来了。
契诃夫曾在小说《海鸥》里写到妮娜的命运:她“像海鸥那样的幸福和自由”,“一个人偶然走来,看见了它,因为无事可做,就毁灭了它。”我们所以为的幸福和自由也是如此:它可能随随便便就被人碾碎了,而直到此时,我们才赫然发现自己赤手空拳。

在这一年里,我比以往更清楚地意识到,以往那个被宽阔的道路和闪闪发光的霓虹灯所点缀起来的文明生活,其实是相当易碎的,有很多深不可测的力量就在我们的脚底下涌动,而我们除了彼此联结、努力面对,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去应对这些,甚至哪怕我们自愿拱手交出,也不见得能就此幸免。
这诚然是痛苦的经历,但它可能也有一个意外的好处,那就是赋予了14亿人共同经历。感染是随机的,这种不确定的风险尽管可怕,但也意味着谁都可能轮上,轮到自己就知道那是什么滋味了,才明白“自由”和“权利”的可贵——这种大规模的启蒙,是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喊破嗓子都做不到的。我有些朋友甚至激进地主张,只有先轮流封一遍,才能建立新的社会共识。
当然,即便这样可能也乐观了。每个地方、每个人都有千差万别的处境,并不是轮到自己了就能产生共情和共识,有时反倒是幸灾乐祸,否则就不叫“一盘散沙”了。
武汉封城时,许多人都曾愤怒,但今年看到西安、上海封城,这些人反倒庆幸了:“我当初不该抱怨,相比起来,我们那会都好多了。”正因此,那种“感谢上海发声,我们自己发不出声音”的观点,已经相当难能可贵了。
改变当然很难,但终究还是有一些改变的。一位亲历了今冬北京疫情的读者向我感慨说,这期间看到了“群”的作用:
无论是邻里社区群、朋友群、家庭群,大家都在分享信息(虽然不一定准确),分享药物,分享个人得病后的体验。这些自发的行为,我觉得比任何宣讲都更有用,也让我觉得这些民间的自发力量其实是很强大的。普通人在这个过程中,总会找到正确方向的。

这也是我在上海封城时所感受到的:为了能活下去,社群被迫恢复了自我救济功能,平日里甚至很少往来的邻居,都在相互支撑、彼此分享。我们所陷入的这一处境,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做错了什么,有时看起来几乎像命运一样非理性且荒诞,但在这与他人联结的过程中,本身也让我们找到意义和慰藉。你并不孤单。
疫情之下,我最大的感触这一是,在国内的环境底下,哪怕是一些基本的东西,都需要拼力去争取(还不一定能得到),这几乎耗尽了我们的精力。也因此,今年我重新认识到一点:“勇气”可能比我之前所认为的更重要。
对孤立的个体来说,要做到这一点太难了,但我们或许可以用微弱的光照亮彼此。有位朋友说,这一年对她来说是无比郁闷的一年,谢谢我的文章,“像黑暗中的光亮给我慰藉”。还有一位住在河南乡下的读者,前一阵给我寄了自家的土产,他说,“这一年是我开眼看世界的一年”,而我写的,就是通向外部世界的出口之一。
今年对我来说也很难,公众号大小号都被封半年,至于豆瓣,先是被封半年,放出来讲了没两个月,又被封一整年,不过朋友的一番话宽慰到了我:“凡是讨论疫情又没有封号风险的文章,都是不值得看的。”
我在这一年里的记录有多大价值,说实话我自己也不确定,只是我早已习惯了:即便是感到写不下去的时候,也要继续写,对我这样的记录者来说,“我写故我在”。如果它能成为一个渠道、一个平台,让你们找到彼此,那就更好了。
不要忘记2022年。不要忘记我们彼此。也不要忘记经历了这一年后重新发现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