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露營
A告訴我這件事,西九龍M+可以露營。他是從捷克來環遊世界,旅居香港三年的吉他手。也許你能在街頭看見他。他有幾個偏愛的地點,例如,佐敦寶靈街地鐵站口,旺角豆豉街一號,銅鑼灣某個街角,深水埗福華街附近。我是在寶靈街遇到他的。第三次見到他時,他把一些行李放在我家。由於沒有固定住所,據他所說,這樣的根據點有四個。
“我覺得這樣不好。”有次他說。“東西過於分散了。”
“沒什麽問題啊。只要你能記清楚,安排得來。”我說。
那段時間我常搬家。他也跟著我掃蕩了深水埗。並嘗試在擁擠的,“看起來不懂得欣賞音樂”的深水埗居民占據的街道上彈吉他,有一次跟一位鼓手即興演奏,當時我也在場。那段時間,他幾乎每天晚上在那個地方彈吉他。他驚訝地發現,“有一些人會停下來認真聽。這並不常見。”

A彈吉他時很專注,並不會擡頭看周圍。而他卻總是能清晰地反饋,比如挑選場地的原因是由於燈光或舞台效應,身旁人的反應,附近是否有流浪漢。看見流浪漢令他傷心。
“我嘗試和ta們聊天。”
有一次午夜時分,我們從深水埗一間麥當勞出來,遇到一個流浪漢。身著黑衣,食指和中指間夾著一只撿來的煙頭,問我們借火。A認出了他,說是一個朋友,還向我講述之前如何給他錢買地鐵票卻發現是花招的事。


有一次在重慶大廈門口,我們遇到了一個“瘋癲的”中國女人。是他住在重慶大廈時認識的。四十歲左右。身著長裙,很有東南亞風情,會說幾句英語,說完一句話總是完成一個舞蹈動作。有時甚至邊跳邊唱地講話。我本以為他說這是個“Crazy Lady”,就此完了。不料A讓我做翻譯,問她在這里做什麽,有沒有錢生活,什麽時候回家,之類的事。她曾邀請A和她共進晚餐。
我問了這些問題。那個女人說,現在沒有錢,家里有很多錢,但是現在回不去,沒有通關,沒有工作。還問我是不是A的wife。仍然,邊說邊跳舞。花裙子擺動著,直到我們離開,舞蹈還在她的前路上繼續進行。
去西九龍露營是在一個周日晚上。當時我已經住進了上環的F書店,書店老板答應我暫住在書店的地板上,提供瑜伽墊,並把我和我的行李從深水埗接到了他店里。那時我偶爾去書店當義工,和進來的客人聊天。有的是從小閱覽群書的銀行家,有的人手上時尚的表是撿來的,有的人的父親是英治時的督察長官。
我們計劃露營已經有一段時間了。當晚A起先沒有帶露營的裝備,我和他去重慶大廈一個根據地拿。
“根據地”在九樓,我在八樓樓梯口等。那里有蟑螂。當我看到旺角深夜街道上四處橫行的蟑螂而心驚時,A說不要怕。“why? why fea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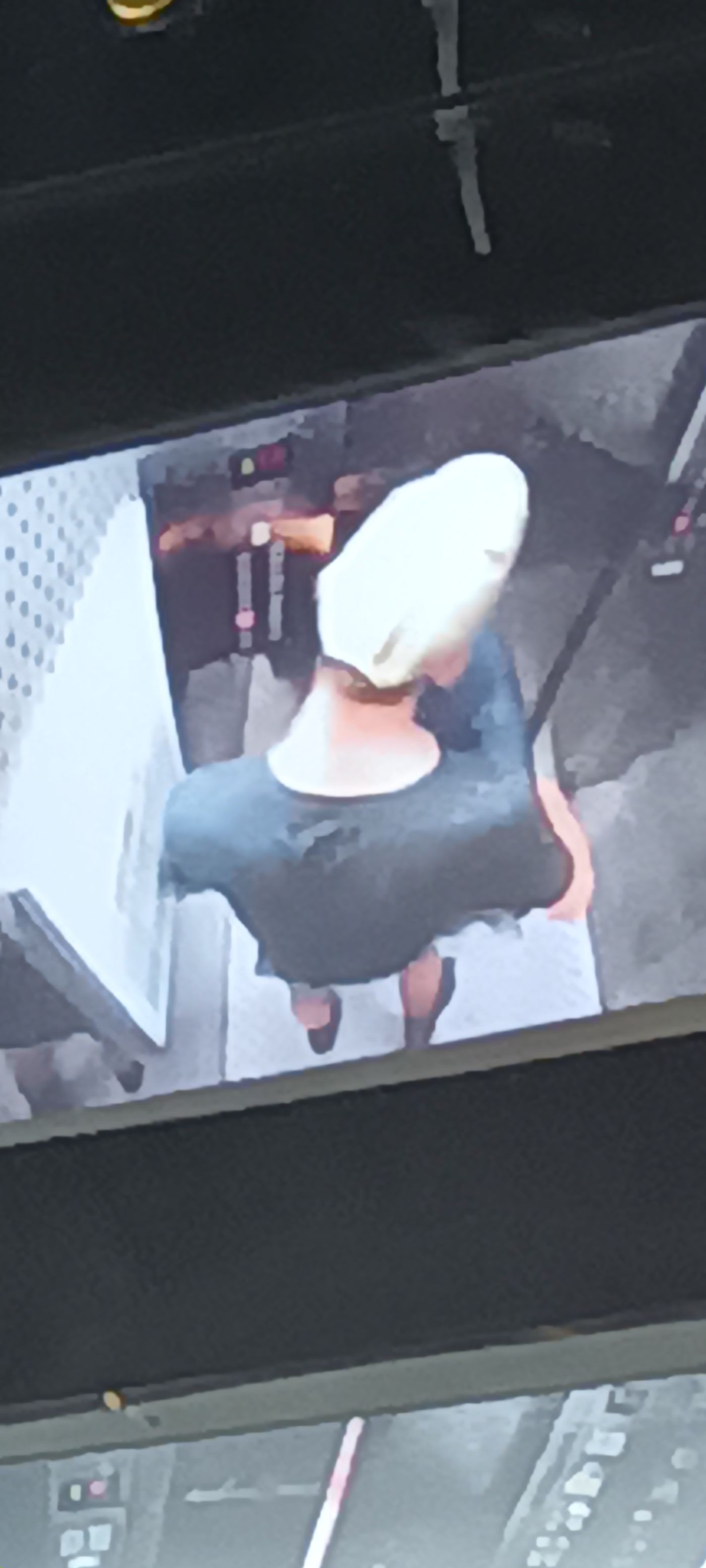
住在深水埗的時候,是在劏房里。室友們有的是沒有work visa的大陸來的打工族,有些人的姐姐已經被關起來十個月了。
有個姐姐,今年五十多歲了,我們叫她miaomiao。那段時間,她和我都沒有工作,我們常一起聊天。她從小來自一個大家庭,做過幼兒園老師,也做過塔羅牌店助手,玩過攝影。年輕時個性內向,長相酷似梅艷芳。現在五十多歲了,等著政府派公屋養老。
她的床頭上掛滿了觀音,寶珠,水晶。有一次,她微笑著,睜著圓溜溜的眼在廚房門口望我,說,“看看,好看嗎?”手里拿著一串紅櫻桃項鏈。
一番交流後,她送給了我一串閃熠熠的十字架項鏈,一串米老鼠手鏈。手鏈上有Disney的標簽。
我每次戴上其中任何一條都會給她看。我們像親人摯友一般。聊她的戀愛往事,交友準則,曾經輝煌的時代。
“當時每個人都好開心,好勤奮。”她總是張著大眼睛,撅著嘴巴說。
她卻很介意A進到屋里,因為很大一部分公共空間塞滿了床鋪,且僅限女士出入。
她會在我天黑後出門說“小心被強奸。”也很害怕公園,“都是些怪大叔,各種神神叨叨的人。”
也警惕我“小心被巴基斯坦印度男人纏上。”
也有些住客搬走了。她總是抱怨同房下鋪的女人“放屁”,還有“誰在洗澡時撒尿,衛生間一股尿味。”
她的這些反饋使得另一個住戶想起曾經有一個人“對著洗衣機出水管的下水道撒尿。”
後來這位意見很多,且情緒化的住客搬走了。房東說她曾在精神病院待過。這個消息在劏房里流傳了幾天。



在西九龍露營那天晚上。我們遇到了保安。保安拿著手電筒四處照。我有些緊張,因為帳篷有一個透明的窗,我只穿了上衣和內褲。A告訴我不要理會ta。那天有很多蚊子。到了天亮的時候,我決定不再嘗試入睡。手機只剩很少的電,我去找過海巴士,回到中環上班。
後來我們因過剩的情緒導致關系不融洽而減少了見面次數。他將注意力轉移到自己身上,也建議我這樣做。我辭掉了工作,離開香港,回到中國大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