歪脑|吕频:被挫败的女权运动如何催生出新一代“白纸革命”者
本文作者为女权活动家吕频,首发于歪脑:《吕频:被挫败的女权运动如何催生出新一代”白纸革命“者》,此处为全文转载。

“白纸革命”像一道闪电,撕裂至暗,是多么惊人尖锐,而又短暂和脆弱。我感恩被它照耀,惭愧于自己不是它的一员,没有为它付出代价。因此我才有了奢侈,从运动的风潮期到报复性的镇压仍在扩大之时,一直在孤僻中思忖,想把握运动所打开的社会变化的不确定性。把他人的投身和受难当作搭建或解开谜题的素材是冷酷的,我原谅自己是因为我有所心系,而这种追寻将导向我也更新自己的政治性决定。我想辩论的是以下问题:“白纸革命”与中国女权运动的联系,它如何标识女权运动的一个重要的阶段性,以及在“白纸革命”后时代中女权运动的可能性。
女权运动在其失去势能之时却催生出了新一代的革命者
没有人能拼出白纸运动的全貌,因为大多数参与者隐藏和面目不清,即使认识其中一些人,他们能分享的也只是片段的见证。在运动可靠和充分地被参与者首要定义之前,其他人对运动做出全称判断是僭越的。当然,有种种迹象——包括众所周知的在北京被捕的那些女生的事迹,提示女性在其中的突出的比例和领导力,以及她们与女权主义的联系。总之,不要标签这个运动,有价值的是讨论女性的身份和女权主义怎么促使一些人站到这个运动的前沿。
今天中国性别问题的主要矛盾在于女性——包括各年龄段和阶级——比任何时候都更强大、独立和有自尊,而国家和社会仍然固执地想让她们停留在从属的位置上,拒绝为她们的劳动贡献支付公平对价。因此女权主义才有了土壤,并且代表女性站在冲突的前沿。女性和女权主义的成长与经济发展同步,现代化对“高素质”女性劳动力的需求的另一面是制造了父权制的新一代反抗者。女权主义的资源和空间一直都很有限,直到互联网带起大众化。这不仅指借助网络能触及到广泛的人群,令理念普及,还指互联网让女权主义与中国女性的日常生活接轨,展开一个颠覆性别不平等正常化的大型话语工程,为种种无以名状的女性困境,发展了过于犀利的批判性解释和反抗策略合集,让许多人从中找到自己。网络也制造了许多激烈而影响广大的辩题,让女性在一次次激越的为性别而战中强化认同。
短短十年中,或许数以百万计的女性认同了女权主义,构建了超越现实桎梏的扩展性的社群,更有力地与父权制作她们个人的搏斗。尽管也存在粉红女权和商业女权的维度,但中国女权者公认的画像基调是日常愤怒不平,这在如此威权加剧的时代是非常特殊的。主要由于被这些女性的战斗力所震撼,社会已经被迫承认女权问题很重要,尽管它所做出的回应往往是反动的。

在2015年以后,行动主义——致力于促进社会改变的女权取向,尤其是有组织有策略的——持续被犯罪化。2015年3月的“女权五姐妹”事件只是一个信号,此后犯罪化的主要表现不是刑事打击,而是对组织者和活动的持续骚扰、威胁和阻止。配合的是针对“寻衅滋事”和“境外NGO”的法律,将女权组织化的资源和策略打入非法。另一方面,行动主义的论述在女权社群中也越来越被降权重,竞争不过那些更能操作情绪的博主。根源上是因为,威权不断规训了女权主义的边界,让人们意识到愤怒也有合法或不合法的形态,也引流了她们消耗愤怒的渠道。
在2018到2020年,行动主义者已经无力设置女权议程,但仍然能通过她们对舆论的把握和职业化操作,从地下策动地上,将一些已经浮现的焦点关切转化成有规模的动员和倡导。2020年12月,弦子诉朱军性骚扰案一审开庭招致数百人庭外聚集,这是一桩惊人盛事,昭告女权和“米兔“的动员力。在这年代,敢于站出来、身体在场的人是如此罕见,而给她们做行动练习的机会也很少,这些人就是下一次最可能会出现的人。不过,这一年有最多流量的是在年底达到顶点的“性别对立”现象,它显示网络女权的主流被与反女权男性网民的骂战所牵扯,看似激亢的对峙背后,是默认国家责任——“房间里的大象”的不可言说和对行动改变路径的失望。
中国的当代女权运动其实一直守在一个不去触碰政治——政权合法性的界限内。它的起源是一群有正义感的体制内学者关心在改革开放中被剥夺的底层女性,希望通过协商而非施压的方式来促进法律资源对女性的释放,及执法者态度与行为的改变。当学者重新回到体制,运动被NGO——一个如今已经在中国近乎消失的行业——短暂接管和转向面对大众的策略性动员,然后在大众化时代成为青年城市女性寄托怨愤的载体。在这个过程里,运动确实选择性地增强了对体制的批判和挑战,但始终主张的是女性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路径则是在承认国家权力的前提下,以法治为杠杆的性别平等改变。运动从未放弃协商,尽管为了开启协商而不得不施压。当然运动中的人有个人的观点,然而这不意味着他们能将其注入到运动当中。
既然绝大多数参与者是带着想消除身边性别不平等的感性愿望而来,而绝非政治反对,这就决定了运动中沟通的主流。但更深层的其实是,人们共识了合法性边界内的活动,期望通过尽用有限空间而争取女性权利,当然前提是仍有空间。在意识到国家对性别平等的承诺并不可追究之后,女权主义者仍然坚持留在政治的中间地带,因为她们认为这能最大化她们的运动并更符合女性的当前利益。
问题在于法治讨论和改革的空间不断被关闭,民意也日益失去撬动改变的功能。例子之一是2021年年初民法典出台设置“离婚冷静期”,罔顾女性网民对离婚自由和家庭暴力问题的强烈担忧,立法者岿然不动,声称“不必过度解读、应正确看待”云云。在中间地带被缩减的大趋势下,女权主义者逐渐失去政治安全区,更进一步暴露在有组织的政治污名运动中,被谥为“敌对势力”、“网络毒瘤”等等。
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许多其他运动都被镇压,不再具有大众能见度,包括人权律师和劳工运动。而女权运动中为刑事迫害所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运动的规模甚至还一直在逆势扩大,尽管一定要首先归因于无数女权主义者的忠诚勇敢智慧,但终究还是因为运动没有失去正当性。
就运动的成果而言,它确实极大地改变了无数参与者自身,它也强有力地冲撞了社会,并且改变了和女性权利有关的公共讨论的版图。然而,事实证明,它没有能力改变国家,或者更细致地说,如果将国家的改变区分为实质、程序和结构三个维度,实质性的改变有——考虑到一些个案的解决和一些局部的法律和政策的改变,而程序和结构的改变则基本没有,而且还越来越不可能,随着运动本身被剥夺正当性和被反向运动所耗竭,更是因为这个国家的大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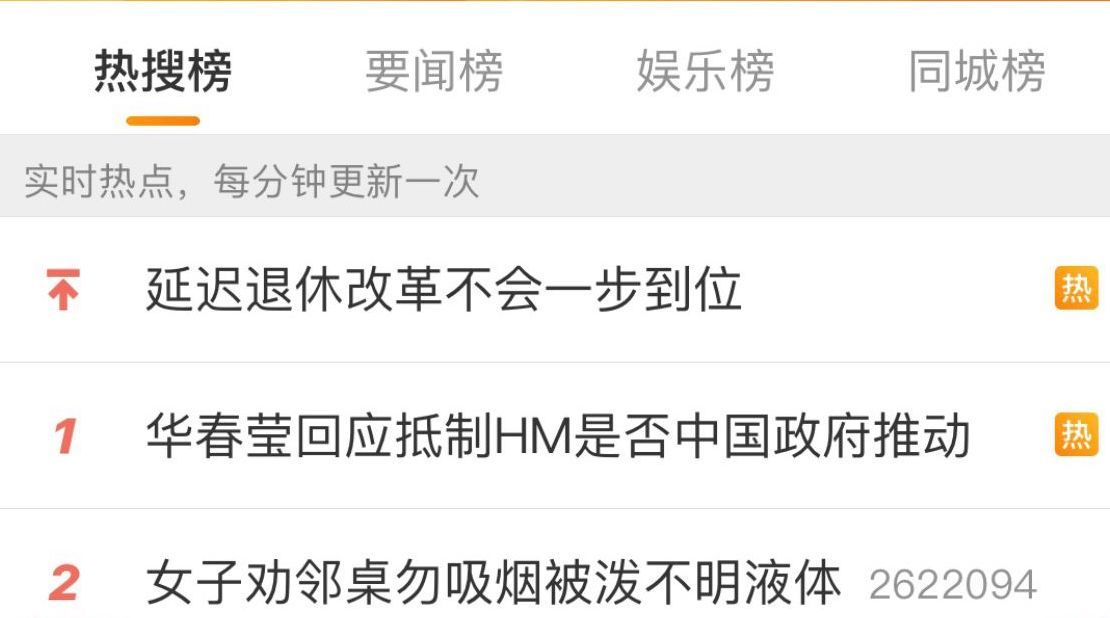
2021-2022年女权运动进入一个特别艰难的阶段。2021年4月,因一起偶然事件引发的对女权主义者的大规模网暴,对处在风暴中心的少数女权行动主义者来说,后果远不仅是失去了网络账号,而是她们被迫沉寂离开运动前沿。大众所不知的是,警察深入介入了这一事件,并且沿着网络暴力指引的线索,部署了严厉而漫长的监控。事件还在女权主义者当中制造了广泛的恐惧,导致社群活动进一步缩减、保密和相互孤立。今天如果一个人没有机会进入深层的女权社群,在公开互联网上已经很难找到女权社群活动的信息了。
2022年1月徐州丰县“铁链女”震惊了整个中国,然而从女权的角度看,这一事件是巨大的挫败——真相始终未明,“铁链女”被变相囚禁,除了几个小人物被示众性地惩罚之外,性别暴力的系统性不受追究。乌衣的被捕令女权社群创痛,所释放出的信息是:没有组织化背景和经历的个人行动者如今也被刑事迫害。以及,警察的骚扰和威胁扩展到许多“普通”的女权主义者,因为她们试图发起小小的抗议,甚至只因为发朋友圈。当有经验的组织者退出之后,“普通”的女权主义者承担起责任而又遭遇清除,我甚至悲观地认为,类似“铁链女”事件的最大的效应是将被激发的抗争者一重重暴露在威权面前,而最终实际加强了统治的稳定。
2022年8月,弦子诉朱军性骚扰案二审开庭,距2020年12月一审开庭只有一年半,数百人聚集法院门前的盛况不再,不是因为人们不想去支持弦子,而是没办法组织也很少有人能到场。弦子案的最终败诉是又一味苦涩,象征着“米兔”运动最终还是敲不开法治的大门。在过去几年里,像弦子这样的当事人,她们将抗争经历贡献出来,代替被迫低调的活动家而成为运动的枢纽,然而她们也因败诉、网暴、禁言……而节节淡出了。
在这一年,我作为组织者的业务前所未有地寡淡,而且我也几乎停止了对运动的公开讨论,一种黑暗的感觉萦绕不去,不知道女权运动还能往何处去,虽然它仍拥有那么广大的社群,却不再有机会和可行的路径。当“二十大”即将召开,我觉得恶心……

另一方面,很快就证明至关重要的是,女权在这一年的挫败促成了许多人的终极觉醒。其实在技术上,也和短视频的直观冲击性有关,徐州“铁链女”和唐山打人事件创造令万千女性一起经历了“道德冲击”的时刻。所谓“道德冲击”,指人恍然意识到自己被不公正对待而重新认知世界。女性被远程唤起的不止是同情义愤,而是性别命运深处的恐惧和绝望:我也将和她们一样被如此残酷对待,而国家原来不会保护我。这些人意识到了与所生所爱的国家之间并无契约;或者说,在内心深处,她们的自我认知走向和宰制性的意识形态的决裂。
人们记述了她们在这个过程中的自我挣扎甚至危机,因为在宰制之外,渺小的个人极难找到立足点。就这种状态而言,“政治抑郁”其实只是一个可说出来的词汇。从这种状态而走向“白纸革命”的人,只能是少数中的少数,她们升华了在女权运动中积累的愤怒,并且完成了足够程度的自我政治化。回顾以上历史,最令人感慨的是,女权运动在其失去势能之时却催生出了新一代的革命者。
“白纸革命”何以成为可能以及它所开启的可能性

“白纸革命”让我从消沉中惊起,至今我还在体会从中学习到了什么。首先我重新意识到那个最基本的事实:社会永远不会死亡,没有人是百分百的服从者,人们永远都在寻求反抗。每个人都心怀恐惧,被以往的镇压所教训,这并不可耻。然而人们心中仍有不会被威权穿透的领地,即使他们表面上服从沉默,随波逐流。这当然和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是这个政权的持份者及被其绑架有关系,中国中产阶级的困难就在于依赖体制所分配的资源,而家庭将维稳延伸渗透到无可逃的私人领域。
不过体制的捆绑是有差序的,而且不以单一标准。那些受过高等教育,在大城市独立生活工作,不在体制内就业,不像草根阶级那样为基本生计所困,又没有“软肋”的“最后一代”,是最自由的原子。原子寻求他们的栖居,人们不断退守,当那些更具有公共性的活动被太多叫停,政府又开始监控小规模的读书会、放映会……于是更进一步,私人的聚会,另类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就成了政治化的载体,而这些载体更隐蔽,不容易被穿透。当然这不能一概而论,我的意思是,这个社会将永远有相对自由的原子和他们的组合及其迭代,而这就意味着国家永远无法安于它的全能。
“清零”政策的一个致命错误在于,它没有对各群体分而治之和有张有弛,而是将绝大多数人几乎无差别地压制到一个极端状态,无论他们是外卖员还是白领,这就制造了所谓“大数”危机,即潜在反抗的基本盘很大,而且各群体因有相通的诉求而可以呼应起来。“白纸革命”也很明显地表现出执政已经失去自我调整和协商改变的可能性。上街是最后的决定,然而人们总会被逼到一个时间点,除了上街之外别无选择。
学者们说,并非压迫深重才有反抗,相反,是哪里有机会才有反抗。白纸运动确实发生在宣布放松的“新十条”出台之后,然而实际的执行却是收紧的,这种状态刺破了人们最后的耐心。不过对“白纸革命”来说动力主要并非来自被识别出来的机会,而是另外两个因素:无法再继续承担的不行动的损失,以及正义感,几乎是注定地,一场发生在大城市的人祸触发了这两点。

彭载舟在四通桥的行动惊天动地,当时我却以为他只是孤胆英雄,而那些在厕所里张贴他的口号的人也过于分散了。事后看来,没有孤立的行动就没有最后形成联结,虽然遗憾的是中国从来不缺少彭载舟那样的先锋,但只有他一个人被看见和被响应了。其实一切都是因为人不是吗?国家已经可以做到广泛而深入地监控全社会,可以锁定每个人,并且将红线前移到威胁发生之前,预警和提前扑灭。那为什么在大城市的中心还能爆发几十年未有的抗议?
第一,有经验的组织者已经被识别出来和被盯死,站出来的新一代却还没有。第二,人们已经学到了要使用墙外联络工具,对这些工具上的通讯监控只能依靠人工渗透,导致反应速度比数字化监控微信要慢得太多。第三,关键在于速度和规模这两个参数的乘积,即,只要能在足够短的时间内聚集到足够多的人,就能突破警戒,只要有不需太多交流的共识作为基础。再次强调,这样的突破是罕见的,其参与者也只是少数中的少数,然而全面镇压在让反抗变得特别艰难的时候,另一方面也让反抗引起统治危机的门槛变低,几百人、几千人和一些白纸就足够,这可以说是威权统治的悖论之一。
以往地方政府总是被设置为执政的背锅侠,而在"定于一尊"的制度之下,所有人看清了,"清零"是所有人服从一人的意志,因此“白纸革命”也共识是对那个人的直接挑战。虽然总是捕捉任何不安的痕迹,“二十大”的顺利举行让我以为中国将进入一个超稳定极权时代。但他原来没那么强大——这是一个极大的泄密。他不敢拿他的权力冒险。
华尔街日报说习近平看了亮马桥抗议的视频就决定放开“清零”,这和习在与其他国家领导人的谈话中提到放开是因为“年轻人”不能忍受相一致。我再次确认了行动者应有的信仰:一切皆有可能。以及,要给予行动足够的承认,虽然事后分析放开“清零”有经济因素,有疫情已然失控的考量,但不可否认,而且最珍贵的是,有一些人付出了行动才真正让改变发生。
改变根本没有发生在制度层面,这当然不是抗议者的错,但或许也告诉我们,激情革命的效应有限。客观来说,“白纸革命”像给一个已经卡住不动的系统按下了强行重启键,当这个系统重新运作起来,它甚至还轻便了一些,而且还再次清除了一些异议的威胁。报复性刑事迫害的程序是如此“合规”,几乎到了荒谬的程度,显示抗议作为异常之事,正在被威权的日常化运作所从容吸收。时间流逝街市太平,在狱中的人将被遗忘了吗?甚至从未为人所知,在监狱之外的参与者吞咽着恐惧。
几十年来,一代代人的牺牲都被绞进这个制度,我们还有什么正当性去鼓励年轻人勇敢呢?我其实一直是一个爆发性革命的怀疑者,尽管我敬重“白纸革命”的参与者,但革命本身的意义在我看来主要是某种指示器,指示的是:策略终结了,此外其他一切行动的可能终结了。但革命本身又是无法策略化和筹备的,而鼓吹革命是不道德的。仍然接受革命所给的教育,但拒绝就这样对中国的未来预言,我还是想回到自己的初心,设想女权主义可承担的责任。
女权主义在“后白纸革命时代”的承担

我想赞美那些维持运动的哪怕菲薄的努力。当运动不断一层层被解散,它的承载就落在那些最微小的单元上。人们仍然在努力连接,并且为运动做功。我看到许多匿名的女权主义者创建了个人或者伙伴的项目,往往是非常有创意的。可能她们还没有来得及壮大就被消失或者耗尽了,但这些项目的层出不穷在今天是运动主要的底层形态。如果运动不能总是波澜壮阔,那我接受它很多时候是暗流和地火,最重要的是能否始终接触到人,并且为人维持着空间。既然统治者所致力的就是让人们分离和相互不信任,那么,所有能够为社群创造社会资本的情感劳动就带有抗争性。而且这些连接维持着身心的健康,这非常重要——最终人们拼的就是能否有力气和长命,坚持下去。
我还想赞美女性不婚不育的集体决定,从它为社会变化准备着更多女性参与者的角度。不婚不育是女性的消极抵抗和非暴力不合作,当她们意识到这个制度不允许协商。在这个意义上,她们确实已经创造了这个国家可能最主要的危机,一个人口负增长的国家还能拥有大国霸业吗?但这个危机本身并不需要庆祝,我的关注首先在于它证明了女性和女权的强大,在这无限封杀的年代,在社会运动退潮之后,女权主义还可以用不婚不育来建立战线和显示它对女性的影响力。而更具有深远意义的,是不婚不育将从父权结构的底层——家庭和日常生活中解放女性被束缚的身体、时间、头脑……有更多女性将因此成为自由的原子,长远看来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趋势。
我寄希望于“白纸革命”能激活女权主义的思想更新。非常遗憾的是在这么大的社群中,却似乎已经看不到什么能激发思辨的讨论,缺少实践就缺少灵感,迫害让人们自我防御和抱团取暖,审查让人们无法畅所欲言。其实女权主义是可以只支持简单的思维逻辑,并且形成思想闭环的。然而,作为一种思想武器,女权主义的魅力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尖锐透辟的批判视角加配套的术语,之后还要进一步将其自身复杂化。
我不想做只用一套话术以不变应万变的偷懒的人,尤其渴望发展女权主义的这样的功能:为这个国家最重要的问题提供解释。“白纸革命”就是打破了思想的闭环不是吗?在这个暴力和不知希望何在的时代,我会坚持自己的信仰,但更想走出去。我意识到“白纸革命”所留下的命题是巨大的不确定性,在此刻的感受远远好过觉得一切注定,但不知前路何在的感觉是惶恐的。我想去拥抱它,并且仍然寄希望于女权主义的指引。
正值三八妇女节之际,分享两个社群活动,转载自:
Instagram: Chinesequeerswillnotbecensored
Twitter: 女的合作社 & Chinesequeerswillnotbecensored
【3.8 声援白纸运动被捕女青年活动】
活动一:【照片100·声援白纸运动被捕姐妹】

三八国际妇女节即将来临,中国的一些年轻女性因参与“白纸运动”的和平抗议仍在遭遇政治迫害,包括已知仍在押的行动者李思琪、李元婧、翟登蕊、曹芷馨。她们已被关押在看守所超过70天。在庆祝妇女运动成就的同时,我们需要记住那些为争取权利而失去自由的姐妹,并为她们发声。因此,我们希望征集100张线下声援照片,为被捕女性发声。
参与方式:
①打印支持海报,参与妇女节相关线下集会/游行,并拍照上传至社交媒体。
②在你希望的任何地点,手持声援海报或标语拍照(可不露脸)表达支持。
照片可注明拍摄地,并附上想说的话,投稿至以下平台:
Instagram @Chinesequeerswillnotbecensored
或 Twitter @女的合作社
海报资料包:https://tinyurl.com/freeprotesters
活动二:3·8联署 声援中国白纸运动被捕女青年

中国的一些年轻女性因参与“白纸运动”的和平抗议而遭遇政治迫害,包括已知仍在押的行动者李思琪、李元婧、翟登蕊、曹芷馨,她们已被关押在看守所超过70天。在三八国际妇女节来临之际,我们作为一群中国的女权主义者,在此发起联署,并提出三大诉求:
1. 释放被捕者
2. 停止秋后算账
3. 终止对女权者的政治迫害。
我们呼吁更多个人和机构关注中国女性行动者/女权主义者遭遇的政治打压和警察暴力。联署结果将邮寄至中国国务院,传递我们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