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0 | 聚焦乌俄 | 最不幸的一代

这幅悲伤的画面,不禁让人想到了这样一段诗篇:“我死后/请把我安葬/我深爱的乌克兰/请把我的墓碑高高地矗立/在辽阔的乌克兰平原上。” 此诗是乌克兰浪漫主义时期最具影响力的诗人塔拉斯·舍普琴科在临死前所作片段,他早年抵抗沙皇俄国的统治,被捕后被流放,晚年获准回到乌克兰。诗歌跨越了时光,历史仿佛在以诡异的方式不断回归。
2022年2月24日莫斯科凌晨,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在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Donbas)地区展开“特别军事行动”。随之,乌克兰当地时间凌晨四点左右,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防空警报,多处出现爆炸声,俄军从北部、东部和南部入侵乌克兰。与此同时,大量乌克兰居民或于当地寻找防空洞自救,或开车逃离基辅。乌克兰政府迅速回应,号召国民、组织武装反击。当地时间2月26日,俄方宣称会从黑海发射巡航导弹,对包括基辅在内的多个城市发动袭击。
在这场震惊世人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中,媒体无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各方——官方、记者、乌克兰公民、在乌克兰生活工作的各国人民——都在通过各种媒体平台,分享信息,更新乌克兰实时状况。2月24日,卫报驻乌克兰记者Peter Beaumont是第一批从报道基辅出现爆炸巨响的记者之一。乌克兰居民用各种通讯媒体交流、自救,并且把当地发生的情况通过社交媒体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普通俄罗斯人也通过社交媒体,表达对俄政府的谴责、对乌克兰的支持,以及对和平的强烈诉求。
然而,我们也需要时刻对接收到信息提高警惕和反思。正如友邻号同时编委会(hxotnongd)指出,“正在发生的,不只是地面上的战争,也是一场赛博世界的信息战,人们被ta们归属的国家所裹挟,狂热随着国界线(及其延展出的阵营)分配,滋养着战争情绪。事实上,这不是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之间的战争,而是普京和拜登及各自所代言的超级权力之间的战争,所有的人民都是受害者。”
本文从新闻媒体视角出发,回溯历史,从西方驻莫斯科记者的报道策略入手,试图理解在普京统治时期中,西方对俄罗斯新闻报道的现状和盲点。作者玛莎·葛森认为,早年驻苏联报道的记者由于扎根现实,并且与权力中心保持审慎的距离,反而能挖得更深更远。反而是2000年后,由于信息来源高度依赖莫斯科,“不管是叙利亚和乌克兰的战事、过去几年政治的镇压,还是与此同时普京受欢迎程度的提升,甚至是2011-2012年领导参与俄罗斯抗议的人的命运,西方媒体对这些事件的报道口吻,很大程度上都由克里姆林定夺”。这样的盲点,可以说深刻影响了报道者对包括乌俄关系在内的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动态、多维理解,也为我们从不同媒体获取信息敲响了警钟(推荐移步阅读《哪里看乌克兰的“真”新闻?一份不完整清单》)。
原文作者 / 玛莎 • 葛森(Masha Gessen)
原文链接 / www.nybooks.com/daily/2015/12/03/writing-in-the-kremlins-shadow/
译者 / 朱瑞翼
译文原载于 / 东方历史评论
编录 / 王菁
01. 最不幸的一代
我的祖母曾告诉我:“沃尔特 •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和其他那些”美国驻莫斯科记者们的弊病在于他们只会反复咀嚼苏联媒体上的内容。在她眼里,唯一例外是《纽约时报》的哈里森 • 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他总能从《真理报》之外找到一些信息和故事。我的祖母当时在莫斯科担任外国记者的新闻审查员。她不能和记者们有直接接触,但是他们的身影在她的想象里变得明晰可见,而她之于外国记者们亦然。她尤其钟爱索尔兹伯里的故事,因为它们有内容,这也给她增加了工作量:每当遇到不是从苏联报纸里直接截取的文章,她就得翻译成俄文,交给斯大林的秘书。什么要删,什么要留,都由克里姆林宫直接做出决定。

索尔兹伯里比我祖母预想的还要有创意:熟悉了审查制度后,他想了个办法使报道变得有血有肉。他会把审查制度当作一种采访,在报道里补充一些合理和不太合理的关于政策的猜测:要是一段内容被保留,那么该内容就得到了证实。虽然这种暗中摸索的报道方法很机智,但索尔兹伯里还是感到很挫败,劝说他的编辑们在他的文章里加上一句声明,好让读者知道他的报道是经过苏联审查的,但几经尝试,他的想法都没有被编辑采纳。他没有意识到的是,担任他新闻审查员的时常是斯大林本人。
所有记者都依赖信息来源。在一个信息高度受限的国家进行报道,对于记者来说意味着特殊的挑战和艰难的学习过程。一直以来,驻俄罗斯的外国记者依赖的即便不是斯大林本人,也是集中了信息的权力宝座。虽然1950年晚期对外国记者的直接审查制度废除,但五花八门的规定还是让驻莫斯科的记者们为了保险起见倾向于官方信息。在(80年代)改革时期,变化不断从顶端向下渗透,当时的新闻故事即是现实的最佳写照。最好的记者抓住这个开放的时机,比他们的前任们在苏联社会里走得更远,挖得更深。“苏联的最后一代外国记者是最幸运的”, 大卫 • 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这位《纽约客》未来的主编就他的书《列宁的坟墓》这样写道。他这本书成为了日后俄罗斯纪实类写作的标杆。
二十年后的驻莫斯科记者可以说是最不幸的一代。不像见证国家逐渐开放的前辈,2000年后驻俄罗斯的记者们被迫记录一个国家走向封闭的过程。这是悲哀又没有丝毫优雅可言的任务:人的视野逐渐被他们想要看清的过程蒙蔽。这也意味着现如今和索尔兹伯里的年代一样,信息又在暗中收归到克里姆林周围。
不管是叙利亚和乌克兰的战事、过去几年政治的镇压,还是与此同时普京受欢迎程度的提升,甚至是2011-2012年领导参与俄罗斯抗议的人的命运,西方媒体对这些事件的报道口吻,很大程度上都由克里姆林定夺,即使写作的记者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这古老的俄罗斯城堡是一尊邪恶王座也于事无补。
02. 靠近中心的代价
在这个背景下,让我们来看看史蒂芬 • 李 • 迈尔斯的书《新沙皇:弗拉基米尔 • 普京的蹿升和统治》。普京在任16年间,迈尔斯作为《纽约时报》的记者覆盖了七年之久,与其他尝试理解过去十五年俄罗斯生活和政治的作家们为伍。这个领域的其他新近出版图书均着笔于普京主义的某一方面,例如彼得 •波梅兰采夫(Peter Pomerantsev)的《无事为真,万事可能》(Nothing Is True and Everything Is Possible)关注政治宣传,安德烈 • 索尔达托夫 (Andrei Soldatov)和伊琳娜 • 勃罗甘 (Irina Borogan) 的《红网》(The Red Web)研究审查,凯伦 •达维沙 (Karen Dawisha) 的《普京的盗贼统治》(Putin’s Kleptocracy)追踪借权偷窃和移花接木术。通过细节勾勒的故事,这些作者为解决信息来源不可靠、不可证的问题提供了局部方案,但有时免不了盲人摸象,以偏概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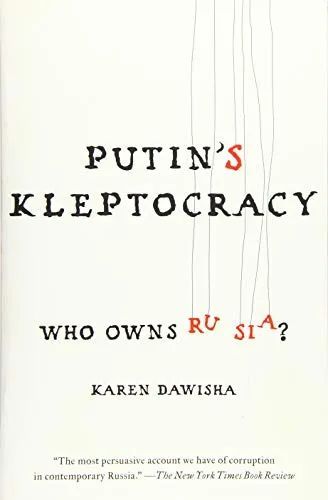
和这些书不同的是,迈尔斯尽力覆盖方方面面,从普京权力的蹿升到梅德韦杰夫任总统的四年间奏,到2011、2012年的抗议,再到索契冬奥会和乌克兰的战争。纵观全局,他认为普京遵循了经典的独裁者之路——从心怀善意到权力无限膨胀,而后孤立,再者进犯。
广阔的视角既是此书的优点也是一些不足的根源。迈尔斯将一些议题置于之前的书常忽略的国际视野下,尤其是不断变化的俄美关系之下。迈尔斯作为面向美国观众报道俄罗斯新闻的记者身份,如今看来尤为可贵,毕竟克里姆林的许多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例如,迈尔斯提醒读者2011年,在梅德韦杰夫的任期内,俄罗斯停止了对美国插手利比亚的反对,因为这恰好可以作为普京对叙利亚总统巴沙尔 • 阿萨德坚定不移的支持的有效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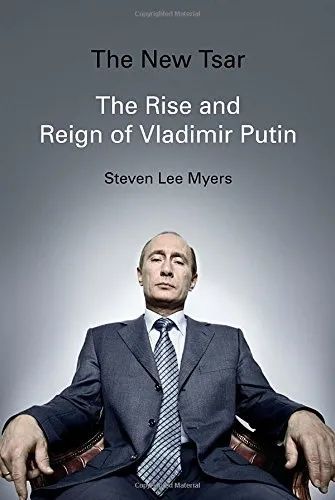
但新闻记者倾向于把信息来源对与事件的解读作为事实呈现也是本书最大的弱点。例如,迈尔斯在描述2011-2012年俄罗斯总统之位从梅德韦杰夫过渡回普京时,他选择了部分克里姆林观察者支持的理论——即普京和他更倾向自由主义的门徒真正地经过了一场竞争,最终普京获胜,迫使梅德韦杰夫心服口服地放弃了总统之位。但这两位都曾公开宣布过:他们数月或数年前就对这次权力交接达成了共识。而迈尔斯亦没有提供可以驳倒两位又令人信服的证据。在这几章节中,迈尔斯把视角从普京转向梅德韦杰夫,描写这位初级政客的感受和想法,并赋予他相比普京对“西方,民主,人性”的观念缺少怀疑的态度。读者无从知晓作者如何获取这些信息。作为本应客观的记者,他潜入角色大脑中写作的声音非常刺耳。
即便是经过深入调查,这种基于猜测的写作在缺乏不同论调时,通过不断重复很容易三人成虎,把一个假设变成广为接受的事实。因为长期主要接收克里姆林及周围的信息,已经产生了好几篇广为传播但无法考证的报道。其中一些并无害处,但其他的却阻碍人们对俄罗斯生活和政治更深入的理解。书的开篇,迈尔斯起笔于对一个故事非常详细的叙述:1941年涅瓦河畔,靠近列宁格勒,弗拉基米尔 • 斯皮里多诺维奇 • 普京,未来总统的未来父亲,受伤了:
“他接到的命令近乎自杀式。他得监控德国的排兵布阵,再尽可能抓到一个‘喉舌’,也就是暗语里对一个用来审问的士兵的代称……没有选择,只能遵命。他和另一位士兵沿着前线的地道靠近了散兵营,周边战壕密布,表面弹坑累累,血迹斑斑。一个德国人突然站起来,把他们仨都吓了一跳。画面静止了一刻后,什么都没发生。德国人最先反应过来,拔了一颗手榴弹的引线,扔了过来,落在了在普京身边,炸死了他的战友,炸得他的双腿嵌入了许多弹片。德国士兵逃跑了,留下普京等死。”
老弗拉基米尔 • 普京去世至今已经十六年,未曾发现他对这场战役的亲口讲述。但迈尔斯却把俄罗斯国家新闻社(RIA)和小普京授权的传记作为依赖。这些不过是制造迷思的工具罢了,应该被反思,不应像迈尔斯那样将它们作为事实推而广之。
宣传最有效的时候就是当它成功主宰描述事件的语言和口吻。迈尔斯自然不是普京的辩护派——他把普京比作“沙皇”丝毫没有褒扬之意。但让人遗憾的是书的后半部分多处印证了克里姆林宣传的有效性。迈尔斯在形容普京2012年反对抗议者的运动时,写道:“其中一个抗议者,列昂尼德 • 拉茲沃茲哈耶夫(Leonid Razvozzhayev)逃到乌克兰后,被便衣拘捕遣送回莫斯科。他自称被绑架而且受了虐待”。事实上,俄罗斯的执法力量没有权利在俄罗斯境外实行逮捕,所以在乌克兰发生的事情是一次绑架。但迈尔斯的遣词造句就显得拉茲沃茲哈耶夫的“逮捕”是事实,而绑架却成了“一家之言”。
在另一处,迈尔斯认为2011和2012年的大规模抗议涉及到了俄罗斯各地,各个社会经济背景的人——这是一个俄罗斯列瓦达中心(the Levada Center)及其周边(波茨坦爱因斯坦中心的米查 • 贾波维兹Mischa Gabowitsch)研究认可的现实。但他进而采用了克里姆林的论调来评价抗议者,将他们称为 “不满的精英分子”。迈尔斯也选择了使用克里姆林对“系统”(融入政府机构的)和“非系统”(受克里姆林排斥的)的对立定义。除了这个句子里的二元对立值得商榷——文明和谐的抗议和野蛮上街的抗议——“对立”这个词本身就词不达意,因为它所暗示的组织规模和影响力是当今在俄罗斯办不到的。
克里姆林对于影响叙事的努力是和我们直觉相反的。我们也许认为宣传主要影响俄罗斯国内的观众——没错,但是当地观众也可以选择关掉电视,对新闻不以为意。但驻莫斯科的记者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需要以收集到的信息来工作,如果他们认为最好和最重要的信息来源是那些拥有最多信息的人,那么他们就不可避免地将自己置于官方宣传高频率的轰炸之下。或许再多批判性思考都不够抵御误导的信息:不仅是事实,基调和基本前提假设都需要质疑。但如果任何信息都不能被信任,那还有什么信息可以使用?
哈里森 • 索尔兹伯里对这个问题有很深刻的认识。在信笺中,他常常抱怨每况愈下的报道环境,告诫他的编辑们他的“新闻灵敏度很不达标”。他寻求外界视角,并在1950年为了清理思路请假离开。他的编辑们在这两件事情上都帮不上忙。索尔兹伯里比起现在的记者们更谦卑,更善于自我质疑。或许这得益于他与克里姆林宫的沟通并非直接,而是需要通过中间人,也就是我在幕后工作的祖母,这使得他免于因为靠近权力核心或者所谓的权力核心而自恃甚高。毕竟在一个万物皆衰,渠道闭塞的社会,靠近权力是件很诱人的事。
本文授权译自《纽约书评》,经东方历史评论(ohistory)授权转载。
最新文章(持续更新)
202. 小结通讯 | 新年推荐 by 五条绳
203. 与蚊子共存
208. 我们留给未来的过去正如何过去
209. 海鲜女的码头江湖
210. 聚焦乌俄 | 最不幸的一代
欢迎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保持联系
独立网站:tyingknots.net
微信公众号 ID:tying_knots
成为小结的微信好友:tyingknots2020
我们来信、投稿与合作的联系地址是:tyingknots2020@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