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的香港還會有____嗎?】
一星期前嶺大編委(ig account: lusu_pb) 連發兩條貼文,學生記者夜晚十一點鐘目擊位於嶺南大學附近的富泰邨夜宵攤被食環署及房屋署身穿制服的職員趕盡殺絕,幾乎所有攤位的木頭車都被充公上繳,攤主無奈地說贖回的幾率渺茫。半個月前我每天都會路過的的一家旺角夜宵攤攤主發ig告知大家:【經食環署提醒,他們的攤位將不再設置座位以免阻礙巷口走道。】
曾經光顧的小攤要被消失或被整治;我工作的社福機構因為某次在路邊派發物資給基層家庭時佔用了街道,恰好撞到食環署來掃街,毫不留情地開了600港幣的罰單;與我們一街之隔,成立於1978年的深水埗布藝市場——棚仔也在與食環署抗爭十餘年的本年初被迫清場。我沒有目睹或參與過棚仔的抗爭歷史,在這裡不多加贅述。知道清場時限後,有幾次吃完午飯會散步過去參觀,那一片鐵皮屋和警署只一街之隔,冰冷建築和鮮活布藝市場的對比顯而易見。幾棵粗壯大樹在棚仔的上方伸展枝丫,遮陰避陽,好像特意為棚仔而生長——因裡面不能開冷氣,只有風扇。從外向內看一眼,只得一條窄窄的昏暗走道,幾十個布藝攤開設在走道兩旁,走進去才能看到一個個布藝鋪。棚仔的布販在一小塊方格天地裡建立起有別於工廠流水線的秩序,來來往往有熟客街坊,服裝設計系的學生,報刊記者....一齊抵制過清場行動,見證不同時代的變遷。



城市管理者從不過問市民什麼是我們眼中的城市美學。現如今幾乎每天早上一出深水埗地鐵站一定會見到穿著食環署制服的工作人員拿著相機掃視街道;許多老字號店鋪的招牌也因違反各種規定需要拆下。他們的架勢似乎想要將我城的所有【騷亂】都踢走,給【文明】讓路,只留下慶祝回歸xx週年的大型橫幅。香港本土學者馬國明時常講述香港小販如何在不屬於自己的空間裡流動。港英政府於移交主權前開始設立專門的部門管治街頭小販,馬老闆在文章中解釋——這樣的時間設定是港英政府為了維持香港移交期間街頭整潔,繼而體現港英政府統治下香港是一座文明的城市。這種解釋也印證了殖民政府統治的其中一個方向即是將文明/野蠻簡單粗暴地二分為有小販/冇小販,而小販的生寸處境並沒有隨著主權移交而得以改善,管制措施延續了下去,【港人治港】的口號在日後顯得空洞無比。九七之後我城的地產商更加肆意妄為,政府管制也越來越嚴格。回想16年旺角爆發魚蛋革命的導火索便是街頭小販與食環署的衝突而起而近兩年民/主派組織被打擊得七零八落,質疑政府的聲音越來越少(民主黨前段時間召開記者會反對巴士漲價,這種關注民生問題的姿態放在今日社會裡居然是極其罕見的。)。多重阻礙之下街頭小販的未來,似乎和香港公民社會的未來一樣,飄忽不明。
來港的第一年在屯門生活,日常活動區域基本是以學校為中心,中心往外畫圓圈,一公里內除了私人樓宇,屋邨及唯一一個小型商場,幾乎只能看見不遠處的山和空蕩蕩的馬路,還有路邊的花草,因此富泰宵夜攤幾乎成了這附近最有煙火氣息的地方。而這宵夜攤又是位於公共巴士總站內,屋邨商場外。一走近,人的聲音便會被汽車尾聲和冷氣排放聲淹沒。一輛輛巴士和小巴從這裡出發,也從不同的方向回來,【有人流的地方就會有小販】。系里的課程大多是十點才放學的晚課,一陣頭腦風暴後急需夜宵來定定神。於是下課後經常和友人一齊穿過學校長廊,再過一條短短的馬路,就可以走到一條夜宵街。

而這地方根本不是街,如同我從網路上找到的這條評論所說,它們選擇的地方不算安全,只是巴士站內商場外的一小塊空地,這廂熱火朝天地炒菜煮麵,那邊一輛輛巴士,的士,小巴在面前或身後慢速駛過,回憶起來嗅覺記憶總是先於畫面衝入腦中。在當時食環署應該已經會時常來巡視,只是仍留有餘地。有次我正在等著取食物,攤主突然推著木頭車往前小跑,直至轉彎處的漆黑空地才停下。可能透過不遠處其他同行的慌亂便可以知道【要走鬼了】,又或者有人喊了一聲【走鬼】。身在其中的我不會領略到屬於攤販之間的交流語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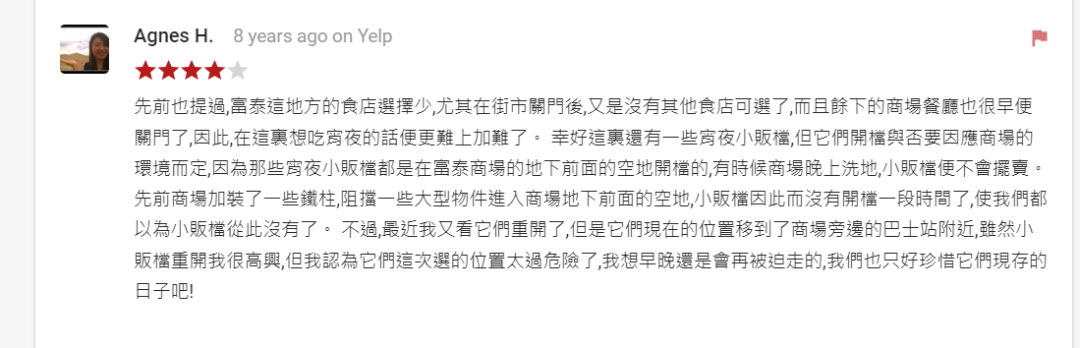
經常光顧一對母子賣的炒雞翼和烏東面,雞翼並不新鮮,已經提前醃製好,味道在整條夜宵攤卻算是數一數二,母子倆幾乎不說話,只悶頭做食物。還有兩兄弟賣乾炒牛河,時常會找食客搭話,手邊放著幾張關於學習普通話的A4紙。這裏是絕沒有電子支付的,忘記帶現金的日子就讓同學幫忙付了先。拿到食物會去富泰屋邨的公共休息區域坐下來一邊聊天一邊吃宵夜,那時還是疫情防控比較緊張的時期,我們無視政府口罩令,摘下口罩講話,大口吃東西,但從沒有附近的居民呵斥或投訴。富泰邨的宵夜攤為我們的圍爐吹水提供了不少實際的養分。後來搬離了屯門,再回系里旁聽幾次,依然要在放學後吃個夜宵再回旺角,好像那已成了必不缺少的一個環節。


到今天已經幾乎不回屯門,學校裡的書店關門,民主浮雕被拆,宵夜攤被撤,系裡課程的重新改動這些事都通過網路才知道,私有的屯門回憶已不知不覺發生變化。仍然留在系里工作的同學說短短兩年,文研今非昔比。【以前的課上大家聊社會運動,聊大學是否是工具人流水帳,聊政治抑鬱民困愁城,內地同窗或多或少受到社運的感召,看見彼此被極權打壓後的創傷。】而這一部分的討論現如今已經不再從課堂上延伸出來。時常僥倖地覺得還好我們是末代學生,而沾上【末代】氣息的事總是被蒙上一層傷感氛圍,意味著往事不再有,甚至擁有的時候就要做好失去的準備,往後只能憑藉記憶唱唱反調。
搬來旺角是兩年前的事,八公宵夜在旺角地鐵站出口附近,有一天終於沒忍住好奇走近,點餐,坐下。那天恰好穿了達明一派的周邊t恤,背面是【我等著你回來】全專輯的歌名。負責燒烤的店員忙完一陣坐在我身後的椅子上吸煙,突然說:【我鐘意呢件t】,我多嘴問:【可唔可以播達明的歌】。於是他進去擰開了音箱,那晚明哥的歌聲就從宵夜攤里傳出來,飄在旺角的巷口。達明作為一種暗號介入了公共空間中,不需要過多的交流和袒露我們已經可以了解對方的音樂喜好和政治身份,這是我城全新的暗流湧動。當歌聲四起,它不再是在成千上萬人的紅館或維園,而是在狹窄的宵夜攤,在一個個同溫層的家裡,在香港之外。
【未來的香港還會有____嗎?】
【我都唔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