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马克思与权力:左派在国家问题上犯的错误│Marx and power: Where the left has gone wrong on the state – book review
﹝英国﹞克里斯·宁哈姆(Chris Nineham)
Guanyu 译、日土兀 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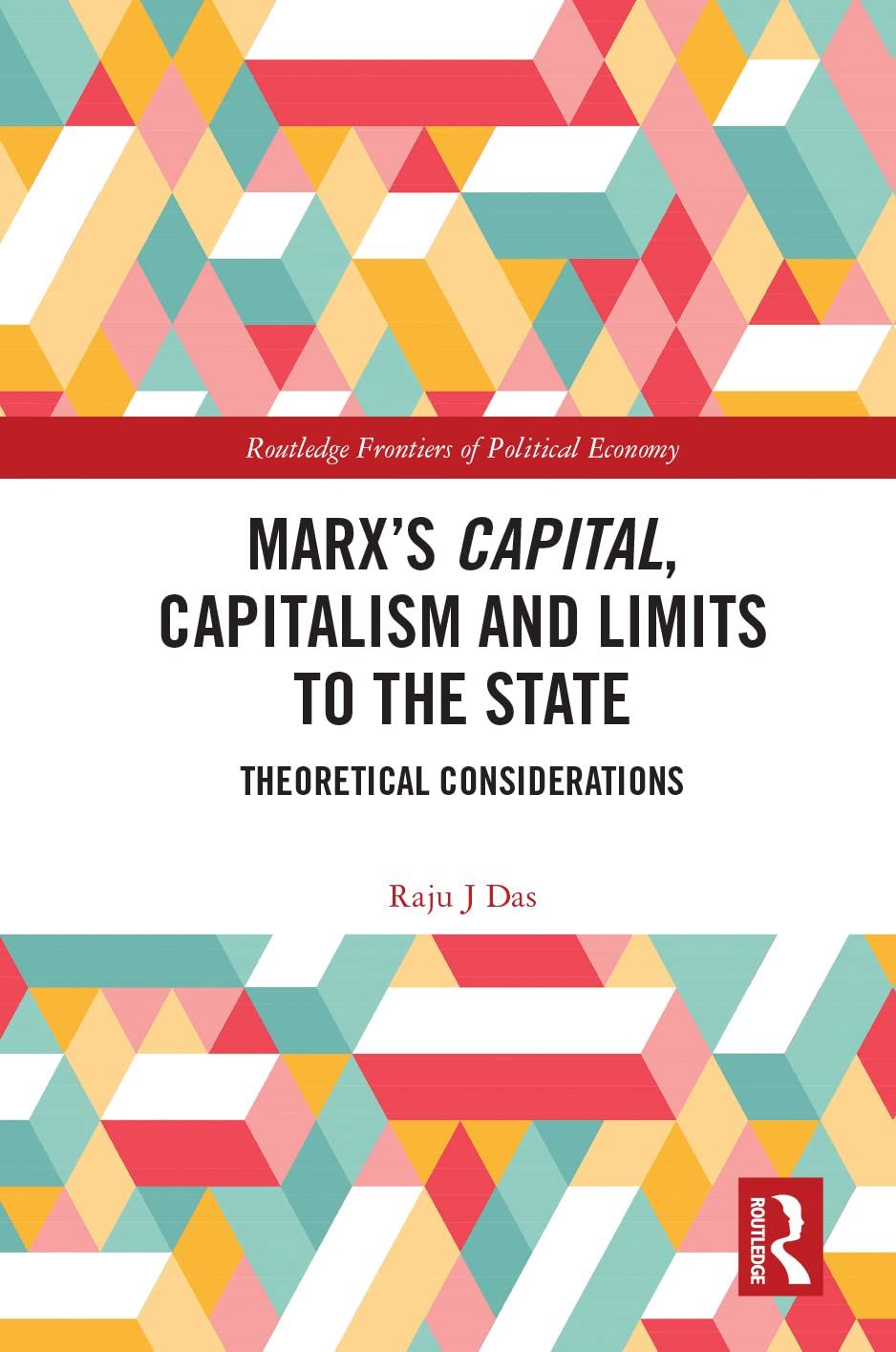
这是一本理论却不失迫切性的书。拉朱·达斯意识到,左派对社会治理机构的理解方式塑造了他们采取变革的策略,实际上塑造了他们的整个政治道路。几十年来,左派一直忽视国家权力的问题,因此近年来对国家理论的重新关注是值得肯定的。从列欧·潘尼奇(Leo Panitch)和山姆·金丁(Sam Gindin)到埃里克·欧林·赖特(Eric Olin Wright)、鲍勃·杰索普(Bob Jessop)、弗雷德·布洛克(Fred Block)和斯蒂芬·马荷(Stephen Maher)等一系列作者都对这一领域有所贡献。许多人继承发展了上一轮在1960年代和70年代辩论中的主题,往往借鉴了拉尔夫·密里本德(Ralph Miliband)、尼科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和对安东尼奥·葛兰西的众多解读而来的思想。
然而,对于达斯来说,存在一个问题。这类的大部分著作都从这样一个假设出发,即《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对国家的描述“作为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是过于简化的。还认为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对马克思观点的著名重述,即资本主义国家必须被推翻和取代,已经显得过时和粗略。列欧·潘尼奇是新国家理论家的代表,他认为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国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粉碎国家”和“国家消亡”的陈旧观念已经无法捕捉到这种变化(第47页)。
尽管如此,现代国家理论被普遍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或至少是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然而,正如拉朱·达斯在这本全新的书中指出的,(现代国家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差异是根本性的。他指出了近期文献中对现代国家的许多有用洞见,他也在试图将其中许多有用的观点纳入自己的分析当中。但这些分歧具有严重的后果,最终导致,按照达斯的说法,“提供了一个理论和政治上逃避革命行动的意识形态正当性”,从而与马克思主义决裂(第6页)。
例如,对于列欧·潘尼奇的追随者之一的斯蒂芬·马荷(Stephen Maher )来说,国家可能被“建构成为使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机构”,但其也“提供了机会,让民主运动在其机构内部和跨机构之间进行反组织”(第48页)。结果是,资本主义国家不应该仅仅被视为阻碍变革的障碍,而应该被看作是一组可以通过社会主义战略在其结构内外进行民主化的机构。马荷说,与普兰查斯相似,“国家提供了一个阵地,让工人阶级的要求得以被形成、被争取、以及(可能)被实施”(第48页)。
达斯抱怨说,在文献中,“实质内容与使用的文字数量之比通常相当低”(第58页);尽管这些讨论大部分是学术性的,但也带有很高的风险。达斯批判的观点主导了左翼讨论的很大部分,并为左翼选举项目提供了理论支持,例如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Syriza)和西班牙的“我们可以党”(Podemos),以及美国的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英国的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等备受关注的竞选活动。然而,这些项目都没有取得好的效果。正如达斯所指出的那样,“国家理论的坚定支持者(密里本德、普兰查斯和许多其他人以及受他们影响的人)的客观效果是改良主义”(第51页)。
达斯的著作很厚,有时也显得冗长。不过,它是一部重要的理论贡献。在耐心地指出当前国家理论存在的问题的过程中,达斯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后续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关国家的思想的有力辩护及具说服力的更新。
众所周知,马克思从未在国家这个议题上做过定论,所以达斯通过研究《资本论》第一卷,来探讨现代国家的问题。简而言之,达斯的观点是,新的国家理论家们在四个关键问题上犯了错误。他们往往过分强调国家的独立性或自主性,误解了它是如何被社会力量所塑造的,夸大了它的内部矛盾。(他们往往)过分强调了,在国家的运行过程中,同意比强制更为重要。
这一切的背后存在一个问题,即新的国家理论家似乎无法从历史上理解资本主义国家是资产阶级崛起的产物和资产阶级社会的不可或缺的推动者。因此,他们忽略了国家机构固有的阶级性质,“国家并不是因为依赖于资产阶级而是资本主义国家,相反,国家依赖于资产阶级,恰恰是因为它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第46页)。
1)国家自主性
当代国家理论的一个反复讨论的主题是,资本主义国家相对不被经济过程和资产阶级所影响。例如,列欧·潘尼奇表示,“国家机构或多或少相对独立于阶级代表和压力”(第32页)。对于先前的普兰查斯,这种自主性对于国家来说有必要,以便能够组织统治阶级内部的敌对派别,并瓦解工人阶级(第24页)。
讽刺的是,这种观点通常是通过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各种段落来证明的。马克思指出,与之前的国家形式不同,资本主义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市民社会之外的”(第92页)。对于马克思来说,这主要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必须能够提供一个资本家公平竞争的行政和法律场所,因为国家正是一种维护统治阶级共同利益的形式。换句话说,需要与特定的资本家利益保持一定距离,才能使资本主义维持下去。
这种与个别资本家的距离,使国家看起来在资产阶级统治下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让它显得中立,从而赋予了它一定的大众合法性。但正如达斯所说,没有人应该被外表所迷惑。将这种与个别资本的相对分离——被资本的整体需求所强制而施加的分离——等同于与资产阶级利益的真正距离不合逻辑的:
“国家的阶级性质与其实际的运作方式(例如,其是否具有自主性)属于不同的分析层次。这两个问题在解释国家的行为时的因果重要性並不同等。前者是首要的。而自主程度比通常认为的要少得多。(资本主义国家需要)非常少的自主性就足以征服群众并重现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国家从资本主义经济的分离更多只是资本主义在表面上浮现的事(第6页)。”
资本主义国家通常由非资本家管理是它看起来无党派偏见的另一个原因。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实际问题。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资本家总的来说,他们无法将全部时间投入到国家管理中。然而,有一个更根本的观点:这远远不是国家(于资产阶级统治下)独立的迹象,相反,这又一次表明资本家意识到国家需要在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下运作。
达斯引用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哈尔·达拉普(Hal Draper)的话来阐述这一点:“资本主义的一种内在特征是……资本家自身作为国家的管理者或经营者的作用被最小化了。”这是为了想要寻找“能够应对并坚持系统长远的整体利益与需求的政治领导者”(第182页)。
这种国家独立或中立的表象受到另一个因素的支持:即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和经济的表面分离。自由市场尤其在当今时代被认为是超越政治或人类干预的。这不仅因为国家在促进“自由竞争”方面超越了个别资本家的利益,而且因为使经济免受民主审查或控制对于资本主义的生存来说至关重要。
再次强调,我们应当注意,不要将表象误认为是根本现实。尽管经济被小心地隔离在议会之外,但整个国家与商业之间存在着紧密甚至是共生的关系。国家机构在资本积累的每个阶段中都扮演着核心角色。它们创建和维护基础设施,执行税收制度,保障银行系统,为企业提供廉价信贷,监管金融,并提供最低限度的福利和教育以保持劳动力足够健康和有足够的技能去工作。关键的是,国家还提供必要的士兵和硬件以强制执行国家资本家的海外经济利益。
所有这些都反映了更基本的现实,即资本主义如果没有国家的存在就无法运转。达斯引用俄国革命家列夫·托洛茨基的话,指出,“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之间的区别...是一个术语陷阱。” 经济权力本身并不存在。托洛茨基说,“只有财产,不同形式的财产”(p.97)。
没有私有财产,利润就再无法获得,因为工人生产的商品将不在资本家的控制之下。这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历史上在各地扮演了强制社会私有制的角色,并继续扮演维护“财产权”的角色。正如达斯指出,如果没有国家机器,就会陷入混乱,“对于财产和剩余劳动的不平等控制的矛盾是根本性的,无法在追求个人利益的社会内化解”(第46页)。因此,任何工人试图对他们的工作条件或场所进行控制的尝试都不仅会受到雇主的反对,还会受到国家各个派别的反对。法律、法院、警方行动,都是围绕维护私有财产这一核心原则来制定的。
达斯还强调了一个重要观点,即使当它必须执行表面上有益于社会的任务时(顺带一提,这也有助于显得它自主、中立),“这种功能仍然是通过阶级利益来实现的”(第182页)。否则,如何解释监狱系统的野蛮、各地社会福利制度的惩罚性与使人堕入贫困的性质,以及应对疫情的方式总仅涉及最低程度的照护,且总是以有利于富人的方式而进行的?“所谓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中立功能最终皆具有阶级性,因为国家本质上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第182页)。
2)什么塑造了国家?
对于达斯来说,当前文献中存在两种主要方法,看起来相互对立,但实际上存在相同的问题,即未能认识到现代国家在资本主义统治中的重要性。一方面,有所谓的“工具主义”方法,认为国家是由统治阶级武装起来的,这种武装通过外部压力(企业游说、国家官员和资本家之间的紧密联系、贿赂等)或国家由统治阶级的成员或支持者担任管理的事实来实现。
正如达斯所说,这些方法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其中一个是它们“有助于祛自由主义关于阶级中立国家观点的魅”(第46页)。它们也可以揭示国家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运行的。但是它们没有触及核心问题。如果决定国家政策的是运作国家的人,那么只需要更换人员即可解决问题。如果决定国家政策的是社会力量的平衡,那么一个强大的工人运动应该能够对国家产生决定性影响。然而,现实是,资本主义国家总是在基于其对现状的承诺中选择其高级人员,并强烈抵制所有挑战资产阶级利益的措施。
然而,有两件事是非常清楚的。第一点是,普兰查斯将国家理解为社会冲突的表达或“凝聚(condensation)”,以及社会解决社会冲突的手段。例如,他说:“国家的功能在于构成社会形成不同层面之间的社会凝聚因素。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对国家作为秩序因素的概念的含义”(第23页)。
这一点,正如达斯指出的那样,对于一个自称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非常奇怪的:
“对于普兰查斯及其追随者来说......国家权力应该被理解为历史和空间上变化的阶级斗争的凝聚或形式。国家是社会形成的凝聚和平衡的因素。这种观点非常接近于国家,即使是通过矛盾的方式,实际上能够调和对立的阶级的观点。这在本质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因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家之所以产生,恰恰是因为基本阶级之间的调和是不可能的。(第44页)”
普兰查斯关于国家的思考的第二个基本特征源自第一个特征。如果国家对普兰查斯而言是阶级斗争的产物,那么国家本身也是斗争的场所。一方面,国家的不同分支“往往是权力集团一个或几个派系不同利益的杰出代表”(第34页)。另一方面,因为国家权力基于统治阶级内部互相不稳定的妥协,它可以成为实际阶级斗争的地域。根据普兰查斯的理解,不同的阶级利益实际上存在于国家之中,“以反对统治阶级权力的中心的形式存在”(第34页)。
当然,阶级斗争对整个社会的形成有影响,并且它能够并且已经迫使统治阶级和国家做出重要的让步。然而,正如达斯指出的那样,重要的是不要混淆“阶级斗争”和“阶级权力”。除了革命之外,阶级斗争并不能改变谁控制着经济或国家的根本事实。即使国家被迫处于防御状态,它仍然是一个以资本主义利益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将在阶级斗争中尽可能地少做出让步,这些让步将旨在缓解或使反对派感到困惑和找不着北,并且一旦有机会,便会寻求收回任何失地。
这其中有几个重要的结论。首先,最有效的改良运动将是革命斗争,通过威胁国家的继续存在来迫使真正的让步。另一个结论则相反,即没有逐步的、渐进的将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工具的道路。正如达斯所说:
“认为国家可以是争取改良的斗争的地域是一回事,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会逐渐消亡,并通过争取改良来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是另一回事,两者不能混淆。(第49页)”
这并不是说国家不会演变。世界各地的国家都已经被显著地重新调整进入了新自由主义时代。统治阶级进行了经济模式和政治策略的改变,从国有化和有限福利主义转向私有化、金融化和在大庭广众下对工人进行攻击。然而,这些变化是自上而下和自内部进行的,主要是对经济危机的回应,没有改变国家的基本阶级角色。国家从根本上就不是一组由各种外部社会力量塑造的结构,而是工具,一个被发展和有时被重新组织的工具,其目的非常明确,即确保资产阶级统治的持续和最大效率。
对于达斯而言,新的国家理论的根本问题在于它们的静态和非历史的方法,倾向于忽略统治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内在、有机和历史联系。这些理论未能认识到现代国家历史性地和有机地与资本主义系统的联姻。在大多数国家理论中,阶级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被视为是外在的,而实际上,正如达斯所说:“它们的关系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
3)冲突和矛盾
现在,新的国家理论家非常强调统治阶级和国家之间的冲突。这里需要梳理几个不同的问题。首先是国家人员的问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国家人员的阶级背景并不决定其阶级性质。例如,在英国,直到20世纪中期,国家的许多部门都是由贵族成员来运作的。但至少从19世纪中叶开始,国家便已经完全是为资产阶级利益而运作的了。
当然,国家自马克思和列宁的时代以来已经大规模扩张其业务,国家雇用了大量的医疗、教育和公务员工人。这些工人在国家机构内的存在对统治阶级来说形成了一个脆弱点。其中一些人(但不包括警察和许多其他人)将在任何成功的社会主义转型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
可是在正常情况下,这些工人对国家政策没有影响力,国家雇佣工人的事实并不自动创造国家内部的“阶级反对中心”,就像工业制造中存在工人并不直接等同于工人在那里的反对。这也并不意味着国家可以逐渐从底层重新定位。毕竟,一个理性和真正民主的社会对现代国家的核心机构——国家的野蛮刑事司法系统,其暴力、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警力,其殖民主义性质的外交部等等——几乎没有用处。这些位于国家核心的机构需要被废除而不是被改革。
即使是使与教育、健康和福利相关的较为边缘化、人畜无害的国家部门进行转变,也需要强制清除国家管理层,并彻底改变所有方法和工作方式。鉴于国家对基本变革的敌意,只有在动员全社会的工人阶级群众并组织新的民主权力机构的情况下,才能想象废除、代替或在某些情况下转变这些机构的任务。这不是一个激进改良主义的内外策略的愿景,该愿景是社会革命的愿景。
第二个问题涉及议会民主对国家功能的影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达斯正确地强调了决定性经济问题是如何被排除在民主政治范围之外的。但也正如他所指出的,即使在议会议程中,选项也是故意被限制了的。议会是如此嵌入更广泛的国家机构中,如此受到大资本势力的影响,以至于大多数时候他们只是统治阶级讨论的论坛,同时为社会提供一些民主的粉饰:
“不同的政治党派都或多或少是稍有不同的机制,用来在政治上代表资产阶级的不同派别或整个阶级的经济利益。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或印度的国大党和人民党,都是资产阶级的政党,在代表资产阶级的经济政策方面的追求上仅有微不足道的差异。”(第93页)
这里,达斯像他在美国写作那样,夸大了他的例子。在许多国家,选举党派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工人运动。他们的存在必须考虑到任何严肃的变革策略中。然而,达斯的中心论点是成立的。如果你接受马克思主义关于基于阶级利益的国家的观念,社会民主主义和大多数左派改良主义政党对建立在国家体系中的政治与经济分工的接受,以及他们对所谓的“国家利益”的承诺,使他们不能成为代表工人阶级根本性变革的领导者。
第三个问题涉及到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在危机时期,主要的分歧可能会出现,尤其是当这些分歧在更广泛的人群中引起共鸣时,(这些分歧)可能会破坏国家的稳定。例如,目前在一些国家中,自由主义的全球主义者和民粹主义的保护主义者之间的分歧正在创造各种程度的动荡。
不过,大多数国家在面对这些和其余的压力时都表现出了韧性。这是因为,尽管资本的不同“派别”确实会在国家中去竞争地位和影响力,并支持不同的国家政策,但它们在很多问题上的共识要比分歧多得多,而国家机构的设计目的之一就是解决发生的争议。
在极少数情况下,当统治阶级内部发生尖锐的冲突且变得公开时,可以为自下而发的运动创造出空间,试图在社会上强加他们的意志。然而,当代国家理论没有意识到,当这些危险的时刻到来时,统治阶级会尽一切可能克服其次要差异,重新组合,并对来自下方的反对采取残忍的行动,这是当代国家理论的致命弱点。所有的历史都告诉我们,这些时刻需要最果断、最革命的行动来推动变革,而不是采取逐步的改良主义的计划。
4)同意与强制
这使我们最终来到了强制力的问题。达斯指出,如今的国家理论系统地淡化了现代国家对强制力的使用。他认为,部分原因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产物。大多数有关的作家都基于较为发达的国家进行分析,这些国家的强制力在某种程度上是被隐藏的。正如达斯所指出,在大多数不发达的国家,阶级统治往往具有更加公开的压制性。全球南方的人口也更有可能经历外国帝国主义入侵的暴力,这是全球资本主义关系所固有的,也是领先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功能的核心。
这种淡化暴力的现象也与上面所讨论的缺乏历史视角有关。在每个国家,建立资本主义关系都涉及对国内外人口的各种形式和不同程度的暴力,包括圈地运动、流浪行为的刑事化以及土地被夺取和整个人群被摧毁等。正如达斯所言,“国家通常使直接生产者与其私人财产和公共财产的使用权被强制分离,并有助于私人财产以其资本主义的形式的出现”(第128页)。
自20世纪初以来,发达国家的国家机构的增长为该系统提供了一些合法性,确实如此。资产阶级已经学会使用福利、国家教育和一个严格局限的民主来限制不满,并加深对于国家中立性的印象。任何认真的社会主义战略都需要认同福利主义国家机构是如何帮助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同意。
同时,这种趋势的重要性不应被高估。在资本主义生活中,强制力和强制力的威胁是不可避免的。正如达斯所评价的,“强制力必须是为了维护商品关系的普遍条件”,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只能通过不断地将工人与他们所生产的商品分离来存在,而他们恰恰需要这些商品才能够生存 (第102页)。达斯引用了柴纳·米耶维(China Mieville)的解释,“如果没有不断的威胁和/或使用强制力,商品生产将面临被快速颠覆和分崩离析的危险” (第103页)。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逮捕和监禁的威胁,再加上因被异化的工作所产生的无力感,足以维持秩序并保证利润继续流动。然而,如果法院和监狱没有人满为患,这种威胁就是空洞的,而且用作镇压的国家机器维持良好状态以便在紧急情况下被全面部署。
这本书的优点之一在于,尽管达斯批评了左派倾向于淡化国家对为了进步而带来的挑战的敌意,但他并没有陷入与其相反的认为国家是全能的危险错误之中。他认识到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经济现实导致了普遍的威权主义增加。然而,他意识到这可能会产生相互矛盾的影响,包括同意程度的下降。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达斯认为,国家统治的性质发生了深刻变化。后殖民国家“因为其对促进经济发展的承诺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合法性”,随之而来的“国家的有选择性的撤退”,甚至放弃了去假装发展,以及其日益增长的暴力“削弱了它在绝大多数农村人民眼中的合法性”(第287页)。
这场讨论实际上存在着一个让人非常不舒服的讽刺,而这也无疑是本书的推动力之一。主张渐进式方法来看待他们认为更为复杂、不那么阶级化的国家的理论家已经在左派获得了至少部分霸权。这恰恰发生在当今真正存在的国家变得更加公开地变得威权主义,更加致力于阶级斗争,而对扩大广大人民的福利的关注可能是自19世纪以来最少的时候。因此,全世界对国家机构的怨恨和疏远正在四处蔓延。拉朱·达斯通过认真对待这些思想,并恢复和重建了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的看法,给我们带来了些许及时雨。左派急需将其牢记于心。
2023年3月9日
克里斯·宁哈姆是英国反战组织Stop the War和左翼团体Counterfire组织的创始成员之一,代表这两个组织在全国各地定期地发表讲话。他是《人民对东尼‧布莱尔》和(The People Versus Tony Blair)《资本主义与阶级意识:格奥尔格·卢卡奇思想》(Capitalism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the ideas of Georg Lukacs)的作者。
原文链接:https://www.counterfire.org/article/marx-s-capital-capitalism-and-limits-to-the-state-book-re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