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並不須好性》一首歌引發四個人對無性戀者、男同志與性關係的探索與反思

撰文:proxlogue
文字編輯:Henry、Mo
網站編輯:Natalie
編按:《我並不須好性》專訪共分兩集。上集<《我並不須好性》創作班底首度剖析作品 無性戀者阿康:從第二角度認識自己>中,三位創作人一邊解構歌曲,一邊帶我們認識無性戀者康,建議先閱讀上集。
力度十足的宣言「我並不須好性」,貫穿了整首歌曲,成為了「無性戀之歌」《我並不須好性》的主軸。作詞人Zelos、唱作人KU和MV導演Chloe分別為此作出不同解讀方式。在語調如此肯定的宣言背後,你能想像康是在交流後期才第一次接受自己「無性戀者」的身份嗎?能創作出如此直白地反映無性戀者心聲的作品背後,你又能否想像班底中有人是第一次接觸無性戀,甚至還在交流中對無性戀有所誤解?繼上集拆解創作過程的彩蛋後,今集就讓我們來了解一下班底與康在交流期間的心路歷程,以及他們期望作品在「主流世界」有著怎樣的定位吧!

KU:我以為無性戀是…… Chloe:我高估了自己的開明程度
「在交流的初期…我以為…以為…無性戀等於…等於泛性戀…」KU尷尬中夾雜幾聲失笑地說。她隨即補充:「在我的認知裡,泛性戀是一種無論對方的性/別是甚麼,也可以對其產生浪漫情感的性取向。於我來說,就是比較在乎對象作為一個個體是怎樣的人,與特定的性/別無關。而因為無性戀者也是比較注重靈魂上的交流,所以我就一直誤解了兩個概念。」KU又表示,她身邊都不乏把無性戀和泛性戀搞錯的朋友,因為不少人都誤以為「無性戀」中的「無性」,是指不理性/別,繼而認為無性戀就是不考慮對方性 / 別的愛。
經由其他組員幫忙「補習」後,第一次接觸無性戀的KU驚嘆:「原來(性/別)小眾的世界可以很大!我所指的除了是有很多不同性取向的存在,還有一個人可以擁有的多重性 / 別身份。以康為例子,他既是無性戀者,又是男同性戀者。原來性取向不只是流動、排他(exclusive) 的,還可以是重疊、共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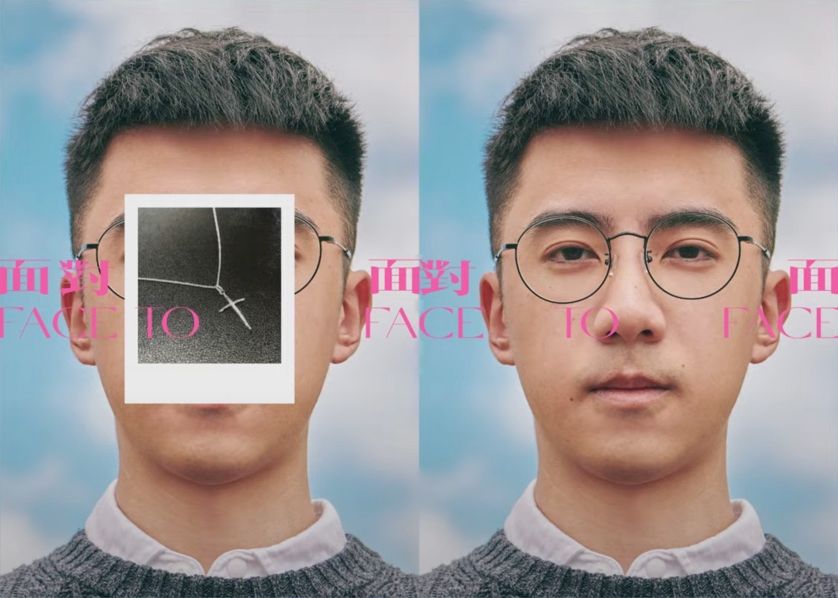
談及誤解,Chloe 坦言自己在交流過程中都有類似的經歷:「訪問康之前,我以為自己都算是一個思想開明的人。」Chloe解釋,因為她身邊都有不少來自性小眾社群的朋友,而他們的故事和經歷都頗多元化。「但在康回應我組員有關他的前度如何解決性需要、他會否同意開放式關係等的提問時,我心裏的自然反應就提醒了我,原來我一直都高估了自己的開明程度。」她續說:「當康表示不希望伴侶在外解決性需要、希望伴侶只忠於自己時,我內心第一個反應是『下!?怎麼會這樣?』事後,我覺得自己當刻的愕然很錯,因為那像是在拿我自己的標準來衡量康、把我自己的標準強加在康身上。反省過後,我才驚覺原來自己某程度上還是未能擺脫『主流』的既定想像 —— 情侶之間一定要有性關係,一定要配合伴侶的性需要。」Chloe直言那次的經歷是一個警號,提醒著她要多留意「主流框架」如何影響著她對日常人事的判斷。
迷惘歲月的一個總結 康首次直面無性戀者身份
作品的緣起,是Chloe無意中在網路上讀到一篇無性戀者的專訪,在製作組敲定以「無性戀」作為主題後,Chloe隨即找來了共同朋友、願意公開分享個人故事的康作為書寫對象。但另一邊廂,當時的康仍在探索自己的身份。一直以來,康都在「無性戀」和「半無性戀」的身份定義之間徘徊。他不敢輕易地把自己放進任何一個框架之中,有所偏差地限制自己。康解釋:「我很執著『無性戀』是用作形容完全抗拒『性』、對『性』反感的人,因此我不想定義自己為『無性戀者』。但對於『半無性戀』的定義,我亦有所保留;因為我上一段關係的決裂正正是我內疚未能滿足伴侶性需要,但又不想蠶食自己『不好性』意願所致的。」亦因為有著這些思想上的矛盾,康在收到班底的書寫邀請時,都有點猶豫,硬是認為自己沒有資格被稱作無性戀者。
幸好,班底每次的發問都為康帶來一些新的反思方向,令他終於能夠梳理到自己的思緒,甚至確立到自己的性傾向。康分享其中一個最深刻的體會:「從我與班底的交流中,我明白到『預設』(assumption)對一個人,甚至人與人相處的重要性。我不介意別人對我有所預設,因為這是他們認識我的第一步,亦是往後更深入了解的基礎。如果他們的發現起初的預設是錯的,大不了就從與我的溝通之中再推翻吧。」於是,當康認識到把自己放進一個身份定義並不是件壞事後,就開始釋懷,並希望找來一個詞語總結自己:「我一直堅信性取向是流動的。經過一番思考後,我還是決定把自己定義為『無性戀』,因為無論以後我多大程度地『無性』,我知道我也能夠安於『無性戀』的光譜之中。」這次企劃不但為班底、觀眾帶來了探索無性戀的機會,甚至還為康帶來了探索自己、肯定自己的契機。

同性戀身份較易被理解 無性戀身份較易被接受?
雖然康的「男同性戀者」和「無性戀者」的身份是不互斥(mutually exclusive)、可重疊的,然而,作為「雙重身份」的擁有者,康卻一直感受到當中衍生的矛盾。康無奈地說:「男同性戀的世界或多或少都會推崇『性解放』、『性崇拜』。例如我玩交友軟件、去酒吧,都不時會被人問是『1』還是『0』,又或者被人一口咬定『看你的樣子一定是1/0!』。那些情況下,我其實是挺尷尬的,因為我兩者都不是。而正因為如此,我在尋覓伴侶這方面,都會份外困難。」
談及大眾對兩者的觀感,康觀察到:「男同性戀者的身份較容易被理解,因為只要『出櫃』,別人就會明瞭你是喜歡同性的男性。」他認為,這個身份定義很清晰,是一個令溝通更有效的「預設」。同時,這個標籤亦有助人與人之間的「過濾」和「配對」。「相反,可能是因為無性戀尚欠代表性,不是每個人都認識它,所以就變得較難被理解。」康概嘆道。縱使無性戀未能被大眾了解,但大眾的接受程度又如何呢?康表示:「無性戀者的身份是較易被接受的。在香港這個較保守的社會,與『性』有關的話題向來都是禁忌,更何況我自己有基督教背景,身邊的人大多都是基督徒,所以這個身份基本上都不會為我帶來太多爭議。」

同為男同性戀者的 Zelos,也認為相比無性戀,男同性戀較難被社會接受,並補充說:「傳統上,男性是第一性。因此,男同性戀者其實是在挑戰父系社會中的男性角色,自然會面臨更多攻擊、更不被接受。另一方面,『有性』與『無性』只是情侶之間的事,與其他人無關,亦不是在冒犯社會的規範,所以無性戀通常都能較輕易地被接受。」但對於「無性戀較難被理解」的說法,Zelos似乎有不一樣的見解:「以我作為例子,雖然我不是無性戀者,但我不會說自己是不理解康。我認為我只是無法感受到他『不喜歡性』的感受。」
被主流看見的序章 拒絕流於「偽勝利」
「我無意代表整個無性戀社群,亦害怕代表它,因為我堅信經歷是很個人的,而我不想一錘定音地向觀眾輸出甚麼是『無性戀』。我只希望這個作品、我的故事,能夠成為主流看見無性戀的序章,哪怕只是引起他們對認識議題的少少興趣。」康輕輕地道出自己對《我並不須好性》的期望。
「其實我覺得(這個作品)已經做到了。我身邊的一些朋友都有在觀看完作品後向我了解無性戀,甚至連一向內斂寡言、不善言辭的爸爸都有傳訊息給我表示支持。」說起家人的反應,康感恩之餘也帶點內疚,要父母透過作品才能認識自己。康繼續說:「除了家人朋友,正如我所說,我從作品中看到班底的用心。即使作品所呈現的,尚未是百分百的我,但至少他們有盡力了解我。這也是他們嘗試接觸無性戀議題的第一大步!」

延伸閱讀:《我並不須好性》創作班底首度剖析作品 無性戀者阿康:從第二角度認識自己
Chloe樂見康對作品成果感到滿意,不禁雀躍地分享說:「我在創作的過程中都做了很多與無性戀有關的資料搜集,其中包括閱讀 Alice Oseman的《Loveless》,一本紀錄無性戀者心路歷程的小說。這些讀物都有助我更立體地了解無性戀的世界。」KU 更激動地補充,「無性群象 A-lephants」的成員Yumi也有前來觀賞總結演出。「在與她交談之前,我一直都只是期望作品能夠表達康的故事。在 Yumi跟我說她對作品很有共鳴時,我真的十分感動。那場對話後,我甚至大膽希望我們的作品可以鼓勵其他性 / 別小眾群體發聲,爭取自己在主流社會中被看見的可能性。」
至於 Zelos,雖然他也很喜歡這個作品,同時對大量的好評感到意外,坦然自己內心還是有些矛盾:「其實我並不肯定它(作品)是否真的能讓大眾接觸到無性戀,始終一次性的流行音樂、流行文化很難有效地用作公共教育(public education)。舉個例子,或許駐足K11觀看總結演出的觀眾,根本不知道,甚至不想理會我們在唱甚麼、在表達甚麼。因此,即使有人認為這個小眾的作品是登上了主流的舞台,我也不會有太大的感覺。」雖然認為作品未必能立竿見影,但他亦緊接著補充道:「我亦不想就這樣安於此刻的『偽勝利』。我相信,只有更多無性戀者持續地為自己發聲、更多有影響力的人持續地為無性戀者發聲,我們的社會才能真正向前走。這才是我最想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