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秩序、大一统与国际民主
王飞凌/滕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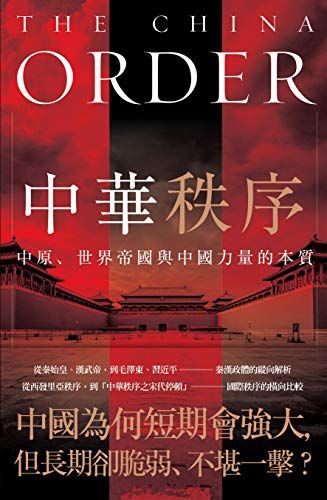
滕彪(以下简称滕):您曾经提到这种秦汉体制、中华秩序和列宁斯大林主义有一些暗合的地方,能不能具体解释一下?我们知道毛泽东说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也许秦体制和和现代的共产极权体制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共产主义、天下大同,和“华夷之辨”的天下秩序似乎很不一样。
王飞凌(以下简称王):我的回答分两层。第一层,秦汉政体与所谓的斯大林式社会主义、共产党一党执政是非常吻合的。号称是现代的政体和一个前现代的东西高度吻合,恰恰说明了斯大林式的无产阶级专政或一党专政,其实是非常前现代(启蒙运动之前)的旧政体。只是辩护词从天命变成了民命,就是说它是代表天意,还是为人民服务,说法不一样而已。毛泽东发现在斯大林式扭曲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秦汉政体、所谓儒化的法家思想之间相当吻合,他很聪明地利用了这一点,号称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第二层,斯大林主义、列宁主义和原来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这样,和中国的天下一统、华夷之辨不同。年轻的马克思当年还是强调个人解放、个人自由的,强调自由体的结合,完全不是斯大林后来搞的那套一党专政,用镇压和控制的方式来统治。不幸的是,中国进口的是斯大林主义,不是现在西方还在实行的所谓社会民主主义或者民主社会主义。
滕:您提到的中华秩序、大一统思想基本上是同义词,这种大一统思想对中国的政治、历史、社会等都有极其深刻的影响。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它和民族主义(在现在的语境下,就是皇汉主义、大汉族主义)有什么联系?
王:简单的说,大一统观念、中华秩序或World Empire(世界帝国)政体,是逐渐形成的。它始建于秦朝,后汉朝把它稳固化,通过引进儒学作为包装把它稳定化,经过隋唐的科举考试和其他一些制度,在元明清走向极端,它是个不断进步、变化的过程。在这过程中又高度内化,变成所谓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核心概念。中国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乃至普通老百姓认为天下一统是理所当然的、正常的状态;而天下分裂像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就是西方现行的国际制度,则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这个观念在最初是由于生态地理环境形成的,经过长期的政治熏陶,后来又被统治者利用,用政治宣教和压制手段,内化成一种文化观念、变成一种根深蒂固的价值观。
那么它和大汉民族主义有什么关联?大汉民族主义只是一种现代人的发现、发明,过去其实没有什么大汉民族主义,只有皇帝的顺民和叛逆之分。
大家会说我是唐人、宋人、明人、清人,没有人说我是汉人和中国人,这些是后来的发明创造。大汉民族主义在我看来是在近代以后被统治者们利用起来了,塑造一个新的意识形态来和其他国家抗衡、巩固自己的权力。
滕:现在中共同时使用世界主义、共产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又鼓吹和推广汉族为中心的大汉民族主义,一种种族主义。对他们来说两者可以无缝相接,其实目标就是一个:我得永远执政下去,至于是什么主义对它来说并不是太重要。——民族主义者经常用的一个词是中华民族,其实这是梁启超发明的东西。它和中华秩序有没有什么关系?
王:当年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政治精英想做成两件事情,一件是把自己和满清统治者分开,同时又把自己和西方列国分开;另一件是他们又想保留清朝的多民族大帝国占领下的领土的完整。为这要达到这两个目的,就必须重新发明一个概念,于是就有了所谓“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在人类学上是不存在的,它是一个政治概念。后来的国民党、共产党都大大利用了这个概念,就是说我们和西方列强一样,也是一个民族,而且还是单民族国家Nation State,这样不会有多民族国家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同时我们要保留这些满清帝国的每一块领土,西藏、新疆、东北等等都要。 “中华民族”这个政治概念由于政治上的强力推广和教育上的灌输,在中国倒成了一个大家都接受的观念。
滕:您提到澶渊之盟是“一个提前了643年的威斯特法利亚和约”,宋代背离了中华秩序的传统长达三个世纪,这是如何形成的呢?
王:谢谢你提到这一点,它是我自己重新解读中国历史的一个心得。现在我发现,有这个看法的人并不少。宋朝在中国历史的论述当中,长期被认为是软弱无力、不值得羡慕的一个朝代。但其实宋朝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高峰。宋朝的统治者们放弃了用武力去统一已知天下的雄心壮志,后来慢慢熟悉了、接受了在一个已知天下里有好几个天子共存这么一个局面。这里有自然因素、历史路径依赖的因素,也有人为的和一些偶然的因素。但是他们从来都不满意,因为他们根深蒂固的还是秦汉体制的施行者,还是时不时的想试一试天下大一统,难以遏制想成为真正的皇帝、真正的天子的欲望。最后促成大错,造成两宋垮台、中国黄金时代的覆灭。在中国历史上,宋朝是唯一的不是被内部叛乱所推翻的、而是被外敌所消灭的主要朝代。错就错在它的外交政策上没能始终如一,而是不时的被自己心中的魔鬼所诱惑,要去搞一个世界大帝国。
澶渊体系是中国人远远走在欧洲人前面的一个发明,没有能坚持下来很不幸。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澶渊体系和威斯法利亚体系不一样,从一开始有先天不足。辽国和宋朝皇帝都发誓,这谁要背离这个条约的话,就不得好死,结果真的是这样。宋徽宗宋钦宗被俘虏,被金国人带到北边去,比较凄惨。这也说明了在欧亚大陆的东部,其实也和欧洲、地中海各族人一样,有能力去创新一个国际体系。
滕:元朝和清朝作为异族的统治,和“中华”秩序是如何统一起来的?在中国之外的世界历史上,是否也存在类似中华秩序的思想传统和帝国实践呢?
王:中华秩序和秦汉政体一样,对所有威权统治者或者帝王们有高度的吸引力,这个吸引力是超出民族、文化、语言的限制。尤其当这套体系比较精细化、运作有效的时候,专制者们都会喜欢。所以蒙古人和清朝满族人后来是接受了这套制度,而且把它更加固化、暴力化。
清朝的皇帝非常勤政,官僚制度相当有效。所以虽然是外族统治,但是汉族的士大夫们发现没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接受,可以为之奋斗。像曾国藩、年羹尧可以为了清朝的统治奋斗终生,在他们看来,所谓民族文化的差别并不像我们今天认为的那么重要,只要有个好皇帝就可以。所谓华夷之辩,外夷如果接受我们这一套,也就成了我们,我们不接受这套了,我们就变成外夷了。雍正皇帝还特地写了一个文章来说明这个问题。这说明中华秩序和秦汉政体有着普世性的吸引力。
世界其他地方有没有这样的制度?有。比如南美洲的印加帝国、中美洲的阿兹台克、玛雅,在非洲,在地中海地区不断有一些统治者希望建立世界帝国。只不过他们大多都失败了。而在中国很多都成功了,而且维系了很久;这又和中国的生态地理环境有关,和中国帝王们有意识的灌输 有关。
滕:葛兆光教授说,中国错失了四次改变世界观的历史机遇,分别在佛教传入中国的时期、宋朝、元朝和晚明时期。天下观念的改变极为困难,直到晚清遭遇列强才不得不接受新的世界观。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的传统文明和思想系统太熟了,所以极为顽固。您是否同意这种说法?
王:葛先生说的很有道理。但我并非完全同意他的一些具体分析。我认为历史机遇只有两次,一次是在汉以后的魏晋南北朝三国时期。魏晋南北朝漫长的分裂阶段,没有能够完善化、制度化。还有一次是宋朝,宋朝的帝王统治稍微缓和些,比较仁政,很少诛杀大臣诸如此类的。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宋朝其实中国已经领先欧洲人,走在现代化的门口了,但是没有进去。我不认为明朝和元朝是什么重大改变,相反它们重新巩固了中华秩序。虽然晚明有顾炎武这些人,但这并不代表当时是个实在的机遇。
至于中国的传统文明思想体系成熟过早、比较顽固,我觉得,改革不是因为成熟早或者固化,而是因为有一个大一统的权力观或者内化的文化观,还有生态地理环境的限制。要有一个外在压力、内部竞争的政治制度,只有宋朝或者三国南北朝时期才有。 因为当年气候变化,让蒙古人南下,弄得宋朝制度没有成功。
秦汉政体和中华秩序维持很久,这个意义上说,它是达成人类政治治理的一个高峰,但这个高峰和现代性之后的高峰相比的话,只是个小山包而已。
人类政治治理制度的进化应该是永无止境的。很多朋友认为中国人比欧洲人成熟的早,未必如此。中国人只是达到了一个高峰以后,由于种种原因不再往前走了;而在欧洲,国际竞争趋势它们不断往前走。中华秩序很早就固化、停滞不前,这很难说是一种成熟,可能应该是说过早老化。
滕:从孔子那个时代开始,很多中国人觉得中国最理想的是在夏商周三代,“人心不古”,以古为好。有的人觉得儒家思想更像西方的保守主义。
知名的汉学家内藤湖南曾经写过:“(中国)只要与外国的战争战败了,总是不时地兴起种族的概念,等到自己强盛了,立刻就回到中就代表天下的思维模式。” 您在书中写道,“中华秩序经过千年实践已经深深地内化为人们心中的唯一且应然的世界秩序。”您是否认为存在着天下主义和种族主义、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不断转换呢?如何理解两者的紧张关系?
王:内藤先生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和阐述非常有意思,他对宋朝历史的高度评价我很赞赏。他说当中国的统治者对外战争失败了就开始煽动民族主义思潮,这个也确实是存在的,古今皆然,目的就是让老百姓为自己的江山当炮灰。统治者动不动就说外国人欺负、羞辱我们了,其实失败的是掌权者而已。所谓“百年国耻”,耻的是统治者们,不是老百姓。中国人民在那一百年里,取得的进步是历史罕见的,包括科学、医学、社会设施、人民的生活水平等,都是质的巨大飞跃,哪有什么耻辱可言。
过去入侵的外族有时候是比较落后的、残酷的,但19世纪中期以来,入侵中国的、或者影响中国的,代表着更先进的科学技术、组织方式和思想。他们当然也给中国带来了很多灾难,但带来更多是好处。而且一些灾难是因为老百姓被煽动起来排外而导致的后果。比如现在,对中国最有好处的美国和西方成了仇敌,经常欺负中国的俄罗斯、北朝鲜倒成了好朋友,这就说明统治者的利益和人民利益是不一致的。
滕: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对中国国内政治和国际秩序有什么危害呢?我们知道有很多追求民主的异议人士、自称自由主义者的中国人,也还有着根深蒂固的大一统思想,以及对黑人、对穆斯林和少数民族的歧视。
王:我完全同意你这个分析。中国的所谓民族主义、乃至于种族主义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是人造的、被煽动起来的。今天的中国人民其实和世界各国、西方各国没有什么根本性的仇恨,更谈不上什么根本性的恐惧。所谓 “亡我之心不死”,到底“我”是谁?其实是统治者,跟老百姓没有什么关系。
被煽动的民族主义对世界和平、对周边各国都是威胁,对中国老百姓也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在历史上被煽动起来的军国主义,老百姓有几个是幸运的?秦朝征服了六国,但秦朝老百姓的灾难简直罄竹难书。秦朝统治者们自己也没有好下场,嬴氏家族统治了秦国几百年,一个巨大的有十几万人口的皇族,垮台后全部被消灭,今天中国连姓嬴的人都没有了。谁歌颂秦始皇?只有张艺谋这种历史观一塌糊涂的人。
滕:中华秩序、天下观,这些观念和传统,与共产党现在提出的中国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一些隐秘的关系吗?
王:当然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重新解读中国历史、重新理顺这些观念,允许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精英自由地阅读和解读历史,讨论一下什么对中国最好。所谓中国梦也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好、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好,在我看来其实是不同程度的中华秩序的包装而已。且不说这些提法的逻辑有问题,其实际运作的后果将是非常令人堪忧的。老百姓会变成军国主义的牺牲品、统治者的炮灰。所谓秦皇汉武、成吉思汗,所谓康乾盛世,这全是统治者们的虚荣和威权,和老百姓真正福祉毫不相干。老百姓反而是非常痛苦的。恰恰因为世界帝国的建立,造成中国的经济文化和科技发展的长期停顿、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停顿。
滕:考虑到西藏(图伯特)、新疆(东突厥斯坦)的历史与现实,考虑到身份政治和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趋势,您对西藏和新疆争取独立的前景有什么预测吗?
王:具体预测很难。但是如果我们对历史有深刻的把握、对现实资料有充分占有的话,可以做一些不那么愚蠢的推理。
西藏和新疆当然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满清多民族世界帝国遗留下来的问题。原来的汉族王朝基本上没有统治过西藏,偶尔进入了部分新疆,但也从来没有完整统治过新疆。这两块地方长期被认为是边缘地带,价值不大。今天新疆变重要了,因为有资源;单从经济上来说,西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其实还是一个赔钱买卖:中央政府投资在西藏的钱,远比西藏能够提供的利益要高得很多。对汉民族来说,有没有西藏和新疆其实是一个政治决定,并不是我们有什么神圣的天赋权利。可以大胆的猜测一下,如果真的有一天西藏新疆都独立了,对汉人来说,甚至对生活在这两个地区的汉人来说,未必就是坏事。春秋战国和宋朝历史表明,分裂时期,汉民族和其他一些周边民族可能生活得更好。没有反思历史的中国人可能很难接受,可能会骂这种说法是卖国。其实西藏、新疆不是我的,中国也不是我的,我没法卖国。
西藏、新疆从来就不是汉族的,只不过是满族把它们带进来了。要说西藏、新疆、外蒙古都是我们的,这就像今天的印度人说加拿大、澳大利亚是我们的,因为我们曾经都被一个统治者统治过,这不合逻辑。
滕:达赖喇嘛提出中间道路而不是独立,当然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仁慈的主张,但我觉得根本原因还是中共的强大专制力量;假如中国是民主的体制、也没有这么强大的话,多数藏人、尤其年轻藏人是希望独立的。我也觉得无论是西藏问题还是新疆问题,对中国将来的民主转型都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问题。请问您对中国民主转型的前景有何看法?
王:我同意你的分析。西藏、新疆问题可能会成为中国政治转型过程中一个不太有利的因素,因为民族主义会被煽动起来。领土问题会引起很多人过于激动,然后就忘掉了什么对中国最好。
很不幸的,中国沿着自由化、民主化这个方向前进的可能性,并不是很高;尤其是内发性转型的可能性更低,就是说统治者靠自己良心发现去改变,不太可能。但是如果说中国统治者在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们可能会做一些让步,这些让步可能会一下子失控,造成真正的变化。中国毕竟经过几十年的西化,对外开放,人们观念发生了许多变化。但中国制度有超强的自我巩固能力,还控制了很多资源。比如中共的思想政治工作,可以说举世无双,极为有效。
民主化的代价,可能是新疆、西藏会离开,还可能有一些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但是人类进步的历史上,没有代价的进步是没有的,但是我们有义务把这代价降到最小程度。
滕:您能否解释一下中共最优化和中国次优化的效应?这是如何形成的?这如何影响中国的政治转型呢?中国共产党积累了天量的经济、军事资源的同时,更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统治经验。Stein Reign称之为“老练的极权主义”(精密复杂的极权主义sophisticated totalitarianism),既残酷凶狠,又有一定的灵活性和调适性,有很强的学习能力。我用“高科技极权体制”来强调它的无所不在的高效监控。
王:我在《中国纪录:评估中华人民共和国》里提到中共最优化和中国次优化。这个体制能够为专制统治者们提供一个相当强大的、有韧性的机制,但这个制度的另外一面就是它的次优化统治、次优化治理。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文化科技、环境保护和灾难控制等各个方面,表现都非常平庸,经常是灾难性的、悲剧性的状态。比如毛泽东时代。今天的中国经济发展举世瞩目,但绝大多数老百姓仍然非常艰苦,只能在一个次优化状态下生存。而统治者拥有巨大的权力和资源。这个也符合西方政治学的一个定论,糟糕的政府其实不见得马上就能垮台。启蒙运动之前,大量落后政体能够长期执政,统治者只要有足够的能力优化自己的统治,拥有足够的资源,尽管治理国家一塌糊涂,照样可以统治下去。
滕:如果中国维持目前的专制体制 ,它有可能和其他国家、尤其是自由民主国家和平共处吗?是不是实力不足的时候就“韬光养晦”,一旦自认为实力强大了就要“有所作为”、“和平崛起”,甚至搞战狼外交,四处推销“中国方案”?有人说,共产党只想维持它在中国的垄断地位和独裁体制,而不想输出革命、输出“中国模式”、称霸全球,那么在您看来,中共是否具有扩张的野心,是否企图用中华秩序来替代作为西方主导的威斯特伐利亚主权秩序?重新建立中国中心论的朝贡体系,还有任何可能性吗?
王:一个建立在秦汉政体之上的中华秩序,是所有秦汉政体统治者的梦想,也是他们的最终使命和诅咒。他们不这么做,就觉得不安全。宋朝统治者们明明活得很好,但他们非要去破坏这个制度,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样才安心。今天的中国也是这样,虚弱的时候,就韬光养晦,一旦自己觉得有力量了,或者觉得世界其他地方很烂了,就要“有所作为”了。在我看来这是命中注定的,红色基因决定的。这很不幸,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更不幸。天天让他们吃苦,又耗费无数的钱去建什么海岛、造什么航母、给非洲撒钱。中国和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只有一个可能,就是放弃中华秩序,改革政治,实行民主。
滕:国际政治上非常知名的民主和平论:战争、军事冲突基本上都是专制国家之间,或者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而极少或者几乎没有在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是不是中国实现了民主之后,对国际秩序的威胁就不存在了?像您强调的自由地学习历史、自由讨论问题之后,这种秦汉体制大一统思想就会慢慢的隐退了?
王:确实如此。中国威胁论有时候是准确的,比如说中共领导下的中国力量是一种威胁。但说中国人作为民族来说一定要征服其他民族,这不一定。当然习近平宣称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爱好和平的,在我们基因里面就有和平,这也完全不符合事实。中华民族或者说汉民族在历史上常有征服他国、屠杀他人,在晚清时还对准噶尔部实行种族灭绝。但制度如果合适了,中国人可以跟其他人一样和平共处。中国制度、观念如果不改变,那么,崛起的中国力量对世界不是好事情。
滕: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一经提出,立刻引发巨大的反响,也引起了广泛的质疑和批评,您的立场如何?您自己的论述是否被当做文明冲突论的一个例子?“中国威胁论”一直非常活跃,涌现了大量的论述,人们观察到的中国对国际秩序的威胁也的确存在,那么,如何在承认、应对中国威胁的时候,不把一个国家或文明本质化、不走向对非基督教的、非西方的文明的敌视和贬低?
王:这个问题很好,有前瞻性。这就是我在关于中国的系列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中想要探讨的问题。亨廷顿的理论是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的一种反对,他提出冲突会继续。我认为至今亨廷顿的判断还是正确的。当然他对文明的划分我是不太同意的,什么基督教文明、佛教文明、孔教文明,分类很牵强,不准确。
若没有足够的社会政治变革,中国力量的崛起害人也害己。但我倾向用“中共威胁论”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威胁论”而不是“中国威胁论”。“中国威胁论”字面上有种族主义色彩。中国老百姓没有理由要去征服世界,要用武力去屠杀别人,只是在政府的煽动和驱使下他们才会这么去做。比如支持俄罗斯等等,并不是老百姓的选择,只是领导人在那决定。
我们要认真对付这个中共领导下的中国力量的威胁,同时也不要把中国威胁变成一种种族主义的喧嚣。就像我的朋友说的“你可以一边走路一边嚼口香糖”。
滕:中国政府、共产党不代表中国、也不代表中国人民,这本来是一个常识,可惜的是很多学者、政治人物忘了这一点。而且中国共产党也利用这一点,说你们是在搞亚裔歧视、搞种族主义等等。
王:对。错误的概念用久了、用习惯了,就会对实际行动有所影响。
滕:随着人权思想的传播、自由民主制度的成功、国际法治的进步,以及全球化的发展,主权不受干涉的原则正在受到某些挑战。人权高于主权会成为国际共识吗?从更宏观、更长远的角度,福山所预言的自由民主成为历史的终结、成为世界各国唯一的制度选择,会成为现实吗?
王:人权代替主权,代表一个比较理想化的一些想法。但在人类的整个的文明历史中,最美好的观念,常常造成适得其反的结果。就是说在人权和主权之间,在普世平等自由和各国并列、竞争之间,应该建立一个平衡,而不是替代关系。换句话说,要维持威斯伐利亚体系而不是要取消它。在人权的名义下取消威斯伐利亚体系,恰恰是从从后门实现了中华秩序。
滕:我觉得,人类历史的趋势大概是朝着自由民主、朝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方向发展,当然实现这个目标还是很遥远的。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访问,也祝贺您三本著作的出版。

【本访谈发在刚刚出版的《中国民主季刊》第二期。https://chinademocrats.org/?cat=8 请下载、订阅、传播《中国民主季刊》,请惠赐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