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徐贲、张弘:警惕中国的“柏克热”和“保守主义热”造成集体思想迷思 丨燕京书评
在徐贲看来,从戊戌变法到新文化运动是一个连续的启蒙时期,因为这个时段的启蒙思想经历了一个从产生到发展变化的过程。在《与时俱进的启蒙》一书中,他研究了梁启超的国家主义后发启蒙、新文化运动与陈独秀的革命启蒙,并分析了两者区别。
而上世纪80年代,李泽厚提出的“救亡压倒启蒙”一说曾经风靡中国知识界。几年之后,李泽厚又提出“告别革命”,并引发了广泛的讨论。近年来,中国知识界对法国大革命引发的暴力反思很多,因此更推崇苏格兰启蒙运动。随着保守主义的兴起,英国思想家柏克备受推崇。但是,徐贲对于保守主义十分警惕,他尤其不希望“柏克热”和“保守主义热”成为21世纪中国的又一次集体思想迷思。
就相关问题,《燕京书评》采访了徐贲教授。因为篇幅较长,全文分三篇刊出。第一篇主要谈论启蒙的历史;第二篇主要谈论启蒙的观念,第三篇则谈论中国的启蒙。今天刊出的是第三篇。第一篇和第二篇已于前天和昨天刊出。

徐贲,美国加州圣玛丽学院英文系教授,复旦大学社科高研院兼职教授。1950年生,苏州人,美国马萨诸塞大学英语文学博士。
▌中国的启蒙运动,应从戊戌变法到新文化运动
燕京书评:你认为,“在现代世界的观念变革范围内,启蒙不仅是一种思想变革,而且是贯穿着某些现代价值观、以其为核心、并对民众形成号召力的思想解放……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这样的启蒙只发生过一次,那就是发生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的大规模思想和观念变更”(427页),时间上大致是从戊戌变法到新文化运动结束。但是,在本书开篇的序言,你就提到了1980年代初期的启蒙。这两次启蒙的区别在哪里?
徐贲:我把从戊戌变法到新文化运动看做一个连续的启蒙时期,因为这个时段的启蒙思想经历了一个从产生到发展变化的过程。现在有人说起中国的启蒙只是回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我不是这样看的。我认为,从康梁在京师开“强学会”(1895)算起,经过梁启超的《事务报》(1896)、《清议报》(1899)到《新民丛刊》和《新小说》(1902),再到与《明报》论战(1906)和《国民风》鼓吹立宪(1910),随后便发生了武昌起义,接着就是民国初期的立宪和乱政,以及以此为背景的五四运动,是一个连续的思想和观念激荡的过程。
1933年,胡适对中国现代思想的演变,提出了以1923年为界标的“两期”说:第一期“从梁任公到《新青年》,多是侧重个人的解放”;第二期则是“集团主义(Collectivism)时代。1923年以后无论为民族主义运动或共产革命运动,皆属于这个反个人主义的倾向”。姑且不论思潮的演变是否因某一时间点而截然两分,胡适所提示的中国现代思想有一个从个人主义向集团主义(或集体主义)的演变大势,一直是有争议的。就我在书里讨论的梁启超和陈独秀而言,梁启超那里更多的是集体,而陈独秀那里更多的是个人。当然,不同意者要提出反证或折衷,也都不是难事。但我关注的他们对专制的看法,不是这段思想史演变本身。
从历史上看,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期也是连续发展和变化的过程,这个时期被称为“长18世纪”,把牛顿和洛克也包括在其中。我们不用回溯得那么远,单就我们今天熟悉的启蒙哲人及其著作而言,也可以把启蒙运动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发生期,包括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论法的精神》、伏尔泰的《英国书简》《哲学辞典》《老实人》和休谟的《上帝的问题》《人性论》;第二个阶段是高峰期,包括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和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爱弥儿》;第三个阶段是衰亡期,包括莱辛、歌德和康德。
从戊戌变法到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成就主要在于政治观念的改变,梁启超在西洋文化中求变,将民权、自由、进步作为他的思想基础,以重新塑造国民道德为己任,陈独秀同样深受西方文化影响,五四运动的大旗是民主和科学。至于当时的一些文化主张,如梁启超发明的“时务体”和倡导的“新小说”,胡适他们提倡的写“白话”都是以新观念为基础,并用来推进新观念的。这就像18世纪启蒙时的美学新创,如布封的“风格即人”、狄德罗的戏剧理论、莱辛的美学理论,也都必须与当时的政治和社会新观念放在一起理解。
我们可以把1980年代的文化热看成是一次“启蒙”,也是从一些重大观念的改变来着眼的。当时有一个影响极大的刊物,叫《民主与法制》,可以说是时代观念转变的浓缩。人们对宪法、制度建设、人的价值、思想开放的意义、实事求是和知识的重要、理性思考的必要、人道主义、人为灾难(人祸)的邪恶等都有了新的认识。但是,这是一个与梁启超和陈独秀时代完全不同的启蒙,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一次昙花一现的“反思”。推动梁启超和陈独秀时代启蒙的是外强的威胁和国家的积弱,1980年代反思启蒙的推动力是在没有外部威胁下发生的人道灾难。这就像前苏联赫鲁晓夫的“解冻”时期,或者1945年后的德国人的反思一样,所不同的是,德国人的反思一直在持续。从最初的雅斯贝斯、托马斯·曼、君特·格拉斯到哈贝马斯、本哈德·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小说《朗读者》的作者),人道灾难记忆和灾难创伤一直是德国人反思的启蒙内容;但是中国不同,还未进入1990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便不得不嘎然而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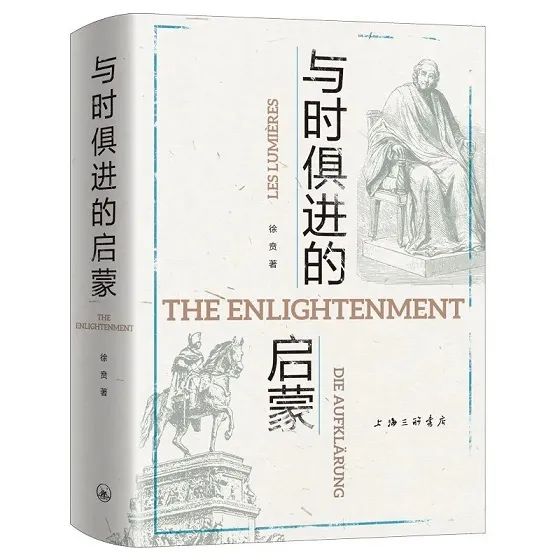
《与时俱进的启蒙》,徐贲著
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1月版
燕京书评:你认为,梁启超“从来不曾是一位自由民主主义者,而一直是一位开明的国家主义者。所谓‘开明’,也就是愿意吸纳对他的国家主义有用的西方或日本启蒙观念或理论。”(401页)梁启超共和理论暗藏着一种当时他可能没有意识到的危险,因为等待条件成熟极有可能变成无限期地拖延共和,拖延宪治和民主。(410页)那么,结合梁启超出入政学两界的情况来看,他主张开明专制,是属于知识不足,还是判断有误?
徐贲:我不认为那是因为他知识不足,他是一位学习能力极强,知识广博的学者,他说自己擅长的就是急用先学,现学现用。在他那个时代,自由民主的知识已经是很容易获得的了。不说别的,托克维尔的《论美国民主》就能提供这方面的知识。梁启超作为清末维新运动和保皇运动的主将,曾两次游历美国,第一次是1899-1900年间到了檀香山,第二次是于1903年去了美国本土。梁启超在游历中,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带着他的中国问题意识观察了美国的现实,留下了两本游记———《夏威夷游记》(又名《汗漫录》、《半九十录》)和《新大陆游记》。他对于美国的政治形态印象很差,认为美国人“迷信共和”,造成两党政争激烈、官吏贪黩、市政腐败,有的大城市简直成为 “黑暗政治之渊薮”。他看到的都是黑暗面,见识未必比今天某些“知美派”人士高到哪里,他与托克维尔访美期间看到的完全是两个黑白分明的世界。
所谓“知识”,经常是特定知识者根据自己的立场和需要所收集到一起,并用来支持自己立场的信息。梁启超主张开明专制,对共和反感,看到的自然是共和之弊。如果说他是判断有误,那也是对开明专制的判断有误,连带对共和的判断也就有误。今天,有人说互联网上的信息太多太杂,影响了人们的正确判断,其实问题在于一个人自己是否有判断的能力,而这个判断能力是与他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联系在一起的。今天,专制和共和孰优孰劣,伦理和政治的理由又是什么,仍然在以变化了的形式渗透在许多思想和观念的讨论中,包括对启蒙观念的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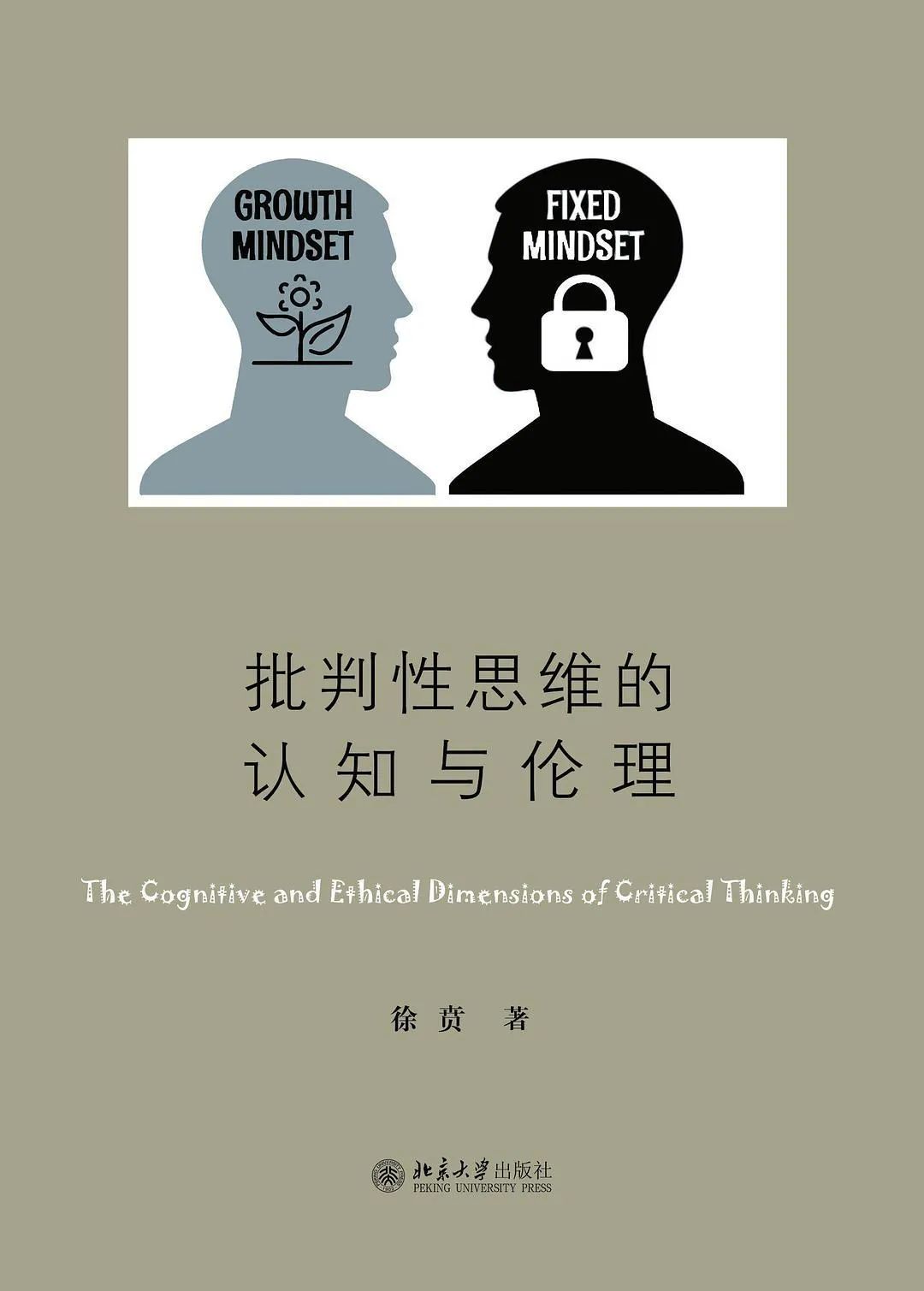
《批判性思维的认知与伦理》,徐贲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2月版
燕京书评:你认为,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首选的是自由和平等的人到价值观,而不是“爱强国爱强种”的国家主义,这比梁启超高明。(443页)但是,陈独秀没有能告诉国人,民主与专制的区别不在于两者不同的伦理,而在于它有不同的价值观。(450页)此外,陈独秀还低估了专制对民主的顽固阻力。那么,作为启蒙者的陈独秀,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不足?
徐贲:陈独秀是一个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者,他和集体主义者的梁启超不同,这注定了他在后来党派政治中的失败。我在书里说,他倡导的“伦理觉悟”或“伦理革命”,也包括政治价值观。这样来联系政治和伦理,也就是倡导一种德行的政治,与阶级斗争的政治自然是有矛盾的。18世纪启蒙哲人倡导的,也是一种德行的政治;因此,他们的政治诉求实现之路艰难而坎坷,而且时常是行不通的。政治问题需要用政治手段来解决,独裁者不会因为有人对他讲自由和宽容的伦理正当性就改变他的蛮横、残忍和专制。作为启蒙者的陈独秀,他的理想主义书生本质使他不可能对残酷的政治斗争有充分的认识,他怕在道德上弄脏了自己的手,他无法让自己成为一个彻底的马基雅维里主义政客。
陈独秀的自由启蒙思想与他的民主思想是一致的,贯通于其间的是反专制,一直到他1942年5月去世都是如此。1949年4月14日夜,在行驶在太平洋上的轮船上,胡适重读《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感到无比激动,写下一篇长文,作为《陈独秀的最后见解》的序言。他对“死友”陈独秀的最后见解由衷赞佩,指出“独秀的最大觉悟是他承认‘民主政治的真正内容’有一套最基本的条款——一套最基本的自由权利——都是大众所需要的,并不是资产阶级所独霸而不是大众所不需要的”。
胡适在序言的最后说:“因为他是一个‘终身反对派’,所以他不能不反对独裁政治,所以他从苦痛的经验中悟得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新文化运动的时候,陈独秀反对的那个专制是传统的专制,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似乎已经足以概括这个专制的所有罪恶。在他走向生命终点的时候,在他留下最后论文和书信(《陈独秀的最后见解》)的时候,他反对的已经不是孔家店的专制,而是他在新文化运动时根本始料未及的一种新的专制,一种从推翻旧专制的革命里产生出来的新专制。研究专制历史的美国学者埃里克·加尔顿称之为法国革命式的“革命专制”(revolutionary despotism)或斯大林主义的“ ‘无产阶级’专制”(“proletarian” despotism)。陈独秀在反对新的革命专制时,已经是一个对历史发展负有责任的反思者,而不再是一个没有包袱,自以为可以凭着革命激情去引导历史新进程的启蒙者了。然而,正是他对革命专制的反思,成为对我们今天比新文化启蒙更宝贵,也更重要的启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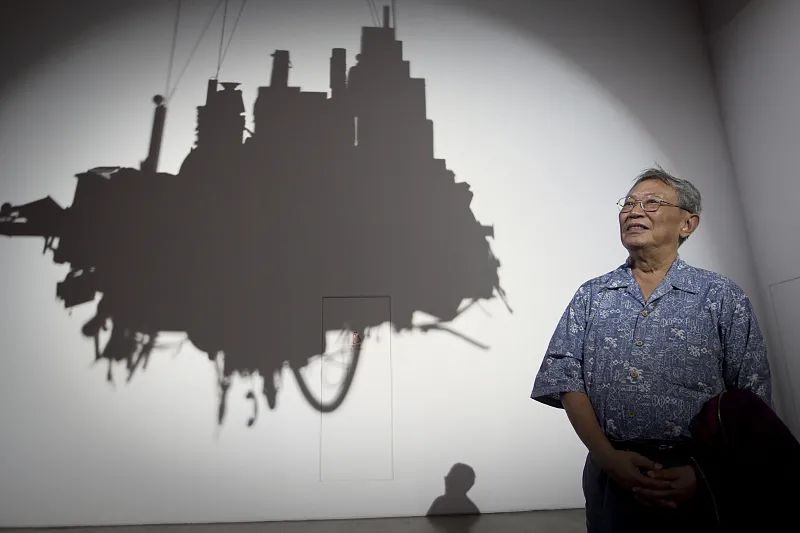
著名学者李泽厚(来自视觉中国)
▌李泽厚的误区:将个人自由与国家集体对立起来
燕京书评:1986年,李泽厚先生发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提出了“救亡压倒启蒙”的著名论点。但很多学者不赞成他的观点,新革命史学者王奇生认为,在当时人眼中,新文化运动本身就是紧接着辛亥政治革命之后的一场“思想革命”。思想的日趋激化,正是这场思想革命的特质,并不存在一个“救亡压倒启蒙”的转变。从思想革命转入社会革命是顺理成章的发展(《高山滚石: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连续与递进》)。
徐贲:我看过一个材料《舒衡哲口述》,舒衡哲(Vera Schwarcz)是一位我也认识的美国汉学家,她说,“救亡压倒启蒙”这个说法是她首先提出来的,后来给李泽厚借去不还了,“我刚刚认识李泽厚的时候,……马上感觉到我们有许多的共同语言。……李泽厚当时非常愿意和外国学者交流他的思想,我也向李泽厚介绍了我的新看法。那时我还没有出版《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我给李泽厚讲了我思考的“启蒙”和“救亡”的差异,尤其是两者存在冲突的看法。30年代抗战时期知识分子为了救国而放弃启蒙,因为爱国,所以知识分子自愿放弃,而不是中国共产党要求知识分子放弃他们的启蒙运动。这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交已经变成了新启蒙运动。……李泽厚说的“救亡压倒启蒙”是用了我的想法。” (第121—124页)但是,也有人引用李泽厚的著作证明,这个说法是他的原创。
为这件事,我曾去信问过舒衡哲,她对我说,“救亡压倒启蒙” (“national salvation overwhelmed enlightenment.”)是一件“不足道”和被“政治化”的事情(petty.... and political)。为什么说“政治化”呢?舒衡哲是肯定和倡导启蒙的,在她附给我的一篇她写的文章最后,她引用了加缪说的西西弗斯神话故事,她把仍在中国坚持启蒙的人们比喻成故事里的西西弗斯:“他们努力向高处奋斗,足以使人充满希望。……我同意阿尔伯特·加缪的观点。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启蒙任务。诚然,我们必须想象,西西弗斯在(一次次失败后,又一次次)再挣扎着爬上山的时候,他的心里充满了喜悦。”这种高昂的语调,与李泽厚的“告别革命”和暗示救亡有理由压倒启蒙,是完全相反的。
舒衡哲给我附来的文章是要在瑞典发表的,她在文章里把与李泽厚的事情原委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因为版权关系,我这里就不复述了。其实,“救亡压倒启蒙”并不是什么至理名言,原创不原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说法里面是否有对我们今天还有用的“启蒙”观念;还有,从对我们今天有用的启蒙观念来看,这个说法是否能站得住脚。
这句话在李泽厚那里,基本上是这个意思,“迫切的救亡局面,把国家富强问题推到当务之急的首位,使严复愈来愈痛感‘小己自由非今日之所急,而以合力图强……为自存之至计’”。也就是,救亡是国家大义,启蒙乃“小己自由”。这样来理解“启蒙”,显然与我们今天对启蒙的理解相去甚远。我们今天理解的启蒙是学会如何自由、理性、宽容和人道地思考,摆脱种种权威强加于个人的桎捁,摆脱人加于自己的愚昧和盲目。一句话,当一个既不受人惑、也不自欺的明白人。这样理解启蒙,虽然是以个人为中心,但与“国家”和“集体”并不相悖,也不对立。
就拿“救亡”来说,国家危亡之时,需要扩充兵力,征调物资,国家以“救亡”为正当理由,可以像杜甫《石壕吏》那样强行抓夫征粮,也可以理性地诉诸个人的觉悟和爱国心,在情绪上影响他,“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这样可以让个人自觉自愿地把当兵打仗这样危险的事情当做他的自由选择。对青年进行爱国启蒙——国家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而是每个人自己的家园。这样的启蒙不是有助于救亡吗?为什么非要压倒它不可呢?
“救亡压倒启蒙”这一说法里的“启蒙”,包含着一种错误的“个人自由”必然与“国家需要”(或“集体”“组织”需要)对立的想法,把启蒙和救亡都当做了被组织和动员的“任务”,哪个任务更迫切,另一个就得让道,闪到一边。就像“文革”的时候,革命运动来了,学校就得停课。其实,启蒙与救亡之间根本就没有这种谁该给谁让路的关系。启蒙就是启蒙,救亡就是救亡,也许有相关性,但没有因果关系。
对个人来说,确实有人选择放弃个人的自由理念,投身到必须放弃个人自由,严格服从纪律的组织中去。这是一个原因复杂的选择,有的人清醒地知道自己选择的性质,但也有的人则是稀里糊涂地被他人“做了思想工作”。虽然看上去是同一个行为,但却并不都是同样的“明白”或“不受人惑”。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信仰的转变,与是否受到启蒙——从别人那里得知“道理”(或理论)——并没有必然的关系。
我在前面提到的匈牙利作家阿瑟·凯斯特勒就有过这样的亲身经历,他放弃了自由的理念,参加了共产党。对这样的转变,他有一个深刻的体会,“一种信仰,不是由理论得来的,一个人(主要是知识分子)并不会只是由于他人的引导或劝谕,没有自己的经验感受就轻易去信仰什么。理论可以为由信仰发生这一行为辩护,但必须于信仰行为发生以后,劝谕可以有一部分作用;但这一部分作用只限于转变的信仰已经成熟,自觉的心情已经达到顶点,既成之局,无所犹豫。”他的这个体会让我们看到,即使在个人的层面上,为什么要放弃个人自由,也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不可能是简单地因为意识到某项“任务”特别迫切就能做出的选择决定。

汉学家舒衡哲
燕京书评: 到90年代,李泽厚先生提出“告别革命”,因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不断革命,造成了中国的大灾难。李泽厚先生提出“告别革命”,也是痛定思痛的产物。但是,邹谠提出,“革命是告别不了的”,革命的因素存在,就会产生革命。是否能告别革命,并不是人为的决定。章开沅先生也认为“无法告别革命”。《与时俱进的启蒙》显示,梁启超警惕革命,担心“革命不得共和而得专制” ,后来的结果如他所料,出现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那么,你怎么看待李泽厚先生的观点?
徐贲:如果不知道什么是“革命”,又如何对本来就笼统的“告别革命”发表看法呢?所以,首先要讨论的是“何为革命”的问题。
阿伦特写过一本《论革命》的小册子,我对此写过一篇《公共视野中的“革命”和“政治自由”》的文章,介绍她对革命的看法。她是一个曾经深受纳粹统治之害的思想家,对极权专制有刻骨铭心的认识,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里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性质和灾难后果也有精深的剖析。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在德国也可以说是一场激进的“革命”,阿伦特亲眼目睹它如何从一场深得人心的社会运动变成地狱般的人道灾难;按照李泽厚先生的逻辑,阿伦特定然是会主张告别革命的。其实不然,阿伦特并没有放弃革命,而是提出了“畸形革命”和“失败的革命”的问题。
在《论革命》中,阿伦特认为战争和革命决定了二十世纪的面貌,而革命的目的,过去是、而且一直是自由。革命是我们不可避免的面对开端的政治事件。阿伦特把革命看作是一种表现人类特殊能力的形式,人类有能力在任何逆境下重新开始、自由行动、创造真正的公共领域。革命首先与历史意识的发展相关。革命包含这样一种观念,即历史会突然开启一个崭新的、前所未有的进程,一个新的故事,一个光明的未来。并非所有的政治剧变都是革命,因此,有没有革命就要看有没有在历史存在中开创未来,缔造社会的新生。革命的主要动力是对自由的渴望,这种渴望成为人类创新能力的价值动力。
革命的创新能力在于,它要确立的不是“另一个”政治秩序,而是“另一种”政治秩序。真正的革命一定会创造另一种新的权威,而不只是另一个旧式权威。权威是阿伦特考量革命意义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极权主义的施虐,让阿伦特看到了现代政治的空前危险,那就是,当传统权威一下子崩溃的时候,革命企图以某种超然、绝对的神圣法则来填补传统权威的空虚,结果造就了与人的自由初衷完全违背的新专制压迫形式。其中最严重的就是史无前例的极权专制。这样的革命是坏死的革命,因为它糟蹋了革命的创新承诺。阿伦特认为,革命并不都是坏死的革命,建立一种与自由相一致的政治权威,最终的希望仍然在革命。她在《什么是权威》一文中指出,“现代革命付出巨大的努力,要通过缔造新的政治实体来恢复在以前许多个世纪中曾将……尊严和伟大赋于公共事务的东西,”那就是与个人政治自由相一致的公共权威。
阿伦特认为,现代革命中最成功的例子是美国革命。美国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建立了一种与自由相一致的权威形式。这种权威对人有制约力,不是因为它能诉诸于某种哲学原理或神圣法则的强制力,而是因为革命的缔造行为(它是一种自由行为)本身足可以让人们知道什么是自由行为,什么不是自由行为。至少美国革命的经验证明,革命不一定带来奴役,而且,革命还能产生一个保障自由的制度,既然如此,也就不能笼统地告别革命了。

埃德蒙·柏克。(来自视觉中国)
▌不要让“柏克热”和“保守主义热”成为21世纪中国的又一次集体思想迷思
燕京书评:最近一段时间,苏格兰启蒙运动受到国内学者的推崇,而法国启蒙运动则遭到一些学者的批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些人将法国大革命中的暴力血腥归罪于法国启蒙运动。但是,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战争传播了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并摧毁了一些欧洲国家的封建王权。另一方面,法国大革命的血腥,与20世纪革命的血腥也不可同日而语。如果一味强调法国大革命和法国启蒙的缺陷,那也会有很大的谬误吧?
徐贲:反对或贬低法国启蒙的一个主要理由,是它煽动了暴力流血的法国大革命。我在《与时俱进的启蒙》里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有详细的讨论,这里就不重复了。有一点是我在这里想要强调的,那就是,与其他国家的革命一样,经济和政现实是直接引发民众反抗的原因,而哲学家的议论则不是。法国历史学家达尼埃尔·莫尔内在《法国革命的思想起源》(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10月版)里指出,在民主反抗发生的时候,“思想的介入是非常罕见的现象,(政治原因)的领域就是人民的不满情绪。当人民饥肠辘辘或受寒冷折磨的时候,他们不需要哲人诅咒这个把他们逼入人最悲惨境地的社会。”民众参加革命并不需要明白革命的道理,但却一定不能缺少他们因为被压迫痛苦而怀有的愤怒。
莫尔内还说,“可以肯定的是,发动革命的不是最穷苦的阶层,他们也不可能发动大革命。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以喜悦的心情接受大革命,他们支持大革命,并在几乎所有地方为大革命提供了决定性力量。他们没有宣战,没有产生战争领袖,但他们组成了军队,没有这样的军队,大革命将是不可能的,或不是这样的面目。”革命中民众的激愤,不只是一种情绪,而且是一种有着对不公不义认知的情绪。莫尔内的结论一语中的,在今天仍然适用:“人民激愤的原因,首先是他们的苦难。”
燕京书评:近年来,英美保守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你强调,英国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柏克的思想价值在于他对自由的执著,而不在于他对法国革命的全盘否定(119页),柏克持有这样的观点,是因为他要避免英国发生类似的革命。在政治上,很多学者和你的观点基本一致,即保守自由的传统。在文化上,文化保守主义无法摆脱启蒙所要批判和摧毁的那些价值观——诸如官本位、等级制、家长制等。如果说,传统一直变动不居,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自由和传统,并且将自由塑造为一个在政治和文化上都可以保守的新传统?
徐贲:我这本书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想提醒一下国内思想界的一些朋友,不要让“柏克热”和“保守主义热”成为21世纪中国的又一次集体思想迷思。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头10年的“后学”,已经有过这样一次集体思想迷思了。上一次是左派以为“后学”为他们指明了方向,这一次是自由派以为“保守主义”为他们找到了出路,二者看上去南辕北辙,其实都是因为看不到现实改革的出路,在为自己画饼充饥。
什么是“保守主义”呢?“保守主义”在英语里来自conserve一词,也就是“保持”和“不丢弃”的意思。这是一个中性的用词,并没有褒贬的意义。作为一个政治术语,它的意思是,反对激进,不要冒进,更准确的说,不要冒进,以免失去什么。这里的关键是那个害怕失去的“什么”,它可以是柏克所特别珍视的自由,也可以是某些人把持着不肯放手的特权或专制权力。由于害怕失去的东西不同,不同的保守主义含义会完全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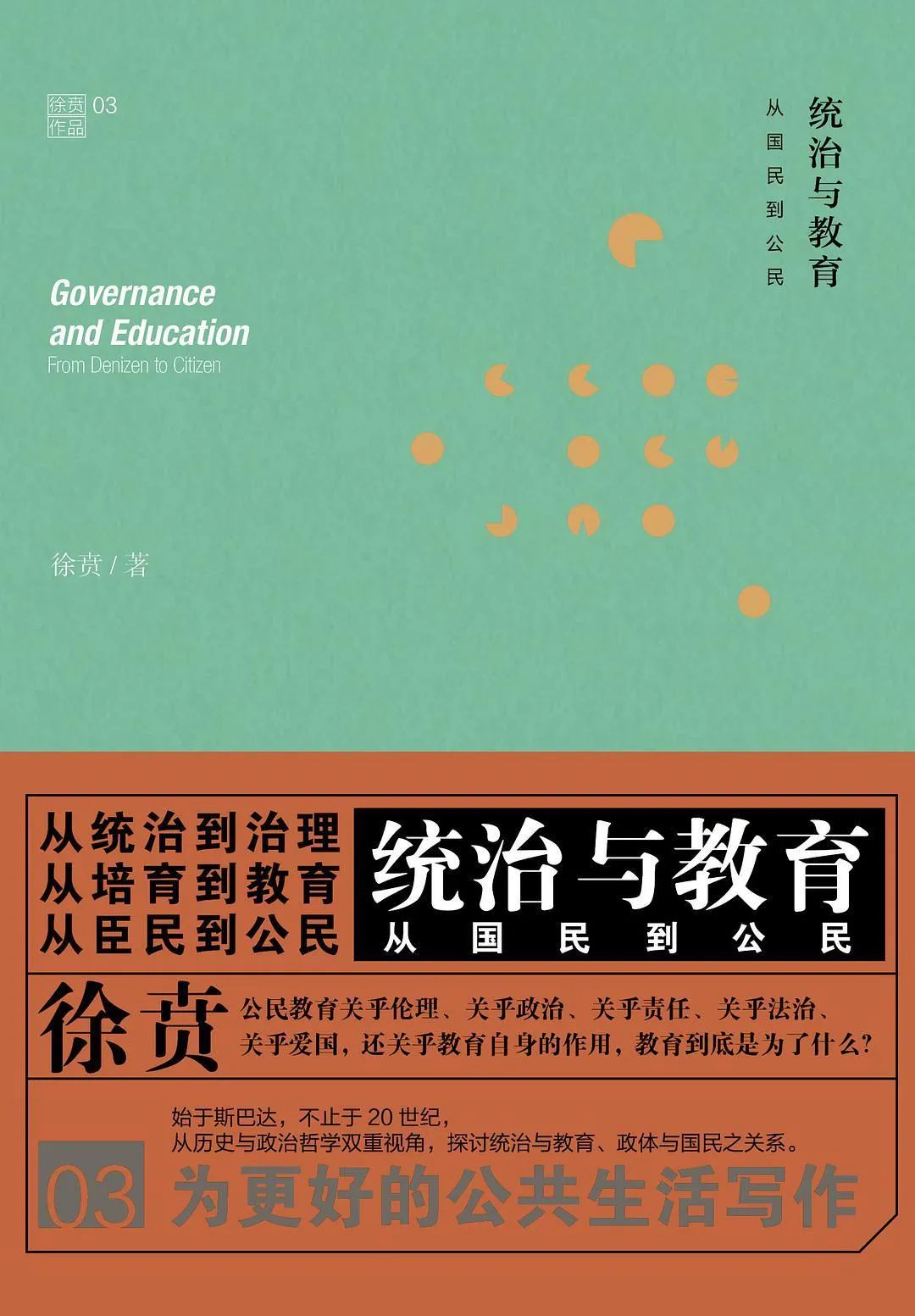
《统治与教育》,徐贲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1月版
柏克要保持或保守的,是英国人的那种来自他们古老政治文化传统的自由;英国的宪制和自由政治文化传统给了英国人民比任何其他国家人民都要更多的自由,所以柏克要保持它,守护它,保持和守护就是保守。柏克的保守,有积极的政治理论意义的自由价值,不在于保守本身。
这种自由不是理想式的自由,而是存在于英国传统宪制中的,因而有制度保障的自由。在这个宪制中,君主权力受到限制,但君主仍然是国家政治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失去了稳定,人民的自由就会受到危害。柏克认为法国废除君主的革命是倡导理想式的自由,这样的自由只会带来不可预测的灾难,英国不需要这样的自由,英国应该保守自己自1688年“光荣革命”以来的传统资源。
今天在中国打出了“保守主义”的旗号,还有提倡新儒学和儒家什么的,我想问的是,你们要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里保持什么,守护什么?是自由,还是专制?是普通人对自己权利的认知和坚持,还是奴性和愚昧?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在中国主张保守主义,尤其是用柏克来主张保守主义,是没有意义的,根本就是无的放矢,甚至更糟糕。
当下的“柏克热”里,还有一个欺骗性的神话:柏克反对法国革命,但支持美国革命。因为他认为,法国革命的“理性”——尤其表现在1789年8月26日颁布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简称《人权宣言》)——“必然”导致革命的暴力、残酷和血腥镇压,而美国革命则成功地避免了这样的悲剧。
那么,柏克真的支持美国革命吗?历史的事实是,柏克同情北美人独立的自由要求,但他并不支持美国革命。然而,13个美洲殖民地从英国独立出来,这并不是美国革命的最实质的部分,更不是美国革命的全部意义所在。美国革命的意义,在于它创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共和国,而这个美洲共和国与柏克所竭力要维护的英国混合君主制是完全不同的,与柏克同样要维护的法国君主制更是南辕北辙。
英国皇家学院(King’s College)历史教授马歇尔(P. J. Marshall)在《什么时候革命不是革命?柏克和新美洲》(When is a Revolution not a revolution? Edmund Burke and the New America)一文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柏克同情美洲殖民地人民的自由诉求,“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柏克支持美国革命呢?”马歇尔教授的回答是否定的。
柏克以为,美国人反对英王乔治三世侵犯他们的自由权利,只是为了维护英国人的君主立宪传统。开始的时候,也许有不少北美人确实如此。但是,这并不是北美人的全部政治诉求,他们的政治诉求很快超越了所谓的“维护英国君主立宪传统”。1776年后,在13个美洲殖民地颁布的一些早期各州宪法就已经证明,柏克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因此,1777年1月,柏克警告美国人,不要使用“未经尝试的政府形式”。真正的自由,只能通过“在当前有限的君主制下”与英国联合来维持。美国人没有听他的,他们要建立的正是令柏克感到不安,甚至害怕的一种“未经尝试的政府形式”,那就是建立一个根本不需要国王的人民共和国!
共和是一个与英国统治的旧殖民秩序和君主制截然不同的新事物,是在柏克的保守主义里不存在的东西,对我们今天来说,没有共和,没有真正的共和,柏克保守主义里的“自由”又能意味着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