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賭與賭城以外:澳門博彩業發展的「另類」解釋
作者:遠東釣魚郎(嘗試以社科方法研究歷史的兩面不是人)
在此不定期出現的新系列中,我將以自己於知識及現實上的興趣,轉介/轉譯與澳門有關或無關的最新人文社科研究。
相比過往以時下議題出發,引介相關學術研究討論及詮釋現象的寫作取向,本系列所關注的,則側重於開拓有關澳門,或來自其他地方,但之於澳門有相當啟示的知識前沿,對象亦不限於學術研究的「完成品」,同時亦關注各類「半成品」、「構想」,或是研究者的表述等。總之,這是一個出於私心,但又希望對讀者有意義的新欄目。
本系列的第一篇文章,正好來自一個「偶遇」。話說一個最常收聽,介紹各種人文社科最新出版的Podcast頻道New Books Network,最近邀請了澳門大學傳播系教授Tim Simpson,來介紹其最新英文著作Betting on Macau:Casino Capitalism and China’s Consumer Revolu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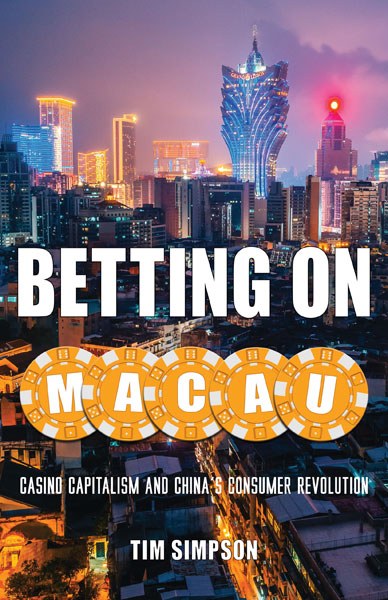
在長達一個多小時的節目中,Simpson重新把澳門賭業的興起及發展,放置於全球政治經濟的背景中審視,提出了一些相當有趣,但「我們」可能從未想過的視角(包括月初逼爆澳門的遊客)。在私心覺得澳門讀者或有興趣,但又未閱讀過全書的情況下,摘錄並引介其Podcast內容,或許不失為一個折衷的辦法。
不只是澳門的博彩業
說起澳門博彩業的「發跡史」,相信各位讀者對以下情節絕不陌生:在葡治末年管治失效,百廢待興的背景下,特區政府於二千年代初開放賭權,多家外資企業陸續進駐澳門並大興土木。此「死水埠」亦因而搖身一變,成為「世界級」的博彩城市及旅遊勝地,並造就了最「黃金」的十多年。
在疫情過後回顧澳門博彩業的「輝煌」歷史,彷彿相當遙遠又帶有諷刺意味,但Simpson告訴我們,如果仔細思考澳門經驗的話,則可發現在賭背後,事實上有著相當深刻的意義:澳門之所以得以發跡,正正是多種全球性因素,於九十年代末至二千年代初匯合而成。
簡單來說,葡萄牙人在1999年離開澳門,以及後續的制度設計及開放賭權,剛好遇上了中國資本主義的轉型。如果1980至90年代是中國得以憑藉其低廉的勞動力,而得以擠身成為「世界工廠」的話,那麼在踏入二十一世紀以後,中國往資本主義方向的進一步發展,則催生了一種對澳門人而言熟悉不過的主體:「遊客」的誕生。

如果回想二十年前,我們或會記得當時的澳門街頭,並不如今天般,大街小巷遍佈各路遊客。僅是在賭權開放後,中國大陸同時開放大陸居民到港澳「自由行」,澳門才逐漸出現今天般排山倒海的場面。
但遊客的出現除了與政策開放相關外,還牽涉了其他因素。事實上,「旅遊」此一行動本身就存在著許多前設。除了政策「容許」你離開(試想像疫情期間的澳門)外,旅遊亦要求一定的消費能力。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之所以有「工人」能搖身一變成為「遊客」,關鍵在於城市化的過程,使一群具有能力及意願消費的群體開始出現。
而「自由行」政策,則順理成章地把這些城市新貴,往香港及澳門的方向「推」,因此兩個新的特別行政區,自然地成為了大陸遊客的目的地。澳門作為中國唯一博彩合法化的地方,外資剛好帶來新鮮的資本及嶄新的娛樂模式,使得澳門剛好(重新)成為中國與資本主義世界接觸的交點。
簡言之,澳門「神話」事實上有賴於多種因素於二千年代初的聚合及相互作用,才得以成為可能。正正是殖民主義的結束及後續的制度安排、全球化與中國的相遇,以及中國往消費社會的發展,三者的疊加作用,促成了澳門經濟的爆炸性成長。重新把這些因素放置進澳門的既有敘事中,或能夠提供我們重新思考其不常被發現的,於全球網絡的位置及重要性。
對倒澳門
至於另一個澳門常被認識的面貌,就是位於世界另一方的「東方拉斯維加斯」。作為同樣以博彩業聞名的城市,澳門博彩業可謂把拉斯維加斯的經驗「照辦煮碗」。除了引入的外國資本正是拉城的美國博彩企業外,澳門博彩業的空間佈局亦參照了拉城的「大道」(Strip)模式。路氹城區及「金光大道」(Cotai Strip)之所以由沼澤地變身為集豪華賭場及渡假村於一身的地段,最初亦是由美資企業發起的構想。

雖然雙城看此雷同,但澳門與拉城的一個關鍵差異,則在於旅客來臨此地時,到底會做甚麼。對到訪拉城的遊客而言,他們的目的,並不僅僅在賭場中一擲千金。「賭」對他們而言,只是拉城其中一項節目。除此以外,拉城還提供了各種不同的娛樂:諸如各種豪華餐廳及酒吧,提供另一種狂歡體驗的夜總會,以及各種不同的表演及休閒活動等。甚至「拉斯維加斯」本身,即是一個旅客爭相到訪的景點。
雖然澳門亦有各種滿足遊客各種需求的設施,但旅客卻並非因為餐廳、酒吧,或精彩表演而「慕名而來」。到訪澳門最主要及直接的目的,依然是在於賭檯前一較高下。這種「賭及只有賭」的模式,雖然重新令澳門登上「世界舞台」(世界級賭城),但這亦鞏固了一種只有「賭」的刻版印象。
而問題亦遠非只是「觀感不佳」;賭的一支獨秀,同時亦揭示一個根本的問題,那便是除了「賭」以外,澳門還有何吸引之處?雖然經濟多元化在今天已驟然成為官方議程,但多元化的具體方向及成效,似乎還有待觀察。
即便在「賭」上面,澳門與拉城亦有截然不同的賭法。在拉斯維加斯的賭場中,主要的博彩遊戲是角子機,或是如撲克或二十一點等桌上遊戲。雖然「賭博」此一行動本身,在相當程度上攸關於運氣,但相對來說,這些遊戲是「有跡可尋」的:賭客可以透過特定技巧進行遊戲,或是閱讀或影響其他參與者的想法或行為,取勝或減少落敗的機會。

但在澳門佔大宗,並產生最多利潤的遊戲,則是「百家樂」。相對其他遊戲而言,「百家樂」是一種「猜」成份居多的遊戲:玩家估計莊家及閒家所持有牌中的數值,並投注較接近特定數值的一方而獲利。
而因為「無跡可循」的關係,「百家樂」對賭客及賭場而言,皆可謂禍福難料:運氣意味著賭客有較高的機會勝出,卻無從控制影響賭的過程本身;而賭場方在一定的時間內,亦難以預計於 「百家樂」賭檯上,到底會發生甚麼事(雖然除著次數的增加,賭場依然具備較高勝率)。
這種規則簡單但「緊張刺激」的遊戲,卻成為了澳門龍頭產業中的主要收入來源,其實亦代表著澳門經濟的特質:無可預測的機會及風險,取決於「運氣」而非「技巧」、被「外力」改變多於內生的更迭。
未來是?
在節目最後,Simspon教授被問及澳門未來的發展方向。正如我們所熟知的那樣,在經歷疫情的沉重打擊後,特區政府正嘗試在賭以外,尋找澳門經濟的新方向。Simpson則指出,政府雖然有各種鼓勵多元化或創業的政策,但歸根究底,澳門唯一的優勢,至少在目前仍然在於「合法」的賭博業。
而我聽畢整集節目以後,對於澳門未來的結論似乎是:意識到澳門賭業受制於產業結構本身,以及諸種結構性因素,因此亦更受各種不確定性的牽動。如果外在力量對澳門有著如此巨大的影響力,那麼「分散投資」到底有多大幅度能達成其宣稱的目標,似乎仍然是一個相當大的問號。
#文章篇數:1️⃣7️⃣2️⃣
--------
👉 講座六月場:中國澳門賭場資本主義的社會與政治:對經濟多元化的啟示(盧兆興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常務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