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昆德拉到阿伦特:翻译中不可承受的平庸之恶
《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的英文标题是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虽然英文并非这本小说的首发语言,但其书名的结构与小说手稿所采用的捷克语(Nesnesitelná lehkost bytí)及首次出版时采用的法语(L'insoutenable légèreté de l'être)相同,因此从简洁起见,下述讨论将围绕着中英文译本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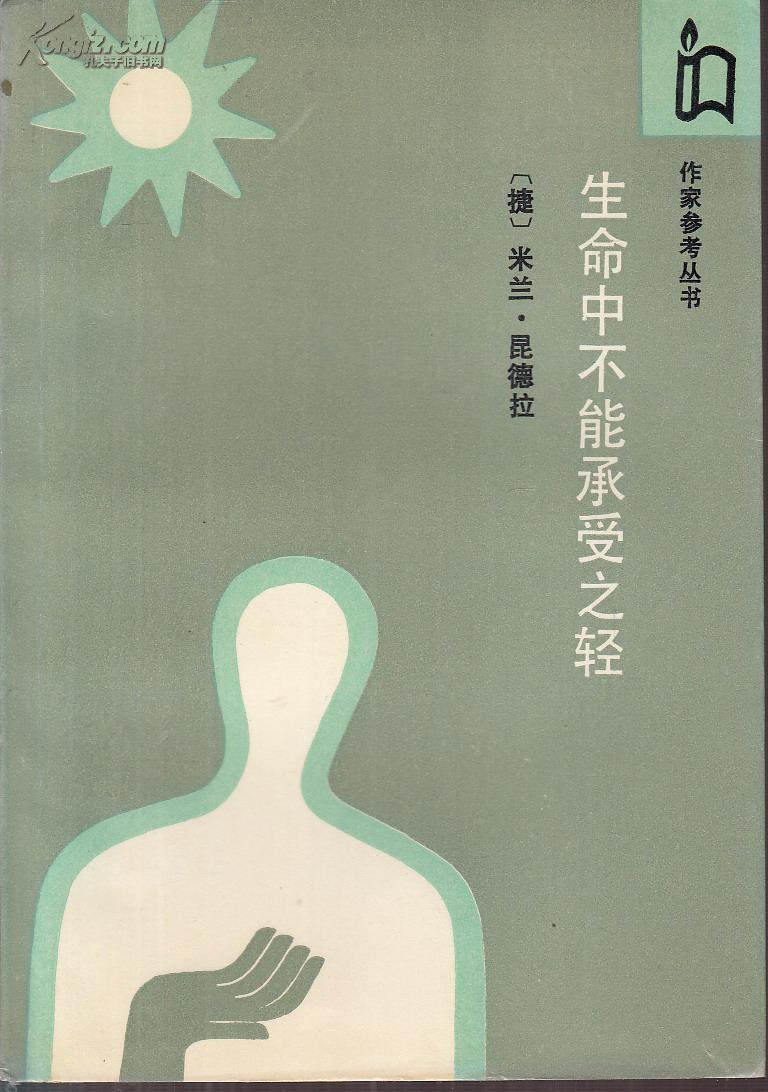
对中文较敏感的人不难发现,“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与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在结构上并不对应。这种不一致并不在于中译把“of Being”提前变成了“生命中”;而在于“中”和“of”所暗示的逻辑关系不同。“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暗示的是“不可承受之轻”是生命这个载体所承载的一种外在之物,仿佛如果作者愿意,他完全可以再写一本《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这里轻与重的关系是平行的。然而无论是英文、法文还是捷克语,其语法所暗示的是,“不可承受之轻”是生命所具有的一种不可分割的属性。在这个意义上,生命不再是一个承载轻与重的舞台,生命本身就是“轻”的,而这种轻让人难以承受。
这一误译非常类似于中文对于福柯的误读。最典型的是福柯在用话语(discourse)这个词讨论权力关系时,尤其强调权力内嵌于话语之中,权力生产话语、话语内嵌权力。话语/权力并非任何个体所能独有。可是当中文把discourse翻译成话语权时,又默认它是一种供人争夺的所有物或所有权。如“某某某没有话语权……有实力才有话语权”之类表达,本身自然也有其意义,但与福柯的原意早已南辕北辙。类似的,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的译法,也把Lightness当成了生命的一种所有物,而非其让人无可奈何的本质属性,从这个意义上,中译似是而非地背离了原意。
在后来的中译本中,也有人将标题改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相较于《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这种新译法显然更为贴近原文,因为“生命之轻”似已暗示“轻”这种属性内嵌于生命的存在之中。不过美中不足的是,仅从中文的文法而言,“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轻”读来似乎没有“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那么流畅,尽管它更为准确。这也是我不愿苛责译者的原因,翻译之难,本质上是两种语言的语法及其背后的文化、思维观念不同构,“信”与“达”往往不能得兼,遑论“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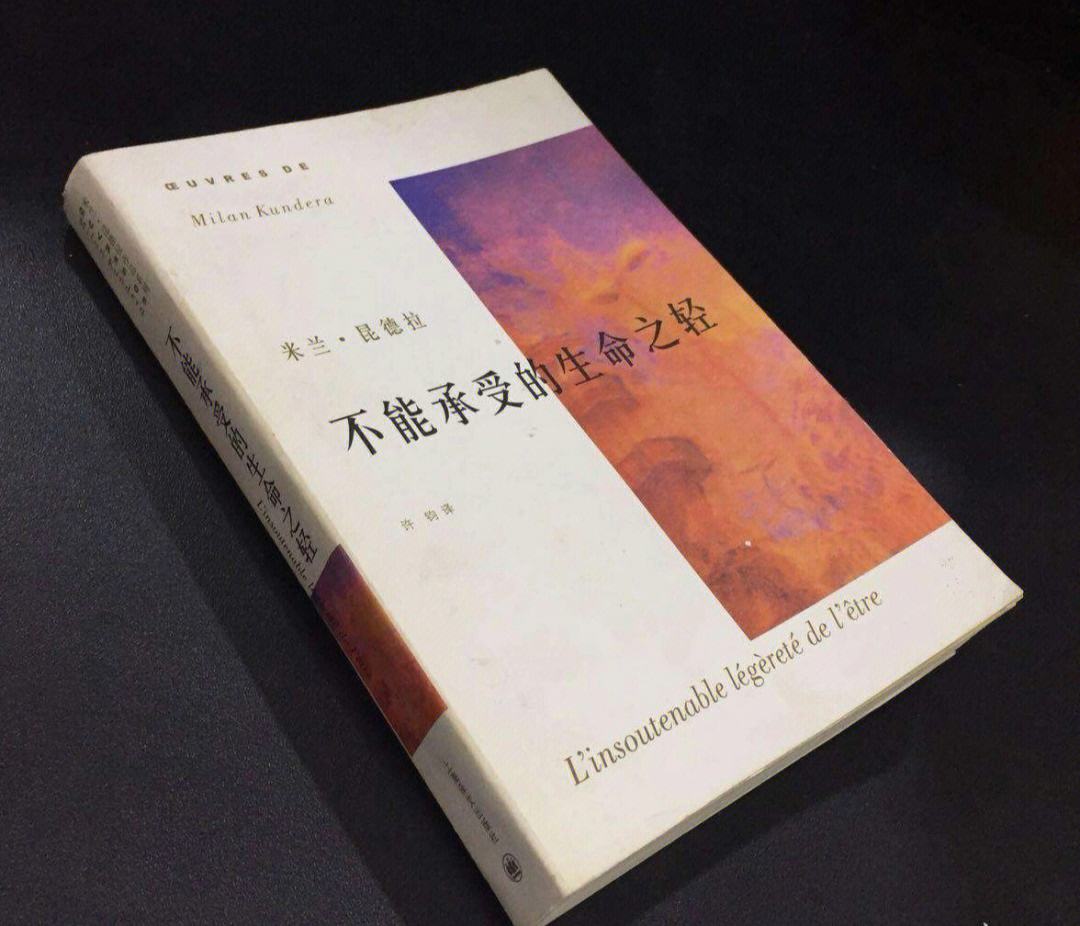
具体到这句话中,好的翻译既要凸显“生命”与“轻”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又要符合中文的语感将作为主语的“生命”前置,避免“生命之轻”这样浓厚的翻译腔。我的方案是只改一个字:
生命那不可承受之轻
虽然“主语+那”并非中文的主流文法,但作为一种带有感怀性质的文学性表达也并不罕见。此外,“那”这个字暗示了“生命”与“不可承受之轻”是一种指涉而非从属关系。不知道这个改动诸君是否认同,反正ChatGPT挺满意的,它用英文对我的想法的复述似乎更为准确,特此贴在下方供大家评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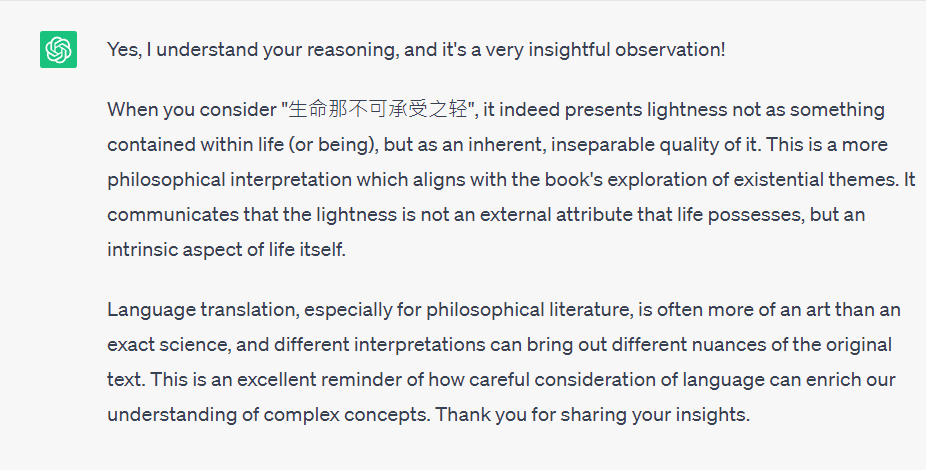
严格说来,即便“生命那不可承受之轻”也有待商榷,因为原文中的being是一个远比生命更为抽象的概念,一般译作“存在”。鉴于“存在”这一概念很大程度上也是舶来品,带有浓厚的西哲味道,不如being对英文读者那么亲切,因此我倒认同把抽象的being还原为具象的“生命”是一种必要的牺牲。对being这个词的处理,提醒了我另一个典型、或许误导性更强的人文名著的误译。即汉娜阿伦特的The Banality of Evil,中译为《平庸之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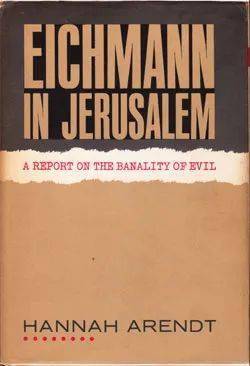
拜这个译名所赐,中文互联网大多数对于平庸之恶的引用几乎都是望文生义的误用,将之视为“平庸”本身所具有或带来的一种恶。然而依照英文文法,作者所讨论的实则是“恶的平庸性”,至于平庸这种品质本身是善是恶,是否会诱发恶行,与此书毫无关系。这本书的副标题是《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主角艾希曼是犹太大屠杀的纳粹策划人。但在阿伦特看来,他只是一个沉闷而普通的平庸官僚;艾希曼并不憎恨犹太人,只是不带感情地试图在纳粹体制中向上爬,由此在不坏恶念的同时做出了历史上最邪恶的事。
人们往往认为犯下恶行者,必然是希特勒一般恶魔化身的恐怖人物。然而艾希曼身上这种平庸与邪恶的反差,促使阿伦特提出了“恶的平庸性”这一论点,借以警醒大众盲从权威、放弃自我判断力所可能导致的灾难性后果。由此观之,大部分诉诸“平庸是一种恶”的文章不过是借阿伦特的权威继续兜售那套“打破平庸”的鸡血,抑或对“平庸者”的污名化。例如百度“平庸之恶”,就会出现下面这张图,实属望文生义、离题万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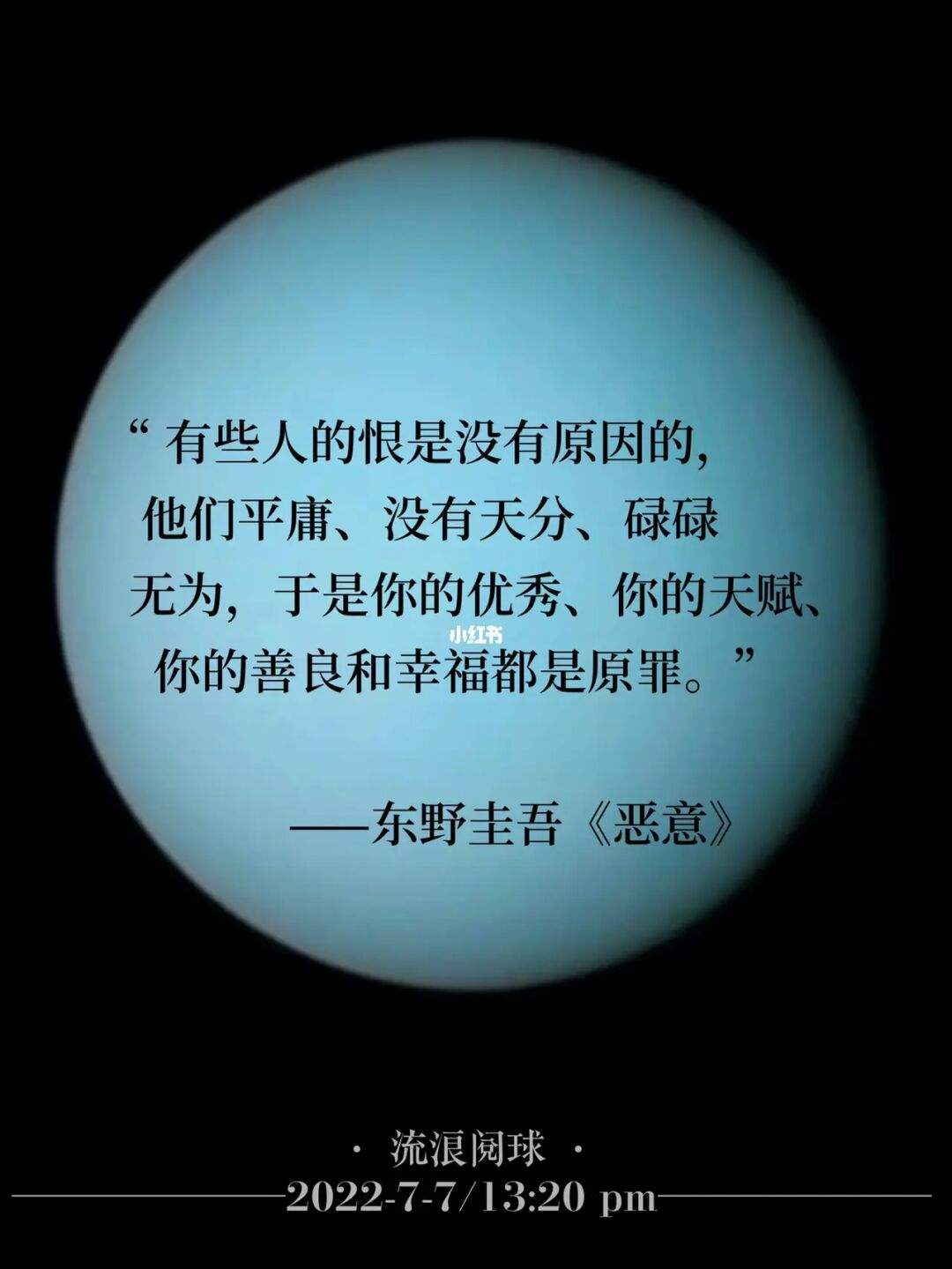
有人或许会问,The Banality of Evil远比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简洁直观,为何译者还是忽略了《恶的平庸性》这种显而易见的译法,而选择了似是而非的《平庸之恶》?我认为根源还是在中文表达的习惯上。中文尤其是古文,相较于拼音文字而言,较为具象而缺乏形而上的本体论观念。例如就构词而言,中文以轻重表示weight,长短表示length,至于重量、长度这些词都是现代文西化后的产物了。即便以轻重而言,轻与重也都是相对而言的概念,并没有lightness这种类似于“轻性”之类本体论意义。原因也是显而易见的,中文本身就不适合以ness、hood之类的词缀来暗示一个词从具象到抽象的变化。因此“恶的平庸性”虽然准确,但以中文的语感读来总有些拗口,不如“平庸之恶”一般掷地有声。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所谓白马非马。公孙龙的曾辩称,假如他去买马,那白马、黑马、黄马都可以;但当他限定在白马时,黄马与黑马就不能满足要求了,可见白马非马。他的话术很容易用现代集合论的观点反驳,即白马属于马的范畴,白是马的一种属性。白马纵然与马不是等同的概念,也不能推出白马不属于马这一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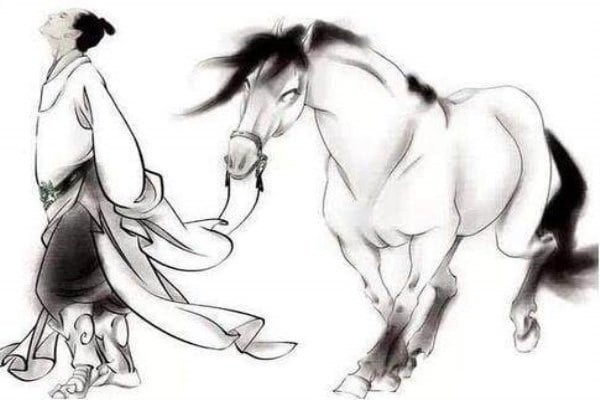
然而问题不在于如何驳倒这个几千年前的诡辩,而在于思考为何这一辩术能在中文世界存在千年之久。我认为其核心还在于中文天然缺乏本体论的思维模式。如果就拼音文字而论,公孙龙或许根本不会产生白马非马的问题意识,因为他不会把horse与horsehood混同,即便他有心诡辩,观众也可以从语言层面指出这一显而易见的区别。正是因为中文缺乏类似“马性horsehood”这样的本体论概念,白马非马才得以利用中文的多意性自圆其说。
同样地,《平庸之恶》之所以成为流传甚广的误译,也是因为中文并不喜欢“平庸性”之类本体论式的表达。徜徉在中文之海,你我早已习惯平庸作为一种描述品性与行径的形容词,而难以思考“平庸性”的意义为何。这样即便阿伦特探讨的是恶的平庸性,大众也难免把他从抽象层面拉入凡尘,理解为平庸的恶。这既是翻译错误的教训,也是一个深刻的例子,体现个人母语的文法特征如何塑造其思维模式。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文不能探讨形而上与本体论问题,毕竟本文也是以中文写就的;也不意味着在西方文化介入前,中国全无本体论的思考,如汉传佛教、宋明理学都不乏相关探讨。即便中文由于其书写模式,不利于上述“平庸性”、“马性”之类的思考,我也并不认为这是中文劣于其他语言的一种佐证。在我看来这些都是思维范式的差异,并无绝对的高下之分,语言的参差反而是人类思维多样性的美妙所在。
不过,本文谈的毕竟是翻译,难免要在细微的区别间大费周章。昆德拉曾说,“历史如同个人的生命一般不能承受地轻。轻若鸿毛、轻若飞扬的尘埃、轻若明日即将消散之物。” 翻译某种意义上也轻地又如尘埃一般。完美的翻译本就不可能,译者尚需在不可能的空间中搭建一座摇摇欲坠的桥梁。更别说译著最大的成就莫过于激发读者阅读原著的兴趣,仿佛这座桥构建的目的就是为了其摧毁本身。
但这种自我否定的性质也正是翻译的意义所在:好的翻译把读者渡向一个认知与思维迥异的彼岸,在读者靠岸时应声瓦解;平庸的翻译则强化了读者既有的认知,像一座坚固却南辕北辙的路。如果能对外文著作中上述极易被中文表达所忽视或误解的本体论层面加以仔细甄别,大概能够避免这些翻译的平庸之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