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的MeToo運動,我們該如何反思
相信在2023過了一半的時點,在大量社群、平台上,無論是在政治、演藝、學術、藝術領域間,都可以「被」揭露出很多過去數年間發生性騷擾、性侵等事件。但在這個運動背後,我們應該要重新審視的問題,除了要求加害人負起應該承擔的法律、社會責任外,我們應該還需要反思什麼樣的問題?本文將從此為出發,與讀者分享筆者的觀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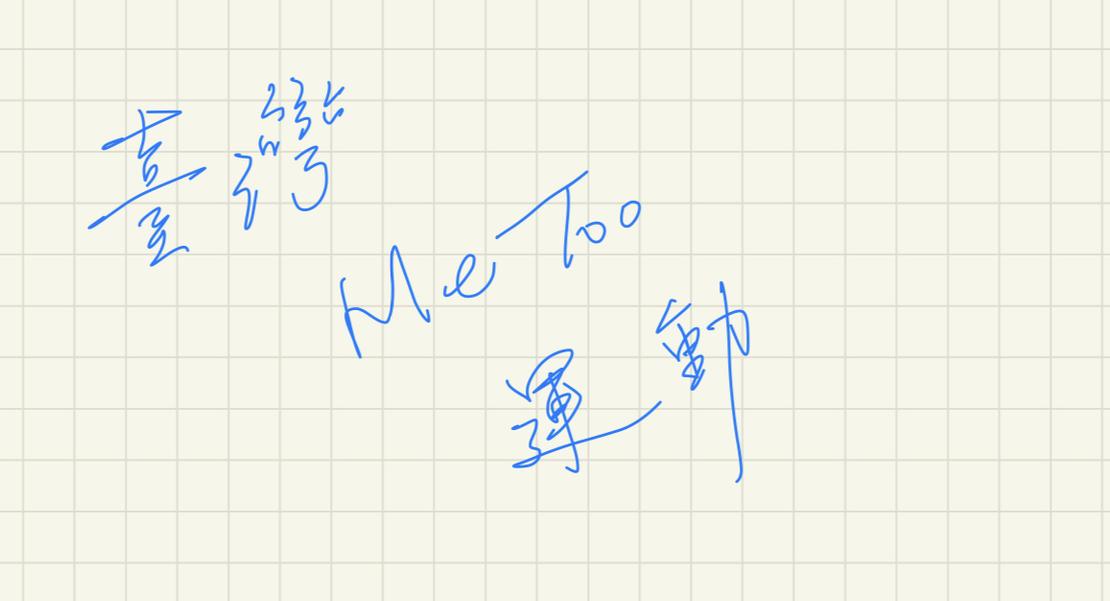
一場重要的社會運動,讓社會新陳代謝。
都過去了,我不是過去的我了
首先,筆者的觀察發現,性別意識在近些年大幅倡議下,對於身體的界線應該有所認識,至少可以對於有潛在不法意圖的加害人,讓他們停止此類想法,使他們意識到「不可以這樣做」、「造成的傷害無法彌補」、「自己無法承擔後果」。
不過,加害者們說的「曾經」就不應該予以評價嗎?他們可以用「結構」上的歸因(按:過去大家都這樣做、不是只有我違法),導致他們不知道這樣做、這樣說不行?
我想,以時間軸來說,我們確實很多時候都是以現在的觀點,去評價過去的可能應該要調整的價值,就如過去社會都對於同性戀族群不友善,甚至在傅柯的文獻討論下,也指出歐洲社會因為希望合理研究同性戀者,就將之定義為疾病,以作為當時權力機構下的正當性基礎。
但是,不代表可以被作為藉口,甚至又被當作「我現在沒有像過去那樣了,請大家原諒我」說詞。就像,在很多地方,對於受威權體制下,推行的轉型正義一樣,為了不是要報復、要攻擊、要拉下台,而是讓受害者的發聲,重新讓這個社會意識的這樣的作為,是危險、是傷害、是不應該被接受。
加害者們除了「現在」公開道歉外,應該要好好思考一件事情,那就是過去的你們「或許」不知道這做這些事情很嚴重,但在至今性別意識更為完善的價值觀下,為何沒有試圖去對你過去曾經傷害的人,好好去說明、去道歉、去彌補。而是等到受害者重新挖掘受傷的記憶,你們才選擇出面。
任何人都應該為自己的行為負責,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因為時間點與價值觀的轉變,差異的地方只是要選擇的承擔方式不同,而非是卸責的說法。
道歉了,然後呢?
如果大家有發現,這些加害者往往選擇是道歉,然後退出原本職業所屬領域,例如有退出演藝圈、退出學術圈等等。而媒體所傳遞的消息也僅止於此,加害人對於被害者所為的行為,有無就這樣雲淡風輕、大事化無的疑慮。這是作為大眾,我們可能要更加留意,也就是有無後續對於被害人有應該的賠償,這也不是寫個幾萬字的道歉文可以解決的。
在這裡,可以看見被害人選擇走上法律訴訟,但我們應該要往下去探究的是,為什麼這個責任又是移轉在被害人身上?這種的「有權利就有救濟」的法律思維,也有可能因為訴訟過程的資訊揭露,讓被害人選擇隱忍。而這些加害人在未被揭露的時間內,卻是繼續在大眾面前發光發熱。
當下為什麼不說?
回應有些人去質疑:「你幹嘛當下不說出來」。首先,我們應該要去檢視的是,真的是所有被性騷擾、性侵害的當下,都可以「勇敢」說出嗎?在某些已知的個案上,可以發現有些人是利用職權上的權力、身體上的強暴等一切無法抗拒的情境,也有些被害人指出,因為加害人可能有社會地位的優勢,怕說了大家都會認為「沒有證據,大家不信」。
上面講的這些情境,可以視為一種「台前」扮演,往往這個人在「台後」胡作非為,皆會因為「他形象這麼好,不可能啦」、「你們之間是不是有什麼誤會」草草帶過。或許這就是一個透過公關行銷手法的「人設」,而一但有人挑戰這個被操作過後的形象,你就要負起相當的說明責任,告訴大家你說的是對的。在通常的政治、時事評論當中,確實是「合理」的事件,因為在這段關係中,質疑者可能並非是當事人。不過,一旦在這類型的事件當中,有涉及到當事人,又更甚至是這次運動下,是受到性暴力的被害者,要求他們主動說出,就會顯見很多阻礙。
保護被害人的申訴、訴訟制度建立
上面談到問題,即是因為社會結構下,對於提出質疑者一種無形的舉證義務,從被害者視角來說,是一種可怕、壓迫的壓力存在。這也可以指出,為什麼許多被害人在時隔多年後,才因為此次的運動說出過去的經歷。對此,如何有一個被害人可以安心提出問題的管道,是非常重要的。這個管道,是不能僅僅只有通案的適用,而必須針對不同的職業、環境有所設定,原因是往往環境不同,所應該採取面對的方式即有所不同。
如在學校發生性騷擾案件,主要可能發生在學生與教授、系上行政人員與學生、學生與學生之間。針對相關通報後,應可按照現行有關實務上保護受害人之方式,以免受害人又受到二次傷害。惟這邊希望可以點出的是,大學環境可能會增加額外的風險承擔(如同學之間上課之間的氛圍、該教授或行政人員可能持有相關考評權力等),對於相關部分可能應就個案情形有所調整,以免於各種其他不利的條件,使其受害人寧願選擇承擔權益受損的不利。
MeToo運動使臺灣社會新陳代謝
本文的結論,想要告訴讀者的是,臺灣的MeToo運動正是對於在過去有違反性別意識者的一種新陳代謝,過去的陋習、潛規則都不應出現。同時,我們也應該透過這次的運動,告訴任何有不法意圖的人,沒有人的身體可以被隨意騷擾、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