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奇幻的成長進路:從《最後的獨角獸》到《回家之路》

《最後的獨角獸》與《回家之路》
《最後的獨角獸》(The Last Unicorn)曾在二十多年於臺灣譯介出版,多年以後當然早已成為絕版的夢幻逸品,直到漫遊者文化於今年二月出版了新譯本;這本1968年推出的作品,講述了一個有著童話外觀、但內裡富涵哲理省思的故事:終年居住於自己的森林中的獨角獸,偶然聽到兩名獵人的交談,從而發現自己可能是世界上最後一隻獨角獸。為了確認真相,獨角獸離開了自己的森林,開始了尋找其他獨角獸的旅程。
1982年,《最後的獨角獸》改編成動畫,精美的畫風與作者彼得.畢格(Peter S. Beagle)親自操刀的改編劇本,讓動畫與原著一同成為西方奇幻的經典作品之一;其中參與製作的動畫工作室「Topcraft」,正是後來大名鼎鼎的吉卜力工作室前身。

《最後的獨角獸》(The Last Unicorn, 1982)
二十多年前的我並未有幸一讀《最後的獨角獸》,也從未看過相關的動畫版,直到今年才真正體驗到了本書的魅力。對我來說,《最後的獨角獸》有一種「古老」的魅力,讓我在閱讀過程中不斷想到當年閱讀《哈比人》(The Hobbit)、《魔戒》(The Lord of the Rings)甚或《永恆之王》(The Once and Future King)的感觸。這類作品更像傳統意義上的「童話」(Fairy tale)而非「奇幻文學」,也更傾向托爾金(J. R. R. Tolkien)當年所謂的「仙境故事」(Fairy-story)——為了區別專為兒童書寫的童話,托爾金創造了與此原文極為接近的仙境故事一詞,強調此類故事與童話相近,卻並非專為兒童書寫,而是大人、小孩皆可以盡情享受的故事類型。
仙境故事就是後來的奇幻文學;而就如同灰鷹爵士在《最後的獨角獸》後記所言,身為托爾金「狂粉」的畢格,必然追尋著師尊的類型定義,撰寫完成了本作。當然,不會劃地自限的類型創作者們,很快就擺脫了托爾金的奇幻定義,開創出更多元、更多面向的奇幻文學進路,像《哈比人》、像《最後的獨角獸》的奇幻故事也越來越少。
然而,對從《魔戒》、《哈比人》「入坑」奇幻的我來說,如此「古典」的奇幻創作,具有一種神奇的魅力,主角們在冒險的旅途上總會面臨看似全無希望的難關,而故事的結尾,卻依然能夠帶給我們某種慰藉。那是一個離我們太遠的世界,是「中世紀」與「現代」般的遙遠,也是「西方」與「東方」般的遙遠;是「魔法師」與「江湖術士」般的遙遠,也是「獨角獸」與「白馬」般的遙遠。所以,這樣的故事充滿了寓意——而奇幻故事的寓意是不該、也不能被說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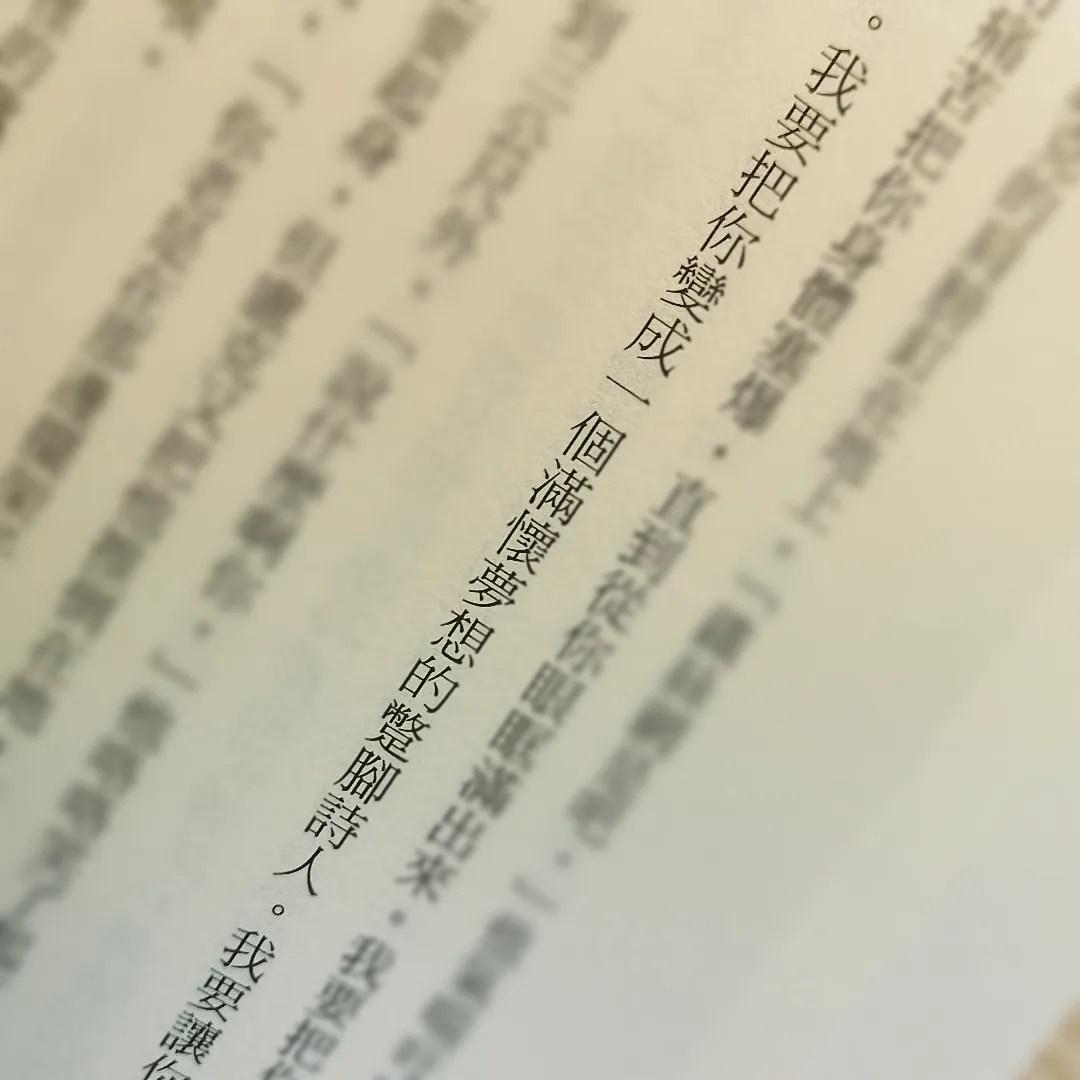
「我要把你變成一個滿懷夢想的蹩腳詩人。」
《最後的獨角獸》就像一篇寫給大人看的童話,有西方人耳熟能詳的獨角獸、魔法師、綠林盜賊,以及邪惡暴君、屠龍英雄、幽暗城堡與恐怖駭人的野獸。故事充斥著歐洲傳統童話中的各種元素,呈現出來的故事卻飽含孩童可能無法理解的象徵及寓意;重點在於,每個讀者都可以根據自己的成長經驗、社會經歷來連結故事中的角色,以及角色遭遇到的困境、難關。
我在讀國、高中的時候,彼得.傑克森(Peter Jackson)的《魔戒》三部曲改編電影才剛在臺灣上映,一時間奇幻熱潮在臺延燒;高中時,有位大概對奇幻創作不太感興趣的老師,在班上說明托爾金筆下的黑暗魔君索倫指涉的就是希特勒,而魔戒象徵了原子彈。當時的我無法反駁什麼;在我研究、思考奇幻創作多年後,我認為當年那位老師講出了自己的詮釋與理解,這沒什麼不好——但奇幻故事給予我們的「距離」,讓我們可以對那些虛構的事物有更多的詮釋空間。因此,要說「索倫等於希特勒」、「魔戒就是原子彈」未嘗不可,但索倫不會「只」象徵希特勒,魔戒也不會「只」暗指原子彈。
而撇除那些可能與現實有所連結的象徵,單純將其視為一個發生在第二世界(Secondary World)、與現實毫無關連的虛構故事,《最後的獨角獸》依然是足以令人感動落淚的動人故事——那些主角們的轉變、成長,其所經歷的苦難、情感,以及因勇氣、犧牲而克服萬難所創造出來的奇蹟,令我在閱讀故事後半段時,視線不斷被淚水模糊。

《最後的獨角獸》與《回家之路》
2004年,畢格完成中篇故事〈雙心〉(Two Hearts),於2005年發表於《奇幻與科幻雜誌》(The Magazine of Fantasy & Science Fiction)上;〈雙心〉是《最後的獨角獸》的完結篇,講述「本傳」故事結束幾十年後的故事。其故事主軸是更「王道」的童話,或者可以說是歐洲神話傳說中很常見的英雄屠龍、斬殺魚肉人民的怪物的故事。但在這些傳統的情節單元(motif)之餘,〈雙心〉更講述了英雄的終末、理念的傳承與女性的崛起;這些轉變,也許與近四十年前創作《最後的獨角獸》的時空環境有了很大差別有關。
〈雙心〉中,將滿十歲的蘇茲(Sooz)所在的村莊受到獅鷲獸的侵擾,接連有好幾個村民被抓去吃掉;老國王派來的騎士從一個變成一批,卻也都無法打敗擁有兩顆心臟的獅鷲獸。於是蘇茲趁著夜色偷溜出家門,決定自己前往國王的城堡中,請求國王親自出征。這則故事中的國王、蘇茲在路途上碰到的旅伴,都是《最後的獨角獸》中曾經出現過的角色,國王的角色尤其令我動容,有讀過《最後的獨角獸》的讀者想必能體會我的心情;看著他,我就忍不住淚水。當這名垂垂老矣的國王決心跟著蘇茲回到村莊打倒怪物時,我不禁想到《永恆之王》中的亞瑟王——
老國王精神大振,神清氣爽,幾乎準備好要再次開始。
會有那麼一天——一定會有那麼一天——當他帶著新圓桌回到格美利,那張圓桌就像這個世界一樣,沒有稜角——那張圓桌不會在國與國之間設下疆界,可以讓他們坐下來舉行宴會。要塑造這樣的圓桌,唯一的希望就是文化。如果能夠說服人民學會讀寫,不再只會吃飯做愛,就還有機會讓他們變得理性。
不過這個時候要做另一項努力已經太遲了。因為此時,他的命運就是死亡,或像某些人所說,被帶往亞法隆,在那裡等待更好的時代。
當故事走向注定的終局時,也暗示了下一個起點;蘇茲在結尾被授予的神秘指示,連結到了《回家之路》(The Way Home: Two Novellas from the World of The Last Unicorn)的另一個中篇故事:〈蘇茲〉(Sooz)中。《回家之路》出版於今年四月,重新收錄〈雙心〉與全新故事〈蘇茲〉;漫遊者文化則打鐵趁熱,於八月將此書譯介給臺灣讀者。
〈蘇茲〉的故事發生在〈雙心〉的七年之後,十七歲的蘇茲聽從了當年的指示,照著對方的要求行動,從而發現多年來自己以為的四口之家,其實另有隱情——他發現除了哥哥威爾弗(Wilfrid)之外,自己其實還有個名叫潔妮亞(Jenia)的姊姊,而潔妮亞早在威爾弗出生之前就被「夢人」給擄走了。儘管父母百般不願,但蘇茲決心出發前往夢人的國度找回姊姊;〈蘇茲〉講述的,便是其踏上這場尋找姊姊的「冒險」之路。這裡的「冒險」之所以用引號框起來,是因為我認為這場旅行,其實更像是一種「追尋」、「成長」之旅;蘇茲將在這段旅途中遭遇諸多困境:男性的施暴、夢人的訕笑,甚至親友的無法理解,似乎都象徵著女性在成為大人的過程中會遇到的真實難關,而閱讀過程中不斷遭遇到的「死胡同」,似乎也具有某種後設意義,我想不論讀者的性別,閱讀〈蘇茲〉都能令人獲得某種啟發。
說起來,《回家之路》的確是一本不需要先看過《最後的獨角獸》就能閱讀的作品,然而看過《最後的獨角獸》再來閱讀,勢必能獲得更多的感動;而作者彼得.畢格從《最後的獨角獸》到三十六年後的〈雙心〉,再從〈雙心〉到近二十年後的〈蘇茲〉,或許讀者也能從中看到創作者的轉變。
漫遊者文化出版、彼得.畢格的《最後的獨角獸》與《回家之路》,推薦給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