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2|纪录一列所有人的列车:非虚构如何写社会 | Corona x 小鸟文学 1

人类学学者项飚曾提到非虚构写作是一种原生态的、原初状的民族志写作。而民族志作为人类学的一种研究方法和写作文本,和非虚构写作具有许多相似的特征,比如大量文献资料的搜集、观察与访谈等。那么做过田野就能写非虚构了吗?何为非虚构里的伦理或问题意识?人类学家和非虚构写作者相互可以学到什么?有人类学感的非虚构写作可以是怎样的?这样的笔下,“我”是谁?“他人”是谁?“公共”在哪里?这一写作/知识生产的意义又是什么?这一系列问题促成了与《小鸟文学》一起合作的这期Corona。
–
本篇推送基于媒体人伊险峰与杨樱老师的分享,来谈谈他们的新作《张医生与王医生》——写作本书的初衷是什么,“社会”与“社会人”这两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尤其是他们如何结合社科的理论和方法来进行非虚构创作。两位作为《小鸟文学》主创,还开设了“田野中国”栏目,推出数篇由人类学学者和学生创作的田野非虚构作品。在后续的推送中,其中一些人类学作者也将分享自己“非虚构”作品的创作感悟,敬请期待。
–
Corona是一个起源于疫情期间的公共讨论平台。底色是人类学,但疫情的复杂性很快溢出了既定的学科边界,读书会也逐渐转化为议题导向的半公共讨论平台,以期实践呼应应急性议题而非拘泥于静态理论的知识-行动联结。疫情和疫情次生社会现象之外,Corona关注的议题包括性别与LGBT、美国黑命攸关运动、基建、诗歌、他者、全球灾难政治等,也力图对紧急议题做出反应,如就20年洪水策划的鄱阳湖批判历史地理学和大坝与水利政治的讨论和今年的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环评阅读。有意加入或主题投稿的朋友请在后台留言。此前书单见石墨文档:
–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N2WHbleK9gN20TXDCvteG13708Jw6hBsAE-kNHL_q9w/edit?usp=sharing
–
以往笔记可以在上述书单中找到,整理后的文章可于结绳志Corona专栏里找见。有意加入本次讨论请直接按照海报上的链接加入,意图长期加入或主题投稿的朋友请在活动尾声联系主持的同学们。
主讲 / 伊险峰 杨樱 周雨霏 林叶
主持 / 张亮亮
客座编辑 / 木子
非虚构的公共性
张亮亮:
首先我想请伊老师和杨老师给我们聊聊二位的非虚构新作,在这里我也为还没有读过的朋友们先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书。
《张医生与王医生》是关于伊险峰老师两位初中同学的个人成长史和他们所处的时代变局,主人公就是题目中的两位医生——张晓刚和王平,他们分别出生于1970年和1971年,来自沈阳的工人阶级家庭。两位医生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成为了专业人士,实现了自身的阶层跃升。不过在伊老师和杨老师的笔下,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简单直白的翻身故事,而是在社会剧烈变革中这两个个体、他们的家庭、还有他们居住的城市所经历的紧张和阵痛。我自己读后觉得这本书的核心议题是在半个世纪的剧烈变革中,作为计划经济重镇的沈阳和作为工人家庭重镇的“奖学金男孩”,是如何提心吊胆地面对险恶的社会和善变的命运?这本书让人类学背景的朋友感觉特别熟悉的部分,是两位老师对于隐藏在生活中约定俗成资料的捕捉和呈现。从日常生活里面打捞出来的很多话语、观念和价值观特别生动,读者瞬间被吸进张医生和王医生所在的沈阳。读过的朋友应该会像我一样对这本书的现场感和复杂性印象深刻,没有看过的朋友也可以把这本书加到2022年的新年购书单上。我想请教两位老师的第一个问题是在写这这本书的时候,你们想象中的读者是谁呢?你们想写给某一个特定的群体吗?还是想更多地回答自己内心一些对于社会的反思和疑问?

伊险峰:
我写这本书的初衷更多是想回答自己的问题和困惑。我对人生要思考的东西有很多,比如我的同学。我跟他们在成长的早期应该是比较接近的,但是在漫长的30年后,我和他们产生了一些差异,这个差异便是我感兴趣的。存在差异可能是因为我离开沈阳,跟沈阳之间有了一种区隔;也可能是我从事媒体行业,而我的同学们都是医生这类专业人士;也有出身背景的差异,这些差异性最后都表现在了这本书里。比如说,在差异化中,沈阳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在家庭的背景差异里,工人阶级家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我的同学们作为专业性动手能力很强的医生角色,和我知识分子形象之间的差异。
我关注的东西是偏人文的,简单讲,就是一个人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这是一个人文的思考,我的同学们可能没有这方面的思考,但是他们对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有自己的打算。某种意义上说,我觉得还真是好像解答了我的一些困惑,也部分回答了沈阳到底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不仅仅是我的同学,很多有专业背景的人,他们变成现在的这个样子到底是什么原因?他们还要面对下一代的发展,他们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未来?我跟比较熟悉的人或圈子里朋友聊的时候,会聊一些比如担忧“犬儒主义是不是会让一个人变得更加圆滑?”这类的问题。
我们在开始做的时候,想的是社会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这不是说大家都是被动的,被一个叫时代的列车给拉到这个地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起把这俩车给推到这的,所以每个人的责任可能都是显而易见的,只是没有一个人去正儿八经地归纳,我觉得是这样一个思路。
杨樱:
我还真没有预设一个特定群体作为读者。我们以前都是从事媒体行业的,有的媒体会预设特定群体作为读者,比如说行业媒体。以我们俩做媒体的经验,我们说的公共写作就是默认的你的读者是所有人,这其实是新闻的一个特点,新闻就是所有人都能简洁直观地理解你要传达的信息。所以,从我们职业角度来看,公共写作这个大前提一直都在。不管是我们写书还是以前做媒体的时候,无论在做《好奇心日报》还是现在的《小鸟文学》,我们往外发文章时,都会先确认发出去的东西,对所有读者来说是不是能够提供一个基础的价值,或者他能否明白我所要传递出的信息。公共写作和你要讨好所有人,不是一个概念。换句话说,公共写作的特点就是它的利益是公共的。当你服务于所有人,就跟基础设施一样,需要考虑到很多普世的东西,这是一个大前提。写《张医生和王医生》时,我们也有这样一个潜意识:默认这是一个公共性的作品。
刚才听伊老师说,包括我们之前也接受过一些访谈,我越来越感受到这本书之所以被认为是复杂的,有两个原因。首先,中国很大,大家提及的地方性会成为一个很容易识别的标签,其实我们在写书的时候反倒是有意识地弱化了东北的存在感,我们不想强调东北,反而希望去强调普世性。很多人在读后感里面会提到,虽然他不是东北人,不出生于70年代,但他也同样能理解这本书里提出的所谓的阶级属性,或者说集体文化的背景,这种共通性是我们想努力传达出来的。其次,中国真的变化很快,40年放在任何一个人类社会语境里都是非常复杂,变化极为迅速,然后它也产生了一些叠加的地域因素,很容易给不同的人制造大量不同的语境。
我是伊老师的第一个读者,因为我们分开写作,有一些与沈阳或者东北特色有关的内容必须要写到,包括一些方言。其实我是南方人,我是第一次接触这些语言,我会去问为什么。不仅是地方的,书里还谈到了80年代的特色,比如金粉、凭票购物这样一些计划经济的痕迹,这些东西已经超出了我的生活经验,我肯定要先问一下你在说什么,这个是我跟伊老师不同的地方。在这本书面前,我跟读者站的位置是很像的,我只不过更先了解这些信息。如果书里所写的内容对一个参与本书写作的人都构成知识壁垒的话,对读者来说肯定更多一些。所以这本书的复杂性来自于知识壁垒和不同的差异造成的语境分化。很多人会问我们怎么把那么多复杂的东西融合到一起,对我们来说,只是写作时有些东西你必须交代清楚。
“社会”和“社会人”
张亮亮:
谢谢二位的分享,像杨樱老师刚才提到的,从一个南方人的视角,第一次走进沈阳的社会,学习到了非常多地方性的知识和概念,其实跟人类学走入他者的方式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二位老师提到对于文本的定义是希望它是公共性的、服务于所有读者的,的确也构成了很多讨论的方向跟一些前提,比如说我觉得你们讨论到的“社会”以及“社会人”在这本书里面是特别重要的关键词,从你们的笔下我们也看到这两个词的内涵跟外延以及用法,在沈阳的很多情境下是模糊不清的,我想请两位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下“社会”和“社会人”这两个概念在沈阳特定的语境下面和在当下的中国是一组什么样的概念。
社会该来还是要来。不管如何被保护,男孩总要长大成人。这些被母亲宠爱的男孩还是要走向社会。有几个跟社会有关的悖论,其中一个应该就是:本来保护你不接触社会,就是为了让你在社会里更容易找到生存的好位置。这些“奖学金男孩”有一个不那么被提起的弱点,就是从小被人夸奖聪明。自己渐渐也就相信了这一点,难免在进入社会时要动用一点智力。但要知道,社会更多拼的是经验值,对智力的要求没有那么高。所以这聪明有的时候运用于社会中,并没有什么竞争力,说不定多数时候还被人看成自作聪明,变成一个笑话,自己还不自知。沈阳有若干民间传说,比如说知识分子整人更狠,知识分子人事关系复杂。这当然有妖魔化的成分,因为工人多,工农干部多,转业军人多,他们觉得知识分子的心思不大好猜测。工人阶级想象知识分子,每个人都很聪明,脑瓜转得比我们快,不像我们工人大老粗,直来直去,所以他们可能无时不在算计着自己的收支利益。王平这样工人阶级出身的角色,当然也从小被潜移默化地灌输类似的观点。这一定程度上夸大了他们对社会的想象。这与王平说的他对“行政干部的反感是一样的:“有些人很势利,看人就是有用和没用。他就是以这样一个标准来区分人。”
——《张医生与王医生》第六部分 社会人
伊险峰:
这个说起来也很复杂,我是这本书写完隔了很久才开始正儿八经地去研究社会和共同体到底是怎么回事,才明白里边的脉络。以前我在写这书的时候,我不太了解这些,所以我就把学术的东西扔在一边。按人类学的说法,假如你面对一群东北人作为你的田野对象,或者说沈阳的工人阶级大背景,你会自然而然地引入一个他们认为的“社会”的这样一个概念。我与很多可能在年龄和文化上都有一些差异的人聊天时,包括我们第一次新书发布会上也探讨过类似的问题。知乎上有一个高赞问答:“在东北如何显示出来你很社会?”有一个大家点赞比较多的回答:“我在法院开车”。这个答案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人类学学者们听完后是不是有一种顿悟。这个答案就代表了一种很深刻的背景,这里面包含了社会资源到底是什么?怎么去利用社会资源?为什么有些人占有社会资源,但是他不敢去用,好比说我是法院的第二法庭庭长,作为庭长,我是不是可以为所欲为,跟在法院开车的人是否存在一些差异?为什么中间会有差异?然后开车这种在野的身份,也就是体制外的人,他又如何去驾驭体制内的资源,同时他又不用受体制内过多的束缚。上面所有的问题都包含在这几个字里边,这几个字就是一个可以去仔细探讨的“社会”概念。
“社会人”在2017年、2018年,也就是抖音、快手刚刚起步时,影响力很大时出现的。大家都知道网上有“社会人”,还有“社会摇”的说法。“社会人”就是穿着阿迪达斯、小细腿儿裤子、还有小皮鞋,及视频上其他一些行为表现,包括后来的抽根“华子”、夹个烟、夹个小包……“社会人”是一个非常漫画化的形象。这个是媒体上呈现的“社会人”的概念,书里医生们提到的“社会人”是有一种“我得进入社会”、“如何适应这个社会”、“进入社会后你得会来事儿”的感觉。从两个医生的母亲到这两个医生在职业和单位里的选择,都能看出来“社会人”的身份对于他们来说,在各个环节或者各个时间段里,本身也有不同的理解,但是不管是怎样不同的理解,它始终是一个目标:你在社会上必须能“吃得开”,你得适应这个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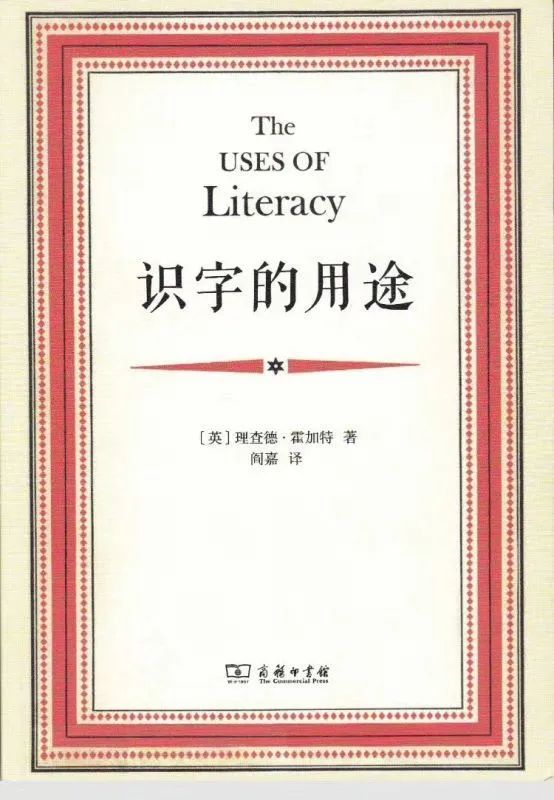
从这个角度看,“社会人”对社会的驾驭能力,如果翻译成社会学的语言,其实就是怎么利用社会和文化资源去实现某些目标,你会看到这里面存在此消彼长的现象。他们怎么挣扎着一点一点让我自我利益最大化,成就最大化,或者是自我的形象最佳,这是他们在社会里的表现。我理解的“社会”和“社会人”,从最基本的这几个资源的使用上可以得到一定解释。
杨樱:
我补充一下伊险峰老师说的,“社会”和“社会人”这两个概念在这本书里很突出,是我们确定以两个医生为核心人物后,很快意识到一个必须要探讨的话题。不是说我们设立了一个议题叫做“他们如何使用社会资源”,我们的介入方式是询问这两个人在过去40年里都做过什么,他们的家庭做过什么,经历过什么样的大事件,我们是通过很普通的方式切入并和他们的交往的,然后从他们的回答中,发现有一些高频词汇,发现他们自己也在有意识地去分析这些问题。
李海鹏在序里面也说,要“会来事儿”,“会来事儿”这个概念和我们说的“社会人”是可以接轨去分析的一个点,上一代人的“会来事儿”和王医生、张医生这一代人的“会来事儿”还不尽相同,最大的区别是他们的社会背景不一样。像张医生的母亲杨淑霞女士和王医生的母亲曾慕芝,她们生活在一个计划经济和集体氛围更浓厚的社会环境里,她们要调动的“社会资源”,更多属于书里提到的“公家”。“公家”是绝对意义上被拥护的,个人“小家”的存在感不是那么强烈,甚至会鼓励大家要忽略。这个现象非常有意思,“田野中国”登过一篇苏联普通人的访谈,那一篇里的访问对象就提到过这一点——个人生活是不被鼓励的,公共的集体生活是全部。书里所谓的调动“社会资源”,就是说你能把多少公家的资源通过某种方式用来补助自己的个人生活,这被认为是一个人有能力的体现。通常是女性完成这个说法,父亲是更复杂的一个问题,一个“单位人”的形象。
书中还有一个很小的细节,王医生的太太提到有男生跟她还在上高中的女儿交往,她女儿评价跟她交往的男生时会说“男生不行,太‘社会’了,嘴巴里经常讲一些脏话”,这里的“社会”跟我们刚刚说的“社会”概念又不一样。大人对于读书的小孩会有预设——你尽量只好好读书,不要去跟社会上的一些人瞎搞,或者说你不需要了解人情世故,有父母替你包办安排,如果你太了解,反倒会被认为是一个复杂的小孩。即便我们现在的家长可能也这么想,然后你一到社会上,你又需要单枪匹马地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这是我们提到的另外一组概念“自我”和“社会”,一个人周围的外部世界和他自己内心世界之间的关系。
把理论作为工具
张亮亮:
你们都说得特别好,“社会”的概念,在不同时代,不同人生阶段被赋予了戏剧性且有巨大区别的价值判断。这里我想请两位老师再分享一下二位对于“自我”跟“社会”之间互相塑造关系的分析。我看到书里既用了非常多从人类学视角可以称为“地方知识”的概念,像您刚才提到的“积极分子”、“干净利整”,“一劳本神”(东北话中意为老实本分、没有主见)等等;同时二位又大量引用了社会学理论,尤其是保罗威利斯和理查德霍加特对于英国工人阶级文化的研究,我还想请两位老师分享一下,二位当时选用这些社会学理论,还有地方概念背后的考量是什么?或者说现在回头看,二位觉得这两类工具对于想讲述的故事和探讨的议题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不成熟的、较真的、工人阶级传承中的王平视张晓刚的批评为一种赞美。只有那些社会上的人才是成熟的:积极分子、告密者、单位里与你打呵呵的、官僚、官僚的跟屁虫、喜欢玩弄形式主义的–那些没有一技之长,只能用嘴皮子和动心眼子的人;警察、税务、城管、社会上形形色色的霸凌者–那些以为可以借身后的庞大机构来霸凌我们这些小老百姓的人;可能还有生意人、南方人、各种中介 -那些以为自己脑袋很好使,可以去算计别人的人……他们组成庞大的社会,王平医生、张晓刚医生,这些曾经的“奖学金男孩”,这些孤傲的认为自己凭本事吃饭、不同流合污的不合时宜的人,挣扎其中,经年不止。
在经典的工人阶级文化研究者眼中,这个另外的人群被称为“他们”。理查德·霍加特在《识字的用途:工人阶级生活面貌》中表明,“他们”与代表工人群体的“我们”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对立存在。这个世界就其本质来说,是“他们”的世界。
一般而言,看待“他们”,就像看待警察一样,基本的态度与其说是害怕,倒不如说是不信任;与这种不信任相伴而生的是,人们对以下事情不抱幻想:“他们”会为一个人做些什么会以那种复杂的方式–显然是不必要的复杂方式–做些什么,而且在这种复杂的方式里,如果接触到他们,“他们”就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活。多年来,工人阶级人民体验到了在劳工介绍所里、在咨询医生那里、在医院里的排队等候。无论是有理还是无理,他们都通常抱怨那些专家,以便得到他们自己背后的某些东西,如果事情出了差错–“啊,要是那个医生知道他在做什么,就绝对不会失去那个孩子了”。他们怀疑,公共服务不会非常轻易、有效地提供给他们,不会像那些能够打打电话或发封语气强硬的信函之人所享受到的那样。
——《张医生与王医生》第三部分 工人阶级子弟的成长
伊险峰:
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的这两本书确实对我有一些启发。我们刚开始对地域的观念跟大家差不多,我本身是沈阳人,所以我有时会怀疑自己身上的特性是沈阳人或东北人独有的,还是其他中国人都有的。有许多人在分析为什么东北衰落了,为什么需要振兴,在看这些问题时,按照媒体思考问题的角度,有些是真问题,有些是假问题,真问题和假问题需要弄清楚。比如说东北是计划经济重镇,受计划经济影响非常大,我们可以去思考这个影响会有多大。假如说“计划经济”这一因素的权重已经达到80%,那东北衰落是计划经济的一个恶果;假如说只有5%,那这个因素可能就没那么重要,这时候你就得重新思考到底什么促成这一变化的重要因素。但是我们书中涉及到的不是东北振兴问题,而是去探索东北这两个医生到底怎么成长的,不过探讨影响因素权重的思路是一样的。
我们刚开始介入这两个医生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的父母属于特色非常鲜明的工人阶级家庭,聊了之后才发现他们是典型的工人阶级。王医生家在“大厂”工作,张医生家在那种经不起风吹草动的小工厂工作,所以在东北下岗潮过程中,他们家遇到的困难最多,所以在不断跟他们父母聊与公家、单位是什么关系的过程中,我发现“工人阶级”身份对他们的影响可能超出我事先想的那么多。最后这本书写完再去复盘时,我觉得40年间,从一个贫瘠稀缺的社会向相对富裕的社会转化过程中发生的一些变化对他们成长过程的影响最突出;第二位是工人阶级家庭;第三位才是地域问题。还有一个对我的启发是像魏昂德,包括国内一些学者对“单位”概念的研究。比如说积极分子在一个组织里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什么时候被人尊敬,什么时候被人鄙视,或者说被人孤立,里边都有很深入的研究,这些都有助于我们更了解张医生和王医生的成长问题。

我以前做媒体时会跟刚入行的记者聊——百闻不如一见,这里我说的不是采访的突破能力,而是说你要有丰富的感受力。我觉得民族志写得好的作者都是感受力特别强的人,假如给感受力做进一步分割,其实就是拥有更多共情的能力,这一定是建立在“看过更多”基础上的共情。比如我看过索尔·贝娄,我知道一个童年和少年期在黑帮社会里长大的芝加哥人会怎么思考问题;然后我就能很大程度上理解沈阳大东区、铁西区的人怎么思考问题,他们为什么会觉得把人脑袋“破”了是一件值得荣耀的事。我不会简单地去质疑他们为什么要欺负别人,而是会思考为什么他的成长环境和文化氛围造就了他这样的想法。
张亮亮:
谢谢您的分享,您的回答也部分回应了我们即将要聊的问题,接下来我想请二位老师为大家谈谈第一年下来你们从编辑的角度出发,觉得看到的“田野中国”栏目人类学的写作有哪些特点,以及一开始没有预料到的问题,我们都很好奇。
杨樱:
其实从《小鸟文学》的角度来说,这个栏目本质上是不讲究出身的,我们只是想知道身边生活的多样性,而且我希望呈现方式是比较文学性的。伊险峰老师刚刚提到一些学术著作,其实都非常好读,我觉得我们国内应该也有很多学者或作者能够写出这样的作品。
如果让我说过去一年都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栏目的繁荣程度跟我们最初的设想是符合的,真的会有那么丰富的多样性存在。而且我感到非常惊喜,收到的很多稿子的质量要远高于所谓的非虚构写作,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大家的确很扎实地进行了一些田野调查,是我们一些传统的、从媒体出身的写作者没办法达成的,因为媒体不会有硬性规定,要用人类学学者这样的时间成本和知识架构去思考问题,所以一般的作者很难产生这种深刻的理解力。理解力是需要支撑的,如果没有就很容易变成滥情,滑坡的危险其实更容易发生在没有经过训练的人身上。
还有一个发现的问题是人类学学者在写非虚构作品时容易走一个极端——会过度避免在作品里谈论自己认为是学术的部分。有时曾梦龙编辑会重新跟学者讨论稿子应该怎么写,最主要的原因倒不是稿子过于学术,而是作者怕别人看不懂,回避了自己学术的那一面,往往由于这种回避会导致写作主体模糊。写作主体的问题就涉及你要写什么,为什么要写,和不一定有人类学背景的小鸟读者的关联是什么?我觉得如果能把这三个普适性问题解决了,任何话题都是可以进行的。所以这一年我很想感谢大家给我的启发,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栏目,不是说我们开启了栏目觉得非常好,而是因为我发现了很多好的作者。
讨论环节
问:
二位老师在写作《张医生与王医生》一书时,是怎样规划和实施的?例如框架或大纲的设计、采访、具体写作过程等等,期间的时间是如何安排的,又是在哪个阶段跟出版社打交道呢?
伊险峰:
准备的时间不是太多。在确定好采访对象之后,我们给张医生和王医生分头发了邮件,邮件里面涉及到我们可能会采访的人,包括他们的同事、家庭成员等人物。采访过程中,还会有2到3次跟对方确认接下来我们会做一些什么事,这有助于整理我们自己的思路,同时也让他们明确这个活动的进展。我们还让他们准备了大约从10岁到采访那一年每年的大事记,写三个“你觉得什么事重要”,逼着他去思考,这有助于跟他深入地去聊。
前期准备工作做好后,等到写作,好比说家庭、社会、学校。因为我是两位主人公的初中同学,所以我对“初中”这一部分的写作属于得天独厚的。我知道有什么事发生,然后把这些东西都放在一个文件夹里。但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得分头去写了一些东西后再判断。整个结构不能头重脚轻,你在建构的过程中需要做一些取舍,所有的构建都要围绕着是否能让读者更了解他们两个人的成长。成长里有正向的,比如说成为一个专业人士;也有一些我们要质疑的,比如成为“社会人”,或者说成为在社会里混得比较好的一个人。最后定下来使用穿插式结构,一个是过去的生活,一个是现在的从医经历。从医经历这部分,杨樱跟两个医生聊得多,会跟他们一起出门诊、上手术室;而我对他们的家庭历史、童年的事了解得多,穿插的时候我就往这个方向去做。还有一些素材觉得哪儿也放不进去,就做成番外,谈一谈计划生育、女性角色等。
总的来说,全书可以分为三条线索。一条线是现在的;一条线是家庭,其中涉及父母、教育、社会的变化,这一部分相对来说是最重要的;还有一条线是番外,写社会大背景里相关的一些人和事,与文章主体有一定关联度,这三条线索同时往下走。因为我做了很多年媒体,虽然写书篇幅变长了,我觉得自己还可以驾驭如何组织结构。我们的出版也经历过一点波折。写完之后我发给几家出版社,看有哪几家想出。最后剩下两家争的时候,有一家更踊跃一些,就给了那家。但是对方删我们稿子删得比较狠,最后就又给了原来那一家,所以耽误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最新文章(持续更新)
纪录一列所有人的列车:非虚构如何写社会 | Corona x 小鸟文学 1
欢迎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保持联系
独立网站:tyingknots.net
微信公众号 ID:tying_knots
成为小结的微信好友:tyingknots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