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3|拯救田野的非虚构?| Corona x 小鸟文学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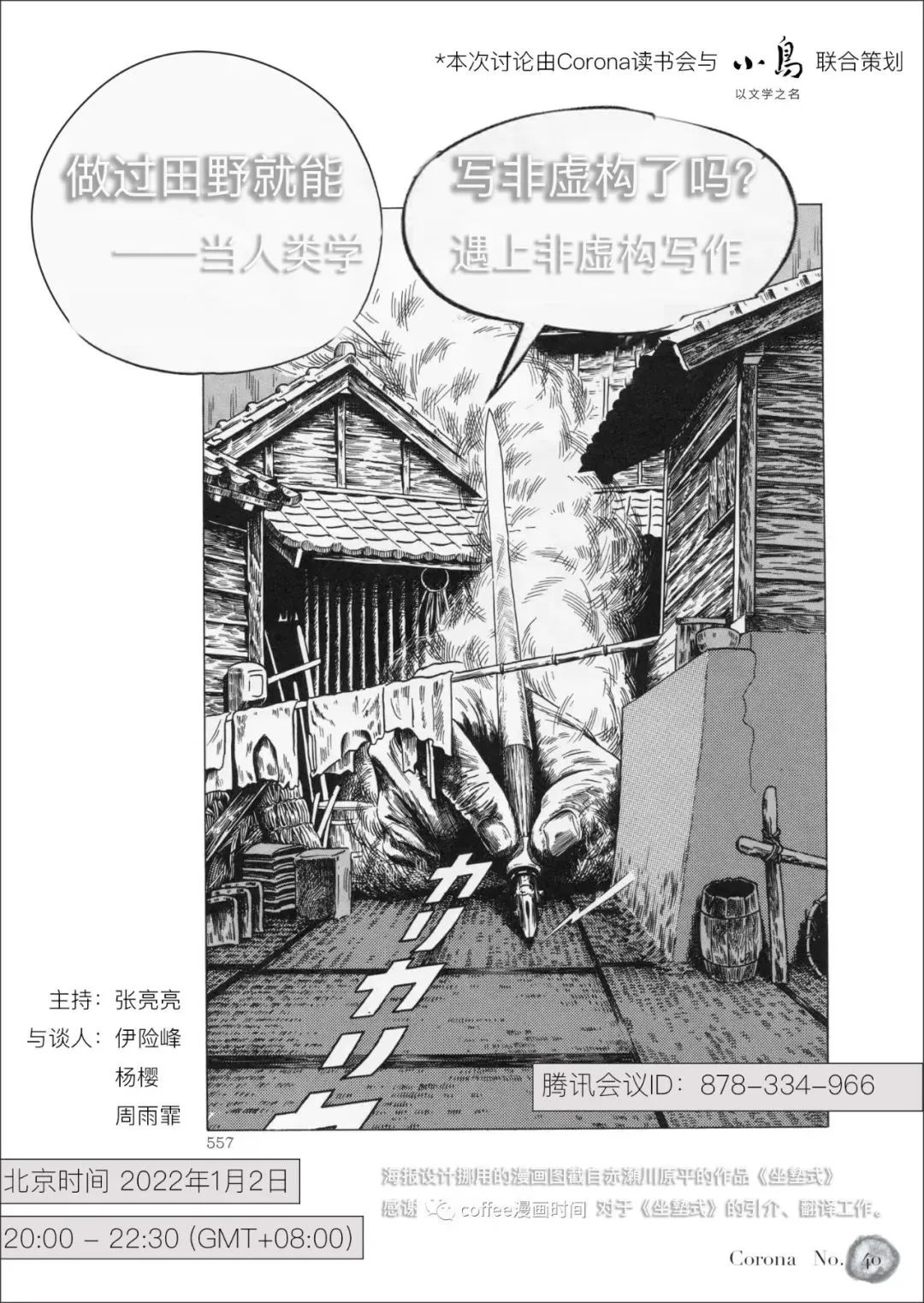
人类学学者项飚曾提到非虚构写作是一种原生态的、原初状的民族志写作。而民族志作为人类学的一种研究方法和写作文本,和非虚构写作具有许多相似的特征,比如大量文献资料的搜集、观察与访谈等。那么做过田野就能写非虚构了吗?何为非虚构里的伦理或问题意识?人类学家和非虚构写作者相互可以学到什么?有人类学感的非虚构写作可以是怎样的?这样的笔下,“我”是谁?“他人”是谁?“公共”在哪里?这一写作/知识生产的意义又是什么?这一系列问题促成了与《小鸟文学》一起合作的这期Corona。
–
本篇推送基于两位“田野中国”栏目的人类学背景作者——林叶和周雨霏的分享。林叶长期关注旧城拆迁过程中的日常实践与空间政治,她的非虚构作品《在“废墟”上过日子》探讨了在漫长的拆迁过程中,钉子户怎样维系一个废墟上的家;周雨霏的研究则关于藏獒经济以及人狗关系,其作品《加、加莫、加霍玛》可以理解为对女性身份的内在性和边缘性的跨物种、跨族群的讨论,围绕这两篇作品,重点关注人类学视角下的非虚构创作,非虚构写作中的伦理问题与“我”在非虚构文本里的作用。
–
本系列第一篇:纪录一列所有人的列车:非虚构如何写社会 | Corona x 小鸟文学 1
–
Corona是一个起源于疫情期间的公共讨论平台。底色是人类学,但疫情的复杂性很快溢出了既定的学科边界,读书会也逐渐转化为议题导向的半公共讨论平台,以期实践呼应应急性议题而非拘泥于静态理论的知识-行动联结。疫情和疫情次生社会现象之外,Corona关注的议题包括性别与LGBT、美国黑命攸关运动、基建、诗歌、他者、全球灾难政治等,也力图对紧急议题做出反应,如就20年洪水策划的鄱阳湖批判历史地理学和大坝与水利政治的讨论和今年的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环评阅读。有意加入或主题投稿的朋友请在后台留言。此前书单见石墨文档:
–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N2WHbleK9gN20TXDCvteG13708Jw6hBsAE-kNHL_q9w/edit?usp=sharing
–
以往笔记可以在上述书单中找到,整理后的文章可于结绳志Corona专栏里找见。有意加入本次讨论请直接按照海报上的链接加入,意图长期加入或主题投稿的朋友请在活动尾声联系主持的同学们。
主讲 / 伊险峰 杨樱 周雨霏 林叶
主持 / 张亮亮
客座编辑 / 木子
人类学视角的非虚构创作
张亮亮:
我想问一下我们在座的两位人类学背景的老师,你们是怎么样走上人类学的道路,然后又为什么对非虚构产生了兴趣?
林叶:
我其实特别同意前面那位老师的观点。你的问题非常正式,但是我很不好意思,我才为《小鸟文学》供稿一篇,我不敢说自己走上了非虚构的道路,但说是喜欢阅读非虚构文本的读者,我觉得肯定是没跑了。另外,我人类学博士毕业刚刚三年,其实也非常青涩和不成熟。我本科和硕士的训练来自于哲学系,确实是因为很喜欢人类学,最后才转换方向,选择人类学领域。在转换中,人类学对我的吸引主要是人类学的学术文本。相较于国内部分哲学文本,我接触到的人类学学术文本更有吸引力,这个观点可能有点粗浅。以前读到应星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和吴飞的《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场的文化解读》,我就非常喜欢;后来博士论文“拆迁研究”写不下去时,便把这两个文本拿出来看。虽然他们的议题已经跟我远离了,本身探讨的学术问题对我的论文也没有直接帮助,但是它们已经成为我文学阅读的文本,可以帮助我找回好的语言节奏。

另外,我特别喜欢侯孝贤的电影和朱天文的小说和剧本,在写作时,包括我写《在“废墟”上过日子》时,我会经常回看他们的作品。尽管朱天文的写作,有虚构的部分,甚至我们本身的方言语感并不相同;但她的文本中也有类似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调查,有很深厚的生活佐料,那种对材料的把握是准确和如实的,给我提供了可以被认为是非虚构写作里的一种方式。所以说作为人类学的学生和年轻学者,我会对非虚构写作感兴趣,除了与人类学民族志的问题本身有关,还和我自己个人的兴趣有关。

周雨霏:
刚才你问怎么走上人类学道路,我第一反应挺懵的,好久没想这个问题了,但肯定是跟刚才老师们讲的比较类似,比如对他人的生活感兴趣。接触非虚构也是类似的理由,特别高兴也特别认真帮「小鸟文学」写了一篇。
刚接触非虚构时,恰恰是因为我学人类学进入一个有点自我怀疑的阶段,那时有一种“我咋感觉我写的博士论文不太对”的感觉,然后才有“要不写个非虚构试试看”的想法。具体来说,田野结束之后,我其实去年刚开始写博士论文,在田野中,我觉得自己搜集到特别多材料,只差把他们写下来。但写作时,我发现自己不会写论文,不会写民族志,很多材料根本写不出来;发现自己读了这么多理论,不会生产理论,材料使用很僵硬,论点和论据结合不到一起,然后就特别自我怀疑。
那个时候我想发泄自己的情绪,想抛开理论,就在个人公众号上先随便写一下自己怎么学藏语、遇到的朋友和认识的老师,把写作完全当作自我疗愈。后来认识了《小鸟文学》的编辑曾梦龙,他跟我介绍了“田野中国”项目。我觉得我可以把更自我一点的反思告诉他,在非虚构这个领域本身再钻研一下,写一个公共性更强些的非虚构作品。我知道梦龙找了许多作者,其实很多人还没交作业,但是我当时干劲特别足,就开始写,写得还挺开心。等我把作品写出来后,自己心情也特别好。跟亮亮一起策划这次活动,也是因为写的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比如:写非虚构与写论文是不是有点对立的关系?我去写非虚构是不是论文更写不出来了,还是说非虚构与论文写作可以变成相互帮助的,发挥“1+1>2”的作用?我先说这些。
张亮亮:
谢谢雨霏的分享,我觉得在你刚刚的反思中,有听到我自己在写论文中的一些困惑。对于都是在英国接受人类学学术训练的我们而言,自己所写出来的东西,有时候会觉得理论性非常强,或是有些僵硬,离所处的现实生活有点远。所以我们对非虚构的兴趣,某种程度上来自于这方面的自我反思。我想请今天的两位作者分享一下,你们在进行人类学视角的非虚构创作过程中,会有什么收获,又遭遇了哪些挑战?对于其他想尝试做人类学和非虚构梦幻联动的朋友们,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周雨霏:
其实现在我最想讲的是刚才听了杨樱老师和伊险峰老师的讲话后,自己的一些感想。还有我读他们的书时,跟我自己脉络相关的回应。比如说我在读二位老师写的“社会人”时,边读边笑,特别有共鸣。这不就是我吗?我们不都是奖学金男孩女孩吗?有人把这种书呆子的感觉写出来,让我觉得很开心。我马上又想到,其实很多人类学家都有点书呆子的感觉,但恰恰人类学家又是所有书呆子里面,最觉得自己“很社会”的那种人:到当地去跟大家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劳动,回来讲了一堆很神奇的故事,跟社会学家、政治学家比起来就要生动很多,有一个悖论存在。我感觉我们这一代年轻一点的学人类学的同学,其实是很不适应这一套做田野的方法的。我们可能喝不了酒,也没法打成一片,有时候还挺社恐。学习人类学理论的时候,读了一堆结构主义之类的理论,真的到你去做田野的时候,其实是很手足无措的,也不知道怎么把经验跟理论联系起来。作为一个书呆子要去写非虚构,感觉又是个更大的挑战。
我是在读《张医生与王医生》这本书时,联想到了这么多内容。其实刚才听杨樱老师分享感受时,我突然一下意识到,有时候我们把自己的书呆子身份,看的有点太重了。所以在写非虚构的时候,就想一定要把我这方面藏起来,多写一点故事,不写理论,全部都是经验材料。但这可能存在一个新问题,就是读者已经不知道这是谁在写,“你是一个做研究的。我咋没读出来?”这里的悖论还挺有意思的。其实我写《加、加莫、加霍玛》这一篇时,带着很强的预设:一点理论我都不要写,我一个人类学家都不提,一个引号都不打,全部都写故事。这样去写一次,我觉得是挺爽的。恰恰在看完《张医生与王医生》这本书后,我发现即使作者本来就不是从学术脉络出发,但也在尝试把一些理论的讨论引入进来,可以让更多的读者读到。所以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觉得也不要太认为理论就不好。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光谱。光谱的一端完全是在学界内部的讨论,全是理论和概念;光谱的另外一端,是那种纯故事,纯公共写作,一点理论都不沾。而这两级之间的模糊地带,其实是挺广的,不要把自己框在某一种套路里,可以用各种各样理论的方式去写故事,或者用故事的方式写理论,我觉得可能都是可行的。不是说人类学和非虚构现在要合作,在中间相遇了,相遇的就是一个固定的点,最后我们所有人量产出来的人类学分析,都是一个套路,不是这个意思。中间排列组合的方式是特别多的,每个人都可以在中间,找到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位置。比如说《张医生和王医生》呈现出了一种模式,林叶老师是一种模式,我也是一种模式,慢慢的模式越来越多,相互之间可能形成一种生态。我觉得这可能是人类学与非虚构梦幻联动更有趣的方式。我还想到一点,我这一篇和林老师那篇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我发现林叶的材料中,非虚构的材料和论文的材料基本上特别相似,但是她用同样的材料,组织出了两篇完全风格迥异的文章,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
林叶:
谢谢雨霏。我的那篇文章,大概有1/4到1/5的内容,跟我的一篇已经发表的论文,有部分是重合的,后面更多的是没有写过的田野材料。我不是一个很典型的社会科学论文的写作者。我的论文很难发表,会被认为不够学术化,大多时候是在一些不那么在意这些学术框架的地方发表,反而是很严苛的地方不接受。尽管我本身也是学术编辑,但是可能我自己也不会接受自己的文章。你看到的我的学术文章,我的方法是把非常像非虚构的文本,直接用楷体字的方式,当成引文,就是我引我自己的田野日记,但其实这不可能是一个真的、散乱的田野日记,这是经过写作的。
很感谢雨霏对我文字处理的称赞,但我认为跟大多数社会科学的作者相比,我的学术论文不太学术,已经不是那么严格的东西了。另一方面,她的提醒很对,因为我在写第一篇文章的时候,感触会特别的深。刚才杨樱老师讲了一个很犀利的事情,有的人——我可能也算——故意把文章里面的学术、概念、和作者对话的部分拿掉了。我们认为要变成非虚构,我首先得把这个拿掉,我也是这样去做的。但是我刚听完她的评价以后,会有点小庆幸。我觉得拿掉那些东西以后,好像我的文章还行,还讲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事情。
这背后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问题,我之前也跟雨霏讨论过。作为人类学的学生,民族志的写作练习者,用同样的材料练习写非虚构作品,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种训练和反省。反省什么?至少我在中文界看到,我们的刊发自由度实际上并不高,并不那么友好,基本还被笼罩在一个因果律下讨论,要对因的事件或因的现象,和果的现象之间,做一个勾连。在这个过程中,尽管你会使用本地的、地方性的知识,我们觉得非常动人的、微小的事件,但是最后你要写成学术文章,一段学术的论述,实际上会不由自主地把那些事情扁平化、普遍化,因为你觉得这是符合社会科学逻辑的,还要被迫或者主动地跟既有的学术脉络去对话,所以这会导致我们的生肉(原始材料),也就是田野里面打动你的、富有价值的原初的东西,经过这么一系列的处理,最后剩下来变成另外一个东西。然后比如说你碰到《小鸟文学》了,他说你给我写个非虚构,得把这段理论拿去,很有可能拿掉以后,最后发现文章不剩什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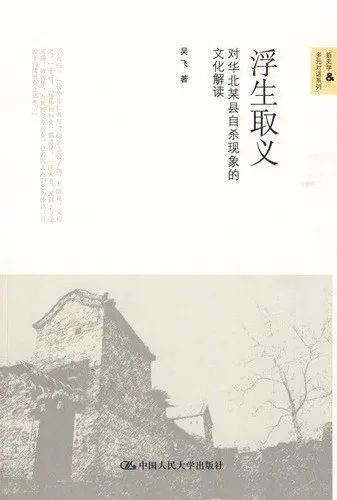
我并不是说大家在田野的时候,没有东西积累。但是你在写论文时,大多情况下,为了要完成它,要对搜集到的素材进行大量地切割,最后会破除掉伊险峰老师刚才说的完整性。 如果我们很笨拙地把这些东西扔掉,只剩下那一点点被切割后的材料交给非虚构栏目,就会得到像杨老师刚才说的结果,那是有点可悲的。所以对我个人来讲,写作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且很好的练习。这并不完全是为了变成更好的人类学者。 我自己是一个主动踏到人类学领域里的学生,真的很喜欢,所以我才进入。我自己还是希望,能够保持当时进入人类学时的初心。人类学打动我的一点,就是你用你超常人的卧底方式身在其中,这是很辛苦的,而且产出很慢。但是这个方式,可以保证我们能够对我们所感兴趣的生活世界更加接近,或是更加理解本地人的那个世界。只有通过这个方法,你才能够进入。你在外面观看,是了解不到的。我们的学术写作在大多数情况下,被迫要你切割你获得的这些东西,这是很可惜的,有点背离我们最初进入人类学领域时,那些苦功背后的动力。我自己觉得,如果大家有兴趣发表或没有发表的非虚构写作,实际上是可以帮助恢复我们最初的动力,这样的动力是我自己觉得特别宝贵的。
非虚构的伦理考量
天伊:
目前我是一个在做人类学田野的学生,我也给《小鸟文学》投过稿,虽然我一开始说我写的是非虚构,但编辑觉得放在虚构那栏更合适。这件事之后,引起了我的一个思考,如果把非虚构作品发到这种文学或更具公共性的平台上时,存在哪些伦理考量?在人类学学术研究中有一些很基本的伦理考量,比如说不要制造伤害,如果预期伤害大于预期收益就应该终止或者考虑其他的替代方式。我在投这篇文章时就已经想到这个问题了,因为那篇文章写的是我自己,最后把它放到虚构那栏,对我而言更安全,我就很想知道这是否出于非虚构的伦理考量。
杨樱:
你的小说写得很好,我们当时的确讨论过虚构与非虚构的问题。先从你的投稿开始说,那篇文章更接近于个人经验与自述,准确来说自述很难证实或者证伪。虽然你自己说有安全性的考虑,所以你觉得放在虚构的范畴里未尝不可,但是从我作为编辑的角度,或者一个信息发布者的角度说,倒不是出于某种伦理,我直觉上把你的文章归为虚构跟伦理没有太多关系,与所写内容是否可以证实有关。如果抛去文章不看的话,广泛地说你刚刚问的非虚构伦理问题,关键就在于我发布的文字信息某种意义上是可以被证实的,这里包括所谓的公共利益,相当于你不能做一个假新闻,你可以这样去理解非虚构的伦理,你也可以说不能侵害当事人的权益,不能对他人造成伤害。
伊险峰:
从媒体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了解到的公共性,对于当事人或者涉及利益方的伤害都会考虑在内。像我们以前做《第一财经周刊》时,因为涉及到很多商业报道,如果我要说这个公司发生一些问题,可能会影响它的股价变化,这个时候我就需要去斟酌,核心是这个公司的问题是否侵犯了公众利益,一般来说公众利益都大于某一个人的利益。美国的《纽约客》设有事实核查部门,会有大量专职人员去调查记者所写的是否属实,这是完善伦理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伦理不只是新闻伦理,也不是人类学的伦理,你要符合整个人类的伦理。
在非虚构的领域里,除了涉及到他人利益的东西外,我们在写作层面,从文学角度也有问题存在。以前《三联生活周刊》有一个主笔,他写“有一个人自杀了,然后头一天晚上想了一夜”,那你这个作者是怎么知道他“头一天晚上想了一夜”这个细节呢?这就是虚构的成分,当它出现在非虚构里会让人不舒服。虽然这个细节无关痛痒,谁自杀前可能都会想一夜,但你不能去编造。一个好的非虚构作者,他笔下的内容都要有出处,不能让人挑出任何的把柄来。非虚构作者应该一直保持一种很干净的状态,即使你现在已经特别有名气了,但是当有人找出你以前写过的文章,发现里边有很多硬伤,这就是写作生涯的一个污点。如果你是一个有野心的作者,为自己的未来考虑,那么你对自己的要求就应该更严格。
把“我”作为工具人
张亮亮:
刚才在我们的讨论中发现,无论是人类学还是新闻界的作业者,在某一个社会现实内进行研究时,会不可避免地对正在生成的事件产生一些影响。我觉得这些问题的背后可能都存在某一指向,就是说不管是人类学还是非虚构写作,作者都会以某种方式存在于自己所创造的画面之内。就像我们活动海报所引用的漫画那样,那支笔和写的手是直接插进了那个世界里面。我想请各位老师分享一下,在写作的创作过程中或者写作方法上,你们会怎么处理自己和故事之间的关系呢?非虚构和人类学之间会有什么不同?

杨樱:
我觉得林叶的“废墟”和雨霏的“藏獒”这两篇文章放在一起讨论,正好可以回应刚刚的问题。因为一个里面的“我”特别多,一个里面的“我”其实没有那么多,但你会发现两个都很好看,且都是相当合格的文章。你说是田野、或者是非虚构写作都可以,其中只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是否必要。有些“我”的出现只是为了“我”,他无法摆脱这个自我,哪怕他并不需要出现在文章里。这某种意义上是写作者的一种紧张,或者说不定是自恋,他无法判断自己在文章里的必要性。但如果作者一旦能认清楚,自己与他要写作的目的也好,细节也好,场景也好,认识到其实有他没他都可以。并且要写的某个对象,其重要性远胜于他的话,那“我”就是不必要出现的。举个例子来说,我要去写张医生、王医生做手术,我在手术室里,这个手术室会因为我的存在而打破他们日常的场景,那这个“我”的存在是有必要的。但是如果要写一个门诊或医疗的场景,按照非虚构的说法,“我”是墙上的一个苍蝇,“我”是不说话的,最好“我”就像旁边假竹子一样的存在。这个时候“我”是不会出现的,这里面只有一个需求性的问题。
伊险峰:
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有价值,我们媒体界就特别在意这个。如果你写一篇文章,然后这里边“我”出现了,“我”到底是干嘛?一般都经不住问的。我看的《秘密生活》写了三个互联网界的人。分别是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比特币之父中本聪和一个去世三十年的数码人。该书作者安德鲁·奥黑根是一个很著名的非虚构作家,他写的故事就是属于“我”怎么跟这三个人打交道,其中“我”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一个存在。“我”被某一个出版机构雇佣去写某一个人的传记,“我”出现在某个人的面前,“我”跟某个人在博弈,每一个人都展现出来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这本书后期也提到,“我”领他们去看病,还借过他们钱,这些事作者都要写出来。这些东西就表示“我”干涉了他们的生活,这个时候就要表现出来,得把这个东西说清楚。

周雨霏:
我特别同意杨老师之前说的“我”有没有必要,我就用一个更极端一点的方式来讲。我们最近不是喜欢说,xxx是工具人,有一种道德是不要把别人当工具人,但我觉得在写非虚构或民族志时,每一次写你自己时,你都得严格地审视“我”有没有做一个合格的工具人。我觉得这是一种监督自己,不要太自恋的方法。但我觉得人类学学者写非虚构时,在此之上又多了一重复杂性。因为人类学做田野的方法就是带着特别强的自我,去跟各种各样的人互动,通过“我”和“你”之间反复、来回的共处,然后才能获取到所需的材料。
我们在写研究内容时,会经常提到我们在使用这样的方法。要提到这个方法就不可避免地要写到你和对方各种各样的互动,就会出现很多很多的“我”。所以有些不习惯的读者会感觉“我”显得过剩,但其实对人类学来说这是我们学科自我定位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也不能一概而论。
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可能看起来这个文章中的“我”全部都是工具人,都在烘托故事真正的主角,那些人和那些狗。但作为我自己这个人的“我”,我是怀着非常强烈的个人感情在写这篇文章。写的时候非常激动,因为田野中你经历过的那些感动,你的挫折,你的痛苦,你就需要写出来。但是当你不能写自己太多的时候,你可以通过去写别人生活的方式间接地写你自己,把你对女性身份、汉族人身份这些问题的思考藏起来,藏在对别人的书写里。表面上好像没有出现带引号的“我”,但通篇都是作为自己在写。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种方式,把自己的感情完全揉碎了,藏在叙事里。别人可能读完后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问题,但是他通过读你写别人的痛苦,你的感情也能间接地传递到读者那里。
林叶:
杨老师刚才的对比做得很清楚,两篇文章适合用不同的处理方法。所以我在自己的那篇文章里把“我”抹掉了。
刚才杨樱老师说“我”要像墙上的苍蝇一样,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是讲美国60年代直接电影发端的时候。他们说“我们做直接电影,就好像要把摄影机器放在墙上的苍蝇一样”,强调的是不干预、不干涉。我那篇文章好像是把自己隐去了,但写出来的那些东西是很近的。就好像我的镜头在那儿,但我在它背后不说话。雨霏那个文章就好像她一直在后面叨叨,像是她把镜头放在自己的眼睛上,是非常主体的视角,让你身临其境、感同身受。
我的文章表面上很客观,但实际上离笔下的人和物很近;离他们那么近,你是不可能隐身的。所以我自己觉得我的那个算是一个比较无聊的,也比较普通,但也是常见的一种身位。你离他们还是非常近的,你看起来的隐身是通过在田野当中漫长的相处,你是对方身边司空见惯的一种人,到那个时候才会做到这样的隐身。但我觉得这个隐身和在墙上的苍蝇那种、直接电影式的不干涉还是不太一样。我也很同意杨老师说的,在处理上,我要写的部分或那个事件、那个过程里面,写不写“我”都可以的话,我可能就会考虑把它抹去。但是如果我们纠结的话,确实这个“我”始终在旁边,我觉得这是无可逃避的。
最新文章(持续更新)
拯救田野的非虚构?| Corona x 小鸟文学 2
欢迎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保持联系
独立网站:tyingknots.net
微信公众号 ID:tying_knots
成为小结的微信好友:tyingknots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