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5|corona回顾|弧线如何弯曲(下)埃博拉与知识-行动共同体

1983年,还在杜克大学念本科的保罗·法默(Paul Farmer)来到海地中部一个名叫康热村(Cange)的地方,开始了他在村诊所的志愿服务。后来很长一段时间,这里成为了他研究、行动的根据地,甚至第二故乡。今年2月,保罗·法默在卢旺达因心脏病发去世,掀起全球广泛的悼念行动。无论如今的人类学对法默秉持的医疗人道主义有多少批判,他都已然是20世纪末人类理解和应对流行病的历史上一个绕不开的名字。
–
在这场持续延宕的疫病之下,重新阅读和讨论保罗·法默并不是一种单纯的纪念,或为令人困惑的当下寻求某种答案,而是要在变动的语境之下进行批判性反思。尽管意图用跨国医疗资源输送弥合不平等、甚至曾与卢旺达独裁政府合作的法默并不完美,但他的思想与行动遗产中始终直指这样的核心问题:疫病向我们揭示了什么?医生能做的是什么?公共卫生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
本期文章是对2022年9月进行的“弧线如何弯曲”corona读书会分享整理,分为上、下篇。上篇由结绳志编辑孟竹和上海教育出版社《当代瘟疫:传染病与不平等》(Infections and Inequalities)中文版责编储德天分享法默关于责难的地理学、结构性暴力的书写,以及他对结核病与不平等的思考和实践。下篇由《瘟疫、世仇与钻石:埃博拉病毒与历史的劫掠》(Fevers, Feuds, and Diamonds)中文版责编郭悦,以及《当代瘟疫》译者、“心声mind”平台创办人姚灏分享法默在西非埃博拉公共卫生治理中的历史思考,以及法默对公共卫生行动者的启示。
分享人 / 安孟竹、储德天
特约编辑 /心澈
03. 瘟疫、钻石与世仇:埃博拉病毒与历史的劫掠
郭悦 中信出版集团回声工作室
大家好,我是中信出版集团回声工作室的郭悦,非常荣幸受邀参加这次活动来分享保罗·法默2020年底完成的一本新书,也是他生前的最后一本专著,名叫《瘟疫、钻石与世仇:埃博拉病毒与历史的劫掠》,这本书目前还在翻译中,预计会在明年和大家见面。
我和保罗·法默这本书的缘分大概是从他2017年的传记《越过一山,又是一山》开始的,读完那本书我很受感动。虽然那个时候我作为一个编辑的主要选题方向是文学,但是已经默默在心里埋下了这个种子。这里还要提到另外一个人就是凯博文(Arthur Kleinman),我求学阶段就非常喜欢的一位作者,他对我对于医学和疾病的认知其实是有非常大影响的。能够出自己喜欢作者的作品当然是一个编辑最大的理想,所以我在2020年的时候就做了凯博文《照护》这本书,这本书的译者姚灏老师也在现场。姚老师翻译这本书的时候刚刚毕业进入临床,他为《照护》这本书写的译后记也非常感人,尤其是关于年轻医生在实践中的照护伦理问题,相信看过的读者都会印象很深刻。也正是因为《照护》这本书的出版,更加坚定了我要继续在医学人类学和医学人文等领域寻找一些优秀选题的目标。所以这时保罗·法默就再次出现在我的名单里,也是在《照护》出版的那个月,2020年的11月份,这本《瘟疫、钻石与世仇:埃博拉病毒与历史的劫掠》也在国外发行了,我很自然地注意到了这本书,也非常顺利地签下了这本书的版权。不过当时也有一些人质疑,说为什么要做一本厚度将近700页的关于埃博拉病毒和西非史相关的书?所以我现在就来给大家简单分享一下保罗·法默为我们留下的珍贵的记录和这本书的价值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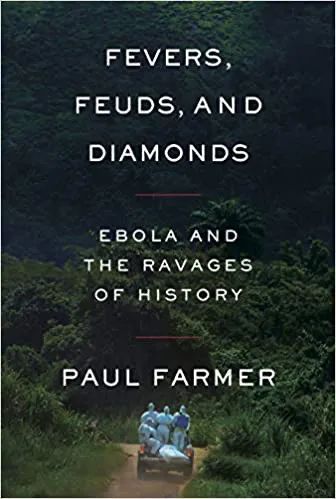
在2014年的时候埃博拉病毒迅速而且非常疯狂地席卷了几内亚、塞拉利昂还有利比利亚等西非国家,这本书里就详细介绍了埃博拉暴发的起源和后果,还有病人、临床医生和护理人员的故事,以及国际社会的反应状况,还有当地的一些幸存者对治疗埃博拉病毒的回忆,以及支撑起这一切的社会历史根源。在2014年的6月份,其实是因为一个关于外科护理的医学会议,保罗·法默就来到了埃博拉疫情中的塞拉利昂的首都弗里敦,当时他只认识四个塞拉利昂人,分别是凯内马公立医院的院长胡马尔·汗,还有另外两位外科医生以及他的学生拜勒·巴里。但是到当年11月份的时候,胡马尔·汗和其中的一位外科医生都已经死于埃博拉病毒。胡马尔·汗是在7月29日过世的,他的死亡在全球的公共卫生界引起了震动,而这场国际公共卫生的紧急事件也很快就把保罗·法默和他健康伙伴的这些同事带到了西非。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奔走游说,终于得到了一个机会,就是在塞拉利昂当地的协助下,将疫情严重的马斯基地区的一所废弃的职业学校转化成了埃博拉的诊疗中心,并且同时他们也在洛克港的一个地区医院工作,重启当地已经濒临崩溃的临床系统。
提到埃博拉很多人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各种宣传资料,尤其是小说、电影,还有网上的一些所谓科普视频中呈现出来的信息,比如七窍流血、比如90%的死亡率等等。但是在这本书中保罗·法默首先驳斥了对埃博拉的这种误导性的说法,他指出即使是在严重的埃博拉病例里,也很少产生类似于普雷斯顿在《血疫》中描写的那种眼球出血,器官几小时内就液化的恐怖症状。在对埃博拉病毒的主要体征和症状的详尽调查中,我们会发现这种不受控制的出血,甚至都没有进入到前10名。在西非的埃博拉疫情中最常见的症状,其实是发烧、紧张性疲劳、食欲不振、头痛、恶心、呕吐和腹泻。而埃博拉病毒在西非的上游地区如此致命的原因,也并不是因为病毒本身下达了这种不可避免的死亡判决,而是因为像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这样的国家,它们缺乏基础的医疗保障。法默在书中写道:“除了一个在利比里亚出生的美国公民以外,每一个因为在西非传播的病毒株而患病的美国人都活了下来,大多数的欧洲人也是如此。”这就引出了社会医学的两个非常传统的问题:一个是为什么埃博拉病毒在某些地方传播如此之快,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却没有?还有就是,为什么它杀死了一些感染者,又放过了另外一些感染者?
在西非的案例中毫无疑问的是,这三个受灾最严重的国家,有着世界上最薄弱的医疗卫生系统。其实只要有一家像样的医院,大部分的埃博拉患者都能得到活下去所需要的护理。这种护理意味着有待命的急诊室、重症监护室和手术室。而即便是在疫情已经非常非常严重的2014年9月之后,当时各方的援助资金已经源源不断地流入了几内亚、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但我们也没有见到太多能够阻止疫情传播的人员或者资源,或者空间。因此法默说:“尽管塞拉利昂的雨量很大,但是他们的公民却困在了医疗荒漠中。”而为了对这一个问题进行开脱,掌握话语权的人会用很多在这一地区非常司空见惯的一些习俗和信仰,来解释埃博拉在西非的出现和传播。比如说埃博拉是由于当地古怪的治疗和性行为,以及神秘的丧葬仪式、放血仪式,以及使用丛林肉等原因而导致的灾难性传播。尽管不可否认,埃博拉传播的原因里面,传统葬礼确实加速了它的传播速度,但是刻板地认为这种做法是西非专属,是荒谬的。法默因此回应说:“我们必须要停止告诉自己关于不可阻挡的突发病毒的恐怖故事,因为这些故事往往使我们的不作为合法化。”
另外法默也从国际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对埃博拉病毒的反应不足里,看到了一个殖民主义的遗产——“防控而非护理”。这也是法默在本书中重点指责的问题。他认为大家都太急于控制病毒、识别病例和隔离病人,以减少疾病的传播,却忽略了更为重要的,也就是为患者提供基础护理,以启动免疫反应。所以在一次采访中,法默有谈到说:“当我还是一个医学生的时候,我就发现这种非常急迫的疾病控制令人很不安。你的所有注意力都会集中在阻止病原体的传播上,但是却没有足够的注意力和资源来治疗有上述病原体的人。所以对于埃博拉,人们会误解说,‘数10亿美元都被投入到埃博拉的护理中’,那是胡说八道,他们根本没有投入在护理中。如果有的话,我们就会有与我们在欧洲或美国看到的类似的病例死亡率。”所以这本书中除了回忆他在西非期间的经历和幸存者的故事外,中间还有一个部分是一段非常大篇幅的历史回顾。为什么要在谈论埃博拉的时候回溯当地的历史?法默说:“首先,如果我们不了解西非和欧洲和美国的长期纠葛,就无法充分理解西非传染病和它的社会反应。此外,这段历史非常耸人听闻:从跨越大西洋的奴隶贸易,到19世纪末欧洲对非洲的分裂,一直持续到冷战初期的殖民统治,以及到本世纪才结束的钻石争夺战和四处暴发的疫情,所有这一切之间都是彼此联系的。”最后一个原因他说:“我们需要正本清源,因为大家会把疾病的发源地称为“发热的海岸”,之后也会进一步炮制发源地为“白人的坟墓”,这些说法带有浓厚的加害者自我开脱的意味。通过这种包藏私心的耸人听闻和老调重谈的种族主义,形塑了我们理解前殖民世界以及今日困境的思维模式,这样一种思维模式所导致的物质遗产,就包括了这种根深蒂固的卫生差距、疯狂传播的流行性疾病、脆弱不堪的卫生系统,以及普遍缺乏的民众的内在信心——这些也是我们整个时代的公共卫生的问题,而它们的根源其实可以在殖民时代找到。所以他也说,理解历史可以帮助我们分辨那些对疾控工作无知而充满敌意的反应,也可以帮助甄别那些专家提出的稀奇古怪的主张,更可以帮我们尊重西非的原住民,让我们在面对疫情的时候做得更好。

我也想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书中的故事,这个故事也是法默写这本书的动因。这个故事的主角是法默在塞拉利昂遇到一个埃博拉的幸存者,叫易卜拉欣。他们的第一次会面易卜拉欣就谈了两件事。一个是当地的ABC(Avoid Body Contact)避免身体接触运动。易卜拉欣非常愤慨地说,所以政府其实是在告诉我,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的母亲虽然她怀了我,生了我,养育了我,但是当她突然倒在地上,吐了一地的时候,我却不应该帮她站起来,给她擦擦身子?我却应该拨打一些永远不起作用的紧急电话,而不是自己去帮助她?这太让人生气了。第二件事是一个数字,23,这个数字是易卜拉欣死于埃博拉病毒的家人的数量,这其中包括了他的母亲、祖父母以及阿姨、叔叔,还有表兄弟。所以在之后法默对易卜拉欣的采访中,易卜拉欣分享了他的家族故事,关于殖民统治对家族所产生影响以及战争所导致的颠沛流离与贫穷。他说“像我父亲这样的人,虽然一直在不停工作,最后却一无所获,而这个国家毫无疑问地拥有财富,腐败的政客却把财富都拿走了,让我们靠分配给狗的残羹冷炙过日子”。战争也让他第一次体验到了饥饿和恐惧,战争也中断他的教育、杀死了他的父亲。而在他的母亲感染埃博拉之后,因为照顾母亲,他也染上了埃博拉病毒,但是他跟法默解释了为什么人们都知道接触死者的尸体有极大的风险,却前赴后继。他说“因为在塞拉利昂人们认为最可怕的其实不是死亡本身,而是孤独地死去,得不到体面的葬礼,让一个人与世界的联系彻底消亡”。而在处理死者和照顾垂死的人这件事上,政府和社会机构没有给他们任何帮助,所以他们别无选择。
非常幸运的是易卜拉欣幸存了下来,之后,他反复跟法默提到,希望能够帮助埃博拉患者,他说他可以做一名护士助手,或者是帮助人们知道他们有机会变好,至少是和他们说说话。但是对于这一点,法默很慎重,一直没有答应他。直到2014年12月底,有一个叫马里亚图的9岁女孩转到了健康伙伴负责的埃博拉诊疗中心,这个女孩亲眼目睹了她的母亲和妹妹死于埃博拉病毒,她自己好不容易才保住了性命。在1月10日左右,血液测试显示她的血液中已经没有病毒,但奇怪的是,马里亚图的身体并没有恢复过来,她既不吃饭也不说话,体重也在下降。于是她被转到了洛科港政府的医院,她拒绝所有食物,医生试图用鼻胃管给她喂奶,她也不说话,并把管子拔了出来。一位幸存志愿者试图让马里亚图吃一种小孩子几乎无法拒绝的高蛋白、高热量的花生酱,她也拒绝了。法默过去看望那个女孩,给她做了临床评估,得出结论:她既没有患结核病,也没有其他未诊断的感染或者癌症,但如果她再不进食,可能很快就要死了。易卜拉欣知道了女孩的情况,强烈要求去看她帮助她。在反复的纠结之后,法默终于同意了。来到医院,易卜拉欣坐在马里亚图的床边,非常温柔地和她说话,把手轻轻地放在她瘦骨嶙峋的肩上。虽然法默前一天也是这么做的,但是没有任何效果。而一分钟后,法默正在翻阅图表的时候,余光瞥到了令他非常惊讶的一幕:马里亚图转过身来,颤抖地坐起来了,把她瘦小的身躯靠在了易卜拉欣的身上,并开始在他耳边低语。医院的工作人员,无论是美国人还是当地人,都非常惊讶,因为他们从来都不确定她是否真的会说话,但易卜拉欣似乎毫不费力地说服了她。马里亚图跟易卜拉欣要了一些果汁和饼干,终于开始进食了,她把储备食物都吃干净了,甚至告诉易卜拉欣,她想要回家。易卜拉欣对她说,你再待一段时间,好好恢复,好好吃东西,很快就可以回家了。而对于易卜拉欣来说,这一天也意义重大。他在当天午夜回家之后,忍不住给法默打电话:“这对我来说,是生命中最伟大的一天。这是家人去世后我去的第一个医院,而事实上,这也是我生命中最棒的一天。”
之后,易卜拉欣得到允许陪伴马里亚图,直到她康复离开。而易卜拉欣也成了健康伙伴的一名幸存志愿者。法默回到卢旺达后,收到了马里亚图的短信,她说:“愿真主保佑你们所有人,谢谢你们照顾了我。”法默把短信转给了易卜拉欣。
正是和易卜拉欣的友谊,和他故事中引发的思考,促使法默写下这本书。他说,“我们的友谊是一份持久的礼物,反映了那个时代最美好的事物——当时有那么多人在实实在在地努力相互照顾。我做人类学家的时间和我做医生的时间一样长,我想,如果我要将易卜拉欣如此苦难的经历写出来,那最好是为了别人,而不仅仅是为我自己。”
2020年的4月,法默写完了这本书的最后一节,他反思埃博拉病毒的核心危机,就是将“防控而非护理”作为信条,而新冠肺炎疫情那时已经引发了防控的危机,当这样的事情出现时,人们突然更加意识到我们对所谓繁荣景象的把握和拥有是多么脆弱。和埃博拉病毒一样,新冠的管理、治疗和最终控制将由“医疗人员、设施、空间和系统”来定义,而这本书提出的一些针对埃博拉的解决方案,包括加强公共卫生系统,建立安全网络,建立失业、灾难性疾病和葬礼的保险等观点,也适用于当下,但这些事情从来没有得到过足够的财政支持。所以法默说,虽然这本书不会产生任何资源,但是如果它能产生理解,引导正确的资金支持,也将是一个伟大的贡献。法默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不仅需要疫苗,还需要更多的东西——拒绝全球性的健康不平等,以及认真地拥抱对所有人的关怀。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真的要从埃博拉疫情中吸取教训,那可能就是在大流行病期间,对于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我们都要持续问同一个问题:这会有帮助吗?”我相信这个问题也会一次一次地给我们一些宝贵的提醒。
04. 法默后,我们该如何行动?
姚灏 心声mind创办人、《不平等与瘟疫》译者
保罗·法默今年2月份去世以后,我一直等着国内能有哪家学术机构、医院或者公共卫生学院能办一些关于保罗·法默的纪念活动或学术讨论活动,所以也非常感谢结绳志能够组织这样一次关于保罗·法默的读书会,有这个机会去讨论法默留下的行动和思想遗产。当然也非常感谢上教和中信,还有薄荷实验这些出版方引入保罗·法默的作品,非常感谢这几家出版社对于法默以及相关医学人文的推动工作。
在《传染病与不平等》里,他讲了公共卫生领域怎么把预防放在了一个优先位置,反倒忽略了我们对于临床救治、临床照护的重视。其实这次的新冠疫情大家也可以看到,对于疫情管控的优先级很多时候大于对于个体和人群的照护。对于法默,我们有很多可讨论的维度。今天我只是摘取了对我自己影响很大的两个点:一是“与人同在”,一是“知识行动的共同体”(或者叫“知行合一”)。法默对于我过去几年的求学、工作和公益行动,都给了我很多启发和影响。
结绳志之前也讨论过研究到底是为了什么目的。尤其是我们在关注一些弱势边缘人群时,这样的研究到底目标何在?有怎样的意义?很多时候我们针对弱势人群去做相关研究,做了几年以后离开了田野,过几年再回到这个田野里去看,会发现同样的问题依然存在,同样的困境和社会性苦难依然在影响、摧残着当地人。做新闻的都知道,那位很著名的记者Kevin Carter当年拍《饥饿的苏丹》时也面临着同样的伦理困境:面对苦难,我们只是做一个记录者,还是应该去做一个充分的、对当下困境产生影响的影响者?很多时候我们的作为临床工作者、医疗援助者,我们来到某个“缺医少药”的地方,这样的短期援助可能是“潮汐式”、“赶集式”的;哪个地方出现了疫情、战乱或冲突,我们会派一些医生、护士去到这里,可一旦这种援助结束了,医生、护士离开了,当地依旧还是面临着缺医少药这种医疗照护资源的缺少。

作为一个医生,我也常常在想,我们在医院里面对个体的患者时,到底只是关注ta的某些健康需求,还是把ta的诉求作为全人类的课题去看待——在看到ta现阶段的需求之外,在更大的社会脉络与场域里所面临的更大的困境?
薄荷实验前不久引入了法默演讲集,里面最后一篇文章,是当时2011年法默在哈佛肯尼迪学院做的一个演讲,题目叫做“陪伴作为政策”。当然,因为他是针对肯尼迪政策学院的学生去做这个演讲,所以“政策“是他演讲的一个关键词。但里面有个非常核心的词——陪伴。陪伴这个词是贯彻于法默所有研究与行动、甚至他整个人生脉络里非常关键的一个术语。在那篇演讲稿中,法默也引用了一位解放神学家的话来解释“什么叫陪伴”:他说,陪伴就意味着你要去到那个人所在的地方。“陪伴”这个词在拉丁语中的词源是“分开面包”,所谓陪伴,就是“面包与人共享”的意思。所以,你需要把你所有的食物和资源给到那个ta,给到那个你能够陪伴的人,共同度过一段旅程——这就叫陪伴。我们在结核病防治领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治疗策略,叫“直接督导下治疗”(DOT,Directly Observed Treatment)。但在公共卫生领域,我们讲的“防控”、“督导”,多多少少都带有一些家长制意味的父权色彩。而法默在他的公共卫生实践过程中,则把那些为当地患者提供直接督导治疗的服务者称为陪伴者,因为在他看来,他们并不是以一个监督、督导、管理者的角色去介入患者的生活。他本人也是作为陪伴者,去陪伴那些患病的个体一起度过疾病的苦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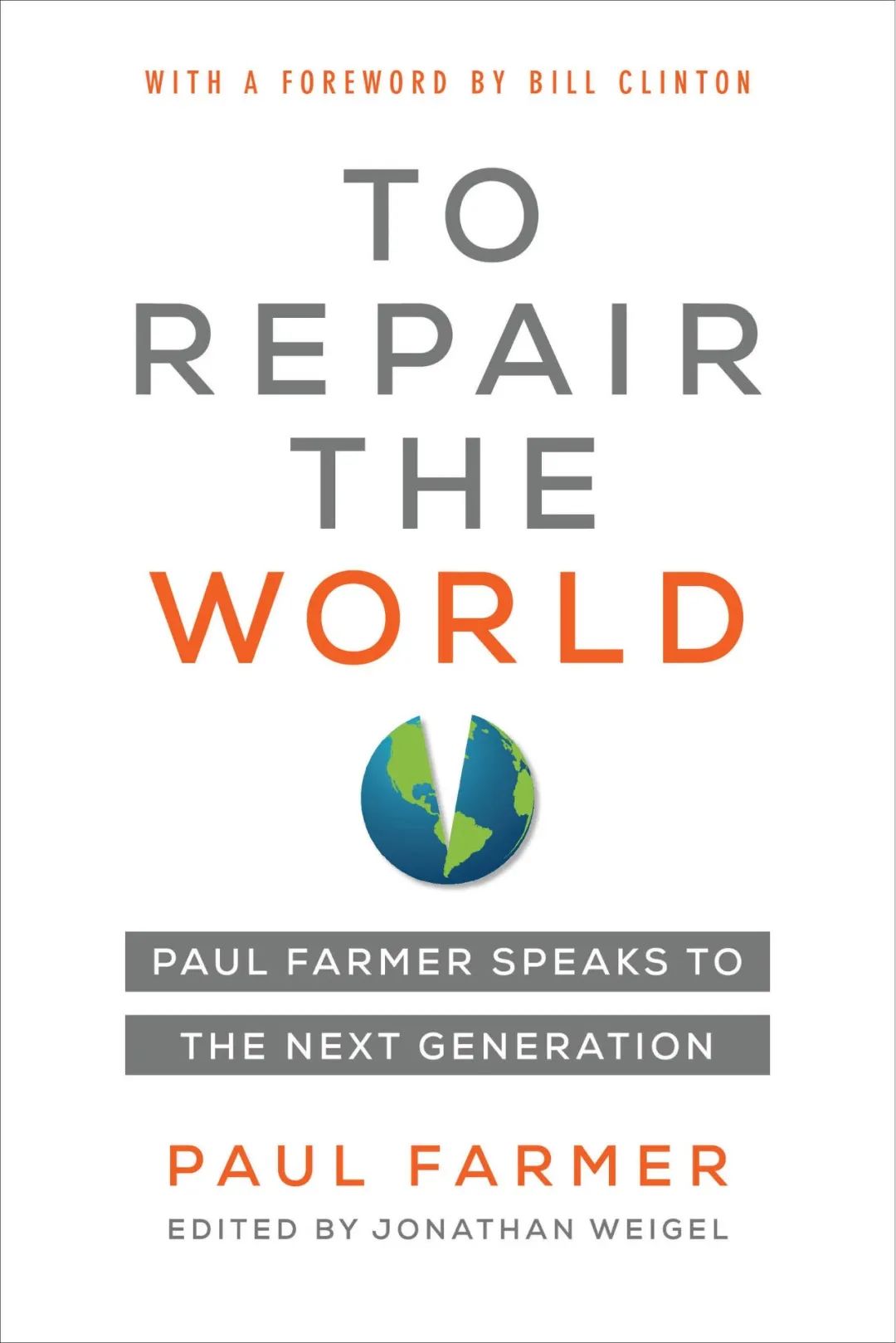
当然,“陪伴谁”则是另一个问题。解放神学的核心特点是“优先选择穷人、给予穷人以优待”,这也是贯彻在今天许多全球卫生行动中的理念,那就是社会正义与健康公平。很多时候,对于那些资源欠发达地区的弱势人群来讲,他们的疾病负担远大于生活于富裕国家与地区的人;另一方面,他们能够享受到的医疗与照护资源则远少于富裕地区的人,因此会出现一种恶性循环。为什么我们要给予那些弱势的人群以优待,因为在健康的梯度上,他们本身就处在弱势的地位。我们所提供的服务、照护、陪伴,如果不能更多地向那部分人倾斜,就会导致整个健康或疾病的梯度上更大的不平等。这不只是法默,是整个全球卫生领域非常核心的理念:把健康照护与卫生的资源更多地向那些更需要这些资源的人做倾斜。
我们经常讲到法默是穷人的自然代理人。这句话其实来自社会医学领域非常著名的一个鼻祖——魏尔肖的一句名言:“医生应当成为穷人的自然代理人。”医生应该要为那些无法享受到适当卫生与照护资源的人做倡导、支持、陪伴。如果你去看法默他整个的人生脉络,就会看到他为什么要做这些研究,为什么要在海地、卢旺达、秘鲁做临床工作和公共卫生行动,以及为什么他要去更大的平台,比如世界卫生组织或联合国,做倡导工作来影响政策。他最根本的立足点就是这样一种陪伴精神,这也是他在伦理上的位置。他和病人之间的关系的深度也是和他的长期陪伴与支持密切相关。有时我自己也反思,我们的医疗实践,尤其在大医院里,门诊和住院时间都非常有限。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很难给被服务人群长久的关怀与陪伴。我们去到某个社区做一些卫生项目,这个研究做完了,项目结束了,经费可能也没有了,就不会再持续下去。我们带给社区人群的公共卫生帮助可能非常有限,这样短期又有限的支持带给个体的帮助到底能不能达到适当的水平,这就需要打一个问号。
凯博文讲“在场”,法默讲“陪伴”,其实都是希望能够给医疗需求者更长久的支持与关怀。他们也认为,这种更长期的“与人同在”的陪伴、支持、照护,才是“健康照护”的核心要素。大家如果熟悉医疗史就知道,一百年前,当时整个医疗环境还没有进入大医院时代。回到这种“前现代”的医疗场域里,我们会看到当时很多家庭医生是要出诊的。对于他们的服务使用者,对于那些需要关照的人来讲,他们就是社区里的存在,是社区里的邻居。他们就是“与人同在”,与他们的患者、服务使用者同在。这种情况下,医生跟患者之间的联系是一辈子的联系,而不是像现在大医院的环境下的短暂关系。这种医患关系的建立,离不开时间和精力的长久投入,以及长期的关怀与照护。
一直以来,很多人类学、公共卫生领域的朋友非常敬仰法默,因为他不只是一个研究者或理念倡导者。就像《爱丽丝梦游仙境》里面讲的,去解释某个理念或概念的最好方式,就是去实践,去把事情给做出来。你是不是知行合一?是不是能够照着你所讲的这样去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说,法默是一个道义与伦理上都非常值得敬仰的人。他是通过他整个人生的实践与行动去阐述、佐证他的理念。我读《越过一山,又是一山》时读到一句话,存在主义讲,人生的意义就是你能否找到一个比自己的生活、比自己的个体更宏大的目标,更大的使命与事业,然后把自己的人生这样一个渺小的存在,抛入到这更大的事业与目标里去。法默早先读大学的时候,就已经认识到他的人生目标到底在哪里。到后来他做人类学研究,读相关的医疗学位,做公共卫生实践,其实都离不开他这个人生目标的出发点。很多时候我们讲,为研究而研究、为学术而学术到底好不好?在伦理道德上是不是站得住脚?这当然有很多值得讨论的地方。法默的出发点则在于,我能否通过我的研究去帮助那些我所需要服务的人群——那些田野里的那些研究对象。当我在看到、面对、记录、揭示他们所面临的社会苦难时,我能不能再往前走一步,通过我的工作与实践,真正地去帮助到那些生活在困境中的个体,就像医学中所讲的“解民于倒悬”;还是说我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去记录、观察整个社会苦难的发生,以及它对个体产生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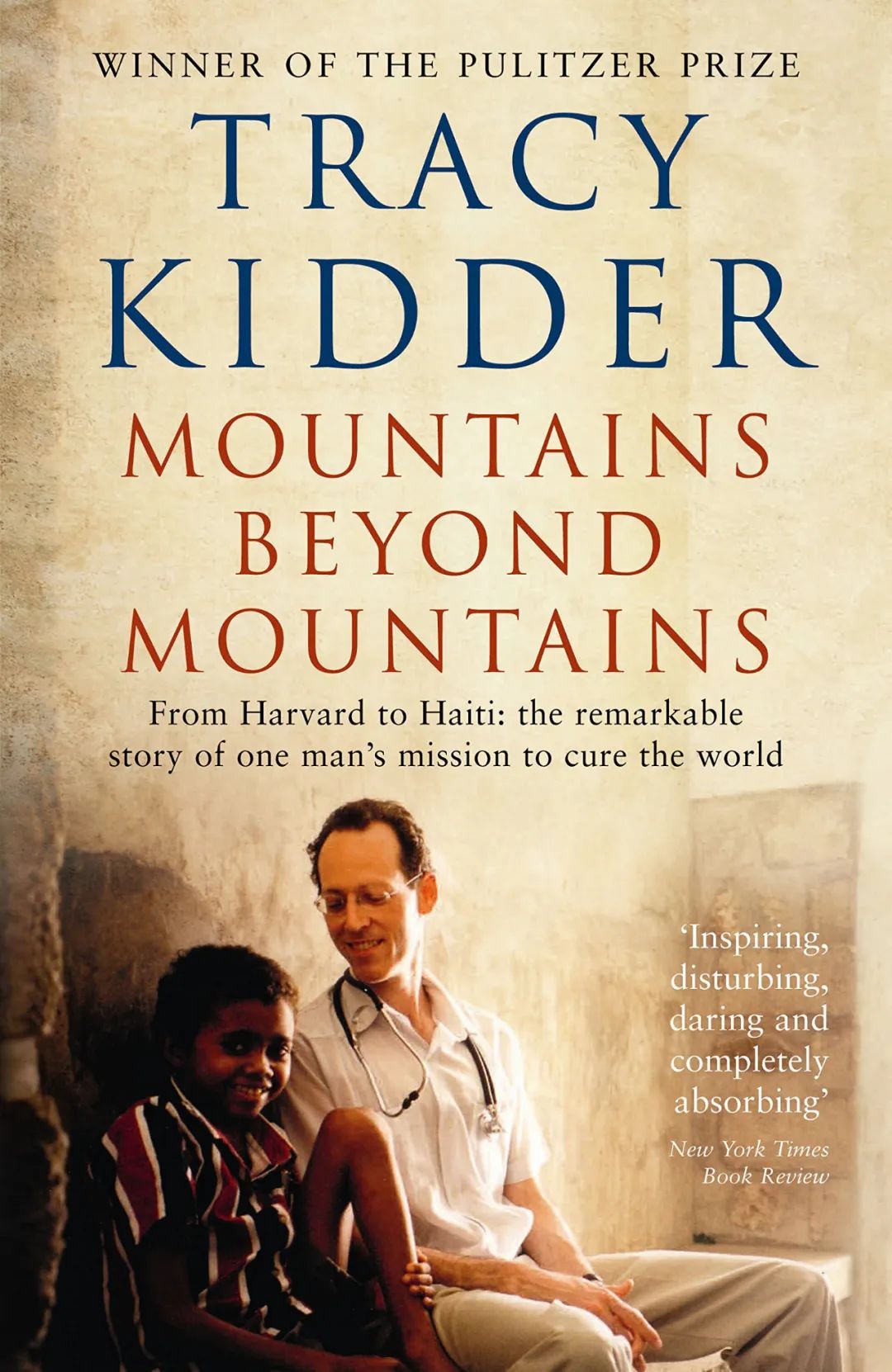
法默把研究作为一个过程、方法而不是最终目的。他希望通过研究进一步检视人们面临的困境,从而能够引起整个学界与行动领域重新认识这些人的处境。在《传染病与不平等》中他也写到,写这本书主要任务并不在于做学术上的漂亮分析,或者是高级的理论建设,他就是要去帮助那些穷人。他的博士论文非常厚,但他同时也说,再厚的博士论文也难以堪比他在海地目睹的那些苦难的沉重。这是他对自己的研究所做的反思。当然,他其实已经在实践与行动了,不光是写博士论文,他已经在帮助缓解他在田野里碰到的那些的苦难了。法默在这本书里也反思了他自己在哈佛、杜克大学接受到的“极尽奢侈”的教育:我们到底该如何充分利用我们得到的教育资源?中国也有“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们究竟是通过教育来获得文凭,写出漂亮的论文、专著,把研究作为进入学术生产场域的一个敲门砖,以此获得一份教职,还是说为了真正去帮助到那些我在田野里碰到的人,去解除他们所面临的困境?
法默一边做研究,一边在海地、秘鲁、卢旺达,作为医生去疏减当地人面临的疾病负担。他同时也是一个公共卫生实践者。不管是建立健康伙伴组织,在当地建立社区卫生服务的递送体系,还是做教育工作,培养当地的医疗卫生工作者,他都希望能够在更大的层面、更上游的位置去改变这些——用法默的话讲“临床荒漠”的地区——健康资源缺乏的问题。在《传染病与不平等》这本书里,法默也引用了格尔茨的一句话:人类学家到底怎样才能让更多人、更多公众去认真对待我们作为研究者所说的话?怎样才能让我们的话更具有信服力?重要的并不是我们理论或概念体系上到底有多么雅致、多么优美,而在于我们是否真的进入了当地人的生活,我们是否真的“在那里”,真能够身临其境地去体会当地人面对的问题。这是他非常核心的立场。法默觉得他必须“在那里”,去记录苦难,才能够在更大的层面上去做一些改变。这其实也与弗莱雷非的“praxis(实践)”理念有呼应。我们的知识、反思和行动,究竟能不能做到非常好的一个结合?爱因斯坦也讲过,如果我们只有行动没有反思,就会走向耗竭;如果我们只有反思而没有行动,就会走向愤世嫉俗,走向犬儒主义。这就是研究和行动结合的意义。

通过行动,我们切实地去改变我们所面对人群的困境;通过研究,我们进一步去阐述他们到底面临着怎样的问题,从而为我们的行动提供非常重要的思路和参考。这里行动和研究是相辅相成、互相影响、缺一不可的。法默一直在倡导“务实的团结”,因为不管是传染病还是任何当代的公共卫生问题,都已经宏大到无法通过单一学科去解决。重要的是,我们能否调动更多学科的力量和资源,共同去省视、反思、批判,进而为相关行动提供参考。法默能够非常好地结合研究和行动这两个不同的面向;但我们很多人不一定能做到,因为现在学科的划分越来越细,能像法默这样同时在临床医学、人类学、公共卫生、公共政策这些不同学科做跨界工作的人非常少。法默经常说,不同的学科都各自会有“视野缺损”——比如,临床医学只关注到个体生理,看不到宏大的、社会性、结构性的困境对个体的影响;人类学上个世纪末只讲文化差异,在行动上会缺乏力量;公共卫生只讲量化、数字,看不到微观的、个体的困境。因此,我们能否把不同学科的力量做好结合,从而共同去帮助我们所关照的人群,这一点就至关重要。
法默也曾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方法上的折衷主义”或者说“多元主义”。也就是说,我们不管用做质性研究、量化研究,或者是行动,所有方法的选择的立足点和出发点都应该是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哈佛社会医学圈子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当然,这也是通过法默以及之前很多学者、行动者一代代的努力把整个圈子的文化和理念建立了起来。从哈佛医学院,到哈佛文理学院,再到相关的附属医院,到法默的“健康伙伴”这样的NGO,再到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这样的国际组织,能够通过机构和社会组织的力量,把波士顿的资源往全世界资源更加缺乏的地区进行整合输送,让关于健康照护、社会苦难的研究和行动触及到更多人群。
归根结底,照护、关怀就在于你能否与你所面对的人群一起淌过生活这样一条湍急的河流。其实在过去几年,研究者、医生、护士、心理治疗师、康复治疗师,都在关注照护,但我觉得,在这些行动与研究之间还是存在着一些裂痕。所以最后,我也想抛出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我们究竟如何才能建立起一个更加整合、多元的有关健康照护的研究与行动网络?不管你是做研究,做行动、做倡导、做服务、做政策,还是从事报道、写作的工作,这是我们共同面临的问题。面对健康照护这样一个复杂的难题,我确实希望能发出这样一个号召,把学院、医院、非盈利机构、私营机构这些不同的力量结合起来,建立这样一个知识-行动共同体,才能尝试共同解决当下面临的问题。
最新文章(持续更新)
corona回顾|弧线如何弯曲(下)埃博拉与知识-行动共同体
欢迎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保持联系
独立网站:tyingknots.net
微信公众号 ID:tying_knots
成为小结的微信好友:tyingknots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