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她们的声音” | 以治疗为名的暴力及怀旧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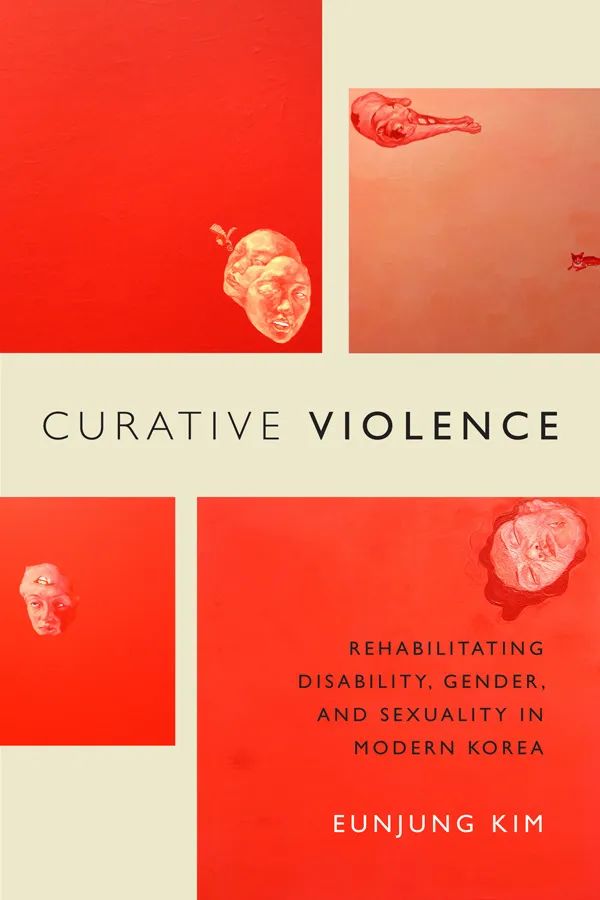
农村残障妇女在教育、就业、建立生活等方面具有多重的阻碍;不同形式的暴力在她们身体上留下痕迹和伤疤,却以各种方式被轻描淡写甚至浪漫化。在《以治疗为名的暴力:现代韩国对残障的治疗、性别和性(Curative Violence: Rehabilitating disability,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modern Korea)》中,金恩廷(Eunjung Kim)回顾了优生学、保守父权、民族主义等权力结构下,当代韩国残障行动者如何寻找自己的声音。金恩廷是雪城大学女性与性别研究系副教授,也任教于该校著名的残障研究项目
本译文为《以治疗为名的暴力》第三章“托爱行暴”(Violence as a Way of Loving)的节选翻译,尤其关注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的怀旧话语如何抹去了农村残障妇女的创伤体验。如金恩廷所强调的,“在当代话语中恢复被理想化的过去是特别危险的,因为这些理想化的过去几乎总是从非残障人士的角度构建的,他们忽视了残障人士在家中和社群中遭受暴力的记忆和经历。”
本译文属于Know Deaf与结绳志联动编校出品,从属“她们的声音”展览材料。“她们的声音”展览由长期关注听障家庭妇女儿童工作的彭霖倩女士发起,邀请多年以来致力于女性艺术的理论研究、艺术批评与展览策划工作的艾蕾尔策展。更多信息欢迎关注“她们的声音”线上开幕:4场跨界会议,邀你共谈艺术无障碍。
原文作者 / 金恩廷(Eunjung Kim)
原文链接 / https://www.dukeupress.edu/curative-violence
原文出版时间 / 2017年1月
编译资料提供 / “她们的声音”展览项目
翻译 / 汤欣如(Xinru Tang),许子萌(Hannah Xu)编校 / 林子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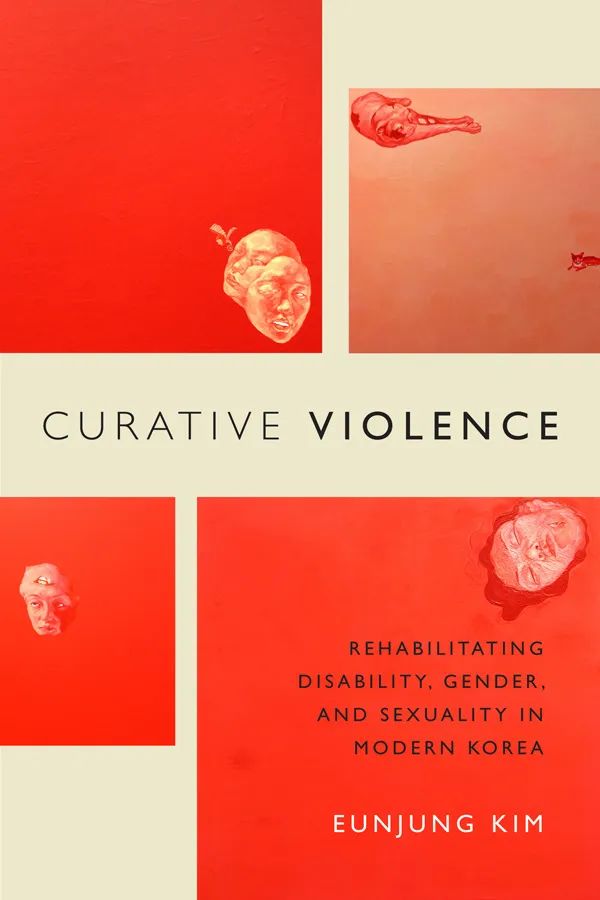
以治疗为名的暴力及怀旧之情
在《雅歌》(Aga [2000],英文翻译版题为The Song of Songs)这部当代小说中,著名保守派作家李文烈(Yi Mun-yol)将二十世纪初的传统农村想象为一个可以包容残障人士的场所[8]。通过对理想过去的怀旧,他批评了现代社会将残障人士赶出他们原本的社群送入特殊机构的做法(译者注:这一做法被称为机构化/ institutionalization) ——但李文烈并不是在支持残障权利积极分子所倡导的去机构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旨在争取残障人士获得在社群中居住的权力),而仅仅是主张回到所谓的没有问题的过去。这种怀旧情绪有效重塑了书中村民对一名残障女性进行的性暴力。李文烈在书中将这名女性遭受的性暴力塑造为一种同情的包容和彰显爱的方式。在一场2011年的访谈中,李文烈说他对这部最终被翻译为英文的小说有着特殊的情怀,因为它“试图唤起很久以前就已经从我们社会中消失的古老韩国文化的光环。[9]” 此前,李文烈的另一本小说《选择》(Sŏnt’aek [1997])激起了巨大争议以及来自女权主义者的批评。这本早先的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讲述了一个来自朝鲜王朝的女性的故事。书中对现代女性角色的变化表示惋惜,并将女主人公符合儒家标准的女性形象视作一种高尚表现。《选择》出版于1997年,彼时正是经济危机和恢复男性在家庭中权威的文化运动流行的时期。这本小说正是当时对妇女运动的一次反冲。
徐智媛(Ji-moon Suh)指出,李文烈在创作《选择》这本小说后成为了“韩国最突出的反女权人士”。她还补充道,“他接着创作了《雅歌》,继续以怀旧的眼光看待过去的日子,在书中即使是傻子也被一种幽默的口吻加以书写,并可以(在故事中)有一个位置。[10]”虽然在徐智媛的描述中,《雅歌》似乎是一个无害的寓言,但这本小说对一名处于多重残障的女性和村民暴力行为的描写引起严重批评。残障行动者朴喜英(Park Young-hee)引用一个在农村发生的真实暴力案件,批评了小说中对主角被强奸的浪漫化描述。在《我不想变成性暴力的对象》这篇文章中,朴喜英介绍了一名名为金明淑(Kim Myŏng-suk)的女士的真实案例。金明淑是一名智力障碍妇女,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她被村里的7名男子施以性暴力,直到2000年他们的行为才被曝光[11]。从金明淑13岁起,这些男性就开始了他们的强奸行为。通过这一案例,朴喜英挑战了李文烈幻想中的农村村庄的仁慈表象。在李文烈的幻想中,村庄中的人们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各司其职,而事实并非如此。李文烈小说中的男性叙述者声称,在过去,村庄的结构类似于同心圆,根据人们的等级和角色,每个圆里都住着相应的人[12]。然而,金明淑的遭遇削弱了小说中对农村的浪漫化描述。朴喜英指出,浪漫化农村并不能保证残障女性的人权和安全。随着90年代末保障残障女性权利和提升残障女性能见度的政治运动逐渐形成声势,残障和非残障的残障人士权利倡导行动者均认为《雅歌》(以及电影《绿洲》)(译者注:导演为李沧东)中对暴力的浪漫化默许和助长了针对残障女性的暴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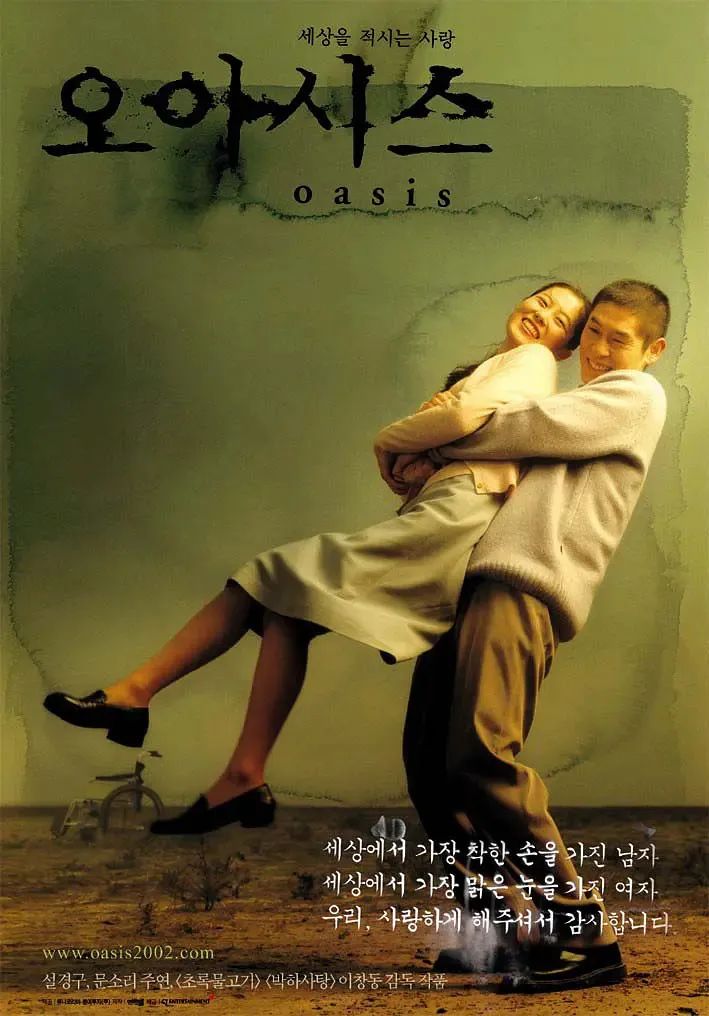
《雅歌》的开头是三个男人在回忆唐佩(Tangp’yŏn),一个在1940年代来到他们老家的残障妇女。唐佩十几岁的时候被遗弃在村中长者洛东(Noktong)的家门口。她的来历不明,但人们普遍认为她来自最低贱的游牧阶层,没有姓氏和故乡。在书中,是这三个男人构建了唐佩的女性身份,如果没有他们,唐佩则不能被认为是一个女人,甚至不能被认作一个人。唐佩在书中起先被描述为“一个颤抖的生命体”,后成为“一个可以自己移动的有机体”,之后则像“一个大蠕虫”[13]。书中的第一叙述者这样说道,“她的外表不仅使得她的性别难以辨认,甚至无法分辨她是否是一个人。[14]” 在《雅歌》中,人之为人需要对于身体进行物理干涉,例如性暴力在书中被认作对社会性别的承认。书中解释说,唐佩的性别取决于外部如何对她的行为和身体做出反应。这一立场的基础与其说是作者持有性别的社会建构观点,不如说作者完全否定了残障人士的身体具有确认性别的资格。书中假定,规范化的男性和女性生物特征是承认一个人为人的标志,而残障则创造了一个例外。书中解释说:“一个能指符号(signifier)并不由其主体确定,而是由其感知者所确定,就像唐佩的性别符号一样。唐佩是女人这一事实在书中被许多独特的符号所揭示。但是,这些符号的意义必须被他人所注意到。[15]”
《雅歌》是这样描述唐佩第一次来月经的,“她向外部世界发出信号了[16]”。当时,整个家庭都惊慌失措,以为她得了重病。之后,家里的另一名女性终于意识到这些血是她的初潮,并喃喃自语道,“啊,那东西也是个女人。[17]”月经是唐佩性别和生殖能力的的标志,这是大家都没想到的。“此后,唐佩被承认为一个女人,不仅通过她的外表,还通过她的内在身体。此外,对其性别的认可还拓展到了这个家庭以外的地方。[18]”
一年后,唐佩在山上被一个男人性侵。这个男人用棍子钻进了她的生殖器。书中将这次性侵描述为“唐佩的女性身份引起的第一个外部反应[19]”。村里的妇女们发现了这一事件,指认了这个男人,并威胁要强迫他娶她。书中这样描述唐佩对性侵的反应:“尽管那家伙一遍又一遍地道歉,但唐佩仍然无法停止哭泣,哭个不停。我很抱歉这样猜测,但她的哀叹可能是由她的悲伤引起的。不是因为一个处女被暴露在一个年轻的陌生人面前而产生的愤怒和羞辱悲伤,而是因为这个异性在认出她的女性身份并接近她之后,还是选择把她一个人留下?[20]”书中的这番猜测是一个危险的迷思,即唐佩想被强奸,并因男人拒绝强奸她而感到愤怒。通常情况下,性侵会损害一个女人的名声,但对唐佩来说却恰恰相反。她的遭遇散发出了她作为适婚单身女性的信号,事发后每个月都有媒人联系她。
在小说中,第一叙述者对传统农村的赞美经常打断故事的正常进程。这名叙述者认为农村是一个人性化的、对每一个人都包容的空间,同时农村也保留了等级制度。他这样说道,在同心圆的中心,“在核心处生活的是健康的正常身心的人。[21]”这个“稳定而统一的核心[22]”使得具备不同能力的人都可以包含在它的关怀下。他谴责了现代化创造了专门的机构(institutions)、精神病院、康复中心和监护中心,把残障人士从他们原先所在的处所赶走,因他们没有生产力,需要隐藏起来。该叙述者还指出,医疗和法律相关的新称谓已经替代了传统的关于残障人士的词汇,例如“需要解脱的人”(kuho taesangja)、“精神疾病患者”(chŏngsin pyŏngja)、“心神微弱者“ (simsin miyakcha)、“受障者” (changaein)替代了例如“矮子”、“聋子”或者“瞎子”这类词汇——而这些传统词汇和“麻风病人、屠夫、乞丐 [23]”并列,意味着属于社群中占据了某个位置(虽然是在边缘)。在因其对现代性的全面攻击而受到批评之后,李文烈为自己辩护,声称书中的视角是叙述者的而不是他自己的[24]。李文烈同时声称说他相信唐佩“本质上卓越的身心”会有效防止小说被解读为不分青红皂白地谴责现代性、将过去理想化为“消失的天堂”。然而,正如女权主义学者金正然(Kim Chong-ran)所指出的,事实上,这书中的叙述者并没有描述唐佩自己的视角:是作者决定了她被呈现为一个他者(Other)在现代发展中受到异化的经历 [25]。
书中显示的怀旧情绪是一种对残障表示同情的慈善态度,但这却掩盖了对残障人士的暴力。这种怀旧情绪呼应了在亚洲普遍存在的迷思,人们认为西方个人主义和现代化摧毁了亚洲传统的和谐和群体性的关怀。研究残障的历史学家迈尔斯(M. Miles)指出人们普遍理想化了亚洲的传统文化:“在遥远的过去,在苍白的外国魔鬼乘着他们的小船驶来之前,残障人士在他们的家中受到照顾,并融入社群。[26]”迈尔斯警告说,虽然现代化的确推动了韩国对残障人士的机构化治疗(institutionalization),但是关乎残障人士经历的问题是高度复杂的,单纯的怀旧仅仅提供了“简化和误导性的答案” [27]。在当代话语中恢复被理想化的过去是特别危险的,因为这些理想化的过去几乎总是从非残障人士的角度构建的,他们忽视了残障人士在家中和社群中遭受暴力的记忆和经历。在下一节我对短篇小说《白痴阿达达》(“Adada, the Idiot”)的分析中,我将展现虽然在《白痴阿达达》这部小说里,残障和非残障人士共同生活在1930年代的农村,没有专门的收容机构(institution),但和李文烈想象不同的是,农村被呈现为了一个对残障女性相当残酷的场所。

在其另一片短篇小说《无名岛》(“Ingmyŏng ŭi sŏm” [1982]) 中,李文烈同样强烈希冀于通过混同性暴力和归属感来提升传统村落的价值。这篇小说围绕一名残障男性展开,在2011年被翻译并发表于纽约客杂志。主人公盖哲[Kkaech’ŏl]是一个对村里的妇女进行性挑逗的外来者,但傻子的标签赋予了他道德上的豁免权。性成为了一种资源,给他提供了住所和食物,从而实现了对其残障的颠覆。《无名岛》故事的开端是第一人称叙述者听她的丈夫抱怨城市化带来的匿名性。在这名男性看来,城市化造成了“这个时代道德的陨落, 并构成败坏妇女性行为的主要因素”。他怀念家乡的村庄,在那里没有人可以隐姓埋名[28]。之后的故事都是这个女性叙述者对她在一个单一民族的岛上的回忆,十年前她在那里拥有了她的第一份教师工作。在到达那个岛上不久,她就注意到了一个男人紧盯着她,这就是盖哲。她也很快发现盖哲与村民之间的相处有多么奇怪[29]。盖哲没有家也没有工作,天天在岛上游荡,却有村民照顾他、给他提供食物。叙述者之后意识到盖哲会跟村庄里的女人们发生性关系。这些女人没有什么婚外情的机会,因为在这个村庄中除了盖哲之外的男人和她们都有血缘或婚姻关系。男人们认为盖哲没有生育能力,盖哲从来没有对任何女人产生过感情,也从未向外谈论过偷情的经历,于是盖哲被“所有人”所接受,尽管他们只把他当做一个孩子(偶尔还会有男人打他)。盖哲被描写成一个独特的、为女性提供性解放的角色——在她们需要他时,他就会在。虽然所有人都认识盖哲,他还是一个自始至终的局外人。他与其他人之间的差异保护着他,让他生活在一个与其他人不同的道德层面中。他的职责是维护这座岛性道德和父权秩序的假象。而当有人小声评价一个新生儿长得像盖哲时,这可能也可以说明他的职责或许还包括解决岛上不孕不育的问题。村民彼此提醒对方,“盖哲就是个傻子”,以此来抑制对于盖哲是否能生育的问题所产生的焦虑,仿佛盖哲的残障就可以证明他没有生育的能力[30]。
这位女教师也在这样的生活方式中被村庄同化了。有一天,她翘首企足的未婚夫并没能如约来看望她,大感失望的她“身体烧得更厉害了”。盖哲在她躲避大暴雨的地方侵犯了她。在她的回忆里,除了最初的震惊,“我没有反抗。我陷入了一种梦幻般的状态。我只是什么都不管了。光是记得这件事已足以让我感到难堪,但我并不觉得自己是受害者。我不太确定我是否享受其中,就好像我们当时是一场不正当的风流韵事。”这种幻想,即一个被描写成非常好色的残障男人对女人的性暴力是一种恩惠的幻想,与《雅歌》中关于性暴力的幻想十分相似,只不过《雅歌》是由一个非残障的男人叙述的。在这两个幻想中,女人都希望被侵犯。在一个幻想中,侵犯者的残障身份使他得以免责,而在另一个幻想中,受害者的残障身份否定了她作为一个受害者的事实。盖哲就像是村庄女性的性“乐土”,否则她们的婚外情就会伤害亲情。盖哲的残障是他维持这一角色的关键。“所有男人都把他当成一个弱智或疯子,但他们似乎都在极力掩饰对盖哲并不真的是这样一个人的焦虑”。李文烈认为性暴力对侵犯者(盖哲)和受害者(唐佩)产生了正面的影响,最终让他们得以在村庄中占据一个位置。
在文章《一首善良的情歌?雅歌?李文烈退化的世界观》中,金正然(Kim Chŏng-ran) 认为李文烈选择残障人士作为主角的本意是消除女性的能动性和主体性。金正然认为《雅歌》和《选择》很相似。在《选择》中,生活在朝鲜王朝的程普英(Chŏngyŏng Puin)自愿接受男性的统治,而《雅歌》中唐佩因为残障需要依赖男性的恩惠。虽然金正然将残障等同于失去能动性这一观点有失偏颇,但她将残障归结为差异,从而挑战了李文烈将残障归结为社会底层的认知。“从李文烈的等级观念来看,即便他想,他也无法理解唐佩并不是下等的,而只是不同的”[34]。金正然批评李文烈傲慢地将性侵犯理解为一种人类同情心的展现并指出他将怀旧之情当成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危险性。这样的怀旧之情不仅在赞扬前现代的社群,还助长了与民主相悖的种姓等级制度的回归。
然而,金正然谴责李文烈时用的“退化”(degenerancy)一词,曾经作为一个优生学术语被用作煽动对残障者的敌意。此外,金正然为了反对李文烈而表达对现代残障人士机构化的支持,也问题重重。在《雅歌》的结尾,叙述者悲伤地描述唐佩不能继续住在村庄里,她必须要被送进专门的机构。金正然问:“难道为(唐佩)去机构哀叹就能解决问题吗?她原来所在的社群瓦解,导致她不能留在那里,真的是件坏事吗?[35]”金正然认为,与其完全废除机构,不如改善这些地方的条件,使残障人士可以得到更人道、更有效保护。在不了解残障人士权利运动的情况下,金正然通过指出残障人士的脆弱性来支持机构的存在,这就把生活在社群中定位为危险的。有些非残障的女权主义者对那些照顾残障人士和老年人但没有得到报酬的女性表示关心和担忧。这些女权主义者可能也会跟金正然有同样的观点。但她们往往忽略了一个事实,机构本身就是对残障人士不合理的隔离。残障人士在社群中生活并被配备应有的资源的权利因机构的存在受到了侵犯。支持残障人士权利的行动者倡导家庭护理和个人援助,通过扩大社会支持使残障人士可以在社群中生活,使社会中没有暴力,使残障人士做出的贡献和对他人的关爱可以被看到 [36]。
在《雅歌》中,朝鲜战争结束后,唐佩遇到了一个叫彭祖(Pŏnho)的人。他也是一个被抛弃的人,村民都认为他是个无能的人。他多次强奸唐佩,唐佩每天晚上都在尖叫,流血不止。村民们注意到唐佩受伤了,就请医生为她治伤,并通过安排两人结婚来处置性侵犯。叙述者将此描写为另一个性别符号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以承认她的月经和受到的性侵犯开始,以强迫性婚姻结束。
后来叙述者承认他曾遇到过唐佩,并多次与一群男人一起对她进行性骚扰。
“唐佩是一个不漂亮且没有性吸引力的女人。而且她缺乏生育能力,无法真正享受性爱。尽管当时我们还不成熟,但通过性行为来挑逗她,似乎确实很残酷刻薄,因为她不具备身为女人的任何条件。
不过,为了防止我们被控诉,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借口,即使这些借口听起来毫无意义。我们迷恋跟她有性行为的原因不是我们像虐待狂一样喜欢看她绝望。我们的目的是补充她性的不完美。我们真正认可她的女性气质,并且我们把她作为一个女人来爱,尽管我们爱的方式是不同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愿意授予她女王的称号,并称自己为她的骑士。[37]”
叙述者的理由是,暴力具有认可女性特征的力量,因此它是一种工具,可以用来“治愈”所谓的性别不完美。残障妇女被认定不受欢迎、偏离了正常女性标准,而这种情况是被认为可以通过性暴力被解决的。这种说法危及残障妇女的生命,同时也将她们与非残障女性区分开来。
在行动者杂志《共感》(Konggam)中,三位残障女性行动者批评了《雅歌》。她们坚持:“认为残障妇女难以体验性是一个大错误。同样,无视她们的愿望和想法,认为应该让她们有性体验,以及认为这样做是最重要和最美好的事情也是严重的错误。真实的情况绝对不是这样的。对残障妇女进行性侵犯并无视她们的意志和思想是一场性犯罪,而不是在向她们伸出援手。[38]”当代父权制对“旧时代”的怀旧被理想化为对残障人士的包容。这种怀旧让非残障男子作为 “骑士”,将性暴力作为一种治疗性干预措施,将一副残障的身体变成一个真正的异性。

本文受作者金恩廷及杜克大学出版社授权翻译转载。
Eunjung Kim, “Violence as a Way of Loving,” in Curative Violence: Rehabilitating Disability,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Modern Korea, pp. 122-165. Copyright 2016, Duke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www.dukeupress.edu
引用
[8] Yi Mun-yol, Aga
[9] Kwon Seong-woo, “Rediscovering Korea’s Literary Giant,” List Magazine 14 (Winter 2011).
[10] Suh Ji-moon, “Yi Munyŏl,” 729.
[11] Park Young-hee [Pak Yŏng-hŭi], “Na nun sŏngp’ongnyŏk ŭi taesang i toegil
wŏnhaji annŭnda” [I do not want to become a victim of sexual violence],
Konggam [Empathy] 4 (2001): 32–35.
[12] Yi Mun-yol, Aga, 30.
[13] Yi Mun-yol, Aga, 17.
[14] Yi Mun-yol, Aga, 18.
[15] Yi Mun-yol, Aga, 55.
[16] Yi Mun-yol, Aga, 60.
[17] Yi Mun-yol, Aga, 61.
[18] Yi Mun-yol, Aga, 61–62.
[19] Yi Mun-yol, Aga, 62.
[20] Yi Mun-yol, Aga, 75–76.
[21] Yi Mun-yol, Aga, 31.
[22] Yi Mun-yol, Aga, 31.
[23] Yi Mun-yol, Aga, 8.
[24] Yi Mun-yol, “Aga e taehan nonŭi rŭl pomyŏ” [Looking at the discussion about
Song of Songs], Chosŏn ilbo, March 27, 2000.
[25] Kim Chŏng-ran, “Uahan sarang norae? Aga?,” 226–227.
[26] Miles, “Blindness in South and East Asia,” 88, emphasis in the original.
[27] Miles, “Blindness in South and East Asia,” 88.
[28] Yi Mun-yol, “Anonymous Island,” 73.
[29] Yi Mun-yol, “Anonymous Island,” 73.
[30] Yi Mun-yol, “Anonymous Island,” 75.
[31] Yi Mun-yol, “Anonymous Island,” 76.
[32] Yi Mun-yol, “Anonymous Island,” 76.
[33] Yi Mun-yol, “Anonymous Island,” 74.
[34] Kim Chŏng-ran, “Uahan sarang norae? Aga?,” 226, 227.
[35] Kim Chŏng-ran, “Uahan sarang norae? Aga?,” 234.
[36] See Wendell, The Rejected Body, 143-144.
[37] Yi Mun-yol, Aga, 214.
[38] Pak Chu-hŭi, Yi Chŏng-min, and Chŏng Yŏng-ran, “Yi Mun-yŏl ŭi changein e taehan chalmottoen sigak” [Yi Mun-yol’s misperception about disabled people], Konggam [Empathy], no. 4 (2002):38.
最新文章(持续更新)
每周人类学家|追思黄应贵教授
“她们的声音” | 以治疗为名的暴力及怀旧之情
欢迎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保持联系
独立网站:tyingknots.net
微信公众号 ID:tying_knots
成为小结的微信好友:tyingknots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