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靠我:我们为他人所做的才是真正值得做的事│Lean on Me: All that is really worth doing is what we do for others
﹝英国﹞琳恩·西格尔(Lynne Segal)
2023年11月14日
米勒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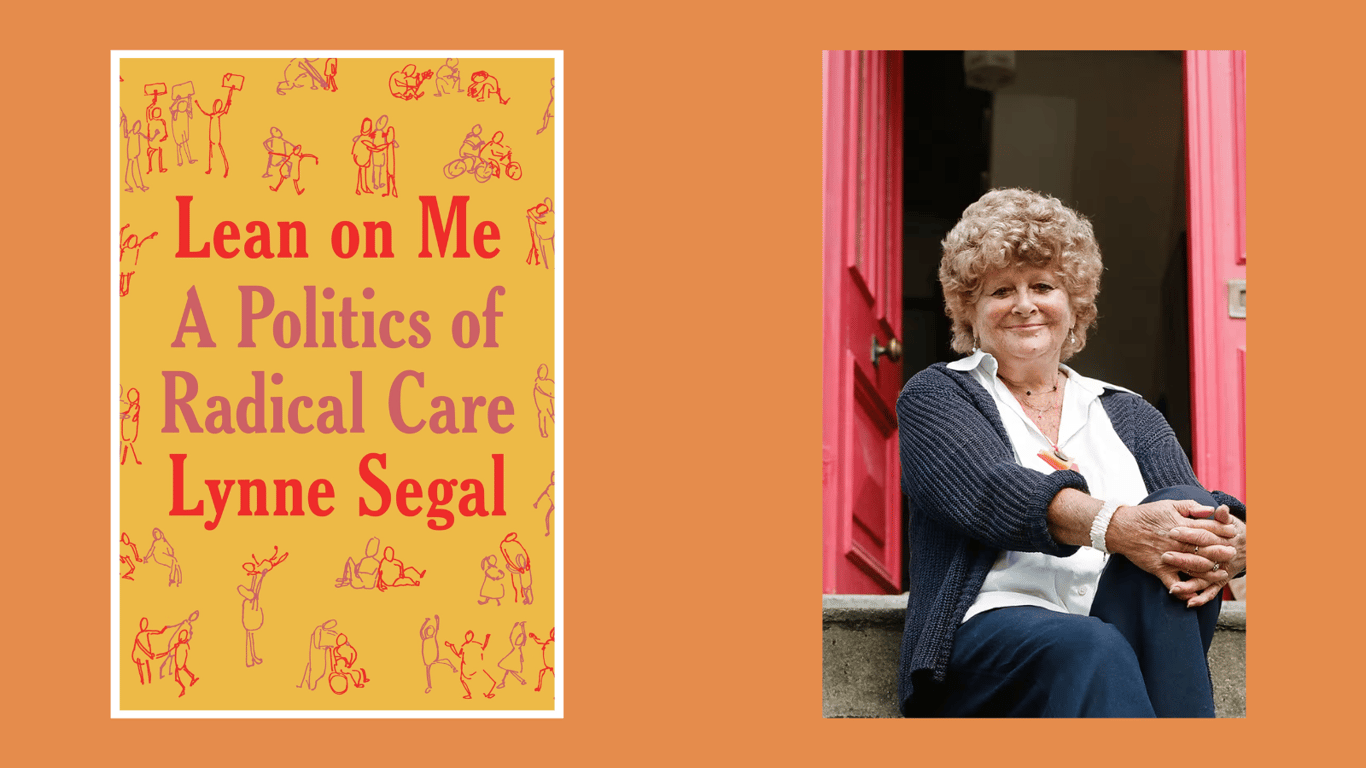
“没有你,我什么都不是”,除了在浪漫激情的时刻,我们很少将这种想法付诸文字。在这个个人主义肆无忌惮的时代,许多人仍然没有意识到,我们只能在与他人(家人、朋友、陌生人,甚至敌人——即他们自己的社会财产的产物)的持续联系之中,并通过这些持续的联系来建立自我意识。从生到死,我们依靠周围的人来保持人性,正如我们所有人,无论年龄大小或身体状况如何,都得依靠我们的关爱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s of care)来维持我们的日常活动和持续生存一样。我在《依靠我:激进关爱的政治》(Lean on Me: A Politics of Radical Care)(Verso,2023)中解释了这一点,同时也列举了我们在关爱方面的失误所造成的毁灭性后果,这些后果从个人到全球的各个层面都是显而易见的。
这本书以下面的内容作为开篇,即长期以来对关爱本身——“妇女的工作”——的贬低,以及拒绝承认我们对他人和基本公共基础设施的终身依赖。除了否认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之外,我们最近还发现了一个更致命的因素:公共部门的市场化,这同样加剧了被贬低的关爱工作的种族化特征(racialised nature),(这种市场化)在确保某些人获得巨额利润的同时,造成了许多人无法获得足够的关爱。
对于那些像我这样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致力于创造一个激进再分配的、更有爱心的世界的人来说,这是再悲哀不过的事情了。因此,在我的书中,我退后一步,对于我一生中发生的一切变化——无论是好事,还是最近发生的坏事——进行了衡量。然而,起初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在各条战线上热切地寻求变革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赢得了许多胜利。我的书一开篇就对——为大多数人提供了关爱蓝图的——母性进行了反思。
在一场关键的斗争中,妇女解放运动(Women’s Liberation)忙于为推翻大多数妇女战后为人母的经历中的孤立感和边缘化而奋斗,这是我们从自己母亲的苦难生活中了解到的。斗争取得了一些胜利:在产科病房中对抗医生的傲慢或无助感从而确保生育权利方面、在为托儿所争取并赢得了更多的资金方面,以及在要求男性更多地参与家务劳动的同时,提高妇女经济独立性方面。
当今令人震惊的是,在后撒切尔时代以及后来的紧缩政策之后——削减福利,使许多人陷入贫困,这些胜利竟会如此迅速地被夺走了。如今,我们很难忽视母亲们的痛苦。在时间、金钱和资源的日常压力下,我们看到几乎没有一个母亲觉得自己在养育子女方面做得很好。即使是富裕的全职妈妈也提到,在我们这个竞争异常激烈的世界里养育孩子时,她们所面临的持续不断的焦虑感,同时还表现出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母亲们曾表达过的那种孤立感和排斥感。杰奎琳·罗斯(Jacqueline Rose)和伊莲·格拉泽(Eliane Glaser)等学者最近提炼出了冷漠无情(这种状况)对母亲们的影响。半数的英国母亲在产前或产后都遭到心理健康问题的折磨,50%的新妈妈表示长期感到孤独,在婴儿出生第一年期间,自杀是导致母亲死亡的主要原因。
类似的模式随处可见。在我工作了50年的教育领域,我们看到伴随着对教育这一概念本身的攻击,学校内部的不平等现象日益加剧。对人文学科的攻击是以下行为的又一次尝试,即将教育进行市场化,并剥夺那些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世界的工具,剥夺那些帮助我们探索更好的方式来创造一个更公平、更有爱心的世界的工具。
我在书中阐述了残障斗争(disability struggles)在揭示“脆弱性”的复杂性方面的重要意义,并说明了为什么自主性(autonomy)和依赖性(dependence)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起初,残障人士活动家在许多次倡导残障社会模式(a social model of disability)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他们拒绝接受自己在本质上是脆弱的这种观念,这种观念通常都是将他们排斥在公共生活之外的借口。残障人士活动家珍妮·莫里斯(Jenny Morris)是走在最前沿的人,在她从一名肢体健全的女权活动家转变为残障人士捍卫者之前,我就认识她。35岁那年,她在试图救起一名邻家小孩时摔倒致残。她突然体验到——大多数残障人士活动家都描述过的——极端的社会排斥,同时也陈述了大部分时间人们对他们的怀疑和轻蔑的态度。
残障人士活动家在争取更多地利用——其他人都可以依赖的——社会基础设施的多次战斗中取得了胜利,他们呼吁制定“独立生活策略”(Independent Living Strategy),该策略于2008年获工党批准,承诺增加用于包容性和自力更生的资金。这很有价值,但亦有不足。“自力更生”的说法可能会被扭曲,以迎合对“依赖”的有害的蔑视——这种蔑视总是将社会福利笼罩在其阴影之下。
正如精神分析学家蒂姆·达廷顿(Tim Dartington)在《管理脆弱性》(Managing Vulnerability)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对“独立性”的强调不仅与对依赖的诋毁不谋而合,而且可能会贬低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并导致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总体上倾向于更加个人主义的方式——从而忽略了真正的关爱。更糟糕的是,在保守党领导的新的紧缩制度下,2010年后,尽管表面上反映了“自主权”的言论,但却制定了有害的“工作能力评估”(Work Capability Assessments ,WCA)。无论其个人状况如何,均反复测试个人是否适合工作,这一做法导致许多被错误评估的残障人士痛苦不堪,甚至自杀——过程中充满了阶级和种族偏见。
鉴于目前有数百万老年人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而且在新冠肺炎早期这些需求被严重地忽视了,所以当我们审视老龄化问题时,类似的故事也在上演。这种状况与至今仍在继续的养老院的金融化和公共护理服务的外包有关。
《依靠我》这本书讲述了我们监狱系统的危害、对寻求庇护者的忽视和虐待,以及拒绝直面和对抗气候变化。我在这里强调了来自原住民的阻力,以及他们所面临的代价——被有组织且无责任地谋杀。事实上,尽管我们的河流遭到污染,气候灾难频发,但我们的政府似乎只对其最大的支持者——破坏性的化石燃料生产商——做出回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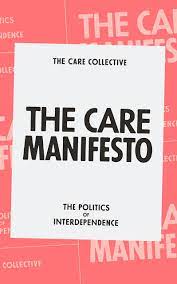
我们如何才能扭转这一局面?正如我们在颇具影响力的《关爱宣言》(Care Manifesto)(2020)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必须在普遍的关爱伦理的基础上,重新致力于各个层面的社会变革。这意味着要全面重建我们所有被削弱的社会基础设施,而不仅仅是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并使其脱离金融资本(的束缚)。这还包括重建我们的地方社区,因为我们知道,对所有人的充分关爱是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的唯一基础。
在主张我们对于相互照顾或支持对方,帮助维护我们的社区,同时总体上保护公共空间负有共同的责任时,我们需要庆祝我们的“互助”(Mutual Aid)实践。一旦我们为所有人争取并赢得更短的工作时间,以及目前一些工会组织正在强调的全民基本收入(basic income for all),这一切就将成为可能。
最后,请允许我以下面的话作为结束:某种程度的公众参与对于维持我们个人的信心以及维护我们共同的人性都是必要的。让我们为相互关爱——而不仅仅是自我关爱——而奋斗,这份关爱能够帮助我们克服孤独,有时还能体验更多的快乐。归根结底,我们拥有的只有彼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