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8|一场学术讲座中,一位学术行政的”过度关怀”

一场讲座之后,你会记得什么?滔滔不绝的分享者?slides上的新名词?尖锐的点评和圆融的回应?你是否思考过,什么使这一切得以成行?
参与过这类活动的你一定遇到过——话筒突然失去声音,网络会议室里总有人忘了关麦,嵌在PPT里的视频无法播放……每当这些状况出现,又是谁在解决问题?如果你也曾在其中扮演协作者的角色,你一定对这些场景中繁杂、琐碎、又往往不可见的工作十分熟悉。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技术准备、沟通应对,让一个知识传播的系统转了起来,但这些工作的意义,以及溢出其中的情感,却很少被讨论。在学院里,这些辅助、支持的工作往往外包给各式各样的学术勤杂工——廉价的学生助理、行政、尚未找到稳定教职的学术市场边缘人。
本期的分享者是一位在国际知名高校提供学术辅助工作的项目专员。在进入“高校”这个职场之前,她也曾是一位坐在研究室里的人类学研究者。如今,系所的会议室、走廊、办公室成了她的田野。她在每一场讲座、会议中练就“万事通”的本领,为所有人解决所有问题,犹如“学术基础设施”一般,以隐身的方式让所有学术活动的流程得以运行。然而悖论的是,这类工作成功的标志之一便是让大家意识不到她的存在;因为她一旦出现,便意味着“有些事不对劲了”。
在这篇分享中,她以絮语的方式把工作中的每个环节、以及溢出知识流动场域的疲惫感展现出来。这并不是纯粹的私人抱怨,而是提出了一系列批判实践的问题:到底是怎样的劳动铺就了知识传播的轨道、帮助实现这个名为“学院”的神话?学者们在作品里咒骂各种等级制的同时,有没有留意到自己身处其中的“等级”?知识生产究竟要依赖于一套专业主义的分工,还可以成为一件“大家一起做”的事?
作者 / Ennael
编辑 / Emma
如果是一场11点开始的讲座,大约10点40分到达举行的场地。先到讲台,开启电脑、投影、音响系统,连上网络,检查麦克风的音量和电量。走到另一边,设置好空调的温度,设计好哪些灯开哪些灯关,太亮看不清屏幕,太暗/太冷/太热,又会令人昏昏欲睡的。再去把门抵住,方便参加者进入。
10点45分,讲者到了。在讲者和一同前来的接待老师聊天的间隙,稍微寒暄几句,询问投影片要如何装载:通常这是事前已经沟通了的,到现场还是要再作确认。用U盘通常最简单,但也可能插入电脑后加载不出来;有的讲者习惯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需要依电脑接口类型用相应的连接线接入场地的系统;也有些放在邮箱或网盘上,要登入下载,有时记不得密码或是要双重验证,需要花费一点时间,有时也是令人着急的。

10点50分,观众陆陆续续地来了。像这种无需报名的公开讲座,虽然制作了海报、在各种渠道宣传,但总是有点难以预测会有多少人来听,尽管可以依据主题、讲者和时间来稍作判断。人太少自然不免尴尬,人太多也要特别安排现场秩序。
10点55分,继续和讲者一起调试。有时要跑去买瓶水、有时要调整椅子的高度和麦克风的角度、有时要把讲稿放得方便阅读和翻页、有时要测试音频和视频能否播放。如果是同时有线上直播的讲座,就更加让人紧张,要再早一点来布置了。说简单也是简单——基本上,只要用讲台上的电脑登入线上会议平台,确保线上观众能听到讲者的声音就好。但讲者未必会一直站在讲台电脑的镜头前,所以通常会再用另一台设备登入,用脚架固定在场地的另一边,静音但开启视频,提供另一个视角画面,也方便操作线上会议。
11点05分,观众大多都已经入座,和主持老师示意差不多可以开始了。去把门关上,然后站在台侧,操作线上会议,输入欢迎话语、流程介绍,也确保观众保持静音。讲座开始十多分钟,确认讲者和讲台、鼠标、麦克风、激光笔配合一切顺利,也拍了一些讲者和现场的照片,可以在前排侧面位置坐下了。

讲座继续进行,即使是熟悉的场地、同样的设定,每一次,对几乎是每一次,总是会有这样那样的技术问题出现的:
是麦克风声音时大时小、有回音/噪音?
是电脑卡住、投影仪的连接断了?
是线上会议中分享屏幕,投影片却没有正常翻页?
是视频播放在现场/线上没有声音,或是两者的音频设定互相干扰,需要不断切换?
是讲者声音比较小又总是不对准麦克风,让你一直担心不知道现场和线上的观众到底听不听得清楚?
是问答环节的时候有人觉得自己声音够大,不顾不用麦克风的话线上的观众会听不到问题是什么?
是线上有人举手提问,请ta开启麦克风和镜头发言的时候,却是一片沉默?
噢,也可能是,你在大屏幕上打开线上会议的对话窗口,才发现那条新讯息原来是一则小广告,而发送的账号已经立刻离开了会议室。
——而出现的时候:讲者或许会显得有点不安无措,观众中也许会有人皱起眉头;又有人会开始左顾右盼,似乎是在寻找工作人员在哪里。
而作为工作人员的你,或是坐着看着屏幕,或是站着操作直播设备,或是在场地走动传递着麦克风,而心里在快速思考着:
这个问题有多影响讲座效果?
有可以简单操作的解决办法吗?
在什么时候上前会影响比较小,怎样能尽量不打断讲者?你也不是什么专业技术人员,就算是技术人员也没有说能保证三十秒内解决问题的。讲座进行的时候,无论场面有多大或多小,讲台总是似乎有个结界,听众坐在下面,讲者站在上面,所有事情理应自然地运作得宜。

这些还都是技术问题。
讲座还有三分钟开始了现场只有三个人,要去哪里现场拉人来当听众?
原本45分钟的演讲时间,讲者到了第65分钟还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谁要去提醒ta?
问答环节开始,没有人举手,要提示主持人来“在大家想问题的时候,我先来问一个”吗?
讲座时间快要结束了,还有好几个人举手,要优先给谁提问的机会?
讲座的内容自然不由得你控制,然而要是偶然听到观众事后的讨论、说好或是不好,还是会感到开心或失落的,毕竟是投入了自身的劳动在其中,会希望是一个有价值的体验。

一段时间以来,我觉察到,自己在一场这样的讲座完结之后,心情总是有点差。是为什么呢?
可能是全程绷着一颗心,似乎要为现场的顺利流畅体面负起全责,因而感到压力和疲倦;
可能是不喜欢在同一个空间中,有两种不同阶级的人的感觉。
可能是结束再收拾完东西已经错过了饭点,饥肠辘辘地再去附近的餐厅,都没有什么可以吃。
这种情形在社会生活中当然是普遍存在的,简单如坐在餐厅吃饭服务员在身边站立行走,或是作为乙方为客户举办市场推广活动。
但在一个“学术”的场合,感觉又有所不同——当你或许亦能听得懂讲座中的“理论讨论”,却因为是“行政人员”,而没有心思去参与“学术交流”,it hits differently.
有次讲座之后,和刚刚也坐在台下的朋友抱怨说“刚才又出了这样那样的状况”,朋友说“是吗都看不出诶你都一副很冷静的样子“,我说”我只是看起来若无其事啊其实心里超烦的“;
另一次讲座之后又有另一位朋友说,”我坐在台下看你一个人跑来跑去全场这么多事情都觉得辛苦甚至有点生气“,我说”没有啦那就是我份内的工作嘛我有拿工资的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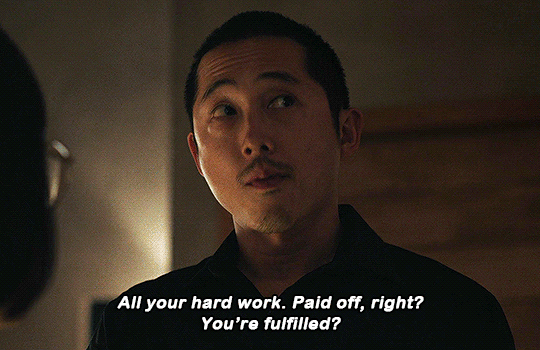
行政工作人员,或许是全场活动最多、却最隐形的人。作为服务提供者,事实上自己实在也不太想要被注视,因为那就意味着有很多问题需要你不断露面去处理。
所以,亦可能是,对于“行政”这一整个概念,我都有点不解的批判:作为令到事情得以发生的基础设施、作为每个人都需要的具体照料,所谓“行政”——例如上面提及的在一场学术讲座之中的种种——为什么要外包给一个固定的群体,为什么不大家一起做就好了啊?
麦克风声音太大太小有回音,观众可以直接告诉讲者;
设置需要调整的,熟悉影音系统的朋友也可以上前试试;
发言时要考虑现场和线上,大家可以互相提醒;
问完问题,站起来走两步伸伸手,麦克风就递给下一位提问的观众了。
讲者与听众、活动参加者与活动工作人员之间的边界,如果在细节中可以模糊一点——我在想——如果大家可以一起去做,不是整件事都会更加轻松自在而顺利吗?
不是这么容易的,我明白,毕竟大家是作为自己来参与活动,我(和许多同行一样)是作为工作人员来使活动得以进行。要是有哪一位讲者在讲座开始前竟然记得对行政同事表达感谢,倒是已经能挽回一点当天的心情。

作者简介
Ennael, 对于自己、工作、生活与世界都在参与式观察。
编后记
从2022年底开始,北美大学里的罢工潮延烧至今,学生工会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不止有教师、博士后、研究生停课走上街头,大学的图书管理员、安保、餐饮服务员和其他学术支持人员也参与其中。在“劳资关系”这个面向上,无论教授还是行政,本质上都是大学的雇员。甚至可以说,以知识生产为己任的“学院”压根就离不开种种辅助劳动的支持:从收集资料的研究助理,到帮系主任冲咖啡拿快递的“delivery guy”。尽管大家都明白,象牙塔里也要有人抹桌扫地,但这类工作却往往被认为无法同那些思辨世界的智识事业相提并论。
读博时同学们一起开玩笑说Ms. X(行政女士)才应该做我们系主任,因为系里大大小小的事务都要依赖她,没了她简直要瘫痪。学术市场的教职机会日益稀缺,不少博士毕业的朋友也不得不找一份类似的工作来过渡。他们踏入学院门槛的第一课,便是学会成为一个系所、研究项目里操心大小事的“保姆”。
保姆这个词并不过份。如果你也承办过学术活动、做过“会务助理”,就会发现许多可以拿起话筒大谈自己如何徜徉田野的学者,不止不会用办公软件,甚至连地图也不会看、地铁也不会搭。而学术活动中所谓的支持工作,实际上包含了大量针对他们的“生活照顾”。
最近几年里,公共场域里的各种知识分享活动似乎尤为兴旺,大学也开始把“走向公共”纳入议程。这些场合尽管表面上开放大门,内里的边界却无比清晰——我们总是默认,那些讲者、与谈人、听众才是活动中的主角;很少去问现场随时待命的技术支持人员想不想、如何能参与到讨论中来。
这种专业主义的隔离很少唤起学术机构内部的反思。但承认吧,如今这一幕幕知识生产的盛景就是建立在一套以分工为名的等级制度之上的:位于核心的人总在谈论“知识”,处在边缘的人常要做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而自诩激进的教授们对身边的人和事往往表现出令人诧异的冷漠——如同大卫·格雷伯所批判的。在这样的环境里,谈论社会关怀会沦为虚伪的职业表演——有头衔加持的学者们继续在讲座上妙语连珠,同时顺理成章地把技术性的、琐碎的麻烦事丢给学术勤杂工们。
套用格雷伯的说法,处于任何不平等社会结构底端的人,永远对那些处于顶端的人有着更多的关切。如同员工之于老板,女人之于男人,行政之于学者。而成为有权有势者最主要的意义,或许就是不用太在意周围人的所思所感,因为他们总是可以雇其他人来帮自己做这件事。当然,这样的情况不止出现在学院。媒体、出版界、影视圈,被权力结构深刻塑造的整个文化领域,都是如此。
最新文章(持续更新)
五一特写 | 琼·纳什与劳动人类学
一场学术讲座中,一位学术行政的”过度关怀”
欢迎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保持联系
独立网站:tyingknots.net
微信公众号 ID:tying_knots
成为小结的微信好友:tyingknots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