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2024,不只談司法覆核 —5個足以影響性/別小眾未來的司法平權動向
1)跨性別換證案終極勝訴 苦等一年入境處政策幾時改?
經過逾七年漫長訴訟,終審法院去年2月終於推翻侵害跨性別人權的身份證更改性別規定,裁定入境處強制跨性別人士完成下身手術方可改身份證性別,違反《基本法》保障下身體完整性(body integrity)的權利,下令入境處撤銷政策。儘管這次終院勝訴是繼2013年W小姐案後,香港跨性別司法平權最重要的一個里程碑,社群也為之鼓舞,但等了整整一年,本地團體和跨性別人士亦多次聯署和到政府部門請願,入境處至今卻仍未推出新的換證規定跟進裁決。
G點今年1月詢問幾位無進行下身手術、但因應裁決已提交換證申請的跨性別人士,他們稱自己去年中遞交的申請仍未獲批,入境處僅在公函中回覆「力求在合理時間內完成檢視現行政策」;而根據裁決前舊規定完成下身手術的跨性別人士,則表示能順利換證,而且過程迅速。G點同月亦再次電郵入境處查詢進度,得到的回覆與去年裁決出爐後幾乎一樣,進度難免令人失望。希望新一年公眾繼續關注入境處修改政策的進度,不要讓這件未竟之事因新聞熱度退卻而被淡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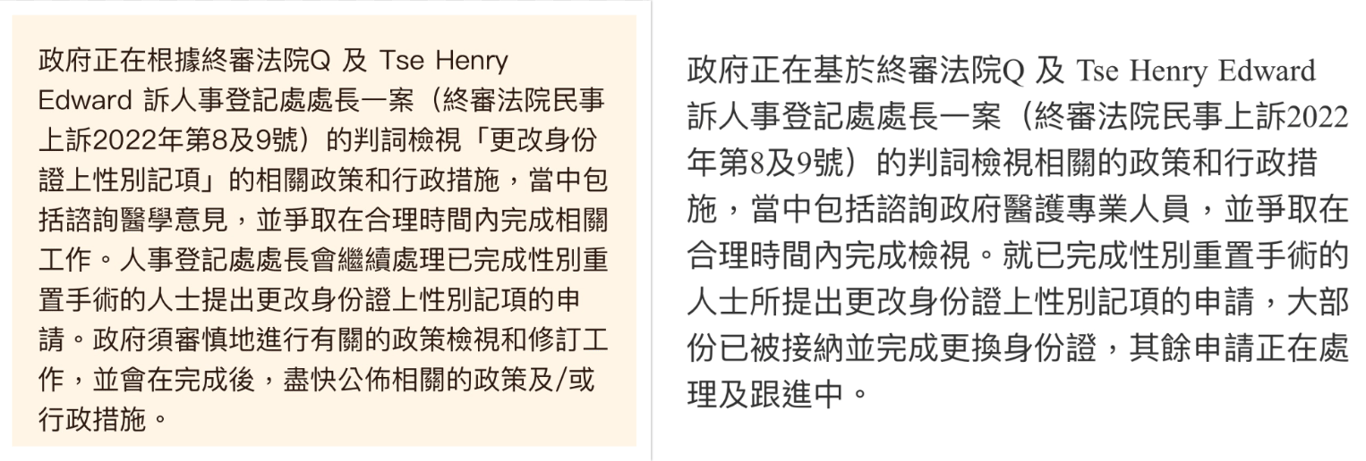
2)岑子杰案開啓立法「關鍵兩年」 同性關係法律承認何去何從?
去年終審法院就岑子杰同性婚權案宣判,「部份勝訴」的結果雖否定港府有責任承認同婚或海外註冊的同婚關係,但五位法官中卻有三位認為同性伴侶有需要獲得替代的法律框架(alternative legal framework)承認其關係,以保障同性伴侶在法律下享有私生活權利和尊嚴。就此,終院更進一步判政府須在兩年內制訂法律框架承認同性伴侶關係,並處理牽涉的「核心權利」問題。值得留意的是,雖然終院白紙黑字為政府定了一個「兩年死線」,但亦認同政府所言制訂和落實框架是「前所未有的重大發展」,須花時間研究,批准政府有需要時可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申請延期。

從較早的QT案、梁鎮罡案,到近年同樣爭取同性配偶平權的公屋居屋案、遺產繼承權案等,無論是政府或申請人一方都經常就「婚姻核心權利」這個概念展開激辯,政府甚至在公屋居屋案中聲稱核心權利就像「私人俱樂部的會員福利和特權」,能維持傳統異性戀婚姻的特殊地位。
然而,這個多次被各方提及的「核心權利」到底是指哪些範疇、類別的權利?其實目前並沒有清晰指引或法律語言能定義,更枉論界定的標準是甚麼,公平與否。結果就是從申請簽證、公務員福利、房屋住權到後事處理,事無大小都要分開遞上法庭、拗到終院。雖然勝訴案例越來越多,這個「核心權利」也不見得越辯越明(如孫耀東教授就曾引用研究指同性伴侶在超過100個法律領域遭受差別對待。逐項權利訴諸法律根本不實際),最終還是要透過立法才能完整處理。可見終院裁決不僅是解決一個合不合憲的法律問題,亦是迫政府就這個因長期消極處理,造成公帑浪費、性小眾被系統性排擠的社會議題有所解答。
2024年雖未到期限,政府不會這麼快有應對方案,但持份者如組織、學者和法律人士等已積極跟進,陸續展開政策研究和倡議工作。一方面,我們可以繼續堅持爭取擴闊婚姻的定義,另一方面亦可以參考歐美、英國等地行之有效如民事結合的其他制度,反思家庭和伴侶關係可以如何被重新定義。相信本年內會有更多討論,值得公眾繼續關注和監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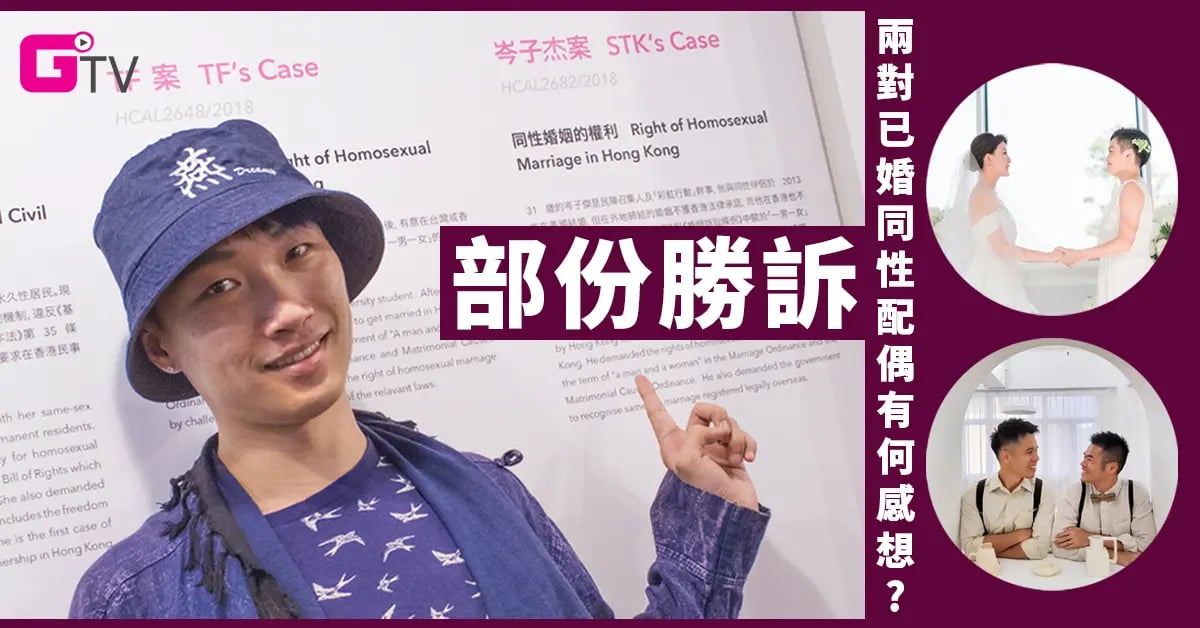
延伸閱讀:岑子杰同性婚權案部份勝訴 已婚同性伴侶:更漫長征途的開始
3)「司法平權」不只司法覆核一途 中學髮禁案帶來的啓發
2022年時就讀中六的林澤駿因不滿母校禁止男生留長髮的校規,以《性別歧視條例》向平機會投訴,引起公眾討論性別氣質、學校對服裝儀容的箝制等問題;平機會在調查和介入一年後,指未有證據顯示校方性別歧視而終止調查。2023年底,林同學與另一名學生黃永熙在沒有律師代表下自行入稟區域法院,控告二人所屬的中學在執行髮禁時無視其性別不安及特殊學習需要,違反《性別歧視條例》和《殘疾歧視條例》,要求校方賠償及道歉。案件暫定於今年8月14日在區域法院進行首次聆訊。
過去通過法庭爭取性/別小眾平權的案件都集中於司法覆核一途,劃時代的勝訴(landmark case)雖直接改變了一些歧視性的政府政策,但司法覆核本質上是挑戰由律政司代表的政府,政府有無盡公帑聘請資深大狀,亦能打消耗戰,案案上訴至終院。最可怕的是如果案件敗訴,法庭可以下令申請人支付政府全部或部份訟費。因此這個「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實質門檻高到普通小市民在沒有法援「包底」下根本難以興訟,或隨時冒着破產風險 —— 過去亦不乏性/別小眾行動者因法援不獲批,陷入無法打官司的窘境。

延伸閱讀:【新聞稿】平機會終止調查校園髮禁事件 冀申請法援開展訴訟|林澤駿
在法援審批收緊、司法覆核越見拖沓的現實下,針對不同倡議對象和改變路徑(theory of change),開發新的司法平權戰場非常重要。林同學和黃同學透過民事訴訟向校方索償,雖然表面上少了挑戰公共政策和法律的「公共性」,但司法覆核層層打上終院,幾乎肯定拖五至十年,民事案的對象則是個人、企業或機構,往往能更迅速推進法律程序,取得裁決並勒令執行,對性/別小眾行動者來說可以是更靈活和成果導向(result-oriented)的策略——一方面旨在實質解決問題,以輿論壓力和賠償,促使訴訟對象停止歧視行為;另一方面同業往往亦會因害怕惹上官非,而檢討自己的做法避免侵權。
過去非司法覆核的民事案往往被視為「私人糾紛」,被記者看低一線,輿論效果略遜一籌;但隨着社交媒體興起,報道法庭案件的話語權不再由主流媒體獨霸。以林同學為例,他一開始就是自己拍片上傳,直面公眾交待髮禁事件和行動的依據,將司法行動結合公眾教育和倡議元素,相輔相成製造了巨大聲浪,為未來希望透過司法手段爭取平權的行動者帶來很大啓發。
4)同志親權新戰線成型 更多案件將挑戰親子定義
承接上文,司法覆核不再是性/別小眾司法平權的唯一出路,過去兩宗爭取同志親權的重要案件 —— AABB案和NF v R案都是以高院雜項申請(miscellaneous proceedings)由高院審理,甚至不是大眾認知有原告被告「對簿公堂」的民事訴訟,但法官在裁決中確立的人性化原則,卻是近年香港爭取同志親權的一大突破。 AABB案中,法官引用「兒童福祉原則」以孩子的最大利益為依歸,判同志父母即使和孩子無血緣關係,甚至和另一半沒結婚,只要能證明盡了家長的照顧和供養之責,都可享共同撫養權,並獲法庭認可為監護人;NF v R案則更進一步試圖擴闊《父母與子女條例》中對「父母」一詞的定義,雖然因條例嚴謹死硬的寫法未能成功,但法官亦在判詞中表達同情,指「父母」定義應隨社會和醫療科技與時並進,亦認同《條例》對案中嬰兒構成歧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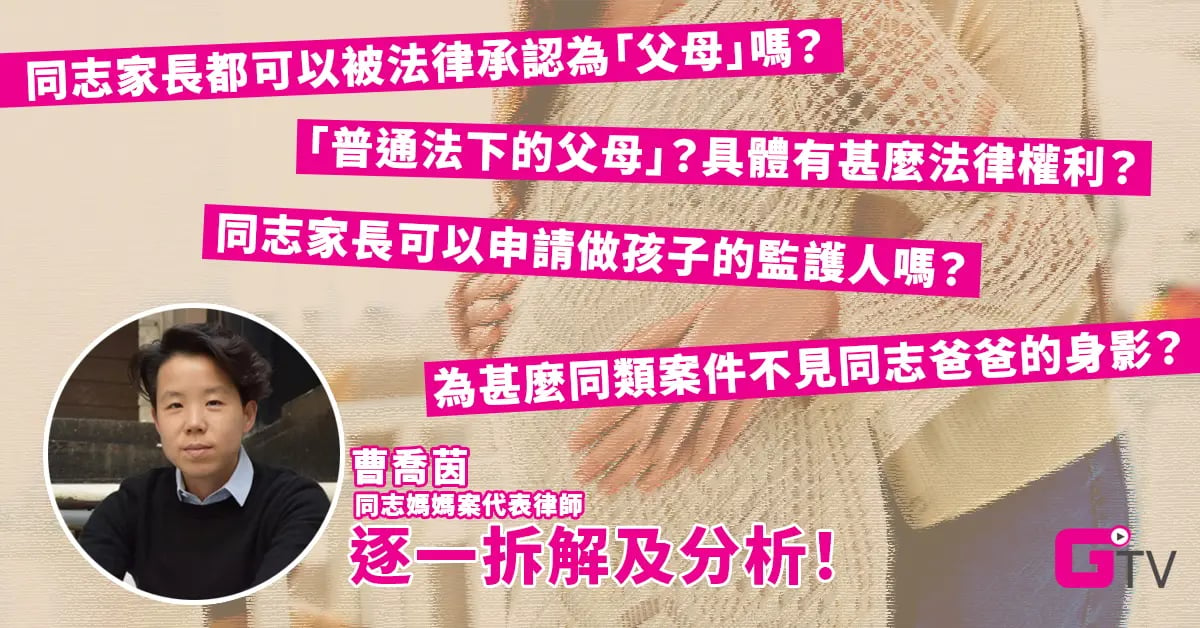
延伸閱讀:【懶人包】一文了解「女同志人工受孕親權案」發生甚麼事?同志親權的未來是?
很多年來,由於香港立法通過同性婚姻遙遙無期,司法平權主要聚焦在同性配偶與跨性別權利,社會普遍對「多元成家」議題(如人工授孕、領養、代母代孕等)的討論非常缺乏,一方面因為這些議題的相關法規(包括《未成年人監護條例》、《父母與子女條例》和《人類生殖科技條例》)都非常技術性和繁瑣,甚至可謂枯燥乏味;另一方面每對伴侶的情況、家庭形態都大不相同,不易引起公眾共鳴。
展望2024年,同志親權有可能朝兩個方向發展:首先,很大機會出現更多司法覆核,指控現行法規歧視、損害同志家長或孩童人權。如在NF v R案中法官便曾指《父母與子女條例》確實對由同志媽媽用人工受孕或其他醫學手段誔生的嬰兒構成歧視,為日後司法覆核挑戰其合憲性打開缺口;再者,乘着政府因應岑子杰案必須制訂「同性關係替代法律框架」,在界定同性關係的「核心權利」時,無可避免會觸及同志家長和子女的範疇,才能處理目前多有灰色地帶的領養和人工生殖爭議。即使政府無意處理其中細節,亦有助掀起公眾討論的熱度,成為性/別小眾行動者進行倡議和公眾教育的契機。
5)同性配偶權利三案連勝 無阻政府堅持上訴終院見
自QT案和梁鎮罡案奠定有利性/別小眾的法律原則後,所有後續爭取同性配偶特定權利的司法覆核全部在高院勝訴,包括爭取平等租住權的公屋居屋案(申請人分別是Nick Infinger和李亦豪,兩案目前已合併處理)和李亦豪手上另一宗爭取遺產繼承權的案件。雖然高院原訟庭、上訴庭已兩次裁定政府敗訴,飽受亡夫之痛的李亦豪亦多次公開呼籲政府還亡夫尊嚴,尊重同性伴侶的福祉,不要堅持上訴;但政府去年底仍正式向終院提出上訴申請,不禁令人失望心寒。

目前三案尚待排期,律政司需先取得高院上訴庭或終院的「上訴許可」,才能繼續法律程序,但根據往例涉及「重大公眾利益」的案件通常都會獲准上訴,因此案件很大機會能在2024年進行審訊。G點屆時亦會發佈開庭資料,方便公眾到庭或在網上旁聽(終院正試行直播法庭程序,讓公眾可以網上旁聽,目前已直播了兩宗民事上訴案,其他級別法院、更多案件未來可能也會有直播審訊的安排)。希望更多人能支持這些承受巨大身心壓力,仍堅持數年為案件操勞的平權夥伴。
結語:法庭與公眾的距離 正是行動者的價值所在
對很多人來說,性/別小眾的司法平權似乎只發生在法庭,只關乎案主或「一小撮人」的權利與公義,法庭戰的門檻高得只有律師和法官能參與其中,沒有法律背景的普羅大眾(甚至是記者和行動者)往往只能被動地接收資訊,等待審訊流程緩緩展開,然後寄望法庭會頒下對性/別小眾有利的關鍵裁決。整個過程中,大部份人被排拒在司法制度、繁瑣程序和法律術語外,無從參與又難以理解。
作為一個從法庭記者轉投NGO的行動者,我常常思考如何縮窄法庭與公眾之間的距離——正因法庭線對本地的性/別小眾平權運動太重要,如果司法平權的過程不能轉化成一般人有感覺、能理解的言語,有平權的成果而無意識的提升,這樣的進步是可惜的。我們可能只停留在「勝訴」或「敗訴」的裁決表面,而忽略了裁決只是更多公眾討論和倡議的開端(岑子杰案就是好例子),而不是終點;我們可能只看到裁決解決了甚麼單一的不公義,但它有時也舖墊了改變的下一步路徑,揭示有甚麼不公義仍在結構之中而我們可以試着挑戰(如QT案、梁鎮罡案影響了後續所有同性伴侶在不同範疇的平權爭取)。
法庭與公眾的距離,正是行動者的價值所在,可以補位的地方。其中一個我很喜歡的做法是常常提醒自己「講故事」,講述入稟狀、判詞背後的人性故事,因為這些才是司法平權最初的初心。就像一人扛起三宗司法覆核案的李亦豪,即使公眾無感他爭取的具體權利,卻可能因為讀了他與亡夫的故事而能同理他的堅持;又像挑戰髮禁的林同學,他在鏡頭前真誠地分享個人遭遇和感受,引發了很多人在網上分享自己面對儀容髮禁的中學回憶,掀起了對性別氣質、學校權威的批判。這些都是司法平權進程中極為珍貴,卻也很易在「目標為本」的策略思考中被忽略的公眾教育、公眾參與面向。願社群一起努力,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