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夾縫中抵抗》港區國安法下的例外法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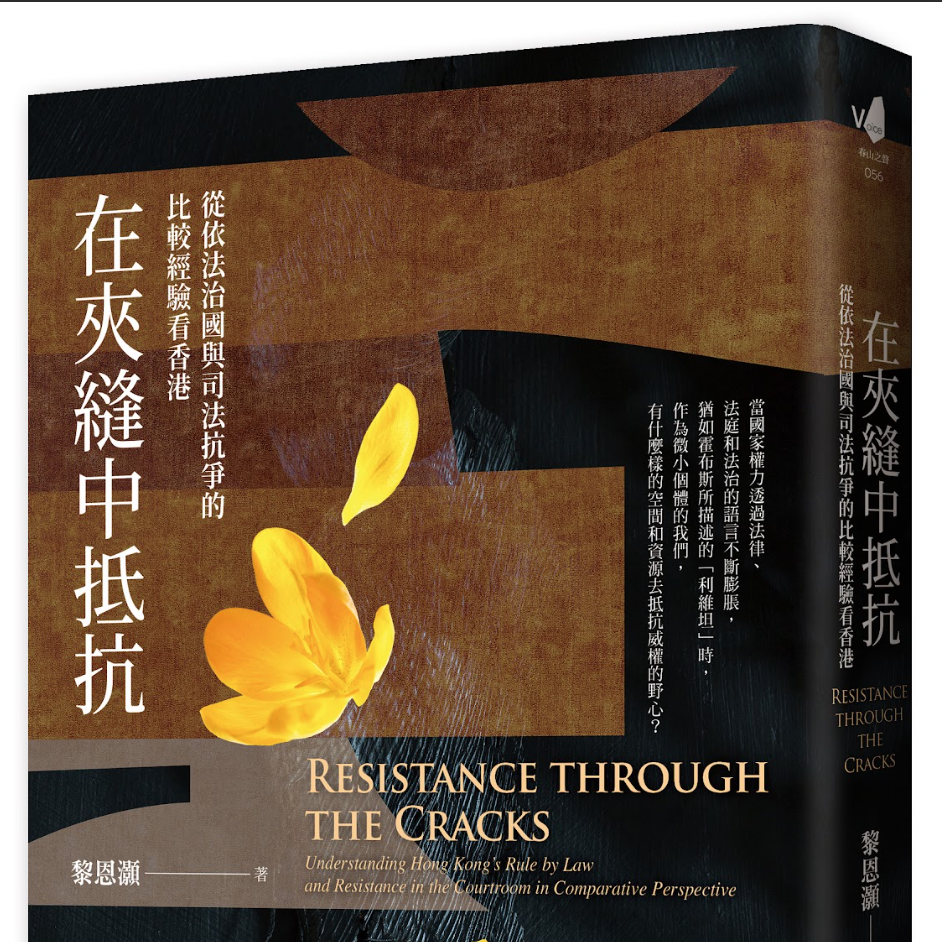
作者/黎恩灝
《港區國安法》下的例外法庭
《港區國安法》對香港司法制度最弔詭的影響,和其他威權政體一樣,是政權既要削弱司法機構在國安系統的影響力,同時又要依賴司法制度厲行嚴刑峻法,懲罰、震懾所謂「危害國家安全」的人士和組織。在這種微妙的行政-司法關係下,一方面行政機關能恃《港區國安法》,延伸長臂到司法機關的人事及審訊模式,削弱司法機構的獨立自主;另一方面,部分法官亦會基於不同理由,主動配合政權以法律和法庭為武器的做法。
根據《港區國安法》,除了特首能指定法官審理國安案件外,主管公共檢控的律政司亦能隨時撤銷陪審團參與審理國安案件,既毋須給予辯護理由,法庭也不能推翻律政司的指令。二〇二一年中,《港區國安法》指定法官李運騰頒下判辭,拒絕受理《港區國安法》首名被告唐英傑的司法覆核申請。申請的背景,是唐英傑被控觸犯《港區國安法》下的煽動分裂國家和恐怖活動罪,律政司引用《港區國安法》第四十六條發出指示,將在高等法院以三名法官取代陪審團審訊。唐英傑指律政司並無就指示提供合理理據,故提出司法覆核。
香港的刑事審訊制度,唯有高等法院才設有陪審團。陪審團的責任,是按證據和證供判斷被告是否罪名成立。但陪審的意義,遠高於純粹協助法官判決。陪審制度能夠透過公民參與審訊,保障被告的法律權利,令民主政治可以更健全發展。正如辯方在入稟狀所指,面對嚴刑峻法,陪審制度能保護被告免於暴政逼害,亦確保政權應用刑法,能順應平民百姓對公平正義的觀念;而且,如果法官被視為偏頗政權,偏離大眾看法,社會大眾或者會更接受陪審團的裁決。可以說,陪審制度能夠制衡政權控制的檢控方和法官在審訊時的超然權力。儘管陪審員的權力總會受到不同限制,但其制衡力量,面對控辯判三方權力極不對等的法庭設計,已經是一道重要防線。
反過來說,陪審團也是培養公民德性和公共意識的重要平臺。擁抱公共價值的公民,才能發揮保障公平審訊的制衡作用。十九世紀初,托克維爾撰作《民主在美國》,提到陪審團不單只是法庭的制度,更是體現共和民主的政治制度。他論述陪審團的公共意義時如是說:
陪審團的制度令民眾─至少某階層的公民─分享到司法權威。陪審團制度繼而促進民眾或該階層的公民更能關注社會……陪審團最大的優點是啟迪民智。它或被視為一個公共學校,讓陪審員學習行使其權利、和社會最上層的菁英對話,在法官、律師和其他審訊持份者身上實質熟悉當地法律。
托克維爾的詮釋,表面看來相當菁英主義。但他其實是藉此說明,要鞏固民主,培養國民的公共和社會意識以及公民參與相當重要;而陪審團制度正好能發揮這項功能。在最理想的情况下,陪審員在審訊過程,透過瞭解案情、反思控辯雙方的論點和證據,和其他陪審員不受干預地商討,判斷被告是否有罪。這個判斷的過程,同時是審判控方和法官對案件的看法。換言之,即使控方濫用權力和程序來對付被告,甚至法官表現得處處維護控方、對辯護者不公等等,只要陪審員做出裁決,認為被告無罪,就等於摑了控方和法官一巴掌。
用一個反例來說,新加坡本來一直承襲英式陪審團制度,但自李光耀掌政後,他因為不滿陪審團判決,在一九六九年廢除了該制度。廢了陪審制,令法庭更加菁英掛帥和「離地」,也減低了國家進行政治審訊和司法迫害的阻力。
李運騰法官的判決,有沒有照顧到以上的觀點?答案是沒有。李運騰對陪審團維護司法公義和民主的功能避而不談,一開始就直言陪審團在香港並非絕對權利,比方在九七前,有陪審制的高等法院可以將刑事案件移交到沒有陪審制度的下級法院審訊。但這個說法,根本和本案毫不相干;同樣,李運騰論述檢控部門有全權決定案件交由哪一級法院處理而不受干預、只要被告在高等法院獲撤控就不享有陪審程序等等,亦只是混淆視聽。因為本案的焦點,並非要求政府交代下級法院不設陪審團的理據,而是針對律政司一紙公文便可以廢除高等法院在國安案件使用本來必須設有的陪審制度,此一做法是否合理。法庭基於特殊原因而增加或廢止刑事程序,總要給予合理理由,這亦是國際人權標準所要求的:
在法庭和裁判所前一律平等還要求同一案件由同樣的訴訟程序審理。例如,一旦制訂特殊的刑事訴訟程序或特別設立法庭或裁判所,以審判某類案件,則必須提出客觀和合理的理由,證明有理由這樣做。
然而,在國際人權標準的要求下,李運騰選擇強調《基本法》第六十三條賦予律政司檢控不受干預的權力作為擋箭牌,拒絕受理司法覆核申請,等於表示《港區國安法》第四十六條已無可爭辯之處。這類判決再一次反映片面詮釋法律條文的問題,只著眼依法而治的所謂法治觀念,忽略真正的法治必須限制政權的權力,保障人民的權利。李運騰的判辭,就是避重就輕、高舉政權壓倒性權力的一個顯例。
或者,李運騰判辭唯一說得準確的地方,可能是他指出《港區國安法》創造了一個在高等法院沒有陪審團的「刑事審訊新模式」,容許律政司決定是否以此模式處理國安案審訊。李運騰的說法其實已留有餘地,因為這個新模式,實質上就是一個例外法庭。以特別法庭來處理政治審訊,在威權國家並不罕見。《港區國安法》的條文要求特首全權委任指定法官,特首又可以用一紙證書確認某行為活動是否關乎國安,容許取消陪審團、閉門審訊,甚至在更特殊的情况下將被告送交最高人民法院審訊等等,等於開設一個有實無名,專門應付國安案件並享有不少特權的特別法庭。這個有實無名的制度特色,就是行政權力完全凌駕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的制衡權力,取代了香港過去篤信的「三權分立、互相制衡」原則。當立法機關或司法機關無法制衡行政機關、反而要事事配合行政機關的指令和政策時,行政機關的權力就可以不受節制地擴張、甚至被當權者濫用,造成「三權合作,行政獨大」的局面。
這種安排有無歷史和理論基礎?如本書第一篇所述,只要回顧一下德國二戰前的司法史,讀讀強世功、陳端洪等中國學者推崇備至的法律學者兼納粹黨員施密特之著作,就知道政權在原有規範運作的法律體制(normative state)之上增設例外(exception)安排,是如何便利主權國建立特權體制(prerogative state),進一步收緊對司法系統和全社會的控制。
李運騰的判決書,影響不只作用在唐英傑身上。沒有陪審員參與國安審訊的先例一開,政權對國家安全、國安罪行的定性、定義就能在法庭定於一尊,毋須憂慮社會大眾是否認同這些詮釋,繼而影響被告罪名是否成立。目前最引人注目的國安案件,包括「支聯會案」、「民主派初選四十七人案」和「黎智英案」等等,已先後交由高等法院準備正審;政權已指令撤銷陪審團。從政權角度來說,抓緊司法,謝絕陪審,審判結果就更穩定,國家安全就更牢固。但長遠來說,法庭更難有空間讓法官和民眾以裁決間接發表異見;法官判決的理據,也更難獨立於政權的政治論述和法律意識形態之外。